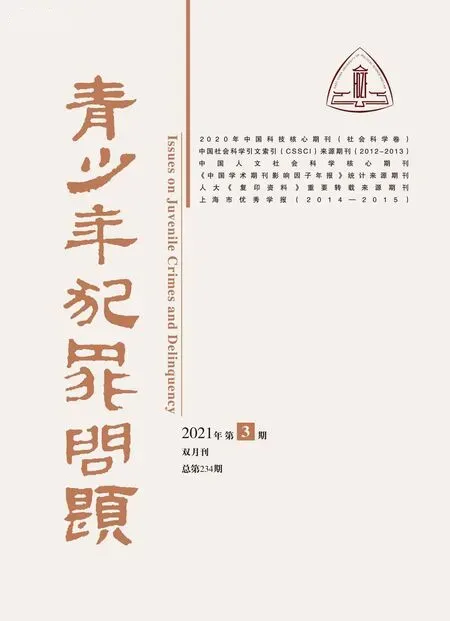终身监禁制度实现刑罚目的可能性之探讨
涂欣筠
在通过古典与现代的刑罚和量刑理论的镜头考察之后,终身监禁成为公民社会一种规范且必要的惩罚。(1)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16.然而,终身监禁制度作为一项刑罚制度,是对罪犯终身自由权的一种剥夺。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各国立法与司法中,都不可避免需回答它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即提供较小或无释放机会否能在道德、法律和矫治上正当化。刑罚制度的设立需能够实现一定的刑罚目的,而对刑罚目的不同理解与认识,又直接影响对特定刑罚制度正当性与否的判断。终身监禁作为一项刑罚制度也不例外,其存在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刑罚目的的实现。
一、关于刑罚目的理论的对立观点
随着刑罚权由私人向公共的转移,原本的一些不法行为被定义为犯罪,所假设的惩罚给罪犯带来的有目的性的影响开始流行。(2)See Edwin H. Sutherland & Donald R. Cressey,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7th edi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6, p.311.不同于古代刑罚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近现代意义上的刑罚目的更多体现为刑罚的正当性。刑罚的正当性既在于其公正性也在于其功利性,刑罚既以报应为其正当根据,又以预防犯罪为其正当目的。(3)邱兴隆:《刑罚理性评论——刑罚的正当性反思》(第二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年版,第86页。启蒙思想家对刑罚目的的看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却承认刑罚具有一定的目的。(4)马克昌、莫洪宪:《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他们反对中世纪的报应刑,而主张刑罚具有“恢复法律秩序”“威慑”“改造”等具体目的。这便产生了刑罚报应主义和刑罚功利主义的区分。对刑罚目的的探索导致对刑罚制度、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现代刑事政策的诞生、发展和完善。(5)徐久生:《刑罚目的及其实现》,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一)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论
刑罚的报应目的和功利目的是关于刑罚目的两大对立观点。报应刑论是最历史久远的刑罚目的论,它源自宗教的神学理论。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报应主义“由康德发其端,经过黑格尔,至宾丁大致完成”。康德运用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了“理性人”的绝对报应主义之定言命令;黑格尔从辩证法的角度论证了绝对报应主义的必然性;宾丁基于规范理论展开了绝对报应主义的论述。有学者分别将之概括为“等量报应刑”“等价报应刑”和“法律报应主义”。(6)邵博文:《报应主义正当性之哲学思考——基于观念论与规范论双重进路》,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作为刑罚目的之报应,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报复。它承认刑罚是一种恶,也认为对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应遭受此种恶,却要求这种恶的施加是有限度的、合乎比例的,且仅可针对犯罪人本身。它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它尊重人作为独立道德主体的存在,反对将刑罚的施加作为预防犯罪的手段或工具。依报应刑论,罪犯所受的惩罚应当与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相一致,不可基于其他目的而对罪犯施加额外的惩罚。等序报应所要求的是以犯罪的严重性作为标准,对犯罪进行轻重次序的排序,以刑罚的严厉性为标准,对刑罚进行轻重次序的排序,在此基础上,追求刑罚与犯罪在轻重次序上的对等。(7)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论》(第二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版,第140页。
后期古典学派的学者大多是坚决主张报应刑论的。“一般认为报应主义的刑罚理论由宾丁大体完成”。宾丁从规范说出发,认为犯罪是违反规范的,对这种违反规范的行为由刑罚法规规定而发生刑罚权。刑罚是对否定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否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轻重成比例,即犯罪人由科刑所受痛苦的大小,应当与法律程序因犯罪所受损害的大小成正比。(8)马克昌、莫洪宪:《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这种刑罚报应目的的出发点在于犯罪行为是对法律秩序的违反,而刑罚的目的则在于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当代”报应论,其在时间上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这股思潮的兴起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主宰大多西方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矫治主义(correctionism)以及复归主义(rehabilitationism)的反动。它认为刑罚在本质上是一种惩罚,而这种惩罚是罪犯所应得的。当一个人应得某种对待,他必须是由于自身拥有的一些特点或是先前的行为。(9)Joel Feinberg, Doing and Deserving: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8.这种对待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大体上可区分为赞成或是反对、追求或是避免、愉快或是不快的。(10)Joel Feinberg, Doing and Deserving: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61.而惩罚作为对罪犯先前犯罪行为的对待,应当是一种表明反对的、带来不愉快的对待方式。因此报应论者反对采取中立的“矫治”来对待犯罪人,而明确刑罚施以痛苦的惩罚属性。司法上根据具体犯罪人在犯罪中所体现的主观恶性程度量刑,明显地使刑罚的严厉性与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对称,符合基于作为法律报应之另一渊源的道义报应所要求的刑恶相称的规定,使配刑因经得起道德评价而具有相应的公正性。(11)邱兴隆:《刑罚理性评论——刑罚的正当性反思》(第二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二)功利主义的刑罚目的论
经过长时间惩罚犯罪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刑罚不仅可以惩罚犯罪,而且可以遏制犯罪。基于对刑罚的这种遏制作用的认识,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将刑罚作为惩罚犯罪的手段,而是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刑罚对预防犯罪的效果,从而形成了对以报复观念为主宰的报复刑体制的否定。(12)邱兴隆:《刑罚理性评论——刑罚的正当性反思》(第二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功利主义的刑罚目的论应运而生。该目的论认为,报应只是刑罚的本质而非目的,刑罚的目的在于其所实现的预防犯罪的效果。大体说来,行为功利主义持这样的观点:行为的正确或错误仅仅取决于其结果总体上的善与恶,也就是行为对所有人类(或许是所有具有感知之生物)福利的效果。(13)[澳]J.J.C.斯玛特、[英]伯纳德·威廉斯:《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劳东燕、刘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具体就刑罚而言,刑罚的实施在于实现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人类福祉。边沁作为刑罚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亦认为刑罚是一种恶。根据功利原则,如果说刑罚应该被完全允许的话,那么,只有在它有可能排除某个更大的恶的情况下,才应该被允许。(14)[英]杰里米·边沁:《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程立显、宇文利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因此,刑罚的实施需以预防损害的效果为前提,而这种效果既可以是预防其他公众犯罪,也可以是预防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依所预防的对象不同,功利主义的刑罚目的论又可分为一般预防论也即威慑论和特殊预防论,前者认为刑罚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使一般公众惧于实施犯罪行为,而后者则强调刑罚通过使罪犯囿于监狱剥夺其犯罪能力、给其造成痛苦而不再实施犯罪行为。功利主义认为的另一个刑罚所追求的社会后果是对罪犯予以改造。由于罪犯的行为采取的是破坏性的和反社会的方式,他们须得到改造从而使其不再具有反社会的愿望。(15)Robert M. Baird & Stuart E. Rosenbaum, Punishment and the Death Penalty: The Current Debate,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1995, p.9.
然而,20世纪英国著名法哲学家哈特却认为,对罪犯的改造不能成为刑罚体系的一般正当化目标。他认为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可划分为两类人:一是已实际破坏特定法律者;二是还未破坏但可能破坏法律者。将改造作为最主要的目标会忽视影响与更严重犯罪相关的、在数量上更多的第二类人。(16)See Richard Wasserstrom, Punishment v. Rehabilitation, in Robert M. Baird and Stuart E. Rosenbaum edited, Punishment and the Death Penalty: The Current Debate,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1995, p.57.同时哈特认为,犯罪人因其罪恶所遭受的痛苦,对刑事司法体系来说从来都是一种代价而没有益处。他赞同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不同于报应主义的观点而坦率主张任何形式的痛苦都没有内在的魅力,即使当其被惩罚性地施加。因此这一系统施加痛苦的任何吸引力在于其工具性的魅力。(17)See H.L.A Hart,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second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Gardn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iv.应当说明的是,无论是对于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的强调,抑或是对罪犯改造的主张,功利主义的刑罚目的论认为刑罚的正当性在于其所实现的好的结果。这也导致了功利主义的刑罚目的论与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论最根本的分歧,即是否始终坚持将报应作为刑罚施加的正当性依据。
报应主义不仅是“回溯性”的,更是发现一些本质的而非功利的,蕴藏在某一特定类型痛苦之内的价值,也即在应得的痛苦之中。(18)See H.L.A Hart,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second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Gardn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v.在报应主义的刑罚论者看来,无论报应源自对法律秩序的破坏还是源自对道德规范的违反,报应不仅是国家机构施以刑罚的正当性依据,也是个案中对具体个人适用刑罚的根据。作为一种报应理论的“公平游戏论”,把原本基础倍受质疑的“报应正义”转化为“公平”的问题,而使得“报应正义”透过“分配正义”找到相对稳固的基础。报应的实现是为了社会公平的结果,公民作为社会秩序的缔造者,其若通过犯罪行为破坏了原本的游戏规则,那么依分配正义的原理就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犯罪人因主观罪过所受的惩罚是应当追求的一种善,即使其他所有痛苦都是应当避免的邪恶。(19)See H.L.A Hart,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second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Gardn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v.而哈特对报应主义者的反对,并不关于“对一刑事惩罚的辩护是否必须聚焦于对社会和犯罪人的未来的善”,当然必须是善的,这点报应主义者也予以赞同。分歧在于是什么作为与之相关的未来的善。哈特发现把因罪过所受的痛苦作为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总体正当化目标”是完全可理解的。但他认为报应主义者将追求因罪过的痛苦作为一种本质的善是不道德的,因为在本质上痛苦始终且只能是一种恶。(20)See H.L.A Hart,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second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Gardn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vii.
二、近现代刑罚目的理论的综合
刑罚报应主义和刑罚功利主义都将自身通过刑罚所追求的善作为其正当化依据,只是他们所追求的善的内容不尽相同。我们可以看到报应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主义的正如古典的功利主义者,同时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他们像古典功利主义者的结果主义之处在于其定义一个值得追求的善,可能甚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其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结果主义者,也不像古典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善不可通过一个完全行为独立的方式获得确认。欲实现报应主义的善,需确认特定痛苦是因犯罪人的罪过所受,这就必须经常定义涉及犯罪人罪过的已经实施的恶行。当然,恶行的问题是一个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恶行”,而不需要是本质上的罪恶。(21)See H.L.A Hart,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second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Gardn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vi.由此可见,刑罚报应主义与刑罚功利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密不可分的,刑罚报应的实现与否亦需要功利主义的结果考量。
(一)刑罚报应主义与刑罚功利主义的矛盾调和
功利主义的刑罚论者在面对单纯从结果出发,有时无辜者将受到惩罚而有罪者无需惩罚的情形时,也许会通过区分刑罚制度的正当性和所实施的特定刑罚行为的正当性来解决这一困境。依此观点,只有作为制度的刑罚是依功利主义的考虑而予以正当化。个案中的犯罪行为则由组成该制度的政策、程序和实践所掌握,并且个案中刑罚施加的正当性仅在制度的语境下所需要,当正当性的问题已包含在内,功利主义的考虑并不在合法性上触及个案。(22)Robert M. Baird & Stuart E. Rosenbaum, Punishment and the Death Penalty: The Current Debate,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1995, p.10.康德对于将人仅作为手段的担忧并没有被忘却,罗尔斯和哈特都试图通过将制度的总体目标与一个特别案件中刑罚的特定目的相区分来回避这一难题。他们认为,刑罚制度可能在功利主义的观点上正当化,对特定个人的刑罚仅可在个人罪过的基础上正当化。报应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可以看做是回答了不同的问题,而不是对于“为何刑罚”这一个问题回答的分歧。(23)Deirdre Golash, Punishment: An Institution in Search of a Moral Grounding, in Christine T. Sistare edited, Punis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Coerc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6, p.21.哈特亦认为需要将刑罚体系本身所追求的一般目标的“报应”与在回答“对谁施以刑罚”问题上的“报应”相区分。他认为,功利主义者与他们的反对者之间令人迷惑的冲突阴影将被避免,如果意识到可以完美一致地认为刑罚实践在总体上的正当化目标是它的有利结果,并且对这一总体目标的追求获得满足或受到限制顺从于分配的原则,即要求刑罚仅可适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24)H.L.A Hart, Prolegomenon to the Principles of Punishment, John Kleinig edited, Correctional Ethic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p.11.这一解释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二者之间的矛盾。
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功利主义的结果考量仅在个案分配上坚持报应,与将报应作为整个刑罚体系的根基之间存在本质差别。如果分配正义难以通过报应来实现,那么功利主义对报应的态度将有所转变。同时,依刑罚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报应主义对个案的适用并不能合法地应用于刑罚制度的正当性本身。(25)Robert M. Baird and Stuart E. Rosenbaum, Punishment and the Death Penalty: The Current Debate,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1995, p.10.这无疑是一个法理上的悖论。在实践中,在决定分配责任时,功利主义的理由实际上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例如,对于累犯(recidivists)、恋童癖者或精神变态等特别罪犯的危险性,施加“额外”的刑罚被认为是正当的。(26)马永强:《刑罚理论的新动向:从综合论到沟通论——达夫(R. A. Duff)的沟通理论及中国境鉴》,载 《刑事法评论》第39卷。因此,难以绝对地将在个案中坚持报应与整个刑事司法体系所追求功利目标相区分。同时,尽管这一路径避免了对功利主义的主要批判(与对无辜者的惩罚有关)和对报应主义的主要批判(要求无意义痛苦的施加),其缺点是要求对犯罪人的损害是善的,且这一善的行为通过整个制度对损害的衡量来实现。(27)Deirdre Golash, Punishment: An Institution in Search of a Moral Grounding, in Christine T. Sistare edited, Punis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Coerc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6, p.21.
密尔认为,刑罚可以被保护他人或是对犯罪人的有益影响正当化。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是理想的功利主义解决方案:如果刑罚不损害犯罪人,并且帮助社会,在衡量中也就没有负面因素。(28)Deirdre Golash, Punishment: An Institution in Search of a Moral Grounding, in Christine T. Sistare edited, Punis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Coerc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6, p.19.然而这一理想结果却难以实现:一方面,纯粹结果式的目的论主义,无法有效地弥补被破坏的正义,例如对于犯罪人进行矫正,并无法取得被害人身心的正义观感的确信(在遭受被害之前,每个人都基于正义观感,确信人人平等且和平相处的基本伦理命令),因此,在这种“目的论”支配下所形成的刑罚建制就不可能是真正正义的;(29)邵博文:《报应主义正当性之哲学思考——基于观念论与规范论双重进路》,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另一方面,事实逐渐地证明,监狱在大体上并没有成功使罪犯复归或者威慑罪犯,也越来越难主张刑罚对犯罪人而言是善的,或者它相较损害而言是善的。由于大多数哲学家已拒绝对犯罪人的损害本身为善是站不住脚的观点,复归和威慑的幻灭可能在逻辑上导致对所有形式的刑罚制度的拒绝。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的正当性跌入幕后,古老的报应主义观念复活。(30)Deirdre Golash, Punishment: An Institution in Search of a Moral Grounding, in Christine T. Sistare edited, Punis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Coerc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6, p.21.
这一当代的讨论自1971年赫伯特·莫里斯《人与罚》的发表而开始塑形。他认为,不同于复归依社会喜好对一个人塑造的寻求,报应主义的刑罚尊重了犯罪人对不服从的选择,也为他留下了基于将再次付出结果的代价而做出同一选择的自由。刑罚的目的按照此观点,是修复由犯罪行为破坏的收益与负担的适当平衡。(31)Deirdre Golash, Punishment: An Institution in Search of a Moral Grounding, in Christine T. Sistare edited, Punis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Coerc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6, p.22.大量的后继者选取了莫里斯的观点,认为“应得”不仅仅是一种限制,而是作为对犯罪人损害的完全正当化依据,享有简明的支配地位。(32)Deirdre Golash, Punishment: An Institution in Search of a Moral Grounding, in Christine T. Sistare edited, Punis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Coerc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6, p.23.然而,无论以何种应得刑罚理念为定罪量刑的分配原则,常见的反对意见是“模糊性”;另一种略有不同的批评意见是:应得刑罚理念对定罪量刑问题无法作出量化界定,而只能根据比例原则辨识出刑法介入或者不介入的大致范围。(33)[美]保罗·罗宾逊:《正义的直觉》,谢杰、金翼翔、祖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一个更微妙的版本是,当一个刑罚的施加与犯罪的严重程度正确地成比例,那么它便是公正的刑罚。这是自18世纪中叶刑罚理论启蒙以来的基本认识。比例原则的观念不仅限于是与贝卡利亚有关的功利主义的目标,它为威慑与报应的支持者所共享。它也被体现在监禁刑的量刑观念上以及对严格刑罚纪律实施的精确计算上。(34)Dirk van Zyl Smit and Catherine Appleton, Life Imprisonment: A Global Human Rights Analysi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4.
(二)刑罚多元目的理论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初,一系列新理论的出现,寻求基于对犯罪人道德上的善(尽管是直接损害)而将刑罚正当化。因为刑罚是为了犯罪人道德上的善,而不需要证明它对社会的全部益处。甚至是,它不需要实际完成道德上的改变而只要它指向这些转变。这些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需要证明的不仅是道德改变的愿望,还有刑罚是实现这一改变的方式。刑罚是道德改变的必要路径,且它的施加即使在这一改变并不即将来临时也可正当化。(35)See Deirdre Golash, Punishment: An Institution in Search of a Moral Grounding, in Christine T. Sistare edited, Punis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Coerc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6, pp.23-24.与此同时,对刑罚有利于社会观点回归的萌芽,体现于自我防卫的理论。这一理论寻求建立“将犯罪人作为实现社会更大善的手段”并非是不可允许的,基于犯罪人所表现的损害威胁和刑罚为了避免这种损害而对其施加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对犯罪人的损害对于阻止他造成无辜者损害是必要的,并且实施这一损害对于未来的威胁是必要的,对犯罪人的损害可基于自我防卫而被正当化。这一理论显然依赖于威慑的有效性。(36)Deirdre Golash, Punishment: An Institution in Search of a Moral Grounding, in Christine T. Sistare edited, Punishment: Social Control and Coerc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6, p.24.
在此情形下,对于刑罚报应主义所主张的“应得”如何确定,美国刑法学家罗宾逊认为,如果无法在经验层面证明应得的份额,那么就应当允许采取预防主义的政策,因为“与担心国家可能滥用刑罚预防功能相比,更为糟糕的是预防功能被刑事司法体系所遮蔽”。(37)Paul H. Robinson, Punishing Dangerousness, Harvard Law Review, Vol.114 (5), 2001, p.1456.现代风险社会下预防性刑事立法的增加,恰是在这一刑罚目的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但这显然与比例原则的要求是相违背的。比例原则是为给各自治利益之间矛盾提供结构性解决的一个工具。任何一个比例性检验的四个阶段包括:合法的目的、合理的联系、必要性、严格意义上的权衡。(38)Kai Möller, The Global Model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5.如此宏观意义的功利主义预防考量,很难说可以全面满足上述四阶段的具体检验。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刑罚实际或可能造成的结果并不等同于特定刑罚所产生的后果。因为刑罚作为一种规则预设,其实际效果取决于人们对于这种规则的认识和态度。如果没有假设犯罪人的理性,威慑并不与实际或可能的犯罪相联系。(39)Michael Davis, How to Make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 Ethics, Vol.93 (4), 1983. p.735.也就是说,如果刑罚所威慑的对象并非为理性人,抑或是这种威慑与公众的道德情感不相一致,那么这样的预防性刑事立法及其刑罚后果便难以实现原本的刑罚目的。
因为任何交换都是等价值的(包括实然和观念两种层面之上的等价),其确保的是刑罚正义的相互性,明确此一点,即可确证犯罪者的应得份额自然等价于自身的道德违反性,如果预防论者仍然批评违法行为的道德损失是无法准确衡量的,那么,其自身所主张的(特殊) 预防根基也会崩塌。说到底,无论是事前预防抑或是事后报应,所依赖的都是行为人通过行为展示出的“道德违反程度”。(40)邵博文:《报应主义正当性之哲学思考——基于观念论与规范论双重进路》,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2019年第3期。故归根结底,无论是将个案公正与刑事司法正义相区分,还是在刑事司法的不同阶段追求不同的刑罚目的,都离不开对犯罪人道德违反程度的具体衡量。
发端于表达性刑罚理论的沟通性刑罚理论,也试图在传统的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外,寻求确证刑罚目的的第三条道路。在报应论者和表达性刑罚理论的倡导者看来,将刑罚与沟通相联系,源于关于刑罚与谴责关系的讨论。与其说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的后果,不如说谴责(condemnation)才是对犯罪的自然而道德的适当反映。而刑罚则是一种表达谴责的方式,是我们对于犯罪人的非难表达。通过这种谴责,表达了社会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并将这种评价传递给犯罪人。(41)马永强:《刑罚理论的新动向:从综合论到沟通论——达夫(R. A. Duff)的沟通理论及中国境鉴》,载 《刑事法评论》第39卷。沟通性刑罚理论与表达性刑罚理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将这一通过刑罚传递信息的过程视为双向的互动过程;而后者则是单向性的且不考虑沟通对象的信息接收程度。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这种表达或沟通均是主要面向犯罪人的,因为报应主义者必须回答犯罪人应得的问题,这一路径表明无论如何刑罚沟通必须主要是面向犯罪人的沟通。至于沟通“什么”,很明显的回答是刑罚传达了犯罪人应得的定罪或谴责。(42)R. A. Duff, Punish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7.
如果刑罚单纯只是为了表达谴责,那么完全可以用其他处遇措施来实现。然而,如今的法律体系所施加的刑罚不仅仅是象征性的:监禁、罚金、强制性的社区服务是独立于它们所可能具有的谴责性涵义之外的负担。为何表达谴责需要刑罚的如此严厉处遇呢?对此,结果主义者认为,刑罚的严厉处遇为法律的道德诉求增加了一个威慑激励,这些严厉的刑罚向他们的施加者传达了权威性的谴责。由此,刑罚沟通有效性的问题成为威慑有效性的问题。(43)See R. A. Duff, Punish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9.但即使采取了最严厉的刑罚处遇,刑罚所具有的表达谴责目的也未必能实现。刑罚沟通理论的创始人达夫认为,可通过将刑罚描绘为一系列世俗的苦修,来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解释“为何我们应当用刑罚的严厉处遇来传达对犯罪人的谴责”。这一解释是报应主义的:它将刑罚正当化为是对应得谴责的表达。然而,不像其他形式的报应主义者,它也给予刑罚规劝犯罪人忏悔其行为的面向未来的目的(表达性的行动在总体上典型地具有一个面向未来的目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一解释是部分结果主义的,它寻求结合报应主义者对应得的关心和结果主义者对未来收益的关注:因为刑罚和它的目的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结果主义者般偶然或工具主义的,而是内在的。(44)R. A. Duff, Punish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0.
综上,由于刑罚实践的复杂性,想要有一个全面的大而无当的证明刑罚正当性的理论,可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45)马永强:《刑罚理论的新动向:从综合论到沟通论——达夫(R. A. Duff)的沟通理论及中国境鉴》,载 《刑事法评论》第39卷。报应主义由于符合人类的道德心理,而更易成为制定惩罚规定的基本原则,但如果没有对犯罪与刑罚予以功利主义的考量,报应主义也将沦为空洞与虚无。这里所谓的“功利主义”并非一般的伦理理论,而仅指任何刑罚理论使刑罚与犯罪相适应需依据特定的惩罚或刑罚规范所实际或可能造成的结果。(46)Michael Davis, How to Make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 Ethics, Vol.93 (4), 1983. p.727.这种相适应与否的判断则依赖于对比例原则的坚持。刑罚是对罪犯权利的侵犯,而被全球模式所采纳的——为了使对宪法权利的侵犯正当化的一个重要工具——则是比例原则理论。(47)Kai Möller, The Global Model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
三、终身监禁制度实现刑罚目的之可能
关于刑罚的证立,有两个层次的课题,必须加以区分:第一个层次是证立刑罚作为一般性制度或社会实践活动,第二个层次是证立特定类型的刑罚是否应被涵摄在此规则或社会实践之下。刑罚理论的主要任务,乃是前者,而后者通常是前者的应用或延伸。应当说明的是,作为一般刑罚理论的刑罚目的论所探讨的刑罚根据与具体刑事政策层面刑罚的设立与实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第一层次的证立主要体现为对刑罚目的的理论探讨,而第二层次的证立则依赖于对特定刑罚可否实现刑罚目的的具体判断。终身监禁制度作为具体刑罚的证立,应是在第一层次证立的基础上对第二层次证立的实现。
(一)刑罚报应主义对终身监禁的需要
作为一个刑罚规则创设的问题,在刑罚目的论上需坚持以报应主义为基础,同时兼具考虑威慑和其他理论后果。合理的刑罚正当化理论应该在涉及该当性之前的正当化阶段,融入结果的意义。(48)[美]道格拉斯·胡萨克:《刑罚哲学》,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604页。哈特在《惩罚与责任》一书中阐述了刑罚报应实现的三个要素:第一,仅当行为人自愿实施应受惩罚的行为时方可对其予以惩罚;第二,刑罚必须与犯罪行为的邪恶程度相匹配或是相一致;第三,惩罚犯罪人的正当性在于道德邪恶自愿造成的痛苦本身是公正的或是道德上正确的。(49)H.L.A Hart,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31由此,对刑罚报应的实现,需回答的是如何将刑罚与犯罪行为的邪恶相匹配,以及刑罚所施加的痛苦何以具有道德正当性的问题。
刑罚报应主义对终身监禁制度的审视也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实施严重犯罪的罪犯的报应源自其给被害人、被害人家人和社会造成的巨大痛苦,而刑罚即是其反过来应承受的必要痛苦。唯一能实现完全一致报应的犯罪是杀人,剩下的如:强奸、敲诈勒索、伪造、严重的亵渎神明等从未以同样的形式被施以报应。如果他们在不同标准下被偿还,又如何将他们进行比较?(50)Mara Jose Falcon y Tella & Fernando Falcon y Tella, Punishment and Culture: A Right to Punish?,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6, p.135.因此,只有对不同种类犯罪施以相对同质性的刑罚,并依犯罪的道德可责难性决定刑罚的轻重,才可实现刑罚的报应。无论是道义主义还是经验主义的报应论,其所关注的核心并非是所施加的绝对惩罚,而是在不同程度道德可责性的案件中施加相对的惩罚。(51)Paul H. Robinson, Life without Parole under Modern Theories of Punishment, in Charles J. Ogletree, Jr., and Austin Sarat edited, Life Without Parole: America’s New Death Penal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46.刑法特别在产生和维护社会一致同意的社会道德形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2)Paul H. Robinson, Life without Parole under Modern Theories of Punishment, in Charles J. Ogletree, Jr., and Austin Sarat edited, Life Without Parole: America’s New Death Penal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50.可见,道德可责性的大小成为判断是否需要将终身监禁刑罚纳入刑罚体系的关键。
早先的报应主义者对死刑和终身监禁均感到不适,而反对者认为固定期限的监禁更易衡量并使得刑罚(剥夺自由的期限)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53)Dirk van Zyl Smit and Catherine Appleton, Life Imprisonment: A Global Human Rights Analysi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5.在古典报应论者看来,一个正当的刑罚是通过比例性来衡量的,即刑罚的严厉性取决于基础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报应主义的理论是回溯性的,并不对未来的损害预防感兴趣。依报应主义的观点,终身监禁仅在当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的应受谴责性,在道德上与将其置于监禁至死相称时才具有正当性。(54)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17.如果有足够严重的犯罪需要通过终身监禁来实现报应,那么终身监禁就具有存在的必要。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该当性的问题。该当性判断很少施加强制性义务或职责于任何人,并以特定的方式制裁应受惩罚的人。(55)[美]道格拉斯·胡萨克:《刑罚哲学》,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598页。对于实施足够严重犯罪的犯罪人,其该当与其犯罪严重程度相适应的刑罚,但未说明这一刑罚应为终身监禁。因此,对终身监禁制度正当性的探讨离不开对整个刑罚体系的综合考量,特别是该规则体系的创设目的、调整范围、是否有其他替代性措施等。
在具体操作层面,可细分为以下步骤:第一,列举可通过刑事程序实现的,除非为了一些可观的利益,否则理性人不会选择去冒险的刑罚;第二,剔除出这些刑罚措施中非人道的;第三,对剩下的刑罚措施予以分类,在各类内部进行排序,并将这种排序统一衡量;第四,列举所有的犯罪行为;第五,将犯罪行为予以分类,在各类内部进行排序,也将这种排序统一衡量;第六,将最大值的刑罚与最大值的犯罪相匹配,将最小值的刑罚与最小值的犯罪相匹配;第七,对新的刑罚依第二步、新的犯罪行为依第四步予以归类和排序,并按以上步骤进行。(56)Michael Davis, How to Make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 Ethics, Vol.93 (4), 1983. p.736-737.
依上述步骤,终身监禁如果要纳入一国的刑罚体系,可能遇到或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第二步中是否会将终身监禁作为“非人道”的刑罚措施而予以排除,以及在第三步中终身监禁在刑罚措施体系中如何被分类并排序,第七步中终身监禁该与哪些犯罪相匹配。只有当在第二步的考察中,终身监禁未被排除,才需要进行第三步和第七步的排序与匹配。在此,假定终身监禁本身不是“非人道”的刑罚措施,而第七步的匹配问题则依赖于对犯罪行为的衡量,并非是针对终身监禁本身的问题。(57)终身监禁是否属于“非人道”的刑罚,刑罚人道主义对此持怀疑态度,争议的焦点在于罪犯是否具有复归社会的人权。然而在死刑尚存的背景下,作为非肉刑的终身监禁虽给罪犯造成长期的身心痛苦,但在充分尊重罪犯人格尊严,也即未绝对剥夺其释放可能性的前提下,终身监禁并非是“非人道”的刑罚。因此,关键是解决第三步中终身监禁在刑罚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刑罚以剥夺绝对有限的个人权益为内容,而犯罪以相对无限的社会秩序为侵犯对象。这就决定了社会无法为每一种犯罪设计出一种与之在损害形态上对等的刑罚。(58)邱兴隆:《刑罚理性泛论——刑罚的正当性展开》,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年版,第140页。刑罚可以按照一个基本的方式,诉诸学说理论和法律假定进行分类。第一层次的分类聚焦于其所“作用的物理对象”,第二层次的分类是依刑法典记录的它的“严重性”。注意到教义方面,可以说,第一是死刑,接着是肉刑、剥夺自由、限制自由(流放、囚禁、驱逐)、剥夺权利、金钱刑罚和道德刑罚。(59)Mara Jose Falcon y Tella & Fernando Falcon y Tella, Punishment and Culture: A Right to Punish?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6, p.107.终身监禁作为终身剥夺犯罪人自由的刑罚,首先应纳入自由刑的范畴。由于自由刑具有可分性,故理论上自由刑可以包含无数种刑罚。而在自由刑内部,通常依剥夺自由的刑期长短对不同种类的自由刑进行排序。剥夺自由刑的严厉性也与刑期的长短成正比。终身监禁则因其终身性毫无疑问地成为自由刑中最大值的刑罚。同时,虽然一国的刑罚体系要求具有稳定性且依罪刑法定的原则,判决时的不定期刑将被禁止。但终身监禁与其他剥夺自由刑的区别在于其刑期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源于罪犯自然生命长短的不确定,还源于在终身监禁实施中罪犯释放可能性的不确定。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6条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可见对最严重的罪行,也即道德可责性最大的罪行方可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适用死刑。而在废除死刑的国家和考虑到终身监禁制度对死刑替代的价值取向,终身监禁制度也只能适用于道德可责性最大的小部分罪行。终身监禁不仅惩罚罪犯,还剥夺了他们实现救赎的任何希望,有很少的机会获得自由。大多数受到终身监禁惩罚的罪犯导致了痛苦的生活。总体而言,罪犯的年龄越小,他因终身在监狱服刑的时间就越长,而报应的后果通常随着监禁的长短而增加。更长的监禁通常具有更多的报应和更大的痛苦,因为刑罚实施的时间更长。(60)Michael L. Radelet, The Incremental Retributive Impact of a Death Sentence over Life Without Parol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Vol.49 (4), 2016, p.806.终身监禁罪犯所受的痛苦源于其身体上和社会上的孤立,以及他们永远从公民社会移除、瓦解与家庭的联系,并时常削弱在社区中所能负担的最小社会控制结构。(61)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16.终身监禁作为在理论上剥夺罪犯终身人身自由的刑罚,其执行时间长、耗费人力物力成本高,也给罪犯家庭造成物质和情感上的巨大伤害。然而,这种痛苦对道德可责性最大的犯罪人的施加却是正当的,绝对意义上复归社会的权利,对这些犯罪人而言是与刑罚的道德性相违背的。
在死刑执行的痛苦被认为是非人道、不道德的情形下,国家有必要通过符合道德的刑罚痛苦,强化公民对道德原则的坚持,保护社会免受最严重犯罪的侵害。但若将终身监禁适用于危害性程度不适当的犯罪,则会丧失刑罚的报应道德规则。刑罚通过识别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作为强化价值的沟通表达。如果一个人特定的犯罪行为按照社会标准如此严重,那么它便引发了对其在公民社会生活权利的剥夺。但如果这种剥夺被滥用,就会丧失刑罚的表达功能。(62)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19.这也正是刑罚报应主义实现刑罚公正的要求。
(二)终身监禁对刑罚功利主义的实现
应当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刑罚分配问题都可以通过仅仅诉诸罪犯的该当性而得到解决,在证成实际施加的刑罚是否具有正当性时,还必须考虑“额外该当性”因素。(63)[美]道格拉斯·胡萨克:《刑罚哲学》,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620页。在决定具体的应得刑罚是否应实际施加的时候,结果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64)[美]道格拉斯·胡萨克:《刑罚哲学》,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615页。这就需要引入功利主义者对结果的考量。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最善结果的行动方案在于对规则的违反,不那么做的话就会构成“规则崇拜”。(65)[澳]J.J.C.斯玛特、[英]伯纳德·威廉斯:《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劳东燕、刘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页。但如果考虑到,违反规则可能受到刑罚惩罚或承受道德上的煎熬,行为人则可能选择不实施违反规范的行为。这就涉及威慑和特殊预防的问题。
1. 终身监禁对一般预防的实现。对一般公众而言,终身监禁的威慑在于,如果实施相当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其将面临终身被剥夺自由不再复归社会的处境。威慑论者认为,即便威慑效果可能难以实现,或威慑效果并不好或是不能依立法者的预期来实现,但只要有证据证明它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即通过对一个人的对待作为其他许多人的例证,那么这种威慑就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66)Gerard V. Bradley, Retribution and the Secondary Aims of Punishm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Vol.44, p.120.这并不是将犯罪人所受的终身监禁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依责任主义原则,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而应得一定的惩罚,而这种惩罚的设定与实施所带来的威慑仅为终身监禁的一种附随效果。但客观上这种附随效果却能起到较好的威慑作用。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的劳苦来补偿其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鉴戒则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67)[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第66页。
然而一般威慑的实现需满足三个先决条件:第一,威慑的规则仅可在其意图威慑的对象直接或间接地意识到该规则时起作用;第二,即使目标受众知晓基于威慑的规则,威慑的效果也仅在他们具有依其最优利益理性计算的能力和倾向时才能发挥作用;第三,即使潜在的犯罪人知道基于威慑的规则,并且能够以他们的最优利益理性计算其行为,规则的威慑也仅在他们得出实施犯罪的代价超出了其所获得收益时起作用。(68)Paul H. Robinson, Life Without Parole Under Modern Theories of Punishment, in Charles J. Ogletree, Jr., and Austin Sarat edited, Life Without Parole: America’s New Death Penal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40.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假设刑罚会跟随他们对正义的直觉。因此,威慑在偏离人们的直觉正义时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就终身监禁而言,如果将终身监禁仅适用于如杀人等最严重的犯罪,依据人们的应得经验这一刑罚是公正合理的,也更易为潜在的犯罪人所知晓。但若如美国的终身监禁制度,不仅适用于谋杀罪等重罪,还适用于大量的毒品犯罪和累犯实施的犯罪,那么将很少有潜在的犯罪人实际知晓他们各州的具体实践。进一步而言,如果潜在的犯罪人知晓威慑的规则,但这些累犯或实施毒品犯罪的犯罪人因长期受到毒品、酒精、精神疾病或是扭曲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他们将比普通人更难拥有理性计算其行为后果的能力。更进一步的是,即使潜在的犯罪人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经过了理性计算,仍有多样化的因素可能最终导致其得出犯罪的收益大于其需付出代价的结论,其中包括逮捕率和判刑率。事实上,对于可适用终身监禁的严重犯罪的逮捕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普遍适用终身监禁的美国,对于可能适用终身监禁的毒品犯罪、杀人犯罪也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实施严重犯罪的罪犯中,仅有很小一部分被适用终身监禁。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可能得出结论:遭受终身监禁刑罚的遥远风险不足以严重到证明超越实施犯罪的现实利益。(69)Paul H. Robinson, Life without Parole under Modern Theories of Punishment, in Charles J. Ogletree, Jr., and Austin Sarat edited, Life Without Parole: America’s New Death Penal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41.因此,终身监禁的威慑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存疑的,它依赖于终身监禁的具体规则是否符合公众和潜在犯罪人的正义观念,取决于可适用终身监禁的犯罪类型及司法实践中终身监禁的实际适用情况。终身监禁的幽灵是假定被认为对所有犯罪都具有威慑,即使在严厉性上并不匹配。(70)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18.
2. 终身监禁对特殊预防的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终身监禁如此严重的刑罚后果与被剥夺一定期限自由的定期刑所带来的后果存在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体现在犯罪人是否具有复归社会的可能性。终身监禁与复归的联系,最早源于监禁刑积极作用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监禁不仅威慑意识到监狱痛苦的罪犯和其他人,还通过提高他们的技能和道德使其复归。(71)See Dirk van Zyl Smit &Catherine Appleton, Life Imprisonment: A Global Human Rights Analysi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7.复归刑罚理念的实施是意义深远的,它很明显地反对报应主义刑罚理论对基于犯罪行为比例性的强调和产生自终身监禁总是对最严重犯罪行为所保留的严酷刑罚的假设。将终身监禁作为其最大值的刑罚可以更自由地且对更广范围的犯罪行为施加。因为他们乐观地认为,即使不是全部,罪犯具有改造的能力,并且保证他们不在监狱待过度长的时间。(72)Dirk van Zyl Smit & Catherine Appleton, Life Imprisonment: A Global Human Rights Analysi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8.但通过科学方法对罪犯改造可能的乐观主义并没有被全世界所接受。如冯·李斯特等欧洲刑罚学者自19世纪末以来提升了对其的注意力,并在观念上认为一些犯罪人因为不可被威慑或是复归,因而是不可救药的。对这些能够被威慑的罪犯,应给予如贝卡利亚所主张的,与能够劝阻他们不再继续实施犯罪所需要的成比例刑罚。然而,真正“不可救药”的罪犯则不应被治愈,因而仅关押他们的余生,且没有任何释放的希望。(73)Dirk van Zyl Smit & Catherine Appleton, Life Imprisonment: A Global Human Rights Analysi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9.
基于此观点而实施的终身监禁是出于剥夺犯罪能力的考虑,也即为了实现特殊预防。特殊预防的对象是因实施犯罪行为被判处刑罚处罚的犯罪人。李斯特是特殊预防论的集大成者。根据他提出的概念,特殊预防具有三重形式的内涵:通过对行为人的监禁来保护一般公众免受其侵害,通过对行为人适用刑罚来威慑其不得实施其他犯罪行为,通过对行为人的矫正来防止其再犯罪。(74)王世洲:《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具体又可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特殊预防两个方面。消极的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刑罚遏制具体行为人重新犯罪,保护社会免受其侵害;积极的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刑罚对具体行为人进行矫正,从而使之重新社会化。(75)王世洲:《现代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犯罪人而言,其终身被剥夺自由与社会隔离,丧失了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和条件,终身监禁发挥了较好的消极预防效果;而在积极的特殊预防方面,犯罪人终生在监狱服刑,其危害行为可以得到长时间的、系统性的矫正,但由于犯罪人缺乏重新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对其社会化再适应能力的培养可能被忽视。据此,有观点对终身监禁积极的特殊预防效果予以了否定,同时对通过剥夺终身自由的方式来实现消极特殊预防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
然而,从理论的角度,贝卡利亚、边沁等古典犯罪学理论推测,使丧失犯罪能力需对一些挑选的罪犯保留:具有极端高危险的应当永远与公民社会分离的个人。(76)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20.但这些罪犯的范围应受到严格的限制。终身监禁者不享有国家给予机会的承诺,再次考虑他们在公民社会生活的自由机会被官方永久地侵犯了。(77)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06.终身监禁却能与剥夺自由的刑罚威慑相适应,如果特定的犯罪依照社会标准是如此严重,那么它便引发了对罪犯在公民社会生活权利的没收。剥夺再犯能力作为一项功利主义的工具提供了防止犯罪的功能。其合理之处在于,允许官方挑选出具有最高再犯危险的罪犯,从而取消他们获得释放的机会。(78)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19.通过监禁的方式终身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对于预防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特别是针对已多次实施严重犯罪的累犯,具有必要性。在美国,终身监禁作为一项现代刑罚制度,其设立之初即是为了惩治累犯。然而,并非针对所有实施严重犯罪的累犯都应适用终身监禁,剥夺能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一种有价值的主张,即我们能够证明,对实施特定行为者若不加以剥夺能力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继续该行为。(79)[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终身监禁显然与剥夺再犯能力的目标相一致,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些罪犯复归社会的可能性。因此,从剥夺犯罪能力的角度,终身监禁对最危险的罪犯以外的犯罪人适用是不必要且无效的。但应当说明的是,单纯因终身监禁剥夺了罪犯复归社会的权利而否定其积极的特殊预防效果是不合理的。因为监禁刑本身能否实现社会化再适应的效果是存在疑问的。作为20世纪现代刑事政策理论的新社会防卫论,就反对通过监禁的方式实现犯罪人社会化再适应的观点。监禁刑本身即是将犯罪人与社会相隔绝,又如何要求通过监狱内的处遇实现犯罪人的社会化?很显然,这种方式是手段与目的的南辕北辙。定期的监禁刑尚且如此,作为长期监禁刑的终身监禁则更难承担使罪犯再社会化的职责。但即使罪犯终身在监狱服刑,也可以通过家人探望、完成工作等方式保持其社会化的联系。无论在过去或者现在,都可以推测出来的一点是,就刑罚的恢复和再社会化功能来说,倒不如说它们与长期自由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80)[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重罪量刑:关于刑量确立与刑量阐释的比较性理论与实证研究》,熊琦等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同时,终身监禁因不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代价低于死刑,其在剥夺犯罪能力方面不如死刑彻底,不但因其所具有的改造作用而部分得到弥补,也因其代价远比死刑小而使得其投入产出比并不亚于死刑的投入产出比。(81)邱兴隆:《刑罚理性泛论——刑罚的正当性展开》,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
结 论
依报应和威慑理论的相对损害排序,终身监禁的极端属性意味着它仅在对最严重的犯罪,如故意谋杀、最严重的累犯的适用上才具有正当性。在剥夺犯罪能力上适用终身监禁,也只有在其作为保护社会的最后必要手段上才具有道德合理性。(82)Melissa Hamilton, Some Facts about Life: Th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fe Sentences, Lewis &Clark Law Review, Vol.20 (3), 2016, p.807.类似的,一些案件不可能精确计算一个罪犯“应得”什么,特别是因为许多罪犯拥有精神健康问题或者是有身体、精神、情感或受性虐待的背景。决定一个人“应得”哪些,完全不是顺从于精确的计算或是衡量,即使是,也有很高的风险在衡量上的错误。因此,我们不能精确衡量刑罚的强度,正如我们不能精确衡量罪犯在实施死刑犯罪时让无辜的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即使我们决定了一个人“应得”哪些,但并不强迫我们去给予或是实施它。(83)Michael L. Radelet, The Incremental Retributive Impact of a Death Sentence over Life Without Parol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Vol.49 (4), 2016, p.803.对于终身监禁的适用亦是如此,它虽然具有实现刑罚目的可能但是否需要通过终身监禁的实施来实现刑罚目的,在具体案件中终身监禁的实施又是否具有正当性,则是需要经过个案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