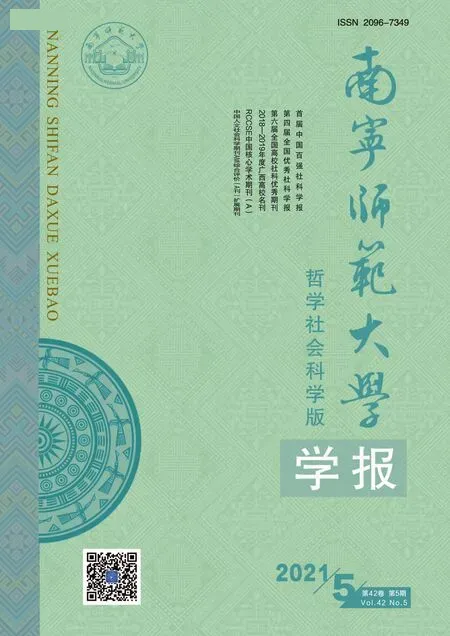王道政治理想的形上基础与价值追求
——评李锋《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
周恩荣
长江师范学院 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中国古典政治理想中,王道还是霸道?道义论还是功利论?理想与现实之间究竟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思想家们对此聚讼不已,南宋时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则将此推向了高峰。此次论辩中,坚持道义论王道理想的朱熹在继承传统王道理念的基础上,将其奠基于天理、人性等形上根据之上,并摆脱了传统王道理想的复古主义倾向,赋予王道理想新的内涵,而以之为理想政治的标准。李锋在《中国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以朱熹的政治哲学为核心》(以下简称“李著”)一书中具体而清晰地呈现了朱熹对王道理想的重构,提供了形上基础,阐明了价值追求。
李著逻辑严密,主题观念一以贯之,对所涉及论题均能追源溯流、厘清发展脉络,功底扎实,能从容游走于中西之间。在总结朱熹政治哲学为中国古代治理所提供的道德正当性证成之前,李著先澄清了王道政治理想的内涵,对王道理想的道义优先原则展开了分析,并对道义原则的“性理”根源作了追溯。不过,李著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论题。对朱熹王道理想在终极价值追求方面的局限性,李著虽有所分析与回应,但仍留有巨大的空间,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拙文拟对此予以扼要分析。
一、王道政治理想
按照李著的观点,王道政治理想内涵十分丰富,“既是理想的治理状态,也意味着恰当的治国之道”[1]143。但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王道,王道与霸道(依恃暴力的治理)之间的界限何在”[1]143等问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认识分歧。由于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的差异,中国传统思想家们的王道理想经历了从“先王之道”到“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1]143的转变。
李著指出,先秦两汉思想家倾向于把王道理解为“先王之道”。原因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重视“参验”的思维方式,将王道理想诉诸经验性的历史过程。质言之,先秦两汉儒者依据典籍中古代圣王统治施政的记载,把王道理念与这种半是源于想象、半是真实发生的经验性历史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道德原则、政治制度与治国方法相等同,并谓之为平汤正直的“王道”。这种基于素朴的、经验性思维的王道政治观直接把古代圣王施行的道德原则、政治制度、治国之策当作“理想”和“标准”,在实质上颠倒了王道理想与古代圣王之治间的因果关系(1)也就是说,先秦两汉的王道理想中,符合想象中的、古代圣王施治的“经验性事实”是因,成为王道理想是果。但事实上,此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古代圣王之治是因为符合道义原则才成为“王道”理想。,带有非常浓厚的复古色彩,引起了“守株待兔”的嘲讽。要使王道理想摆脱“守株待兔”“抱残守缺”之讥,跳出“复古”窠臼,需要以新的思维方式,从经验性历史过程中抽象出王道理想的规范性内涵,以为社会政治生活应然的理想与标准。李著指出,这项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的肩上。
自“二程”兄弟体贴出“天理”二字以来,儒学借助于道、佛二氏之襄助,思维的形上化和抽象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也为王道理想摆脱诉诸偶然性经验事实的局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朱熹完成了“道”的形上学论证,并明确指出“道即理之谓也”[1]147。“理”是天地万物所以为其自身的根据,“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1]147,以此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终极标准,乃是对尧舜之道、文武之政的抽象,超越了古代学者关于“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争论,以贯穿于历史过程中恒久不变的“道理”作为评价政治善恶的标准。如此一来,理想的政治、治理便拒斥了关于王道的相对主义理解,正确地将王道之值得欲求的根据置于其内在价值之上。质言之,“王道”之神圣,不在其由先王所施行,而在其自身具有内在价值。于是,规范性政治理想与经验性历史过程既相互剥离,又保持着理论上的关联性,而王道政治理想“符合道义原则”的内涵亦得以厘定。
然则,“道义”是何原则?亦成必须解答的问题。
二、道义优先原则
王道政治即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同时亦以道义原则为品分政治的标准。王道与霸道的区分就在其与道义原则的依违之间。因而王道与霸道泾渭分明,性质根本对立。与此相对,在陈亮及其功利主义同道看来,唯有事功或政治统治之功效,才是衡量政治优劣的标准。因而,王道与霸道并无质的不同,差别只在于获得事功的量有大小而已。质言之,在功利主义政治的倡导者看来,霸道政治或许采用了与所谓王道政治不同的统治方式与手段,但它们都同样以政治功效的最大化为目标,因而都在好的政治之列(2)在此,功利主义政治的倡导者们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把“效果”视为衡量政治之善恶、优劣的标准,另一方面又仅仅依靠“动机”——以政治功效最大化为目标——便以为王道与霸道没有质的不同。。顺此逻辑,陈亮甚至把汉唐这类虽在“历史上曾经获得成功”却依恃“暴力”为治的王朝“都看作王道”[1]151。陈亮的做法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王道政治的根本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帝王的事功,还是所谓“道义”原则?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什么样的“道义”原则有资格成为王道政治的依据?
对此,朱熹的回答是,必须以道义原则为王道政治的根本内涵,在“仁义”与功利之间,必须以“仁义”优先于功利。朱熹在《送张仲隆序》中说:“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2]尽管朱熹承认功利在政治的评价中应有一定的位置,但绝不能将功利当作决定性的标准。以孔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3]144为据,朱熹认为,虽然圣人孔子也称颂管仲的事功,但孟子和董仲舒根据仁义至上的“法义”标准,对管仲推崇功利、霸道却一点都不宽容;原因无他,乃因管仲之“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相对地,只有“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4]。这即是说,圣贤、英雄所建立的成就,只有通过“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工夫,并依据“仁义”之道,才有可能被纳入“彻头彻尾,无不尽善”的王道。相反,以赢求功利为目的的政治,虽常因偶然地为统治者带来可观的富强事功而被误认为是王道,但亦难以消减朱熹的质疑与批评,因为其中“可观的富强事功”的取得,依靠的是外在的、偶然性极强的“力”。根据孟子“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3]218,“霸道”寻求政治统治的事功,依赖于“以力服人”,如此,“力”在身时“人”服,一旦“身”失强力,或被他者的力量超越时,其政治统治的事功也将失效;与此相对,“仁政”或“王道”乃是“以德行仁”,其收获事功之效,靠的是“以德服人”[3]219,是人民的“中心悦而诚服”[3]219,故而“王不待大”[3]218,而有长久的政治事功。以此,虽然“王道”和“霸道”都以追求政治功效的最大化为目标,但由于各自所依循的原则、依据,采纳的手段、方式不同,所取得的政治功效不仅在道德上有异,而且在盖然性和持久性方面也有差别。
对朱熹而言,义利之辨不止于个人品德,更是政治方面好与不好的“分水岭”。只有在坚持“道义优先”的前提下,对功利的追求才可取,所取得的功利也才有必然和长效之可期。此外,李著还联系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正义优先于功利”的立场,强调正义之于社会政治的首要价值和绝对标准的地位,“在正义与不正义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过渡形式……无论采用霸道的形式获得了多么大的事功,都会因为违背天理道义而不能被接受”[1]154。
总之,在国家治理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争论中,朱熹坚持道义论,强调以道德法则为主导,以公平正义等价值为目标,通过“以理制欲”“义为利之依据”等原则,为理欲之辨、义利一体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解答。朱熹不仅贯彻了“道义优先”的立场,还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回答了“道义”的性质、源头等问题。
三、“道义”源于性理
对何种道义原则有资格成为王道政治的根据这一问题,李著认为朱熹的回答是,源自天理人性的道义原则或道德法则,有资格成为王道政治理想的根据。由于“天理人性”问题的基础性地位,李著首先讨论了朱熹这两个方面的思想。
把社会政治秩序奠基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永恒持存的可能,是人类长期以来的追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奠基,经历了从“天”到“天理”的变迁。根据李著,这一变迁的背后是人们思维方式抽象化水平的提升。李著指出,先秦两汉思想家深受参验思维的影响,因而在探索社会政治秩序的形上基础时,往往诉诸经验性事实而非形上概念[1]44-48。“天”或“天(之)道”是他们为社会政治秩序的持存及各种德行品质,如仁、义、忠、信等,找到的基础。他们甚至在争论人性善恶、为政治哲学提供逻辑起点时,也常常将其当作可经验实证的“事实”,而不是“应然”的抽象假定(3)当代学术界与先秦两汉思想家一样,都有把人性善恶问题错误地当作经验实证的“事实”而非“应然的”抽象假定的情况。事实上,人性问题颇为复杂,从不同的研究进路出发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但无论如何,一旦对人性判之以善恶,也便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质言之,“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的问题,根本上并非经验实证的问题,而是一种价值评判。李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但颇为遗憾,其未能展开深入讨论。。其结果是,混淆了理性世界与现实世界之边界,难以为那充作社会政治秩序基础的道德法则及其普遍性提供充分的证成。
凭借对“易学”中“形而上之道”的发挥,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完成了为有道德基础的治理(或可谓之“善治”)提供本体论依据的使命。这一工作是通过从形而上学层面论证“天理”或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与绝对性来完成的。
李著指出,朱熹在“把天理理解为逻辑先定的宇宙本体的同时”[1]66,首先“实现了伦理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统一”[1]66,进而“在 ‘理在气先’的本体论结构下”[1]68,把“天理”理解为由“理性建构”的永恒者,“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以往思想家对于道德法则的相对性的理解”[1]68,把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的哲理化提到了更高的水平;并一改过去委诸“历史经验”的做法,从“符合‘天理’”的角度,为治国理政的正当性提供了新的解释与说明[1]67-71。于是,理性建构的、绝对普遍的天理,作为伦理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统一,不仅为天地万物提供了本体论根据,也为王道理想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尤其自休谟以来,道德哲学的主流强调自然领域与道德实践领域的区分,对于道德的本质或本体问题,出现了实在论和建构论的争议。道德实在论者认为,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与自然中的客观实体类似的价值实体,故而道德要求有绝对的、普遍必然的效力。道德建构论者认为,道德本质上是人为建构的价值观念,其要求是否具有绝对的、普遍必然的效力,依赖于其是否与普遍必然的理性的道德法则相一致。因此,主张道德情感主义的休谟才会提出“事实”与“价值”判然分离的问题;而坚持自律道德论的康德则通过把道德律(或道德法则)处理为“理性的事实”,以回应事实与价值二分的问题。朱熹视“天理”为伦理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统一,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此处“伦理法则”究竟是道德实体,还是观念的建构?当作为伦理法则的“天理”是人为建构的观念时,它如何能规约自然实体?当它作为与自然法则类似的道德实体时,人按照它而起用,如何可能是能动的、自律的?李著未能处理此问题,诚为一小小的遗憾。
除此之外,朱熹还结合“理一分殊”与“性善气禀”,回应了性善论视野下人的道德品质何以有等差的问题。对此,李著认为,朱熹的贡献是把“气”这一概念引入传统的人性论,“找到了沟通性善论与现实道德差别的理论依据,从而解决了传统儒家人性论中的逻辑矛盾,进而为儒家德治主义治理方式提供了人性根基”[1]90。至此,朱熹完成了道义原则的“天理人性”溯源,证成了王道政治的“道义优先”原则。
四、王道理想的价值追求:“王道”耶?“恤民”耶?
恰如李著所说,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王道政治存在着“崇道”与“尊君”的两难选择[1]135-136。朱熹不可能超越这样的时代背景,在“尊君”或“崇道”之外,提出新的价值追求之可能。他在“尊君”同时还能坚持“崇道”理想,已属难能可贵。李著指出,在朱熹政治哲学中的“君”与“道”之间,朱熹的立场是要求“君”遵“道”而施治,“道”之为形上的道德法则,无人可垄断、独享[1]136-138。尤其是“三代”以后,“治”“道”分离,“道”不行于天下,须有儒者讲明为治之道,以为理想政治秩序之重建提供标准,为批判君权提供思想资源。在朱熹和持相近立场的儒者看来,君臣相与的理想模式是:共同履行“弘道”的使命,君主臣辅,共襄“行道天下”之盛举。朱熹反对“尊君卑臣”的观念,因为其有神圣化现实君主、使君取“道”而代之的可能。不过,“尊君卑臣”固然有“骄君”之虞,但“崇道”又何尝不会产生“乱臣”?历史上篡弑之臣,全都是一副“道在我身”的样子。虽然由“崇道”到“乱臣篡弑”之间存在着“跳跃”,其亦非朱熹所愿,但皇权专制制度下王道理想中“崇道”与“尊君”的两难,是朱熹政治哲学无法走出的藩篱。
因此,当“崇道”有产生“乱臣”之可能时,朱熹的立场立即退回到“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不易,不变也)”[5]之上。质言之,“无论朱熹怎样把‘道义’置于绝对的地位,他都无法跳出君主专制的思维定式和尊君罪臣的窠臼”[1]138。亦即,朱熹的“崇道”其实是在“尊君”的前提之下,寄望于“君”之与道义相合。“篡弑乱臣”不可能合于道义,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他们都难脱“罪臣”之名。
概言之,朱熹王道理想的价值追求,在“崇道”与“尊君”之间。这是由于他的价值观念与思想资源的局限。作为南宋道学的旗帜,朱熹坚守“以道为尊”的道学立场,阐扬自伏羲黄帝尧舜而“二程”的“道统之传”。对他而言,“正君心”以崇道、弘道是“天下之大本”。言下之意,现实中的君王虽有聪明睿智,但亦难免受到蒙蔽而有“一念之间未能彻其私邪之弊”[6]27,故而需要向君王讲明“正心诚意”之旨,以辅助君王能“行道天下”。正如李著所说,朱熹所“尊”并非现实中的君王,而是理想的、完全合于道义之君,唯此,“崇道”与“尊君”始能合二为一[1]138。但现实中君王不可能完全合于道义,“崇道”与“尊君”始终不能合二为一,致使面临着道义原则与任性权力冲突的道学家,必须在以至上的道义法则及相关制度约束权力或通过“格君心之非”以塑造理想君王之间作出选择。由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思想资源不足,朱熹只能把王道理想的实现寄托于为政者之“心”。而此“心”能否(更遑论自觉)接受“道”的规范、引导,实是极为偶然。李著对朱熹政治哲学思想的这一局限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强调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142。
不过,就政治哲学本身的普遍价值追求而言,在道义与权力之外,甚至在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之外,还有没有更高的追求?质言之,追问为什么要严守道义原则、规范君主,为什么要建立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等,是否是合理之事?对此,答案是肯定的。政治哲学的终极价值追求,应当是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盼的满足。朱熹曾于1180年(庚子年)应诏上书直谏,“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但旋即转回来说,“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6]12,一下子从忧虑、体恤民众疾苦,落回到“正君心”“立纲纪”之上。可见,在朱熹政治哲学的王道理想中,“崇道”与“尊君”仍然是终极价值追求,而真正应该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终极理想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尚未被提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日程。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余英时把宋、明两代理学的政治文化概括为“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7]36。姑且不论此种概括是否合乎实际,即便事实如此,“得君”与“觉民”只是“殊途”,“行道”才是“同归”。只是所行之“道”究竟如何,具体所指究竟为何,宋明诸大儒未确然明指,但应不出“仁义之道”。余英时则笼统言之以“道体”,指其为“一种永恒而普遍的精神实有”[7]28,但其究竟是何种精神实有,其具体的含义与功能究竟是什么,仍处于抽象、朦胧之中;而李著以“先王之道”或“天理”“普遍而绝对的道德法则”概括之,其实是一种“错置”,或至少仍稍嫌抽象。此处所行之“道”,或“善治”的终极价值,当以美好生活的满足与实现为旨归,或如牟宗三引《易传·乾彖》之“各正性命”:每个人遵循其作为圆满具足的个体人格而得以实现,或者顺其“本真之性”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各遂其生”[8],达到“程夫子与苏东坡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
五、余论
除了探讨朱熹王道政治理想的形上基础与价值追求,李著还提出了一些启人深思的观点。
一是在讨论“天理论”时,把陈来关于朱子理气论的“本源”与“构成”区分[9],抽象为“本源论”与“构成论”,弥合或解释看似矛盾冲突的观点,使之和谐共存,并以理气关系论“性善”“情恶”,以说明性善前提之下道德品质差异的存在根源。二是扭转了中国政治哲学逻辑起点——人性善恶争论的发问方向,指出其理应为“逻辑假定”,而非可由经验实证的“事实”。人性善恶争论不可以科学实证之法证实或证伪,因其并非事实之真假;关于人性的善恶判断实质上是一个基于价值评判的信念,是实践哲学各门类的逻辑起点。三是在讨论朱熹理欲对立时,借助康德关于意志或法则与经验幸福之关系,澄清其有效性的边界,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质言之,理欲对立只有在何者能规定行为是否有道德价值时才有意义。离开作为道德价值的规定根据来讨论理欲对立,都未能真正理解朱熹“存理去欲”说的意义。四是援引亚里士多德公正论中的“几何或比例平等”来解释朱熹“理一分殊”中的平等观念,颇具启发意义。
至于其以理气关系论性善与道德品质差异,为本原的性善与现实的道德品质差异分别提供先验的依据,使传统儒家人性论臻于完备,以及朱熹并非简单照搬孟子的性善论,而是明指人先验地“具有全部的道德能力和道德内容”[1]68等,亦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李著亦有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除了前文提到的“道德实在论与道德建构论背景下伦理法则的效力”和朱熹王道理想的终极价值追求应当是什么,还有以下问题:王道政治之可欲,人所共知,但其如何可能、其实践效果如何、怎样防止理想的政治秩序滑向其反面?在讨论王霸义利之争时,李著指出,“由于人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这种合目的性的特点,陆九渊把道德法则与人自身联系起来就更有意义”[1]88,其潜台词是朱熹未能把道德法则与人自身联系起来,这如何与书中对朱熹道德哲学的自律(4)关于朱熹的道德哲学是否自律,李著认同陈来的观点,以为“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是把正谊不谋利作为基本实践原理”,并据此强调程朱伦理学与康德的他律“有很大的距离”。陈来把“正谊不谋利”当作自律伦理学的标志,此显然与道德自律的内涵“有很大的距离”。就字面意思看,“自律”是“自我约束,使遵循法度”,而非“正谊不谋利”;前者正与康德把“自律”理解为“自立法、自守法”相当。亦可参见周恩荣《牟宗三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治理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中关于“天道性命”的探讨。以及建构主义定位相协调?此外,在讨论王霸义利之争时,李著以道义优先和功利优先区以别之,倘若能结合当代“利益政治抑或原则政治”的讨论,将会使论述更为深入和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