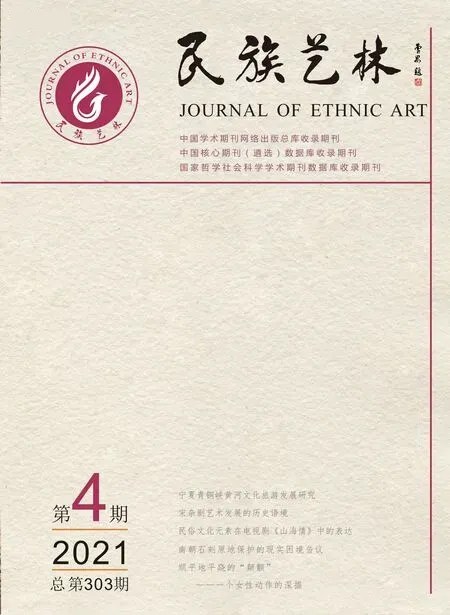论四川地区东汉陶俑的古拙美
刘兴勇
(吉林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汉代,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与艺术的发展。在儒家、道家哲学的影响下逐渐构建起了社会的伦理道德风尚,并深刻反映到汉代的绘画、书法、音乐、雕塑等领域,彰显着时代整体的民族精神。
在汉代多样的艺术形态中,陶俑以其在造型、制作手法、题材等方面表现的奔放、简朴的审美特征,在汉代美术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目前出土情况来看,东汉陶俑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突出,以其内含旺盛的生命力,形象生动地体现出四川地区人民乐观、朴实的生活状态,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社会生产水平,也是陶塑工艺高度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奠定了其在中国雕塑史上别开生面的历史地位。
无论是在博物馆还是相关历史文献中所见,东汉时期陶俑多表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情态。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每一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1]在东汉时期所盛行的“孝悌之风”以及“世以厚葬为德”的文化观念与四川地区独特、朴素的社会民俗多重影响与作用下,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如此数量庞大以及具有丰富生动性的陶俑艺术作品。
一、四川地区东汉陶俑基本状况
中国陶塑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陶俑则属于其中较为常见且取得巨大发展的一种类型。1937 年在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灰陶人形俑是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最早的陶俑。[2]
经过商周时期的孕育与发展,陶塑艺术至东汉时,各方面都已经趋于成熟。东汉初年,在一系列减赋政策的实施推动下,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为文化艺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四川地区是东汉时期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几个地区之一,《后汉书·公孙述传》中记载:“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3]天府之国的富裕程度可见一斑,强盛的经济与优良的地理条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加之隶属于少府的东园设东园匠令丞主管陵内器物制作[4],至东汉晚期,四川地区陶俑制作已发展至鼎盛阶段,陶俑种类丰富多样,题材的表现则倾向于轻松自由,表现了舞乐、侍女、劳作、奴役甚至手持刀盾的武士俑等大量的人物形象与日常生活场景。无论是乐舞说唱俑还是生活劳作俑,工匠在造型上都抓住了人物对象在活动过程中瞬间的姿态动作,面部表情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传达出了东汉社会真实的生活形态与人物情感,给人一种既浪漫朴素又乐观稚拙的风格特点。制作手法大多是模制而成,少数小型的陶俑则采取的是直接用手捏制成型再进行窑烧的方法,虽然部分陶俑的头和四肢等部分是分模制作然后进行组装拼合的,但陶俑形象并没有因为模制而出现呆板雷同的现象,大多数陶俑都取得了和谐一致的视觉效果。不同于西汉陶俑面部神态庄严端庄的是,四川出土的东汉陶俑在面部上多是喜笑颜开、眉开眼笑的神情;在艺术风格上有着突出的地域特色,始终散发着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以及自内而外的喜悦与幸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汉代第一俑”的东汉击鼓说唱俑便是四川地区东汉最富特色与代表性的一件陶俑作品。
总体看来,成就卓著的东汉陶俑不仅是汉代开放自信的时代特征与四川地区文化融合的产物,而且在吸收借鉴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包含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呈现出一种古拙朴素、质拙大气的时代美感。
二、四川地区东汉陶俑的古拙美
“古拙”有着“古旧朴拙、古雅质朴”之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道:“‘古’,故也。”[5]即时代久远的、过去的,与今相对;“‘拙’,不巧也。”[6]即笨拙、不灵巧。实际上,“古拙”的形态特征并不是在东汉时期才产生的,早在原始陶塑中就已经有所显现。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仰韶文化中的陶塑都已经出现了这种古拙的样式。这些陶塑的制作过程似乎有着很强的随意性,手法粗糙,造型简练,形体厚实,尺寸普遍偏小,但是依然塑造出了表现对象生动活泼的姿态。至东汉时,陶俑的制作技艺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原始陶塑中笨拙的造型和样式特征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和发展。
从陶俑风格形成的文化背景来看,汉代虽然在法律制度与政治经济等方面承袭了秦朝体制,但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却更多受到楚文化影响,“四面楚歌”以及刘邦衣锦还乡大唱《大风》等都能见出楚文化的影响,楚汉文化可谓是一脉相承,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极为明显的连续性和承接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汉代艺术的核心精神正是源自楚文化。李泽厚在谈及屈骚传统时,甚至认为楚文化中的浪漫主义精神是主导汉代艺术特有的美学思潮。[7]在《美的历程》中谈及汉代艺术时提到:“……对象,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8]这种古拙依靠动作、神态、情节表现而非细微之处的刻画以及粗轮廓塑造决定了汉代艺术“古拙”的整体艺术风格;从艺术外显的形式来看,“汉代艺术形象看起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9]正是这种带有不合乎现实情况的姿态和形式的“笨拙”与来自运动、力量的气势感共同决定了陶俑“拙”的形态特征;从艺术内涵来看,在汉代艺术粗糙、简单、笨拙的外表之下隐含着一股面对未知自然继续生存的豁达精神,与艺术形象融合便形成了一种带有天然韵律的古拙美感。进而以一种沉着、古朴的精神与气质构成了汉代艺术的基本风格。
四川地区东汉陶俑在汉代社会思想文化潮流以及沉着、古朴、浪漫的精神气质的双重影响下,古拙的美感逐渐在造型上、制作手法上以及题材上得到显现。在造型上,大胆、夸张的造型给人一种笨拙的感觉;陶土原始的古朴气息与不做细节刻画的捏制、模制、模捏结合等制作手法的运用使得东汉陶俑形成了一种具有粗犷外形和粗糙肌理的质拙感;对背儿女以及日常劳作、民间说唱等底层市井生活的表现又在题材上体现出了东汉陶俑的敦厚淳朴。
在造型上,“大巧若拙”是东汉陶俑的一大特点。虽然陶俑外在形象是笨拙不巧的,但依然体现出了表现对象的神完气足。四川地区的陶俑主要集中在成都、绵阳、新都等平原地带,且陶俑体量往往很小。在四川众多陶俑形制中,说唱俑最具代表性,主要有坐式和立式两种形态,多为一手抱鼓、一手执槌、袒露上身的形象,动作神态淳朴诙谐。在立式说唱俑中分别以1963 年在成都郫县宋家林东汉砖室墓出土以及1986 年在绵阳市河边乡九龙山东汉崖墓出土的两件说唱俑最有代表性。前者为泥质灰陶,通高66.5 厘米,后者是泥质红陶,高55 厘米。人们所熟知的于1957 年在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的“东汉击鼓说唱俑”,则是坐式说唱俑中最具特色的一件陶俑,独特想象力和夸张造型的完美结合,使其在当下看来亦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样式;该俑像为红陶材质,通高77 厘米,坐于一圆垫上。表现的是一名男性艺人正在认真表演的场景,他头顶系一花结,咧嘴大笑,耸肩塌胸,小腹圆鼓,左手环抱扁鼓于腰间,右手举槌上扬作敲击状,右脚赤足上翘,刻画的正是说书艺人说到精彩的地方而忘乎所以、乐不可支的状态。雕刻家在陶俑塑造过程中,忽视了人体比例的准确性,而更注重表现说书艺人在舞台上表演的动人情景,将不合比例发挥到了极致,陶俑外表也称不上华丽,表情略显夸张。这种憨厚可爱、朴实淳厚的表情与动作难以掩盖陶俑所表现的四川地区人民真实欢乐的生活情态与精神气质,于笨拙中见出灵巧,让观者被其滑稽的动态和表情所感染。
楚文化中狂放的思想和不羁的原始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汉陶俑大胆、夸张的造型手法。雕刻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删减了细枝末节的东西,舍弃了西汉宫廷舞俑姿态优美、举止高雅的刻画方法,利用粗轮廓写实的造型手法将人们乐天淳朴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征融入陶俑中,以及说书艺人内在的精神气质也以一种概括、夸张、提炼的手法表现了出来。但这种笨拙古老的形象以及不符合比例的姿态不仅没有减弱说唱俑在表演过程中的气势、运动和力量,反而使这些感觉进一步增强。将笨拙的“形”与生动活泼的“神”统一起来,于和谐中见出美,从而在“不巧”的外表下生发出“巧”的意蕴。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谈“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时说道:“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10]东汉工匠在制作陶俑时,不斤斤于人工纤巧的计虑,将概括夸张的造型和汉代人民乐观、淳朴的气质与精神面貌统一于陶俑笨拙的形态中,表现出了一种质朴大气的古拙形态,以求达到形与神的和谐统一,形成了四川地区东汉陶俑寓巧于拙的风格。这种风格所体现出的古拙美远高于工巧的审美标准,因为欣赏者欣赏的并非其外形,而是透其形赏其神以及形而上的内在品格体味。
四川东汉陶俑不仅在造型上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制作手法也较前人有了一定的进步与发展,主要有捏制、模制、模捏结合等几种方式,加之泥土原始、朴素的气息与忽略细节的刻画,使陶俑表面显得粗犷而又拙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质拙的感觉。丰富的制作手法决定了东汉陶俑以及我国古代雕塑善于用整体形象表现题材的特点。通过美术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古罗马雕塑中大多都是高度写实的人物胸像;而在出土的众多东汉陶俑中,不仅大多为完整的人物形象,工匠在进行塑造时还往往将穿戴、手执之物也一一表现;如郫县宋家林出土的东汉陶说唱俑,直接捏塑而成,俑身表面粗糙,不加修饰。头戴小尖帽,上身赤裸、下着长裤,整个人歪头耸肩,一手执鼓、一手执槌。又如1963 年于成都市郫县宋家林东汉砖墓出土的东汉陶执镜俑,通高61.4 厘米,黄灰陶质,头部稍稍扬起,以两花相饰,嘴巴微张,表情生动可爱至极,左手持一圆镜置于胸前,右手覆于腿之上,表现的应是正在伺候主人梳妆打扮的场景;陶俑由头和俑身分别制好后组合拼贴而成,手中的鼓、槌、镜子等物品在陶俑制好以后再捏塑于上,仔细观察可见明显的手捏、拼合的痕迹,但并不妨碍陶俑的整体性表达。这样的塑造方式不仅增加了陶俑的完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表现对象的真实性。其次,陶俑本身属于圆雕,但是我们所见的大部分陶俑都施用了线条,以此来表现面部表情或者刻画衣纹,线条劲力挺拔,给人一种流畅、轻快之感,真切地勾勒出东汉陶俑质拙的时代特色。如说唱俑额头以线条刻画的因卖力表演而导致的皱纹,便使陶俑顿时充满了诙谐、俏皮的感觉;又如舞乐俑等服饰的衣纹仅通过几根略显随意的线条来刻画,但却十分恰当地表现出舞蹈的轻快以及质朴。尽管此时的线条运用还不是特别熟练,粗重变化较少,但是依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且取得了活泼生动的艺术效果。
《淮南子·说林训》中说道:“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悦)于目。”[11]捏制、模制以及模捏结合等手法的运用,使得陶俑避免了千篇一律的程式化样式,而是各有特点。捏制即直接用手捏制成型最后入窑烧制而成,形体普遍较小且多为实心;相反,模制的俑像则多为空心,先根据俑像翻制出“范”,再进行成批制作,经过入窑烧制而成。最后则是模捏结合的方法,即同时使用捏制和模制两种方法,在制作俑像时,待俑像主体用模制好后,在未干时便以捏塑的方法制作衣纹头饰和手提之物等黏合在陶俑的相关部位。并对面部、手足等局部使用夸张、概括的手法来进行削、刻、画等补充,此种方法在陶俑身体接合转折以及细节的地方往往会留下明显的削刮修整的痕迹。制作手法以及原材料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使陶俑显得平淡自然、古朴质拙。不难发现,无论是与之前的秦俑或西汉陶俑,还是与后来有着丰富成就的晋唐陶俑相比,东汉陶俑总是能够因其朴实无华的外表脱颖而出,让人一眼便被其粗糙、拙笨的外在形象所吸引。
在题材方面,不同于西汉陶俑多表现宫廷乐舞生活、仪仗队伍等题材,东汉时期的陶俑更多地表现了平民、市井等底层生活。东汉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促使社会普遍开始追求现实生活的享受与满足,这种对生活的追求以及丧葬习俗观念的转变也反映到了艺术创作中。陶俑工匠开始将这些生活题材纳入自己的创作中,以独特的方式取材生活、表现生活、记录生活,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同时,这也是东汉陶俑比西汉陶俑反映内容更广泛的原因之一。恭顺的男女侍从,负责清扫、农事、庖厨等劳作的仆役,专职奏乐、舞蹈、说唱等事务的百戏以及执械保护庄园的武士俑等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四川地区东汉陶俑的题材范围,而且都是当时豪门强户、地主豪绅“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千”[12]的丰富生活的真实反映。
东汉陶背负俑、东汉陶背儿捧箕俑、庖厨俑等表现刻画的都是彼时底层劳动人民日常的现实生活场景。庖厨俑表现的厨师、厨房、菜肴等,我们常见的多是一人袖口上卷,跪坐于案前,案几上堆满了鸡鸭鱼肉等各类食材,正在杀鱼或是择菜之类的形象,生动展现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和饮食文化。又如新津县出土的几件陶俑:背负俑,表现的是一人背背篓的形象;背儿捧箕女俑,表现的是一妇女背着幼儿筛簸箕劳作的形象;背儿女俑,则是一妇女背着一幼儿望向远方的场景。这几件作品形象简洁,刻画出了东汉时期四川地区人民朴素简朴的日常生活。
四川地区东汉陶俑与西汉陶俑在表现题材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汉陶俑主要有表现军事题材的兵马仪仗俑(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秦俑的题材特点)和表现贵族宫廷生活的男女侍俑、舞蹈伎乐俑等。舞乐俑大多身材纤细,着贴身长袍,体态轻柔优美、端庄恬静;男女侍俑多为双手交于身前或直立或跽坐的形象,显得闲适安静又谨严恭敬。与西汉陶俑多表现贵族生活题材不同的是,四川地区东汉陶俑显得更加生活化与世俗化,题材多来源于现实社会中底层人民和日常生活的场景。构思简单,既富于生活气息又不流于自然主义,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东汉陶俑古拙、质朴、诙谐的风格基调。对比西汉淳朴写实的严谨风格来看,东汉陶俑所表现出的朴拙、质朴的风格特征明显更加悦人眼目。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质朴大气、拙朴奔放的时代精神被一一展现,深刻体现出了汉代艺术的基本特征。其所传达出的简单古朴拙的视觉效果和洗练质朴的抒情所带来的卓绝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审美精神中必不可缺的重要部分。
三、古拙的美学意义
在造型、制作手法以及题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四川地区东汉陶俑形成了一种古拙之美,普遍给人一种笨拙、质拙、朴拙的感觉。汉代艺术具有既自由大气又质朴厚重的时代风尚。汉代美学则在结合了先秦道家思想的自由朴素精神与屈骚美学奇幻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厚朴实的意境与注重生命力内核的美学意识。[13]
汉代思想家刘安在《淮南子·说山训》中说道:“求美则不得,不求美则美矣。”[14]即刻意追求美而不能得到,无意于美则美自得。因此,在反对过分追求美的思想影响下,汉时逐渐形成了一种自然、朴素、不加修饰的古拙的美学精神和价值取向。李泽厚等一些美学家都认为汉代无论是雕塑还是书法绘画整体上都呈现出一种“古”“拙”的形态特征。“古拙”在汉代美学发展中逐渐成了一种主流的审美倾向,被雕塑家和画家以及文人阶层所追捧,极大地影响了汉代艺术的风格特征和审美精神。不同于先秦儒家学派注重艺术的政治教化作用的是,一些汉代思想家更强调观赏自然本身的美,强调艺术要通向自然之道。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形神论”的美学观点,《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论及道家思想时,对“形”“神”之间的关系说道:“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15]即是说生命的根本便是“神”,“形”“神”不可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形”“神”二者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淮南子》把这种“神贵于形”“以神制形”的思想应用到音乐、绘画等创作实践中,进而形成了“君形者”的哲学思想。《说山训》:“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16]认为即使西施外在形象刻画得很漂亮或者孟贲的眼睛画得很大,但如果没有“君形者”,即对象的内在精神没有表现出来的话就不可能使人感觉愉悦或敬畏。这种内在的精神正是表现对象外在形体的主宰,没有“形”之“君”,形则没有主而将徒具其形。东汉陶俑工匠在制作陶俑时,正是抓住了表现对象形神兼备、趋向自然的审美艺术特征而使得陶俑体现出古朴、笨拙的古拙美感。
同时,通过陶俑的“古”与“拙”也可见彼时人们对“真”的关注与探讨。“疾虚妄,求实诚”作为《论衡》的写作旨纲。东汉哲学家、思想家王充在继承了先秦美学关于“善”的基础上强调“真美”,认为有“真”才能生出“美”,“善”则“有用”,从而对艺术品提出了“真”与“有用”的基本要求。在其看来,一切文章辞赋均应从“实”出发,以“实”为基础,将事实本身与真实性两相结合,方能见“真美”,没有“真美”则是虚妄,便是没有审美价值的东西。[17]
将汉代画像石与唐代画像石、汉代陶俑与唐俑等对比分析,便不难发现,虽然汉代艺术各方面都还处于草创未就的时期,在各方面均显得较为拙笨与粗糙,但正是汉代陶俑等艺术形态中所包含的那种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以及活泼朴素的生活气息使之显得愈加高明和优越。虽然唐代陶俑也有扭动、真实的动作姿态,但相较于东汉陶俑却总是缺乏那种朴素、狂放的气势;虽然东汉陶俑也不乏端坐静立的形象,但却依然充满了厚重、浑厚的动势与力量;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俑以及肌肉骇人、力量感十足的天龙山唐代雕像在粗糙、笨拙的东汉陶俑面前似乎也显得逊色。

图1 石刻拓片 荆轲刺秦王 东汉

图2 砖刻拓片 弋射收获画像砖 东汉
从整体上体现出汉代艺术生命的亦是诸如各类陶俑,表现弋射收获、荆轲刺秦(图1)等图景的画像砖(图2)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没有细节修饰与个性抒情的简单纯粹、粗轮廓的整体形象。在这些不事细节的动作与姿态中,汉代艺术生命精神中的“拙”得到体现,同样也是汉代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汉代艺术的形象“拙”,构图同样“拙”,汉代艺术在构图上还没有“计白当黑”“以虚代实”的概念,铺天盖地而来的画面形象相较于后世艺术的空灵与秀巧显得更加实在饱满与粗重笨拙。[18]至于汉代艺术中的“古”,首先之于陶俑,其制作手法可以追溯到陶塑刚刚产生的旧石器末与新石器早期这一时期的陶塑制作技艺;其次,对于汉代另一类重要的艺术形态——汉赋来说,则直接脱胎于流传甚广且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的“楚辞”;最后是汉代的画像砖,来源于神话故事中的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与历史故事中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人物形象的题材。“古”与“拙”二者的合而为一便后成了汉代艺术的主体特征,亦决定了东汉陶俑的主体特征与“古拙”的独特之处。同样地,古拙的美学形态亦体现在汉代的书法、绘画、雕刻等多样艺术形式中。从画像石到汉赋,陶俑到汉隶,汉代艺术更多地呈现出了汉代整体性的民族精神与那种来自楚文化中天真烂漫的浪漫主义以及对琳琅满目的世界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东汉是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成就丰富,有雄强朴茂中见活泼的《衡方碑》、厚重古朴中见变化的《阁颂》、稚拙凝练中见精巧的《张迁碑》等(图3),画像石、画像砖的技法大多粗拙凝练,偏重大的形体概括,风格质朴粗放,自然平实、简率,极富装饰趣味。如出土于四川大邑,表现射猎和农家收获场景的《弋射收获画像砖》,构图精炼简洁,人物形象生动,风格古朴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东汉时期内容丰富的题材以及饱满朴实,灵活自由,浑朴单纯的艺术风格至今仍以古朴、质拙的样式特征在中国雕塑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古拙”在中国美学和艺术风格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对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形成和艺术形态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即使是在面对西方艺术形态和美学精神冲击的当下,也依然有着独特的美学价值。

图3 碑刻拓片 张迁碑(局部)东汉
四、结语
东汉时期,四川地区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儒道楚文化的共同影响,促进了陶俑艺术的极大发展,题材广泛,陶俑的样式形态也随之变得多样,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艺术宝库。西汉刘向在谈到我们今天关于“美与审美”的本质问题时,反对过分追求奢华与审美娱乐,认为:“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19]如果国家或地方的主事者过分追求奢华享乐生活则必然会增加底层百姓的负担,从而造成人民的怨恨以及进一步的反抗,所以那种“放纵奢侈,荒淫无度”的行为实乃“伤国之道”[20]。这种观点虽然是站在政治的角度谈论礼乐之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也体现出了汉代思想家那种蔑视“雕文织采”的美学精神。四川地区东汉陶俑以笨拙、夸张的造型风格,质拙的制作手法,朴拙而丰富的市井生活题材共同决定了其古拙的审美特征,呈现出一种古旧朴拙的艺术形式与奔放、古拙的生命活力,构成了汉代艺术基本的审美精神。极大地启发了后世包括书法绘画、诗词歌赋等在内的众多艺术、文化形式,对研究汉代艺术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