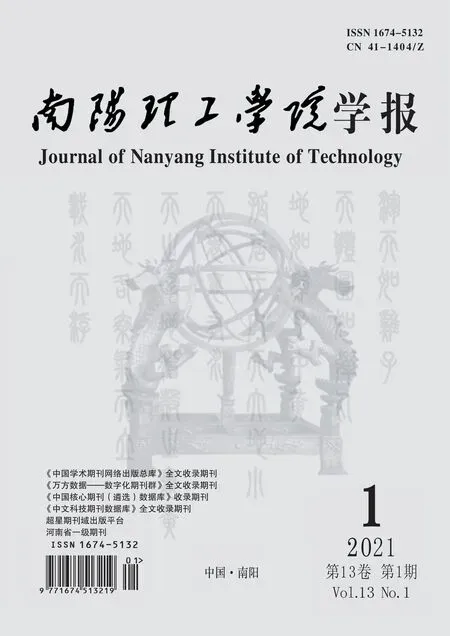曾巩主要是文章家,其次是文学家
——以曾巩作品中的“文章”和“文学”用词为证
曾祥芹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一 引言
2019年9月30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诞辰1000周年纪念日。对这位文章和文学的双创作家,其人文形象究竟做怎样的总判断,文论界绝大多数学者只认为“曾巩是文学家、散文家”,仅有少数学者认为“曾巩是文章家、古文家”。细读曾巩现存的文字作品《曾巩集》(全二册,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11月出版)和《隆平集》(全二册,王瑞来校证,中华书局2012年7月出版)两书之后,笔者欲批评“曾巩是文学家、散文家”的片面性,论证“曾巩主要是文章家、古文家”的正确性。本文专就曾巩文字作品中的“文章”和“文学”两个概念内涵做全息性澄清。这种结合具体语境进行词义确解的研究貌似笨拙,实为聪慧可靠。训诂学是文章学研究的基本功,下面按作品体裁统计其数,分辨曾巩所用“文章”和“文学”两词的广义或狭义。
二 曾巩作品中的“文章”词义考辨
(一)曾巩诗歌中的“文章”一词13见
1.“文章气节盖当世,尚在功德如豪氂。”(古诗 哭尹师鲁)
2.“雉鸡美文章,贽赠理亦宜。”(古诗 庭木)
3.“百家异旨趣,六经富文章。”(古诗 读书)
4.“炳以霸王业,信哉文章伯。”(古诗 刘裕故宅中有寿丘山)
5.“清风凛然在,素壁盈文章。”(古诗 题张伯常汉上茅堂)
6.“自有文章真杞梓,不须雕琢是璠璵。”(律诗 简翁都官)
7.“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律诗 祭致仕欧阳少师)
8.“荆州南走困尘埃,应喜文章意自开。”(律诗 寄王乐道)
9.“集贤自笑文章少,为郡谁言乐事多。”(律诗 戏书)
10.“节行久穷弥好古,文章垂老更惊人。”(律诗 赠张济)
11.“枣木已非真篆刻,色丝空喜好文章。”(律诗 寄孙莘老湖州墨妙亭)
12.“尺牍百封虚有意,文章十帙更传谁?”(律诗 刁景纯挽歌词)
13.“使者文章工不浅,尽将模写寄柴关。”(辑佚诗 依韵和酬提刑都官寒食阻风见寄)
上面13个“文章”概念,从诗句语境和全诗语境来看,呈现多义。除了“雉鸡美文章”中的“文章”作“错杂的色彩或花纹”解,形容雄鸡的羽毛美丽之外,其余12个“文章”皆指组成篇章的文字团体,或为广义,或为狭义。如“四海文章伯”颂扬“文坛盟主”欧阳修是“文章伯”,即“文章老大”。又如“六经富文章”一句中的“文章”涵盖《诗》《书》《易》《礼》《乐》《春秋》,属于包含文学(诗歌)的广义文章概念,但“六经”的主体是涵盖经、史、子的狭义文章。曾巩效法韩愈“以文为诗”,其诗歌中所用的“文章”大多指狭义文章。
(二)曾巩散文中的“文章”一词30见
1.“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更欲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穷居则欲推而托之于文章,将与《诗》《书》之作者并,而又未知孰先孰后也。”(《王子直文集序》)
2.“宋受命百有余年,天下文章,复侔于汉唐之盛。盖自周衰至今,千有余岁,斯文滨于磨灭,能自拔起以追于古者,此三世而已。”(《王平甫文集序》)
3.“乃知公于六艺、太史、百家之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詭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紬绎,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坏之理,显隐细钜之委曲,莫不究尽。”(《类要序》)
4.“是时文叔年未三十,喜从余问道理,学为文章,因与之游。”(《张文叔文集序》)
5.“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历教国子生,入馆阁为编校书籍校理检讨。其文章学问有过人者,宜在天子左右,与访问,任献纳。”(《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6.“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7.“其文章、智谋、材力之雄伟挺特,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8.“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然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虽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寄欧阳舍人书》)
9.“巩顿首李君足下,辱示书及所为文,意向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师其职也’,顾巩也,何以任此?足下无乃盈其礼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答李沿书》)
10.“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宜黄县县学记》)
11.“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学舍记》)
12.“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鑱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皆伏羲以来,下更秦汉至今,圣人贤者魁杰之材,殚岁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长,分辨万事之说,其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南轩记》)
13.“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及其奋然自立,能至于此者,盖天性然耳。”(《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14.“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筠州学记》)
15.“唐之文章尝盛矣。当时之士,若常衮、杨炎、元稹之属,号能为训辞。”(《辞中书舍人状》)
16.“伏以某官梁栋瓌材,琮璜茂器,发文章之素蕴,当仁圣之盛期。”(《应举启》)
17.“伏以都官学士英材杰出,玉璞混成,遘时运之光华,奋文章之温雅。”(《回人谢馆职启》)
18.“发明吾道,则有文章之深惇,推行当时,是为治行之尤异。”(《贺提刑状》)
19.“伏以提刑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温,文章为国之光华,治行乃时之表则。”(《越州贺提刑夏倚状》)
20.“后皆如其言。复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学者。人或劝复著书,复曰:‘古圣贤书已具,顾学者不能求,吾复何为,以徼名后世哉?’晚取其所为文章尽焚之。今其家有书十余篇,皆出于门人故旧之家。……复之文章,存者有《慎习赞》《困蒙养》等篇,归于退求诸己,不矜世取宠。余论次复事,颇采其意云。”(《徐复传》)
21.“又尝学文章,而知穷人之辞,自古皆然,是以于贾生少进焉。呜呼!使贾生卒其所施,为其功业,宜有可述者,又岂空言以道之哉?”(《南丰先生集外文卷上 读贾谊传》)
22.“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称其行。今之人盖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为也。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南丰先生集外文卷下 怀友一首寄介卿》)
以上出自曾巩“序、书、记、状、启、传”等散文中的30个“文章”概念,联系具体语境定义,除了“骚人墨客之文章”“唐之文章”等包容诗歌之外,其余如“天下文章”“道德文章”“学问文章”“文章学问”等绝大多数是区别于文学的狭义的实用文章。
(三)曾巩骈文中的“文章”一词8见
1.“属尔以文章之选,其体予奖遇之恩。”(《林希著作佐郎制》)
2.“非能见于文章,何以究宣朕志?非能通于世用,何以弥纶庶务?……其文足以代王言,其智足以谋治体。”(《中书舍人制》)
3.“维能守其所闻,可以辅予不逮;维能明于体要,可以见于文章。”(《知制诰制二》)
4.“麟台著作之任,郎以词学为之,必惟其人。尔以材选,惟能明于理要,乃可见于文章。”(《著作郎制》)
5.“议先王之制作,尝究本原,论夫子之文章,颇探阃奥。”(《齐州谢到任表》)
6.“号令风采,卑秦汉而不言,纲纪文章,体唐虞而特起。”(《谢赐唐六典表》)
7.“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将传后世,儒者文章之用,正在此时。”(《英宗实录院谢赐御筵表》)
8.“伏念臣器非闳远,性不敏明。徒嗜好于文章,寖推移于岁月。滥名儒馆,接武朝绅。”(《代宋敏求知绛州谢到任表》)
与散文相对的骈文,按“四字六字相间成文”,亦称“四六体”。以上出自“制、表”两类骈文中的8个“文章”概念,个别包容文学(如“词学”),其余“文章”(如“文章之选”“夫子文章”“儒者文章”“纲纪文章”等)皆“通于世用”“明于体要”“明于理要”,几乎都是狭义的实用文章。它不但在表达形式上体现了曾巩文章骈散结合的特点,而且在内容和功能上反映了应用文的特点。
(四)曾巩诗歌以外的韵文(哀祭文、墓志铭)中的“文章”一词15见
1.“惟公学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发,醉深炳蔚。体备韩马,思兼庄屈。垂光简编,焯若星日。绝去刀尺,浑然天质。辞穷卷尽,含义未卒。读者心醒,开蒙愈疾。当代一人,顾无俦匹。”(《祭欧阳少师文》)
2.“子之文章,杰立人上。地辟天开,云蒸雨降。播产万物,玮丽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泻,末势犹壮。”(《代人祭李白文》)
3.“明允姓苏氏,讳洵,眉州眉山人也。……嘉祐初,始与其二子轼、辙复去蜀,游京师。今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明允所为文,有集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者一百卷,更定《谥法》二卷,藏于有司,又为《易传》未成。读其书者,则其人之所存可知也。……二子,轼为殿中丞直史馆,辙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丧归葬于蜀也,既请欧阳公为其铭,又请予为辞以哀之,曰:铭将纳之于圹中,而辞将刻之于冢上也。余辞不得已,乃为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气甚夷兮志则强。阅今古兮辨兴亡,惊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马兮驰无疆,决大河兮齧浮桑。灿星斗兮射精光,众伏玩兮雕肺肠。自京师兮洎幽荒,矧二子兮与翱翔。唱律吕兮和宫商,羽峨峨兮势方颺。孰云命兮变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阳。维自著兮暐煌煌,在后人兮庆弥长。”(《苏明允哀辞》)
4.“容季孝悌纯笃,尤能刻意学问,自少已能写文章,尤长于叙事,其所为文,出辄惊人。……初,子直之遗文,深甫属予序之。数年,又叙深甫之文。复数年耳,而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坚又属予铭其墓,而且将叙其文。……学足以求其内,辞足以达其外。”(《王容季墓誌铭》)
5.“君少孤,能自奋厉,力学问,工为文章。……始,大臣荐其文章,宜在馆阁。近臣又荐其修洁,官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为江西转运判官。命始下,而君盖已死矣,死时年三十有九。闻其丧者,识与不识皆哀之。”(《都官员外郎胥君墓誌铭》)
6.“君读书务知大义……为人疏达自信,持之以谦,轻财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维子若孙,同时三人。擅名文章,震动四方。”(《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誌铭》)
7.“士之能修其内,洁身累行者,非自好之笃,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为之见于文,使后之君子得览焉。君于文章,尤长于诗,有集三卷,藏于家。”(《库部员外郎知临江军范君墓誌铭》)
8.“于临川,出其文章,因与予言古今治乱是非之理,至于为心持身得失之际,于其义,余不能损益也。”(《张久中墓誌铭》)
9.“夫人讳琬,字东玉,姓周氏,父兄皆举明经,夫人独喜国史,好为文章,日夜不倦,如学士大夫,从其舅刑起学为诗。……有诗七百篇,其文静而正,柔而不屈,约于言而谨于礼者也。”(《夫人周氏墓誌铭》)
10.“故自上古以来,至今圣贤百氏、骚人材氏之作,训教警戒,辨议识述,下至浮夸诡异之文章,莫不皆熟,而于治乱兴亡、是非得失之际,莫不能议焉。其文章尤宏赡瓌丽可喜。”(《亡兄墓誌铭》)
11.“君聪明敏悟,少力学问,为文章,数就进士试,不合,乃叹曰:‘与其屈于人,孰若肆吾志哉?’”(《天长朱君墓誌铭》)
12 “君少孤,自感励好学,能文章,为人聪明敏达,喜事有大志,不肯少屈。”(《秘书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铭》)
韵文不限于诗歌,还有诗歌以外的辞赋、颂赞、箴铭、碑志、哀祭五种文体,均可划归到“文章”大类(散文、骈文、韵文)之中。以上15个“文章”集中出现在曾巩的3篇哀祭文和9篇墓志铭中,联系上下语境,皆属音韵和谐、情文并茂、神采飞扬的文章。
(五)曾巩史传中的“文章”一词14见
1.“《文苑英华》一千卷,雍熙三年学士宋白等奉诏,以前世文章纂成。”(卷一 《馆阁》)
2.“晏殊:七岁善为文。……其为文章赡丽,应用无穷。尤工风雅,才有余思。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有《临川集》《二州集》《二府集》,又取梁、陈至唐人文章为一集。”(卷五 《宰臣》)
3.“宋祁:有文集一百卷,《广乐记》六十五卷,《唐书》列传一百五十卷,修《唐书》十余年,虽外官,亦以藳自随。非特文章有见于世,其守边议兵,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章疏之达于上者,尤切世务。”(卷五 《宰臣》)
4.“刘熙古:少通经史,……好学,明阴阳象纬书。……有《历代纪要》五十卷行于世。……五代丧乱之间,仪、俨乃以文章学问,自见于一时。所谓豪杰之士也。”(卷六 《参知政事》)
5.“苏舜钦:景祐元年登进士第,因范仲淹荐,除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舜钦慷慨有大志,好学,工文章。……当时伟人如欧阳修辈,皆相友善。”(卷六 《参知政事》)
6.“宋绶:年方十五,召试中书。真宗奇其文,特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同校勘天下图经。……知河南府。……经史百家,莫不通贯。朝廷有大议论,皆所裁定。于前世文章,必深考其得失。”(卷七 《参知政事》)
7.“周起:……东封还,群臣多献文章以颂德,起独上书言:‘天下之势常患恬于安逸,而忽于竞慎,愿无以告成为恃。’帝嘉纳焉。”(卷十 《枢密》)
8.“钱惟演:……少富贵,能志于学,有文章,与杨亿、刘筠齐名。……所著有《典懿集》二十卷、《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集》《金坡遗事录》《飞白书序录》《逢辰录》《奉藩书事》。”(卷十二 《伪国》)
9.“徐铉:十岁能属文,与韩熙载齐名。……李穆常使江南,见铉及其弟锴文章,曰二陆不能及也。有文集二十卷,又有《质论》《稽神录》行于世。常受诏与句中正重定《说文》。”(卷十三 《侍从》)
10.“王禹偁:……及长,善属文。太平兴国八年登进士第,太宗闻其名,召试相府,擢词馆,献《端拱箴》。上深嘉纳,赵普尤器重之。……驾幸琼林苑,召至御榻前顾问,语宰相曰:‘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禹偁辞章敏赡,喜谈世事,臧否人物,以正道自持,故屡被摈斥。……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议十卷,后集、诗三卷。”(卷十三 《侍从》)
11.“杨亿:……入翰林学士。……特赠礼部尚书,赐谥曰‘文’。……同王钦若修《册府元龟》,诏书局众论取决于亿。修《太宗实录》八十卷,亿独成五十六卷。……经传子史,百家之学,罔不通贯。为文敏赡,起草细字,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竄。……晚年留意释典,临终有《空颂》一章。其文有《括苍》《武夷》《颖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鼇》《内外制刀笔集》共一百九十四卷。……文章有正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卷十三 《侍从》)
12.“吴遵路:幼有俊才,韩熙载、潘佑皆以文章著名江左。……编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迁秘阁校理。……有文集二十卷,《说文》及《秘阁闲谈》各五卷,《江淮异人录》各三卷。”(卷十四 《侍从》)
13.“石介:介笃学,气节劲正,尝谓,时无不可为,不在其位,而行其言,言见用,利天下,不必出诸己。言不用,获祸至死而不悔。故其文章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无所讳忌。”(卷十五 《儒学行义》)
曾巩《隆平集》20卷,原文12万字,是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的简史,属于道地的史传文章。以上14个“文章”概念,依据具体语境定义,只有少数(如《文苑英华》中的“前世文章”)可以泛解为广义文章,而绝大多数指狭义的实用文章。
三 曾巩作品中的“文学”词义考辨
通览曾巩450多首诗,不见一个“文学”词。通览曾巩的849篇文章,可以看到少量的“文学”一词,兹分体裁罗列统计如下。
(一)曾巩散文中的“文学”一词14见
1.“自周衰,先王之遗文尽丧。汉兴,文学犹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尽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几于汉,及其衰而遂泯泯矣。”(《王平甫文集序》)
2.“晏元献,翰林学士,公遂管国枢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余年,常以文学谋议为任,所为赋、颂、铭、碑、制、诏、策、命、书、奏、议、论之文传天下,尤长于诗,天下皆吟诵之。”(《类要序》)
3.“以文学吏事称于世。”(《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
4.“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以其汇进,非空文而已。”(《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5.“齐固为文学之国,然亦以朋比誇诈见于习俗。”(《齐州杂诗序》)
6.“而孔子之称其门人,曰德行、文学、政事、言语,亦各殊科,彼其材于天下之选,可谓盛矣。”(《齐州杂诗序》)
7.“尹公有行义文学,长于辨论,一时与之游者,皆世之闻人,而人人自以为不能及。”(《尹公亭记》)
8.“臣性姿固塞,人品眇微,独于辈流,素嗜文学。”(《亳州谢到任表》)
9.“至于寻类取称,本隐以之显,使莫不究悉,则今文学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移沧州过阙上殿剳子》)
10.“一岁皆课试,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今州郡京师有学,同于三代,而教养选举非先王之法者,岂不以其遗素励之实行,课无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欤!诚令州县有好文学、厉名节、孝悌谨顺、出入无悖者所闻,令左升诸州学,州谨察其可者上太学。”(《请令州县特举士剳子》)
11.“皆择当世聪明隽乂、工于言语文学之臣,使之敷扬演畅,被于简册。”(《辞中书舍人状》)
12.“窃以高丽于蛮夷中为通于文学,颇有知识,可以德怀,难以力服也。”(《明州拟词高丽送遗状》)
以上14个“文学”,词义多变。第一个汉代的“文学”(如“汉兴,文学犹为近古”中的“文学”)专指学术,相当于实用“文章”;而汉代的“文章”专指文采缤纷的辞赋,相当于“文学”。其余13个“文学”(如“素嗜文学”“文学之国”“文学之臣”“文学之士”“文学掌故”“文学吏事”“文学政事”等)可理解为“文之学”,属于包容诗文的“杂文学”,而不是“纯文学”概念。
(二)曾巩骈文中的“文学”一词4见
1.“某文学行义,有闻于时。”(《吏部侍郎制》)
2.“帝王之治,必有国籍之藏,又择当世聪明拔出之士,聚于其间,使得渐磨文学之益,奬成其材,以待国家之用。”(《秘书监制》)
3.“博士以文学为官,往者列于成均,其秩未正。”(《太学博士制》)
4.“尔以经行文学,选自朕躬。”(《新及第授官制》)
以上四个“文学”词义,结合语境,同样是包容文章的“大文学”概念。
(三)曾巩诗歌以外的韵文(箴、铭、赞、颂、哀祭文)中的“文学”一词8见
1.“大父讳同文,唐天佑元年生,历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学义行为学者师。”(《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铭》)
2.“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义文学退而家居,学者所崇。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学器识名闻当世。”(《王容季墓誌铭》)
3.“维吴氏以文学直道继有显人,其家子晚出并茂,亦多以材能见于世。”(《光禄寺丞通判太平州吴君墓誌铭》)
4.“黟县之孙氏有起进士、为尚书工部郎中、广南西路转运使以卒者,讳抗,以文学见于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进士,为永州推官以卒,卒时年二十有八者,讳适,亦以文学见称,葬在其父之左。将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铭于南丰曾巩。”(《永州军事推官孙君墓誌铭》)
5.“其子既就学,夫人常夜治丝枱,居其旁以勉之。至其后,其子遂以文学名天下。”(《天长县君黄氏墓誌铭》)
6.“兄洞名能文,见国史。……曰括,扬州司理参军,馆阁校勘,有文学。”(《寿昌县太君许氏墓誌铭》)
以上8个“文学”的词义,结合语境,也不是“纯文学”,而是“文之学”,即涵盖文章和文学的双重含义,属于“杂文学”概念。
(四)曾巩史传中的“文学”一词7见
1.“寇准:器识文学,时鲜其比。”(卷四 《宰臣》)
2.“刘熙古:少通经史,……好学,明阴阳象纬书。……有《历代纪要》五十卷行于世。……禹钧五子:仪、俨、僖、偁、侃,皆有文学。”(卷六 《参知政事》)
3.“李穆:累擢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文学操履,为上所知。”(卷六 《参知政事》)
4.“钱若水:十岁能属文……若水风流儒雅,有文学,善议论。……有文集二十卷。修《太宗实录》。”(卷九 《枢密》)
5.“陈从易:擢知制诰、谏议大夫。……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书制稿》五卷、《西清奏议》二卷。尝与杨大雅同在西掖,俱以文学知名,时谓之‘杨、陈’”。(卷十四 《侍从》)
6.“尹洙:与兄尹源亦以文学知名……洙博学有识度,遇事无难易,勇于敢为。……有文集二十七卷。……洙以传文吏无军责而死行阵被诬,作《悯忠》《辩诬》二篇。”(卷十五 《儒学行义》)
7.“王回:有集二十卷。弟向亦以文学知名,善序事。……回孝友质直,博学知要,与临川王安石友善。安石谓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轲所为,而不为小廉曲谨以求名于世。”(卷十五 《儒学行义》)
以上7个“文学”词义,不论单词(“文学”)或词组(如“文学操履”“文学知名”等),依然不是“纯文学”概念。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与西方的“纯文学”概念有所不同,是包含诗文的“大文学”或“杂文学”概念。
四 结论
人文形象的科学判断孰重孰轻,要以文本为依据。总体看来,《曾巩集》[1]和《隆平集》[2]两书中“文章”一词共出现108次(《曾巩集》94见,《隆平集》14见),除别人评曾巩所用“文章”一词28次外,单是曾巩自己就用了“文章”80次。两书中“文学”一词出现33次(《曾巩集》26见,《隆平集》7见)。而“散文”一词,两书中一次都不见,显然“散文家”是文学专家给曾巩美容的。相比之下,“文章”在曾巩文论中的分量和地位比“文学”重得多、高得多。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对曾巩这位文章和文学的双创作家的人文形象,总判断为文学家、散文家是片面的,外塑的;而认定曾巩主要是文章家,其次是文学家,才是正确的,内塑的[3]。文学家、散文家、诗人,只是曾巩形象的几个侧面或“第二存在”,而文章家、古文家才是曾巩的正面形象或“原始面貌”。什么“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校勘学家、校雠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皆以“文章家”为本来面貌、为底色,才会一一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