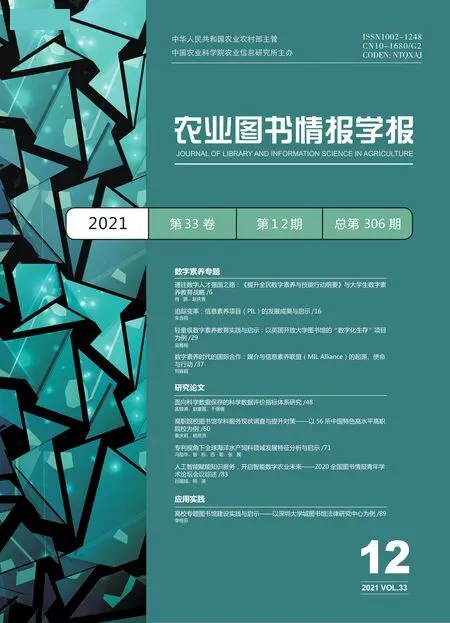追踪变革:信息素养项目(PIL)的发展成果与启示
朱含雨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民众的智识要求已经逐渐从传统的“读”与“写”提高到对信息技术的理解、运用和掌握,近年来又进一步聚焦到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相关领域[1]。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信息素养(以及作为其纵深发展的数字素养、乃至人工智能素养)开展追踪性质的长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
本文聚焦的信息素养项目(Project Information Literacy,简称“PIL”)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信息学院领导展开,该项目从2008 年延续至今,其研究成果已在哈佛大学等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得到应用和推广,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作者立足于PIL 项目的已有研究,按照研究主题特征对项目的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旨在为国内的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相关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
2 信息素养项目及其研究综述
PIL 项目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项目,致力于对数字时代的大学生及其研究习惯和信息实践开展持续的、大规模的研究。该项目研究学生如何发现、评估、选择和创造主要用于课程学习和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信息。在过去的10 余年中,该项目共收集了来自美国的93 所大学和34 所高中的近21 000 名学生的数据。自2009 年以来,PIL 项目组已经制作了12 份开放获取报告,调查了大学生如何利用研究技能、能力和策略来完成课程作业、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信息问题[3]。
2013 年,PIL 项目被美国《图书馆杂志》评为信息和图书馆利用的四大研究之一[4]。多年来,该研究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截止到2021 年4 月28 日,PIL 项目发表相关文献53 篇,被引1 740 次。其中,该项目发表的期刊文章和研究报告是最主要的被引文献,相关论文被引次数占总被引次数的52.36%,平均被引次数达到82 次;研究报告占比47.18%,平均被引次数达到68 次。尽管研究报告比之论文在被引数方面要逊色一些,但相关论文其实是研究报告的延伸,研究报告系统地构筑了PIL 项目的主体内容。
当前学界关于PIL 项目的介绍和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如BELL[5]早在2011 年就介绍了PIL 项目的运转方式,并阐释其相关的研究结果。几乎同一时间,就有国内学者[6]关注到PIL 项目的研究成果,并从情境与信息源、信息评估与教学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评价;而较新的研讨则是在2018 年徐文静等[7]的论文,该文作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对该项目的研究报告进行分析,总结了PIL 项目的研究特点和成功经验。尽管存在以上的相关研究,但总体来讲,现有的工作尚未能充分反映该项目最新的成果,对PIL 项目还有待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
3 信息素养项目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研究主题
经过10 余年的发展,PIL 项目追踪过多个不同的研究主题,在信息素养领域积淀了丰富的成果。基于相关主题,笔者将该项目划分为4 个历史阶段,即:学术信息行为研究阶段、信息过渡研究阶段、媒介素养研究阶段、“激发”系列研究阶段。
3.1 学术信息行为研究阶段
学术信息行为研究阶段从2006 年持续至2011 年。作为PIL 项目的起步和发端,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学生的信息搜索选择、使用和评价等过程,并发布了5 篇研究报告,分别是《查找背景:大学生谈数字时代如何开展研究》(Finding Context:What Today's College Student Say About Conducting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Age)(下文简称《查找背景》)、《经验:数字时代大学生如何搜索信息》(Lessons Learned:How College Students Seek 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下文简称《经验》)、《讲义调查:布置作业的讲义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Assigning Inquiry:How Handouts for Research Assignments Guide Today's College Students)、《真相:数字时代大学生如何评估和使用信息》(Truth Be Told:How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e and Use 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下文简称《真相》)、《平衡行为:大学生关键时刻如何在图书馆管理技术》(下文简称《平衡行为》)(Balancing Act:How College Students Manage Technology While in the Library During Crunch Time)。在这一阶段,PIL 项目收集了有关大学生开展课程学习和研究实践的定量数据,以了解他们在进行课程学习和开展学术研究时使用的信息的来源、评估信息的方法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为向更多的学生传授信息素养技能、标准和能力提供实践依据。这些研究重点关注大学生如何“找到”信息,探讨他们在课程学习、学术研究中对信息源的偏好,从大学生的研究经历、教师布置作业的讲义等多方面切入开展实证研究,并期望通过收集到的数据,促进信息素养的相关教学。
3.2 信息过渡研究阶段
信息过渡研究阶段从2012 年延续至2016 年。PIL项目从2012 年开始推出了“过渡阶段研究”(The Passages Studies,过渡,即大学生从一个信息环境进入另一个新的信息环境)系列研究报告。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以下3 篇研究报告,分别是《学习曲线: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后如何解决信息问题》(Learning Curve:How College Graduates Solve Information Problems Once They Join the Workplace)(下文简称《学习 曲线》)、《学习诀窍:新生进入大学后如何进行课程研 究》(Learning the Ropes:How Freshmen Conduct Course Research Once They Enter College)(下文简称《学习诀窍》)、《保持智慧: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大学后如何继续学习》(Staying Smart:How Today's Graduates Continue to Learn Once They Complete College)(下文简称《保持智慧》)。这些研究以“大学新生步入大学这一新的研究环境”“大学毕业生走向职场这一新的工作环境”为切入点,将信息素养与大学生的终身学习联系在一起,旨在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大学生在进入新的环境时的信息需求及策略的变化,并基于调查结果,向教师、图书馆员等相关群体提出建议,为大学生适应新的环境提供更实际的帮助。在这一阶段,各项研究综合运用网络调查与访谈等方法,基于大学生的亲身经历进行数据的收集,在重视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持续变化的同时,将研究视角延伸至学术之外的职场生活,丰富了读者对信息素养的理解。
3.3 媒介素养研究阶段
从2017 年开始,PIL 项目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和新闻工作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年轻新闻消费者的偏好、行为和动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第10 至第12 份研究报告中,分别是:《学生如何参与新闻工作:对教育工作者、记者和图书馆员的五点启示》(How Students Engage with News:Five Takeaways for Educators,Journalists and Librarians)(下文简称《学生如何参与新闻工作》)、《算法时代的信息素养:学生对新闻和信息的体验,以及改变的需要》(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Age of Algorithms:Student Experiences with News and Information,and the Need for Change)、《新冠病毒:美国新闻报道的前100 天:图书馆员、教育工作者、学生和记者关于媒体生态系统的 课 程》(Covid-19:The First 100 Days of U.S.News Coverage:Lessons About the Media Ecosystem for Librarians,Educators,Students,and Journalists)。大学生作为新闻消费者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其今天的新闻习惯将影响新闻生产的未来(如他们的喜好可能影响未来新闻内容的走向等)[8]。因而,研究大学生在数字时代如何收集信息和接触新闻、当前的新闻环境如何影响大学生获取、评估和创造知识的方式等,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在这一阶段,大学生是否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是否能够批判性地接受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成为PIL 项目的研究重点。
3.4 “激发”系列研究阶段
在对数字时代大学生的信息实践进行了长达10 余年的研究的基础上,PIL 项目于2021 年推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系列——“激发”系列(Provocation Series),这一系列的文章旨在表达与信息素养相关的较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与想法,同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新的思维方式,以激发读者的思考,鼓励读者参与对相关问题的分享和讨论,最终达到改进教学的目的[9]。在这一阶段,该项目主要发表了以下4 篇文章:《图书馆里的蜥蜴人》(Lizard People in the Library)、《缺乏信任的时代的阅读》(Reading in the Age of Distrust)、《iSchool 的平衡》(The iSchool Equation)、《告诉我甜蜜的谎言:种族主义是一种持续的恶意信息》(Tell Me Sweet Little Lies:Racism as a Form of Persistent Malinformation)。每一篇文章都从学术和时事中汲取了灵感,并提出了对现实问题的新见解,如:随着信息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哪些值得研究的方向被忽略了?后续研究应该在信息素养和高等教育方面探索哪些新的切入点[9]?“激发”系列研究阶段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①研究主题具有新颖性和趣味性,如《图书馆里的蜥蜴人》这一研究,从古怪阴谋论者倡导的“自己研究”(Research It Yourself)切入,引发教育工作者反思他们在信息素养工作上的不足之处;②写作风格上具有高度的可读性,表现出较强的新闻性,即及时且精炼;③重视对较为紧迫的信息素养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呼吁新的思考角度和写作方式。
4 研究成果与核心发现
自创始以来,PIL 项目已经进行了10 余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以大学生面临的信息情境为切入点,探究出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信息行为具有差异性;②关注大学生所处的人生阶段的变化,了解到他们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信息难题与挑战;③从教师、图书馆员等相关群体出发,为他们如何促进大学生的学习研究等提出了建议。在这一部分,笔者对PIL 项目的研究成果与核心发现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4.1 系统梳理了不同情境下大学生的信息行为
PIL 项目一直关注大学生面临的不同信息情境和信息任务,特别是大学生在特定时刻为完成学习、研究等任务所采取的独特的方法和策略。该项目从学术研究情境、关键时刻情境、新闻参与情境等不同情境切入,并对大学生的相关信息行为特征作了分析与总结,其主要的研究发现可归纳如下。
4.1.1 学术研究情境
学术研究,即大学生基于研究任务,开展研究(包括课程相关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的过程。PIL 项目在学术信息行为阶段的研究聚焦于学术研究情境下大学生的信息行为,对其信息寻求、使用、评估等行为的特征进行了总结:①大学生在开展研究时需要查找4种“背景”(Context)知识[10]。《查找背景》发现,这4种“背景”分别为:大框架背景(Big Picture Context),即对研究主题的构想;语言背景(Language Context),即了解与研究主题有关的语言、术语和著述;情境背景(Situational Context),即了解研究的具体情况;信息收集背景(Information-Gathering Context),即查找、评估与研究相关的资源[10]。②几乎所有大学生在研究过程中都采取同一种信息搜索策略,这种策略依赖于一小部分常用的经过验证的真实信息源[11]。《经验》发现,在开展课程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受访的10 名大学生中有9 名求助于图书馆的学术数据库等资源,8 人则表示很少使用需要与图书馆员互动的服务[11]。此外,大学生在进行信息搜索时表现出对少数真实权威的信息源的依赖,而害怕接触不熟悉的可信度未知的信息源[11]。③大学生的信息评估标准和形式存在相似性[13]。《真相》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采用相似的标准评估从网络和学校图书馆中获取的信息资源,不仅包括及时性、权威性等标准,还包括了网站设计、网站知名度等标准[7]。样本中近2/3 的受访大学生(61%)在评估个人使用的信息时会求助于家人朋友,近一半的大学生(49%)则会请求导师协助评估课程研究资源的质量[12]。这说明大学生的信息评估通常是一个协作过程,且对于不同种类的信息,他们的协作方式也不同。
4.1.2 关键时刻情境
关键时刻(Crunch Time)指学期末的最后几周,这一情境下大学生通常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平衡行为》这一研究探索了大学生关键时刻在图书馆相关场景中管理和使用技术的方法和策略,总结出如下特征:①大多数大学生可被归类为“轻度”技术用户(“Light”Technology Users)[13],即大多数受访大学生(85%)只使用一到两种信息技术设备开展一两项学习和交流活动,主要用于支持课程作业,其次是保持社交联系[7,13]。②在图书馆技术和服务使用方法的选择方面,报告指出,大学生们学期末压力最大时倾向于采取“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方法来管理和控制可用的IT 设备和信息系统,即倾向于操作和运用已有的设备和知识[7]。所有受访的大学生都在其主要使用的设备上创建了高度个性化的信息空间(即个人用于学习、研究、交流和社交的网站和应用程序)[13]。总而言之,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在学期末面临巨大压力时,会专注于课程作业,更加追求学习与工作的效率。但是仍然不能忽略他们在图书馆中的社交行为,他们依旧会通过相关设备和软件与人们保持社交联系。
4.1.3 新闻参与情境
新闻参与,指大学生接触新闻信息并参与到新闻工作中的过程。PIL 项目的研究《学生如何参与新闻工作》对5 844 名美国大学生进行了大规模在线调查,并对调查样本中的37 人进行了后续电话访谈,调查并梳理了美国大学生对新闻工作的认识、参与新闻工作的方式及获取、消费与参与新闻的策略。该研究的具体发现如下:①样本中大多数大学生(82%)认为新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许多大学生对当今的新闻质量感到严重不满,近一半(45%)的大学生对辨别“真新闻”(Real News)和“假新闻”(Fake News)缺乏信心[8]。②大学生在参与新闻工作时呈现出“多模式”(Multi-Modal)和“多社交”(Multi-Social)的特点。多模式,即获取新闻的渠道非常多样和广泛;多社交,即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接触和分享新闻信息[8]。③许多被调查大学生(68%)的新闻获取、消费和参与策略是复杂的,他们需要对新闻内容进行选择,关注能满足其当前迫切需求的新闻话题(如天气和交通报告、有关国家政治的新闻)。58%的人过去一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向朋友传递了他们认为重要的新闻信息[8]。总的来说,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新闻环境不断受到来自媒体、互联网平台、应用程序中的算法推荐引擎和各种未知来源的数字推送的影响[8]。面对海量零碎的新闻,大学生往往会自己判断新闻的重要性并构建新闻语境,他们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批判性思维来收集、评估和解读新发布的新闻信息。
4.2 全面总结了大学生身份转变中的信息挑战
身份转变意指身份发生变化,如大学新生初入大学,大学毕业生初入职场,他们从一个复杂的信息环境走向另一个复杂的信息环境。PIL 项目对当今大学生在经历人生关键转变时面临的信息挑战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2.1 大学新生面临完成研究任务的难题
《学习诀窍》这一研究对美国6 所大学的35 名一年级新生进行了访谈,发现新生们在完成研究任务方面面临着困难。这些困难具体表现在4 个方面:①难以制定有效且高效的在线搜索策略[14]。近3/4 的受访新生(74%)表示,在进行学术信息搜索时,他们在选择关键词和制定高效的搜索查询策略时遇到了困难,超过一半(57%)的受访者因为在线搜索返回的大量无关结果而感到困扰[14]。②难以识别、选择和定位资源[14]。51%的新生表示出对大学图书馆资源多样性的不适应,认为很难跟踪他们从网络和纸质文献上找到的各种信息资源[14]。③难以阅读、理解和总结材料[14]。大约1/3(34%)新生表示,阅读不同格式的信息和理解所获取的信息内容等具有难度[14]。这也说明搜索技能,并不是新生完成研究任务所需的唯一技能,它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学术资源,但却难以帮助他们理解资源的内容[14]。④难以了解教师对研究任务的期望[14]。大学的研究没有评分标准,许多研究任务都需要新生自己确定主题并查找相关的信息,但约1/3 的新生表示,他们不确定自己找到的信息是否符合教师的期望,他们很依赖教师的指导[14]。综上所述,大多数新生都面临着挑战,试图将自己在高中阶段积累的有限的研究经验复制到大学生活,但却难以满足大学研究任务所提出的更高要求。
4.2.2 毕业生面临在工作场所研究的挑战
《学习曲线》这一研究对来自4 所美国高校的33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访谈,并从以下3 方面总结了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场所进行研究所面临的信息挑战:①工作场所研究面临强烈的紧迫感[15]。毕业生在工作场所开展研究往往面临着来自最后期限(Deadline)的压力。在压力之下,他们只能调整在工作场所的研究策略,缩减时间并使用更快捷的方式查找信息[15]。②研究任务几乎没有结构或方向[15]。工作场所的研究是在高度不稳定的组织环境中解决信息问题的过程,可供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向也相对有限,受访的毕业生对此感到迷茫和无从下手[15]。③工作场所信息的寻求和使用具有社会性[15]。工作场所的研究具有比大学研究更强的社会性[15],在工作场所获取信息不仅需要毕业生们利用获取在线资源和纸质资源的能力,更需要他们学会利用人际关系,而许多毕业生对与陌生人交谈感到有障碍。总而言之,访谈结果显示,大学毕业生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快节奏的工作场所的研究需求,许多大学毕业生为解决信息问题而采取的快捷查找信息等策略,与雇主需要其在工作场所展现的研究能力不相匹配。
4.2.3 毕业生面临在终身学习方面的阻碍
《保持智慧》对来自美国10 所大学的1 651 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需求集中在个人生活方面,包括需要学习如何解决个人生活中的紧迫问题(75%)、希望掌握业余爱好的技能(70%)、需要学习如何管理金钱和个人财务(69%)[16]。同时,该研究也发现毕业生们表示其终身学习面临着如下阻碍:①缺乏时间。样本中88%的毕业生表示,他们继续学习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缺乏时间,许多毕业生的可用时间被通勤、工作绩效和家庭义务所占据[16]。②缺乏金钱。近3/4 的毕业生(73%)表示他们难以找到负担得起的资源,甚至还在还贷款、为获得相关工作所需的证书而苦苦挣扎[16]。③难以追踪最新的信息。70%的毕业生认为数字时代的信息量过于庞大,难以与时俱进地了解所需的新资源[16]。④无法保持学习动力。近2/3(62%)的受访毕业生对学习这一永无止境的过程感到沮丧,他们对此缺乏热情与动力[16]。总体而言,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在离开大学校园后的学习仍旧面临着许多阻碍,其终身学习的需求还未得到满足,工作任务的存在也使得他们难以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继续学习生活技能。
4.3 为不同群体提出了促进大学生学习研究的建议
PIL 项目的研究不仅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经历与体验,更重视解决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关注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图书馆员、记者等其他相关群体,最终从完善对大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指导、为大学生规划更科学的学习空间、规范大学生接触的新闻信息环境等3个方面,提出了实际可行的对策与建议。
4.3.1 完善对大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指导
《经验》针对大学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图书馆员等群体提出了4条建议,以加强对大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指导和支持。①根据教学目标检查大学生的研究工作。当前大学生深度学习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面临阻碍,影响了相关教学目标的完成。管理者和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对现有成果和预期结果之间的差距进行分析,对大学生的学习研究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查[11]。②给大学生布置与课程相关的研究任务。许多大学生死板地采取熟悉的策略来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教师和图书馆员应检查基于研究的作业是否可以开拓大学生的思维,鼓励他们从各种来源收集、分析和综合多种观点,帮助他们更积极地调用、实践和学习信息素养[11]。③弥合教师、图书馆员、大学生群体之间的鸿沟。很多大学生忽视了图书馆员对其学习研究的指导作用,研究建议图书馆员应通过发起圆桌会议等方式,促进与教师和大学生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寻找为大学生提供最新的信息获取渠道等的机会[11]。④系统地检查为大学生提供的服务。大学生们经常使用图书馆的资源而忽略了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如很少使用与图书馆员互动的服务。基于此,研究建议图书馆员,应了解大学生对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的使用方式及原因,而不只是关注使用频率,并不断更新和改进服务[11]。
4.3.2 为大学生规划更科学的学习空间
《学术图书馆学习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建筑师、图书馆员和图书馆顾问的专家视角》(Planning and Designing Academic Library Learning Spaces:Expert Perspectives of Architects,Librarians,and Library Consultants)这一研究,从学习空间的规划存在的不足切入,针对其缺少对大学生群体的意见的系统收集、对学习空间成效的评估仍不完善、图书馆员缺乏对学习空间的相关决策的参与等问题,为建筑师和图书馆员等群体提出了以下建议:①需要更多的预设计(Pre-design)用户研究。建筑师和图书馆员需要使用更正式的方法(如大规模调查或深度访谈),直接收集大学生和教师的意见,以了解其在新空间创建后使用图书馆的情况[17]。②需要更多的使用后研究。研究建议图书馆员等群体对新学习空间怎样影响大学生的学习需求等进行系统的衡量,将大学生的学习研究成果与图书馆学习空间的建设联系起来。③需要图书馆管理人员更多地在全校范围内参与决策。他们需要与到图书馆规划与设计的全过程中,与关键的决策者建立联系,并积极反映大学生的意见以支持他们的学习[17]。④追求图书馆学习空间设计的原创性。图书馆学习空间的设计应是不断发展的,以应对大学教育和课程计划等发生的变化,其为大学生提供的技术和设备需要与时俱进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17]。这一研究建议图书馆员和建筑师通过为大学生在图书馆的协作讨论、个人学习、课程培训等活动合理分配空间,提供更完备的学习设备与技术,方便获取研究所需的纸质文献信息以及网络资源,创设更科学的学习研究环境。
4.3.3 规范大学生接触的新闻信息环境
《学生如何参与新闻工作》则立足于当前的新闻信息环境,致力于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并帮助其更有效地理解和利用新闻信息,为教师、记者、图书馆员、社交媒体平台工作者等群体提出了以下建议:①将教授行动认知(Knowledge in Action)技能纳入整个教育过程。这一建议强调将新闻与媒介素养的教育落实到课堂、工作场所、个人生活等不同场所的实践中去,指导大学生对各种类型的信息进行更有效的辨别和评估[8]。②将新闻讨论融入课堂。教师应鼓励学生在新闻实践和学术工作之间建立联系,同时将新闻置于学科中,将理论与时事联系起来,以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8]。③完善教授大学生评估新闻信息的方式。新闻和传播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解释职业新闻采集等方式,提供更多关于新闻的产生和传播的信息,为大学生的新闻信息评估提供特别的帮助[8]。④重视情境在新闻报道中的价值。这一建议鼓励新闻生产者提供尽可能完整的故事与情节,让新闻受众更清楚地了解新闻的情境背景;同时鼓励教师通过布置研究任务的方式,引导大学生批判性地认识新闻信息所处的情境及所表达的感情[8]。⑤记者需要采用新的叙事形式和受众参与策略。记者等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在新闻报道中融入不确定性的表达,突出不确定的内容,帮助大学生新闻消费者和媒体之间建立更真实的关系,塑造更真实的新闻环境[8]。⑥社交媒体公司赋予年轻的新闻消费者更多权力。具体而言,社交媒体公司可以通过支持开发更多的课程和工具,以促进对新闻的分析思考和推理,从而帮助教师等群体减少对错误新闻信息的传播[8]。《学生如何参与新闻工作》为各群体在培养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规范大学生接触的新闻平台和内容等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以期为提升大学生接触到的新闻质量以及塑造更加规范的新闻环境贡献专业力量。
5 信息素养项目的意义
PIL 项目开展研究的模式与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与发现,对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素养教学、研究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该项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指导图书馆改进业务和工作、指导推进信息素养相关教学、指导创新信息素养相关研究3 个方面。
5.1 指导图书馆改进业务和工作
PIL 项目及其研究成果对图书馆的业务与工作的改善具有指导作用,其关于大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评估以及当前社会对大学生信息能力和技能需求的发现,为大学图书馆的创新服务提供了参考。例如,克莱蒙特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参考了《经验》等研究报告,并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大学生的知识往往依赖于他们在中小学阶段积累的图书馆使用经验和研究经验[5]。因此,他们在推进服务工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大学生们的研究水平和技能受限。馆员们召集了教师和管理人员对此进行讨论,主张对大学生进行研究指导和信息技能指导,积极以此推进图书馆服务的延伸,发掘大学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帮助大学生完成研究的价值[5]。哈佛大学及其图书馆则加入了PIL 项目的部分研究,共同参与收集和评估大学生研究过程中的信息行为数据。这使得哈佛大学图书馆员意识到需要评估图书馆所做工作的价值[18]。他们开始更加关注数据本身,并积极与教师等其他群体进行交流,分享各自从PIL 项目研究报告中了解到的情况,并用于图书馆与教师合作开展研究活动、设计研究策略等[18]。
5.2 指导推进信息素养相关教学
PIL 项目对学生进行课程作业和研究任务的过程进行了持续研究,其关于学生的研究策略、需求和研究困难等研究发现,为高校改进信息素养教学提供了建议和参考。天普大学基于PIL 项目的研究,发现了学生在研究工作中遭遇的困难,列出了学术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还基于此创建了一个研究评估准则[19]。此外,天普大学针对教师如何帮助学生完成研究任务提出了建议,如鼓励学生咨询图书馆员,发挥图书馆员帮助学生规划研究策略、搜索和定位信息以及减少研究中遇到的阻碍等作用,向学生提供咨询服务或学科专家的联系信息,帮助学生获得更多专业的研究信息和帮助[20]。菲尼克斯大学Maricopa 社区学院校区则基于PIL 项目关于研究讲义的调查发现(即大多数研究讲义没有充分发挥出指导学生发现和使用信息的作用)[21],为所有学科的教师创建了关于研究讲义的研讨会,用以讨论和研究如何为与课程相关的研究作业制作更有效的讲义。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教学讲义获得了更多的重视,教师更加了解设计良好的教学讲义对研究作业的重要性,并将提供具体的指引来改进研究讲义,以帮助指导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和利用资源[20]。
5.3 指导创新信息素养相关研究
PIL 项目中关于当前大学生的信息搜索行为和习惯的研究发现和结论,对于创新信息素养相关理论研究教育和推进相关研究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2009 年,《经验》研究发现:在数字时代,很多大学生的信息搜索策略,都是依赖于一小部分容易获取的、权威真实的信息源,他们几乎不愿意改变资源的使用频率和顺序[11]。而这样的信息搜索策略,使得大学生在进行信息搜索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基于这一研究,研究人员在探索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草案的实践中,构建了一个“阈值”概念,假定学生必须通过克服一些困难,才得以加深对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的理解[22]。同时,研究人员也创建了一个鼓励学生与教师、教师与图书馆员之间互动交流的框架,用以指导课程规划和教学研究[22]。另一方面,基于PIL 项目的研究数据和调查结果,以及它在全美范围内关于大学生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等多维度的调研,各方专家们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IMILS(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Media Literacy Survey:Survey of the Research Habits and Practices of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国际媒介和信息素养调查——大学生研究习惯和行为调查)项目[23]。作为一项大型国际性调研项目,IMILS 项目借鉴了PIL项目统一规划及协调合作的经验,以大学生的媒介和信息素养为调研对象,探索他们在日常生活与课程研究等不同情境任务下的信息行为与信息能力。它效仿PIL 项目为教师、学者等相关群体提出了建议,以改善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教学方式,提升大学生的相关信息素养[23]。
6 信息素养项目的启示与思考
PIL 项目及其研究成果影响了高校、图书馆等机构的信息素养理论和实践,其研究内容与方法、合作对象与模式等都值得相关研究与实践的借鉴[7]。目前中国的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相关等研究与实践仍存在需要学习与改进之处,可以批判性吸收PIL 项目的先进经验,以推进中国相关研究与实践的改进与创新,并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6.1 紧跟时代发展,重视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持续变化
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当前教育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信息素养调研与实践需要不断更新,结合数字时代大学生的信息需求、学习方式,紧跟时代发展,探索与时俱进的信息素养调研与实践的框架和体系[24]。首先,应重视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持续变化,帮助其适应社会需求。具体而言,应将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与终身发展联系在一起,了解他们在各阶段各场所的信息素养需求,探索其在不同研究任务下对信息的搜索、选择、使用、评价行为。同时,深入挖掘大学生在学校之外被期望拥有的各种研究、工作、生活策略,以帮助他们更有针对性地提升信息素养水平,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应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立足他们的实践体会。在信息素养实践与研究中,可以设计并开展以问题为导向、基于项目的学习、嵌入式教学等多样化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25],并建立大学生信息素养数据集。基于大学生在不同的教学模式下的经历与体会,对调研结果进行跟踪,关注他们的信息需求与策略的变化,致力于帮助学生明确认知信息需求并制定合适的信息策略,从而解决其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后,应关注新的环境和事件,了解大学生收集、理解不同信息的能力。PIL 项目从新冠肺炎新闻数据集切入,调查了大学生在数字时代收集信息和接触新闻的方式。这也为中国信息素养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新闻时事切入,收集大学生对其的理解与认知,建立数据集以为培养批判性思维提供参考。
6.2 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大型研究项目的长效机制
作为一项跨地区的大型信息素养调研项目,PIL 项目得到了各大基金会、多所世界顶级大学、出版商和数据库的支持[3]。PIL 项目的顺利进行,取得的显著研究成果,都离不开广泛而深远的合作,这也启示中国的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调研实践,应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大型研究项目的长效机制。首先,应全面面向社会开放,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和动员不同类型的高校、相关政府部门、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共同参与到信息素养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以获取更广泛多样的研究数据。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信息素养项目(如PIL 项目)的经验,依托图书馆、相关学会等专业的力量,对项目的实践发现及成果进行监测与评估[26]。其次,协调整合社会资源,推进信息资源共享。积极开展跨机构合作并利用外部资源,如鼓励学生探索和利用公共文化机构的特色资源[26],或推动学生深入挖掘和开发互联网上独特的数据资源。最后,统一协调规划,推动项目共建机制的形成。开展跨地区的大型信息素养调研项目,需要面向大学生等群体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长期行动规划并严格执行,积极争取各大数据库和出版商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信息素养项目的共建机制,形成信息素养建设的组织实施、资源保障等体系,为探索提升大学生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的实践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撑。总而言之,大型研究项目的开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实施和推进信息素养项目的过程中应有规划地逐步深入,为项目的实施提供长远发展的动力,建立长效发展机制。
6.3 理论联系实践,重视信息素养研究的实际作用
PIL 项目的研究模式为后续开展的一些项目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其研究发现被应用于高校、图书馆等机构,以改进信息素养教育和研究模式、改进相关业务与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25]。信息素养调研与研究应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视信息素养研究的实际作用。首先,积极拓展研究模式,重视相关技能的普及。不只局限于信息素养本身,还可以拓展至数字素养、职场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等维度,不断在新的主题和领域进行尝试。在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和研究时,应该注重对信息素养通识技能的普及,将信息素养的提升细化并融入到具体的学科,可以跨学科地尝试如文本挖掘软件、数字可视化技术、知识图谱等数字工具与方法[27],帮助学生更高效地交流学习成果与解决学科难题。其次,拓展研究对象,发挥不同群体的不同作用。信息素养调研和研究的对象不只局限于大学生群体,也需要发现和总结教师等相关群体在课堂教学、技能培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针对性建议,充分发挥学生、图书馆员、教师之间合作与交流的作用。应鼓励学生在教师和图书馆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利用各种数字化工具以获取所需的信息,营造数字化、网络化、协作化的信息环境,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大学生信息素养乃至数字素养。最后,不断完善研究实践,实现渐进式发展。信息素养调研实践需要关注不同情境和不同身份下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提炼相关特征并厘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及时根据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对后续的研究进行指导和改正,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关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例如,可以关注教育环境中,信息素养教学的整体框架应该是什么样的[28]?这样的框架应用到后续的大学生毕业步入职场是否仍有帮助?随着调研和研究过程的展开和修改,相关研究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7 结语:从信息素养到数字素养
不难发现,作为一项大型信息素养研究项目,PIL项目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不止于信息素养,不仅是研究大学生“识别信息需求的能力、查找、评价、利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29],也拓展至对大学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的研究,即“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30]。信息素养与数字素养都注重培养人们高效地获取、理解、评价、整合和表达信息的能力,在强调信息自由的同时也呼吁信息责任与安全意识[31],主张对各种信息的批判性分析与使用。而数字素养则更加聚焦于使用数字技术与设备的能力[32],强调对创新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培养。
PIL 项目也对数字环境下大学生在学习研究中展现出的数字素养与技能进行了探索。具体而言,PIL 项目更关注大学生对数字信息资源的定位、评价、选择和使用,它总结了在网络资源和新技术的兴起的背景下,大学生在研究过程中查找和使用相关资源的策略,如大学生在开展研究时需要查找4 种“背景”、大学生在搜索信息时依赖于一小部分常用的经过验证的真实信息源,并就如何将终身学习所需要的信息素养与数字素养技能更有效地传递给大学生提出了建议[10]。此外,PIL 项目还重视大学生使用数字设备和软件的能力,调研了大学生在关键时刻对图书馆的技术和设备的管理与使用情况,发现他们在学期末时使用上文所提及的“少即是多”的方法来管理图书馆的技术和设备,并通过在设备上创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空间等方式,更加有效地完成课程作业与研究任务[13]。PIL 项目还聚焦于数字和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媒体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大学生对新闻媒体信息的认识,了解到他们从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多种途径获取新闻媒体信息。基于当前的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素养的课程中存在的不足,该项目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教师应将新闻讨论融入课堂、重视情境在新闻报道中的价值等建议,以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帮助他们更有效地收集、评估和解读数字时代海量的新闻媒体信息[8]。
2021 年7 月23 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对“关于细化落实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任务的建议”的答复,从整合开发优质教育资源、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师队伍建设融合的新路径、全面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制定师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4个方面出发,为进一步提升师生的信息素养指引了方向[33]。2021 年11 月5 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强调要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30]。这一系列政策的发布,都说明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工作,高校、图书馆等机构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通过批判性地学习PIL 项目的研究模式与方法,或能为中国有力提升全民的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打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