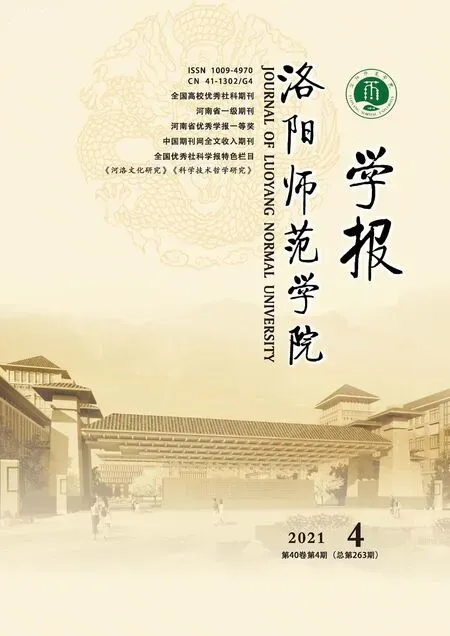生态中心主义与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之比较研究
黄越泓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生态中心主义(ecological centralism)又被称为“生态中心论”或“生态整体主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主流学说之一。现代生态学从整体的角度关注生态系统的发展,强调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依存的关系。环境伦理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居住在道德世界?人类是道德世界的唯一成员,还是说其他要素单位也是成员或者拥有成员地位? 如果说只有人类是道德公民的话,那么就要提出一个相关问题: 其他要素单位是否应该具有一定的道德可考量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利益虽然没有内在价值,但是否也应该予以考虑?[1]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应将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拓展至生态系统,把生态系统视为拥有道德地位的道德顾客。作为一种整体主义的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关怀包括动物、植物、无机物乃至整个生态共同体的生存状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他们将道家思想视为反思西方机械论的世界观、天人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有益参考。正如当代著名环境伦理学家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所言: “道家思想首先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态形而上学的概念资源。显然,在生态学的理念中潜藏着一种对西方世界观的彻底修正。环境哲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准确、概括和抽象地表述生态学所要求的基本概念重构。也许道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例……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道家为环境文献中的‘适当技术’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和理论原则。”[2]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道家始终关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之道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阐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尽管道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伦理的主张,但却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中国人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坚守的生态伦理理念。
生态中心主义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理论视角主要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自然价值论(theory of the value of nature)和大地伦理学(land ethic)三个方面。本文从生态中心主义的三个主要视角出发审视道家思想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探析其中可以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的思想理论资源。
一、道通为一与生态的自我实现
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在《浅层与深层——长期生态运动综述》[3]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一词。深层生态学旨在强调人类之外的生命形式具有独立价值,人类应确保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生态系统应确保最大的复杂性和最大化共生。深层生态学认为,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的理由,人类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此即“生态中心平等主义”(ecocentric egalitarianism)或“生物圈平等主义”(biosphere egalitarianlism)。此外,随着人们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此即“自我实现论”(self-realization)。[4]深层生态学家认为,世界上许多文化和宗教传统中的生态意识传统,保持了“自我实现”和“生物圈平等主义”的最高规范,超越了西方现代的“自我”意识。
作为东方智慧结晶的道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与现代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伦理理念不谋而合。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分析“道通为一”“物无贵贱”等思想,可以发现道家的许多主张与深层生态学的“生命物种平等”理念是相通的。
首先,道家思想与西方的深层生态学观念一样,反对仅从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唯一性角度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层生态学认为,所有的生命个体都具有内在的目的性,从地球生物圈的整体性来看,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类,各自承担着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调控者的功能,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自然界的价值,不仅仅是对人类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也包括对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和地球生物圈整体系统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自然界的生态价值是内在固有的,对人类的价值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应当服从地球有机整体的价值。自然界的多样性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因而地球上存在的物种都平等地拥有生存和繁荣的权利,在狭隘的人类目的的范围外,有使自己个体得以展现和自我实现的权利,这就是深层生态学“八条行动纲领”的第一条: “人类和地球上的非人类生命的福利和繁荣本身就具有价值(内在价值、天赋价值)。人类之外的生命形式的价值独立于它们对人的目的的有用性。”[5]
其次,在人与物的价值评价上,道家主张从道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反对人类中心论以人为宇宙主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道家主张从形而上的“道”的角度重新审视事物的关系和价值,“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6]254。贵己贱物,是人类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投射。但是从道的观点审视人与万物,人类只是在地球上存在的众多生物之一,在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不应该存在等级差别。人如果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把人以外的事物仅仅看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就违反了万物的自然之性,扰乱了生态系统的整体进程,破坏了天地万物的自然秩序。“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6]320道家认为人与万物都是由通天下的“气”所产生,气在动态转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创造新的存在,人与万物在本质上都是气循环往复过程中的存在,宇宙万物虽有形态的殊别,但是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由此可见,道家主张的万物平等与深层生态学的平等主义观念殊途同归。
再次,在人的生存境界的问题上,道家所追求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对于人类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意义,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从而正确对待自然环境,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会经历一个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进而到“生态的自我”(ecologic self)的过程,只有“生态的自我”,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7]170由此也可以看出,道家追求的“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精神境界与深层生态学中自我实现的价值理念相一致。
二、万物皆有道性与自然价值论
自然生态系统拥有客观的、多元的价值,维护和促进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是人类应尽的客观义务。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了一个以自然的内在价值为核心的新型环境伦理思想体系,成为自然价值论的奠基人。罗尔斯顿深刻反思了人类中心主义只关注大自然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内在价值的问题,他认为人对自然存在着客观义务,应将道德视域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中。罗尔斯顿主张大自然承载着多种价值,包括生命支撑的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使基因多样化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多样性和同一性的价值等多种价值。这些价值是并不以人类的偏好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人类所应承担的义务。罗尔斯顿认为价值属性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具有创造性,“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就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而言,都是有价值的”[8]。
道家从道的角度审视万物,万物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被称为“道性”。道性理论在早期道教思想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最初道教所关注的是道的内在属性或人得道的可能性; 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以及道教思想自身的发展,道性思想的内涵拓展至万物皆有道性。万物价值的来源不是能够为人所用的工具价值,而是具有周备万物、清虚自然的道性。
“道性”一词最早出自汉代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河上公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注释是: “人当法地安静和柔,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有功而不置也。天澹泊不动,施而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道清静不言,阴行精气,万物自成也。道性自然,无所法也。”[9]“道性自然,无所法也”意指道的本性是自然而然的,没有需要效法的外在对象。
南朝道士宋文明在《道德义渊》中指出,非止于人有道性,含识众生乃至虫兽皆有道性。“夫一切含识,皆有道性。何以明之,夫有识所以异于无识者,以其心识明暗,能有取舍,非如水石,虽有本性,而不能取舍也。既心有取,则生有变,若为善则致福,故从虫兽以为人; 以为恶则招罪,故从人而坠虫兽。人虫既其交换,则道性理然通有也。”[10]宋文明以心识的取舍和认知功能界定道性,认为水石没有道性,但是人和虫兽皆有道性。
入唐之后,孟安排在《道教义枢》中又进一步扩大了道性的范围: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本性。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性空,即是道性。”[11]除了以传统的“自然”解释“道性”,《道教义枢》还接受了佛教中观思想的影响,从不因不果、不色不心的角度对道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人类、动物、果木乃至石头皆禀清虚、自然的本性,故而必然被道性所摄。
罗尔斯顿提出自然价值论的时代背景是工业文明发展导致了现代严重的环境危机,受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支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使得人类只关注大自然的工具价值而忽略了其内在价值。自然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都承载着独特的价值。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实际也是在守护多元价值。道家所主张的道性论与当代自然价值论都试图改变人对万物的狭隘认知,尽管道性论并没有像自然价值论那样直接对自然界投以伦理关怀,但在今天看来,道家思想无疑对人类超越工具价值认识生态环境和自然万物具有借鉴意义。
三、三才相盗与大地伦理的整体主义
大地伦理学将直接的伦理关注(ethical considerability)由人类社会伦理共同体拓展至包括水、土壤、植物、动物在内的整个大地,即非人类的自然实体(nonhuman natural entities)。大地伦理学的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认为,西方的伦理观念最初起源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随后扩大为处理人与社会的观念,而他所提出的大地伦理学则极大地拓展了道德共同体的内涵: “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 土地。”[12]
作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大地伦理学着眼于生态共同体的稳定性、生态结构的复杂性和生物多样性,人类之于环境的义务就在于保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机制。大地伦理学强调整体主义,并不直接把道德地位直接赋予植物、动物、土壤和水这些存在物。共同体的健康或者善是确定其构成部分的相对价值的标准。[7]142从整体主义的角度出发,大地伦理学认为人类对于生命共同体本身的持续和发展承担义务。只要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获得了稳定和发展,则人对于自然资源的有序利用就是合理的。大地伦理学将共同体的边界拓展至非人类自然实体,并将它们作为伦理责任的受益者,但是并未将相互的或者共同的责任、义务或者伦理限制强加于这些实体上。[13]因为,让动植物或者山河大地承担道德上的责任是难以想象的。
道家虽然认为一切含识乃至草木皆有道性,各自都有内在价值,但是道家同时也认为人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故万物芸芸,命系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寿,失天意者亡。凡物与天地为常,人为其王,为人王长者,不可不审且详。”[14]道家认为万物“命系天,根在地”,万物与人一样都源自天地。人对于万物而言是“为其王”,是“用之者”,道家肯定了人有使用资源的权利,但同时也提醒人在使用自然资源之时需要谨慎,唯有如此,人的活动才能顺应天意,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天地,万物之盗; 万物,人之盗; 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15]821《阴符经》认为天地、万物与人构成一个循环动态的系统,“盗”意味着生态系统内部的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运行机制。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天地乃是指非生物环境,万物则是指除人以外的生物,天地、万物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生物和非生物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循环运转、流动往复的动态场景。如果把天地万物视为生态共同体,则人应该致力于维护生态共同体多样性和稳定性,从而实现“三盗既宜,三才既安”,由此可见,《阴符经》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大地伦理的整体主义有内在相通之处。
《阴符经》的“三才相盗”肯定了人对于资源的合理利用符合“自然之理”,人在参与自然资源利用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也即遵循自然规律而安排人类的活动。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阴符经》的生态观念肯定了人使用资源以谋求发展的基本需求。李筌在《黄帝阴符经疏》中指出:
万物盗天而长生,人盗万物以资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疏曰: 人与禽兽草木俱禀阴阳而生,人之最灵,位处中宫,心怀智度,能反照自性,穷达本始,明会阴阳五行之炁,则而用之……人于七炁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潜取以资养其身,故言盗,则田蚕五谷之类是也……万物盗天地以生成,国氏盗万物以资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万物人之盗也。[15]740
在肯定人拥有使用资源的正当权利的同时,《阴符经》主张人对资源的利用只有做到“知分合宜”,才符合自然之理。《阴符经》也肯定了人对于宇宙规律的认识能力: “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15]821人之性与天地之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对人能够合理利用资源持乐观态度,认为人类可以发现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规律,进而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范,从而使人的行为符合宇宙规律。
四、 道家生态伦理之于生态中心主义的独特性
面对近代以来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危机,生态中心主义将道德关注的视野从人类扩大至非人类实体,提醒人类对于其他物种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负有道义的责任,这无疑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基础上对西方工业文明反思的结果,是西方学者对工业发展导致生态危机后进行的探索和思考。与个体主义相比,生态中心主义强调生态的整体主义,把自然万物的共生共存作为衡量生态的最高目标,把大地共同体的价值作为生态系统的最高价值。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在理论层面存在契合相通之处,体现着东方特色的生态整体观。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主题是“天人合一”,在现实层面强调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在心性修养层面追求人之性与天之道的统一。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中,是古人对生存环境深入观察及生存经验总结的产物。现实世界存在着种种对立冲突的现象,道家通过对“道”的阐释揭示宇宙的运行机制和根本动力,认为人可以通过对“道”的领悟以及个人修养的提高实现与环境互依共存。“在道教的情景化的框架内,个人的修养和环境的修养是相互的。我们对环境的培养不是在培养他者, 而是在培养自己。”[16]
生态中心主义和道家生态思想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两者的关注视野和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相通之处,但也应注意到二者的区别,这种区别展现出了道家生态思想的独特价值。道家“天人合一”“道物不二”的整体性宇宙观更契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同时道家的生态理念是经过千百年历史沉淀的经验总结,对于指导今天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而言,无疑更具有文化亲切感和现实意义。
首先,道家“道法自然”“道性遍在”的生态整体观、平等观与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不谋而合。“一切含识乃至草木皆有道性”的思想从“道性遍在”的角度肯定了万物的内在价值,这可以认为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古典表达方式。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独立价值,意味着对动物、植物乃至山河大地的保护是从“道”的层面守护人类的多元价值。只有当大众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良知被唤起,环境保护的主张才能为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和遵守,才能促使更多的人发自内心地践行“顺应自然不妄为”“慈利万物不私为”的理念,并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着眼,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正确处理好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其次,道家思想在生态应用层面更具有切实的可行性。例如《道德经》所载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17]41,“治人事天莫若啬”[17]36等思想都可以从生态伦理层面进行深入解读。道家倡导俭省朴素、惜物爱物等理念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应该秉持“去甚、去奢、去泰”[17]17的原则,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处理好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再次,道家对于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更加契合现代社会的需要。道家、道教学者千百年来始终致力于科技的探索,“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至少有三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与道教相关……道教曾经是促进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宗教”[18]。科技的进步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能力提高的体现,道家对人认识客观规律、掌握技术并最终实现“以道统术”的能力持积极的态度。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甚至导致部分地区发生生态危机,但是生态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化解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也不可能脱离科学技术而寻求出路,这就要求当代的生态伦理思想必须对技术文明有深刻的理解。若“道”是循环的,我们用人类自身的行为贯彻它,则人类的技术可将此原则考虑在内。环保主义者为了实践目的而提倡“循环”作为其立场之象征,很符合道家之精神,将人类的微观世界调整到符合生态系统性的宏观宇宙中。[19]
如何立足于现代科学视野构建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生态伦理,如何将科技的发展与生态系统自身的规律进行融通,如何将科技的发展方向引向增进人类福祉的轨道,这些是当代人需要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道家思想无疑为我们解答这些时代命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