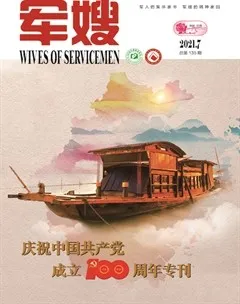铮铮乔有看沧桑
家国情怀融血脉接续奋斗传薪火
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孙子王军,曾多次在本刊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讲述他家的红色传承故事。本期,他再次撰文,赓续永恒的主题——家·国·传承,以表达他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喜悦心声。
一
我的家乡,是山东诸城一个叫大北杏的百年村落。
村东南有一座山。站在山上,透过郁郁葱葱的松柏,向北可望到辽阔的昌潍平原,南面是浩渺的墙夼水库,缎带般的潍河如母亲的臂膀,拥绕着村庄,静静流淌。
乡亲们告诉我,这座山原来叫东南岭,是我爷爷王尽美将它更名为乔有山。
爷爷1898年6月出生,家中靠租种地主的薄田度日。因为给地主家少爷当陪读,他迈进了知识的大门,并有了大名王瑞俊。一天,他告诉村民:“我把东南岭改名为乔有山了——就是要把原来只归地主家的山,‘乔迁’给我们大家所有!”
1921年春,爷爷创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他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这次“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表达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爷爷激情赋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他因此改名“尽美”以自励。

在爷爷倡议下,1921年9月,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7月,中共济南支部成立。
在终日奔波中,爷爷积劳成疾,感染肺结核病,经常咳血。1925年4月,爷爷再次来到青岛。当欢庆罢工胜利的锣鼓响起时,他病发倒在工人队伍中。同年8月19日,爷爷病逝于青岛,年仅27岁。病重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记录,口授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二
爷爷去世时,家中留下爷爷的奶奶、母亲和妻子三代寡妇,我父亲王乃征当时才6岁,叔叔王乃恩才2岁,生活几近陷入绝境。在组织的关爱和爷爷的战友王翔千等人帮助下,全家人才得以生存,父亲和叔叔还相继读上了书。
王翔千曾对我父亲说:“我和王尽美是为了劳苦大众而一起奋斗的战友,你将来出来闯荡社会时,不要随便参加什么党啊派的;要参加,就参加你老子那个党——共产党!”父亲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启蒙。
1937年秋,日寇铁蹄踏入山东。民族危亡之际,正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的父亲返回家乡找到王翔千,欲跟着共产党杀敌报国。当时王翔千的女婿赵志刚也在家中,还是刚刚成立的中共诸城特委负责人。他们当即发展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赋予他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任务。父亲马上赶回大北杏村,发展了王东年、王迂民等几名进步青年加入了共产党。
1937年10月,父亲等几名青年登上了乔有山。大家围绕着一块“饽饽石”(裸露于地表的山石),在翠绿的松柏上挂上鲜红的党旗,大北杏村中共党支部就此成立,父亲任党支部书记。
此后,他们根据党的指示,携笔从戎,建立抗日武装,走进了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之中。母亲臧校先、叔叔王乃恩、婶婶曹建民等都浴血奋战,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敬爱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直至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三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成为返乡知识青年。母亲特意送我回大北杏村,领我到爷爷王尽美故居看了看。那时,故居已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房子的低矮、阴暗和简陋,使我十分惊讶:“咱家……就住这破房子?”
母亲笑答:“你们老王家哪有这么好的房子?这还是重修的。”她告诉我,老宅是地主在牲口圈边上画了一块区域,向地下挖一尺来深,沿坑向上垒土成墙,上苫茅草而已;刮风进风,下雨漏雨,猛地“掉进屋内”,便伸手不见五指。
乔有山下的知青生活,是我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的第一站。劳动之余,我特别愿意到乔有山上去,那里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可以坐在树荫下,听乡亲们讲老辈的故事。
2006年9月,我女儿王丹娃上大学前,我带她回了一趟家乡。
登上乔有山,四面群山连绵,潍水滔滔。我向女儿讲述家乡诸城丰厚的人文历史,从舜帝、张择端到王尽美、臧克家、王愿坚的故事,还有我在乔有山下的一些经历。
上大学后,女儿写了一篇纪念曾祖父王尽美的文章,其中写道:“如果没有信仰、理想和追求,无论是一个群体或民族,都只能或被奴役驱使、或被抛弃湮没。”女儿在大学期间入党,立志要像祖辈一样,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女儿大学毕业前,曾专程在诸城团市委实习,她住在市实验中学的教师宿舍——这所学校,前身是她爷爷当年读过书的省立十三中。毕业后,她成了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一名编辑。
2020年底,我再次回到家乡。乔有山依然屹立,家乡焕然一新。村里的乡亲们,全部住进了同城市一样的居民小区——尽美家园。在原来的村址上,兴建了一座党员干部培训院校——尽美干部学院,建有党性教育主题展馆、教学研究中心、培训中心以及古村落教学点等,一期工程已经竣工,占地2万多平方米。在学院党性教育主题展馆正门上方,金色的党徽熠熠发光。
应学院邀请,我参与学院的长期授课,其中一次课名为:《家·国·传承》。
(作者为济南王尽美暨中共早期党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诸城王尽美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牛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