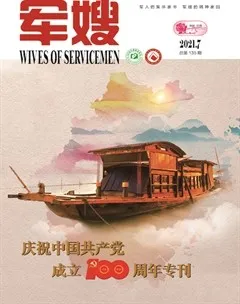闪光的榜样
一
2021年7月,我回到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看望战友,那里曾是我学习、工作的地方。夜晚,我独自在校区大院里随意走着,不知不觉来到学员路的南端。那幢老式两层楼仍静静矗立着,这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原南京炮兵学院四大队十五中队的教室。1995年12月,我在这里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开启了党员初心之路。
学员路一路向北,沿途设置着十余个灯箱,图文并茂展示着学院自1947年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驻足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怡昕教授的事迹展示灯箱前,思绪回到2000年。那年3月,我刚到学院政治部任新闻干事不久,有幸参与了“将军教授”刘怡昕的典型宣传。
在刘怡昕办公室的书柜里,珍藏着一本《来自世界屋脊的太阳》——这是毕业学员吕雄文出版的诗集。吕雄文1990年毕业,毕业前夕主动申请赴藏工作。赴藏前,刘怡昕多次和他交谈,并送他踏上赴藏征程。

尽管吕雄文进藏前做好了吃苦准备,但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还是产生了动摇,随后他给刘怡昕写了一封信。刘怡昕敏锐察觉到小吕的思想疙瘩,很快回了一封长信,字字句句透着殷切期望和人生感悟。吕雄文从中受到了启发和激励,逐渐坚定了扎根边疆的信念。
“为师一时,育人一生。”吕雄文的思想变化也启发了刘怡昕:自己教过的3000多名学员中,每年都有学员进藏,他们工作、生活情况怎样,成长如何?从那一刻起,刘怡昕产生了进藏看望学员的念头。
1991年7月,年逾半百的刘怡昕踏上了雪域高原之旅,专程赴藏考察毕业学员和驻藏炮兵部队有关情况。一到拉萨,刘怡昕的身体便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浑身像散了架,但他背上氧气包、揣上救心丸便下了部队。

期间,刘怡昕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累了吸口氧气,胸闷气喘就含几粒救心丸。当他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米拉山,来到吕雄文所在连队时,小吕颤抖着双手紧紧拉住他的手,惊讶得半天没能说出话,黑红的脸颊上热泪长流……那段时间里,刘怡昕跑遍了西藏的炮兵部队,看望了数百名学员,带回了数百张照片和10多公斤重的调研资料。回校后,他利用这些生动事例,对学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在学院兴起一股投身边海防的热潮。
在对刘怡昕教授长达数月的采访、接触中,我的内心一次次被震撼着,我读懂了一名“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矢志国防教育事业的执着坚守。
二
与刘院士“相邻”的是被誉为“军中保尔”的学院自行火炮教研室教授张战平。2002年,在参与张战平典型事迹宣传中,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热爱”二字。
张战平曾是全军为数不多的坦克特级驾驶员。1993年8月,他在某集团军任处长,得知南京炮兵学院新开设自行火炮专业急需教员,他毅然调入学院自行火炮教研室当了一名普通教员。
1995年6月,在一次教学实验中,张战平身受重伤,不幸失去右腿、右手食指、左眼和两耳鼓膜,成为一等伤残革命军人。与死神擦肩而过,张战平对三尺讲台的眷恋和热爱依然如故。受伤10个月后,他重新站上了讲台;两年多后,他独腿驾战车驰骋沙场。
从张战平身上,我看到了一名军人的光荣与梦想,感受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又一座闪亮灯塔在我的心中悄然屹立。
三
2018年12月,我转业到江苏省镇江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从部队政工干部到城市管理工作者,我内心一度充满困惑和疑虑。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刘怡昕与张战平。他俩当年都是年届不惑改行当了炮兵教员,却凭着对教书育人事业的执着与热爱,在各自领域取得骄人业绩。如今,两位教授虽均已退休,但依然在发挥余热,关心着炮兵事业和学院的教学工作。
在他们的精神激励下,我打算重新开始。2019年上半年,考虑我在部队曾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单位让我牵头负责全市城管系统首届“最美城管人”评选表彰活动。在此期间,我对10名“最美城管人”进行了采访,为他们撰写视频解说词和颁奖辞——这也让我对城管工作有了全新认识。2020年暑期,镇江处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攻坚阶段,作为局机关党委书记,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机关党员与社区结对共建,有效提升了城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每当走在镇江的大街小巷时,看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内心充满自豪。从入党至今,我已经走过26度春秋,虽然身份一直在变,但党员的初心永恒。灯箱上的榜样,也永远在我心中熠熠闪光。
(作者单位:镇江市城市管理局)
编辑/张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