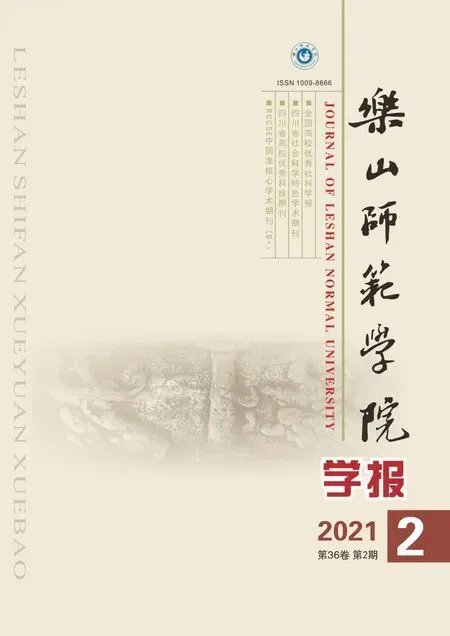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说中的“外省人”与城市化反思
魏 懿
(上海建桥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2)
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其著作《自由的想象》(TheLiberalImagination)中首次提出“外省人”(the Young Man from the Provinces)这一概念。特里林注意到,外省人这一形象“贯穿于整个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并成为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他还注意到,外省人形象较为集中地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英美小说中。这一时期的英美小说大都以大城市为背景,而外省人则是小说中极具鲜明特色的城市人物群像,并且为之后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所继承和发扬。然而,特里林并未深入探讨外省人形象背后的社会因素以及社会反思。具体到美国小说,“外省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美国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有何特质?这一人物形象传达了小说创作者对于当时美国社会的何种反思?探讨这些问题不仅能使人们更好地品读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把握美国文学的思想精髓。
一、“外省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条件
根据特里林的定义,“外省人”指的是那些出身乡村或是贫困地区,只身来到大城市寻求人生财富的年轻人。“乡村的出身与单纯的成长环境意味着他们一开始满怀天真与极高的期望——他们一开始对于生活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对于人生的复杂和前景充满惊奇。他们可能出生于书香门第,但是却十分贫困。他们有聪明的头脑,或至少意识到自己拥有智慧,但是对于世俗事务却一点都不精明。”[1]61根据这一定义,不少美国经典小说都可被视为外省人小说。例如,西奥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巨人》、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斯蒂芬·克莱恩的《街头女麦吉》、威廉·豪威尔斯的《新财富危机》等。
与所有的人物形象一样,美国小说中的“外省人”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身上所体现的生活与职业上的地理位置的迁移——从农村到城市——折射出的正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根据相关统计,从内战结束后的1865年至经济大萧条前的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将近7倍,5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从内战前的16个迅速增加到109个,其中25万人以上的城市达到了11个。[2]1880年至1890年十年间,芝加哥的人口翻了一番。同一时期,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这两座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了3倍,而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和克利夫兰等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也达到了60%至80%。[3]迅速且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彻底改变了美国原有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也重新塑造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人际关系。农业生产的迅速工业化使得乡村地区出现大量的剩余青壮年人口,这些剩余人口开始从村镇向新兴城市移动,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城市丰富奢侈的物质生活,各种生活上的便利设施也是吸引大量乡村地区年轻人进入城市的重要原因。美国女作家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在其短篇小说《一段好时光》中描写了19世纪末纽约市的一家旅店中的场景,这对来自新英格兰乡村地区的女主人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我们去了一家非常漂亮的旅店,大厅里铺着红色的天鹅绒地毯,还摆放着红色的家具,还有一个绿色的客厅和一个蓝色的客厅。…… 厅里铺着天鹅绒地毯和结实的家具,壁炉架上还有一个镀金的时钟,此外我们的房间里有两个卧室和一个浴室。我们的小镇上没有一个房间能与之相比,就连汉姆镇长也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房间。……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饭厅和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实在不忍心吃它们。在我们坐的椅子背后还站着好几个男士一直在为我们服务呢。……所有人都在买圣诞节礼物,商店里摆满了圣诞树——你从来没见过这种景象。”[4]女主人公纳西莎处处将城市里的一切与乡村进行对比。纽约市里的一家旅店尚且如此充满魅力,整座城市对于生活在小村镇的人们而言更是有着难以抵抗的诱惑力。“对她而言,城市里的一切一定是那样快活和充满生机。男男女女都一定快活而自由地生活着。大家彼此结交,互通友谊,就像清风吹拂在脸颊上。……她梦想着能进入那温暖且跳动着生命力的氛围之中。”[4]57-58《嘉莉妹妹》中女主人公嘉莉也是带着极为羡慕的心情审视着城市里的一切。“羡慕的火焰在她的心里燃烧着。她隐约地意识到城市承载着多少东西——财富、时尚、舒适——每一样东西都是女性所追求的。她满怀欣喜渴望着打扮和魅力……她禁不住觉得每一件饰物,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对她都有切实的吸引力。”[5]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小说中充斥着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无限遐想与向往。诚如英国学者哈罗德·戴欧思所认为的那样:“十九世纪的城市化发展标志着一个能够感受到许多现代性的渴望与期待的新时代的开端。”[6]
以火车为代表的工业时代交通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为“外省人”进入城市提供了技术条件。“在最近的五十年里我们人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事实上一场革命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伴随着各种喧嚣与吵嚷。数以百万的新声音从域外来到我们中间。来来往往的火车,不断壮大的城市以及正在建设之中的城市间的铁路。它们彼此交织,从小镇延伸,穿越农场,而最近一段日子汽车的出现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中西部的乡下人的习惯与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7]自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开始了以修建铁路和公路为主要内容的交通革命,美国的铁路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至20世纪初,美国铁路的总里程数已达到258 784英里,居世界首位。《哈帕斯新月杂志》在1887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热烈宣扬火车铁路对于美国人的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男孩在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运动。他在不同的路段上晃动着,他对人生的感觉就是在一望无际的空间中飞快运动,越过牛群遍地的田野和一排排的楼房。火车似乎已经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人,那便是铁路时代的直接产物。”[8]铁路时代所创造出的“新型的人”便是大量进入城市谋生的“外省人”。铁路交通的发展为乡镇居民进入城市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方式,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从乡村前往城市的旅途成本。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小说中时常可见“火车”和“铁路”的身影。当小说主人公想要进入城市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铁路交通。在《嘉莉妹妹》中,主人公嘉罗琳·梅柏坐着一列下午始发的火车前往芝加哥,“那座伟大的城市愈加紧密地被每天来往的火车连接在一起。”[5]1在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中,当艾尔姆·考利想要离开闭塞愚昧的瓦恩斯堡镇时,他想到的是“一列驶向克利夫兰的列车会在午夜时分经过瓦恩斯堡镇。黎明时分便能到达克利夫兰。他可以偷偷登上这列列车。当他到达克利夫兰时,他便可以隐没在城市的人群中。”[7]152小说结尾处,主人公乔治·维拉德在聆听和目睹了瓦恩斯堡镇以各种方式扼杀了小镇居民的激情并将他们变成“畸人”之后,也是以坐火车的方式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瓦恩斯堡镇。“西行的列车在早晨7点45分离开瓦恩斯堡镇。他的列车从克利夫兰一路驶向在芝加哥和纽约两端之间运行的铁路主干线。”[7]191“列车”“芝加哥”“纽约”“铁路主干线”表明铁路和列车已将美国的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越来越多的“外省人”通过这种新兴快捷的交通方式进入城市,在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中感受着工业文明的进步与便利。
可以这么说,美国小说中的外省人形象是美国城市物质文明发展与交通科技发展共同催生出的产物。从乡村向城市的迁徙增强了人们对于机会以及成功的信念。“迁徙——物质上和地理上的迁移——是社会和经济流动的象征。它也是进步、独立和个人自由相互融合为一体的象征。在向城市迁徙的过程中,在城市内部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在从一个城市迁向另一个城市,从城市迁到郊区和从郊区迁回城市的过程中,美国人不论新旧都已经把自己同民族的移民史、殖民史、西进运动和边疆史联系在了一起。”[9]从美国国家发展史的角度而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小说集中出现的“外省人”也是以迁移流动为叙事范式的必然产物。
二、幻想与现实的断层:悲剧的追梦人
“外省人”从农村到城市的旅程不仅仅只是职业与生活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同时也是精神层面上的社会流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处于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之中,整个国家已经从过去的农业生产转向市场经济和城市工业生产。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汇集到了以纽约、芝加哥、费城等为代表的大城市中。城市中繁荣的物质文化和消费主义吸引着外省人涌入城市。他们渴望把对于城市的各种欲望变成对于自身变化的渴望,想通过获得物质的帮助来改变自身的形象与处境。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名“外省人”,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于1884年第一次跟随家人从印第安纳州的小镇来到芝加哥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里是天堂!是人们梦想的环境……对我而言,这个城市是希望之地,拥有牛奶和蜂蜜的不真实的世界……不像其他地方,在这里,年轻人可以获得成功。”[10]德莱塞对于城市的这种高度赞美的态度在当时极具普遍性。如同德莱塞笔下的嘉莉妹妹、柯伯乌、珍妮姑娘等人物一样,许多年轻的外省人都把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视作充满机会和希望的地方。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小说中也大量出现外省人形象,如狄更斯笔下的奥利弗·特维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和哈代笔下的裘德等。与英国小说中的“外省人”相比,这一时期美国小说中的“外省人”似乎对于城市生活尤其充满了热情与期待。和现实生活中的德莱塞一样,美国小说中的“外省人”对美国迅速的城市化发展感到无比的惊讶与激动。与伦敦,巴黎等欧洲大都市相比,美国的城市显得年轻而充满朝气,同时也更为现代化。自从19世纪70年代美国“自由企业经济的浪潮,无限制的移民政策以及一系列在建筑、运输和通信方面的革命性发明创造”[11],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相继崛起,并成为当时西方世界最为新兴的现代城市。这些新兴城市在美国作家眼中犹如“巨人”一般,“(它们)挟着青春时期粗野的气质,傲视着一切竞争对手。它们明智、健康、朝气蓬勃;它们野心勃勃,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而显得十分狂妄”[12]。与乡村相比,大城市成为了“外省人”心中充满了自由和机会的幻想空间与精神乌托邦。就像《嘉莉妹妹》中所描写的那样,“在1889年芝加哥拥有特别的发展特质,它使得年轻姑娘都觉得前往城市进行冒险式的朝圣是合情合理的。越来越多的商机使得芝加哥声名远播。这使它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磁石,从四面八方吸引着充满希望和绝望的人来到这里。”[5]11-12欣欣向荣的城市化大发展为初到城市的“外省人”提供了无限的机遇与可能性。除了日新月异的城市物质条件之外,美国人喜欢打破传统的精神信念也为“外省人”的追梦之旅提供了心理层面的解释。美国学者凯瑟琳·休姆认为,美国人固有的“人生来平等”的理想信念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进一步被强化,“美利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沸腾着一股地狱般的力量,它要求摧毁所有传统并因此给予世俗生活以真正的意义。……美国被赞美成一个充满革新和一切新鲜事物的国家。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即使没有高贵的出身和血统,每一个人都能往上爬。”[13]根据美国宪法,“这个国家没有上等的、主导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公民阶级。这里没有等级”[14]。与欧洲上百年的等级社会相比,美国社会更相信“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最卑微的人与最有权势的人平起平坐”[14]332。这一信念使得美国公民坚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坚韧不拔的努力在“机会均等”的大城市里追求梦想并最终实现梦想。这种追梦的动机也逐渐演变成美国文学中最重要的创作母题——美国梦。美国人追梦的特质自然也体现在“外省人”身上,初到芝加哥的嘉莉妹妹坚定地相信,“她要在芝加哥生活,她的意识不断地对自己说到。她会比以前拥有更幸福的时光——她将变得更加快乐”[5]22。《巨人》中的柯伯乌凭直觉认为,就连芝加哥的空气里都“含有一种劲头、引起了他的幻想。……这儿的世界是年轻的。生活有了新的气象”[15]。柯伯乌踌躇满志地认为城市将会是他施展抱负的大舞台。
然而,现代化的新兴城市在激发“外省人”无限欲望与希望的同时,也让许多“外省人”感到焦虑和恐惧。“(在城市里)一切奢侈汇集而来,所有的东西都是那样炫目而诱人。而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令人绝望的饥饿。”[3]559特里林在定义“外省人”时,特别强调了“外省人”身上简单朴实的特质。在离开“单纯的成长环境”之后,当面对复杂而陌生的城市环境时,“外省人”的简单与城市的复杂构成了性格与环境层面上的极大反差,以致使“外省人”隐隐感到震惊与恐惧。“她的心被一种恐惧干扰着。她独自一人,远离家乡,闯入犹如大海般充满生命与力量的城市中。她不禁感到呼吸有点困难。她的心脏跳得如此快,她感到有点恶心。”[5]7“外省人”以乡村的淳朴经验为主导形成了对城市新环境的期待。当他们的淳朴经验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刺激形成了巨大的偏差或陌生感时,他们便会陷入惊恐之中。对于身处大城市的“外省人”而言,城市中海量的信息对其身心都会产生冲击甚至伤害。城市作为工业文明聚焦和活动的中心,这里汇集了人类所有形式的堕落与腐败。“城市揭示了事物的道德目标、汇集了生活中的大量问题。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高尚与邪恶也都被集中激发出来,暴露于表层。城市是原则的大课堂,因为它会给原则提出尖锐的质问。”[16]自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物质欲望开始逐步上升为美国城市生活的主导力量。美国战前原本主张民主,自由与和谐的农业文明悄然地转向了崇尚实用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工业文明。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便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理想、信仰以及主体心理与行为发生断裂性的变化”[17]。全新的城市环境让守法者变得谨小慎微,同时又让冒险者变得如鱼得水。“外省人”逐渐开始意识到,城市繁荣绚烂的表面之下其实隐藏着一个冷漠森严、没有底线的等级制度。“一个人想要尽可能从中赚钱,他不必在乎以何种方式。在他之下有如同军衔等级一般的各个阶层。经理、监管、包工头,每一个人都驱使着比自己低一级的人,都试图从这个人的工作中榨出尽可能多的油水。同一阶级的人也彼此倾轧。……更糟糕的是人没有体面,甚至没有任何的诚信可言。”[18]《屠场》中的“外省人”约吉斯意识到,想通过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技能的手艺人实现城市梦是不可能的,“他很快发现自己的这一错误——因为在芝加哥没有一个人是通过好好的工作来发家致富的”[18]63。原本以机会均等,靠坚韧不拔的努力便可获得成功的美国梦对“外省人”而言已经显得遥不可及,取而代之的是难以逾越的城市阶级和被扭曲的发财梦。这种心理与环境的极大落差是导致这一时期美国小说中的“外省人”唏嘘命运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文学批评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将“外省人”的悲剧命运归结为城市底层社会的贫穷和城市道德堕落等外在因素。然而,“外省人”自身对于城市的天真想象以及对自我逐梦的盲目幻想也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内在原因。虚幻的想象与真实的现实体验之间出现了断层,这种“断裂性的变化”使得“外省人”要么以死抗争,要么随波逐流。其具体的表现便是强烈的命定论倾向。在一个理想与现实出现断裂的世界里,人只能受到外力的驱使与支配,并逐步变成渺小而可怜的动物。“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都充满意志,希望和内心的渴望,……然而一个黑影却笼罩在上方,可怕的命运正等在路上。忽然命运向它们扑去,死死地无情地抓住它们的腿。任凭它们如何挣扎和尖叫都无济于事。”[18]37《屠场》中等待被屠宰的牲畜的命运与城市中的“外省人”的命运何其相似。主人公约吉斯不禁开始思索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象征与隐喻”。[18]37即使对于那些看似结局“幸运”的“外省人”而言,他们的命运也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过去的评论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小说中所弥漫的悲剧宿命论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欧洲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然而,就“外省人”的主体心理层面而言,强烈的宿命观和命定论也是其在经历了幻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之后所产生的自然心理反应。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社会里,旧的价值观已经摇摇欲坠,而新的价值观还未占主导地位。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必然会感到无所适从。
三、外省人:城市化进程的人文反思
从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期,美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化进程。狂热的商业氛围以及轰轰烈烈的贸易活动奠定了美国城市化进程的主基调,同时也影响到了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城市高楼拔地而起,城市物质和娱乐生活日趋丰富的同时,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也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作为这一时期美国小说中重要的人物形象,“外省人”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的作家对于城市化弊端的反思。“外省人”的命运也透露出作家对于个人价值欲望的人文主义关怀。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地区和生活于这个地区的民众的物化过程。美国学者凯瑟琳·休姆认为,以美国梦为代表的美国城市文化其实质是一种过度追求物质财富享受的浅层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没有精神维度”[13]113,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属于自己的富足生活本来无可厚非。然而,裹挟着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城市化进程使得美国梦的价值体系发生了改变。“当美国的物质主义使得金钱的价值高于道德时,我便看到将会发生什么。这种结果是灾难性的。”[13]16在城市丰富的商品环境里,欲望调动了“外省人”的内在主体需求,同时身处城市中的漂泊无依感又会让他们担心自己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用乡村小镇的思维理解呈现在眼前的各种物质商品。“谁不会坐在一把镀金的椅子上哀嚎呢?当站在散发着香水味的地毯上,倚着带有靠垫的家具,看着身穿制服的服务生时,谁不会在心里感到难受呢?在这样的情形下,痛苦也变成了迷人的诱惑。”[5]245“外省人”的身体和心理需求都在告诉他们,只有占有这些物质商品才能体现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他们将物质和金钱等同于幸福和成功。可以说,“外省人”是最容易受到美国梦鼓舞的一群人,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误导和物化的一群人。他们往往最终背离了美国梦的原始精神,走上一条机会主义者的道路,例如《嘉莉妹妹》中的嘉莉、《巨人》中的柯伯乌、《深渊》中的杰德温等。他们都被所谓的梦想和幻觉所蒙蔽,自我欲望不断膨胀,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自我。究其原因是由于美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过度强调物质文明的优越性,而忽略了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城市是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综合文明的载体,……物质文明是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保障,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灵魂和核心。”[19]没有精神文明为依托的物质文明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物质化和货币化,进而造成个体之间的冷漠与疏离。就像嘉莉妹妹所惊叹到的那样:“住在同一幢楼里的十户人家彼此始终保持着陌生和冷漠。”[5]236这种人际间的冷漠感也会延伸到城市的最小单元——家庭,并最终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例如在《嘉莉妹妹》中,嘉莉与其姐姐一家人的关系近似租客与房东,毫无任何姐妹亲情可言。在斯蒂芬·克莱恩的小说《街头女麦吉》中,麦吉的悲惨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其母亲和哥哥的极度冷漠。在一座缺乏精神文明的城市中,一切人际关系都将以市场价值的方式被重新审视。这也是早期城市化进程中较为普遍同时又较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通过“外省人”这一形象,当时的作家们透露出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精神文明缺失的隐忧。
波顿·帕克在《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中认为作家观察和叙述城市一般采用三种视角:上面、街道水平面以及下面。[20]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小说中的“外省人”多采用后两种视角来呈现城市布局的非正义性。在《街头女麦吉》中,克莱恩通过麦吉的街道水平视角描绘了她所生活的纽约巴伐利街区。那是一个充斥着马厩式的低矮房屋、厂房和低级娱乐厅的街区。那里的居民是操着不同方言的一群“愚民”,他们物质匮乏,精神贫瘠。威廉·豪威尔斯在其发表于1889年的小说《新财富危机》中,通过“外省人”马奇夫妇的视角描绘了纽约的平民街区。“灰色的桶在人行道上排成一排,水沟里充满了垃圾;做生意的小贩懒散地站着……醉汉歪歪扭扭地沿着人行道走着。这不是一个极度贫困的住所,而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是毫无希望的贫穷住所。”[21]而离此不远的地方便是纽约最繁华的百老汇大道和华盛顿广场。随着19后期美国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市道路不断向外延伸。上等阶级家庭为了逃避城市中心的喧嚣和脏乱,逐渐搬迁至较为安静的市郊。城区的房子则被多重转卖或转租给来城市谋生的外省人或移民。在外省人眼中,城市规划将不同阶层的人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划分。“整个城市中心拥有一种高尚而威严的氛围,这足以让普通人感到敬畏和惭愧,而这又让贫穷和成功之间的鸿沟变得又宽又深。”[5]12这种城市空间的划分往往将包括外省人在内的底层民众禁锢在一个静止的、无希望的空间里。“城市将不同类型的人分离出来,也将同一类型的人放在一起。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一部分就是他们所占的空间、居住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相同点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共享的空间和共享的地点。”[22]早期城市化进程按社会阶级对居住地界进行划分的空间布局显然容易造成阶级的对立,违背了美国所倡导的平等、民主和多元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得城市空间被打上了非正义的烙印。“真正的城市正义应该回到正义的本质,即包含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23]当时的作家通过外省人的视角似乎在警示: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严重背离了空间正义。居住在非正义空间中的居民最终往往会陷入贫困与犯罪的深渊,这不仅拉低了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也加深了美国社会的矛盾与分化。
长期以来乡村一直被视为城市工业文明的隐形参照物。在美国的城市发展史上,一股强大的反城市传统也如影随行。“美国人在这个时期(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全部思维都受到乡村心理的影响,与这种经验形成对比的是城市的各种现象:拥挤、贫穷、犯罪、腐败、冷漠和伦理混乱。……城市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对文明本身的一种奇特威胁。”[24]舍伍德·安德森在《小镇畸人》中将美国的乡村描绘成一个闭塞、沉闷、扼杀人性的荒原,身处其中的年轻人渴望逃离乡村涌向城市。然而,当外省人在城市的追梦旅程中遭遇各种挫折和逆境时,乡村又成为了他们寻求精神慰藉的唯一寄托。《屠场》中的约吉斯在芝加哥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之后在乡村大自然的怀抱里得到了心灵的休憩。“他感觉自己犹如一只被托举的鸟,乘风而去。他停下脚步,凝视着这令人惊奇的全新景象——牛群、开满雏菊的草地、铺着厚厚的六月玫瑰的灌木丛以及枝头鸣叫的小鸟。”[18]227嘉莉妹妹在开往纽约的火车上也对乡村泛起眷恋之情,“她忘记了赫斯特伍德的存在,用充满惊奇的目光看着犹如家一般的农舍以及村镇里温馨的房屋。”[5]218即使《小镇畸人》中那些对城市充满向往的年轻人也无法放弃对宁静乡村的美好回忆。对于这些外省人而言,他们来自乡村,乡村是他们的精神伊甸园,是一个可以在冷冰冰的物质世界里找到诗意的意识空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所给予的精神寄托只是暂时的。大多数外省人最终并没有选择回归他们的精神家园。约吉斯昄依左派思潮回到了芝加哥继续谋生,而嘉莉妹妹选择与赫斯特伍德姘居继续在纽约生活,并最终被纽约的消费主义彻底物化。他们都选择继续在城市工业文明的阴影下竭力寻找已经失去的幻想。城市化的进程一旦开启,便不可阻挡。人们涌向城市是因为那里集中了全社会最丰富的资源与机遇,这些是乡村所无法给予的。因此乡村的没落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外省人来自乡村,但却无法回归乡村。面对城市丰盈的物质生活,人们应该学会护持内心的伊甸园,寻求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让城市变成使人们的精神无所归依的罪魁祸首。这或许也是当时的作家们希望通过外省人形象引导读者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世界必须严肃思考的命题。
四、结语
作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小说中重要的人物形象,“外省人”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和欣欣向荣的物质文明,同时也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和弊端。当时的作家通过外省人的经历和视角揭示了城市化进程对于个体精神建设的忽视。城市规划缺乏空间正义布局,城市的快速发展让许多外来者的精神无处安放。这些反思也被后来的美国作家们所继承与深化。例如,索尔·贝娄笔下那些面临都市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犹太裔青年,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中那个感到生存焦虑和失去自我本质的“隐身人”等。这些人物身上无不透露出“外省人”的影子。他们在以物质财富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都市里所遭遇的失落和精神漂移也正是“外省人”在城市化早期所具有的心理状态。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现代和后现代作家继承了早期作家的人文反思,将“外省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进一步上升到对于人类未来生存状态的关注。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开始暴露出各种负面影响和问题。有些问题——贫富差距、消费主义、外来人口等——与当时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如何规避和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平衡健康的城市文明,读者或许可以从外省人形象中得到某些启示和教训。这也是当前研究外省人形象的现实意义所在。
——嘉莉妹妹成长引路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