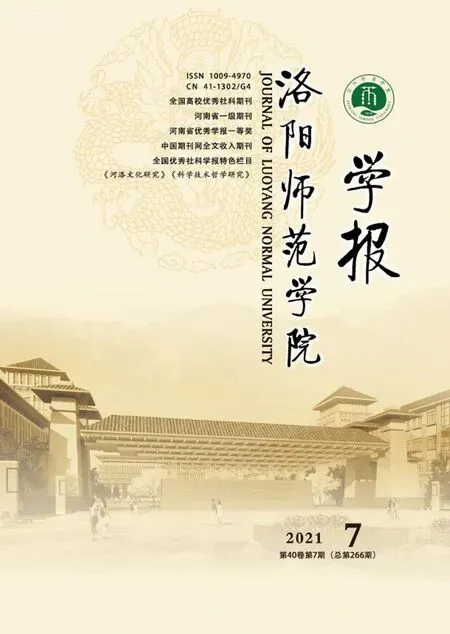南宋笔记中的临安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汤清国
(武警海警学院 军事训练系,浙江 宁波 315801)
杭州,古称“钱塘”“余杭”,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始得“杭州”之名。北宋靖康之难后,赵构于南京应天府(治今商丘南)登基称帝,南宋立国。后南渡至杭州,将杭州改名“临安”,是谓“行在”。行在,即天子行銮驻跸之所; 临安,乃临时安顿之意。从地名寓意上看,反映出南宋初期君臣上下尚怀收复中原之志,可惜终南宋一朝,不但中原故地没有收复,还终至覆亡,洵为历史之憾。
对临安的抒写,是南宋笔记中的重要内容,具有城市符号、政治寄寓和人文意蕴等文化内涵。从南宋开始,临安抒写逐步转变为杭州抒写,临安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符号,而是成了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文学意象,对后世文学作品中杭州的抒写有着重要影响。每当国事衰微、改朝换代之际,杭州就往往成为文人抒发兴亡之慨、寄托故国之思的意象载体。
一、城市符号与都市文化
中国古代的笔记,发展到宋代,在题材类型、写作风格、思想主旨、艺术手法等方面,都趋于完善和定型。特别是到了南宋,笔记的作者群体进一步扩大,作品数量进一步增加,题材内容更为丰富,艺术手法更加成熟,达到了中国古代笔记发展的空前高峰。
南宋时的杭州,作为首都,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南宋众多笔记作品中,多有对都城临安的文字抒写,其中还有不少围绕临安而创作的笔记专著,如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这些笔记作品,均以临安为背景,记述临安的城市建筑、朝廷礼仪、典章制度、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等,构成了笔记中的临安意象。笔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特点可以概括为: 内容杂,形式散,写作随意,文风质朴(1)关于笔记的文体特征,可参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及吕叔湘《笔记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因此,笔记中的临安抒写,就与正史和地方志中纯客观式的记录不同,而是融入了丰富的情感因子,文字典雅质朴,叙述委婉情深,具有更为浓郁的文学色彩。
南宋笔记中的临安意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是作为地理概念的城市符号; 二是象征王朝政权的政治寄寓; 三是作为都市文化名片的人文意蕴。
杭州自古风景优美,物产富饶,自古为江南繁华之地,特别是南宋定都以后,城市经济和市民文化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发展,并逐步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临安首先作为地理概念上的城市而存在,它的城市符号内涵就主要体现在对城市景观的描写上。
临安的城市景观,以西湖为代表。在对西湖的众多描绘中,值得注意的是以西湖为背景的有关君民同乐的抒写。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云: “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比。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1]99对西湖美景的热恋,连贫者也不能例外。除了公子王孙和普通居民外,皇帝也迷恋于西湖的风景。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专门记述高宗退居德寿宫后游幸西湖、与民同乐的情景。高宗及众多随从“各乘大舫,无虑数百”。官民同乐,有赖于宋金合议之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午如织。”城市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民休闲文化的逐渐繁荣。“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不游,而春游特盛焉。”[2]69春季的西湖,也就成了临安市民游玩的绝好去处。有关君民同乐的抒写,在南宋诗词作品中不多见,而在笔记中却有着众多的记载。这一点,体现出了笔记与诗词不同的文体特征。临安的城市景观,除了西湖名胜,还有居民建筑、诸色市场、勾栏瓦舍、酒楼、作坊、寺庙以及钱塘江等。围绕着这些景观的描述,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临安城市景观。
作为南宋首都,笔记中的临安意象,还时常与南宋王朝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临安城的兴衰,是南宋王朝兴衰的象征。因此,临安意象也就具有了象征南宋王朝政权的政治寄寓。临安意象的政治寄寓,主要体现在对皇城布局、朝廷礼仪、朝政故事的记述上。
皇城代表了政权,是国家的象征。皇城布局,就成了临安意象政治寄寓的首要内容。《梦粱录》中就记载了临安城的官僚机构、朝会活动、官私祭祀等内容,对研究南宋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记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读是书者,于以知有宋一代都邑繁华”[3]625-626。《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记载皇家宫殿建筑二十类三百一十七处,可以概见临安宫殿建筑之繁华。
朝廷礼仪作为国家大礼,朝廷尤为重视。以《武林旧事》为例: 卷一“庆寿册宝”条,记述宋孝宗为太上皇庆寿; “四孟驾出”条记述皇帝祭祀宗庙; “大礼”条记述朝廷祭天大礼; “登门肆赦”条记述朝廷为了显示德政而举行释放罪犯的各种仪式; “恭谢”条记述皇帝在大礼后向神灵与祖宗礼拜恭谢的礼仪; “圣节”条记述为皇帝庆祝生日的各种礼仪。在卷二中,还记述了皇帝重视武备,举行阅兵仪式的场景,“都人赞叹,以为盛观”[2]35。
朝政故事,也是临安意象政治寄寓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记述上。这些朝政故事中的人物,大都生活在临安,故事的发生地,也大都在临安。有的故事中的人物没有生活在临安,故事的发生地也不在临安,甚至故事的发生时间也不在南宋。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记述这些故事的笔记作者,却是生活于临安,或写作地在临安。因此,这些记述,也可以构成临安意象政治寄寓中的朝政故事。以周密《齐东野语》为例: 卷一“孝宗圣政”条,记录了宋孝宗治国理政方面的几则故事,赞扬了孝宗的圣德; 卷三“绍熙内禅”条,记载光宗禅让皇位的历史内幕; “诛韩本末”条,记载韩侂胄弄权误国,引起众怒,终至被杀的历史内幕。此外,又如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卷五“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4]等,所记也均为朝廷卓荦大事,较正史记载,更为详细,有裨于考证。
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发达,同时也促生了奢侈享乐与扶贫济困共存的社会风习。在《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笔记中,就多有关于临安城市文化与社会风习的详细记载,历来也最受关注。这些记载,组成了临安的城市文化名片,使临安意象具有了丰富的人文意蕴。仅以《武林旧事》关于元宵观灯的记载为例: “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著色便面也。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前后设玉栅帘,宝光花影,不可正视。仙韶内人,迭奏新曲,声闻人间。殿上铺连五色琉璃阁,皆球文戏龙百花。小窗间垂小水晶帘,流苏宝带,交映璀璨。中设御座,恍然如在广寒清虚府中也。”[2]49-50且不说元宵夜的其他娱乐活动,单单是“荧煌炫转,照耀天地”的灯品,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了。
与发达的城市文化相对应,临安城的社会风习也悄然发生着转变,以致上至君臣,下至平民,形成了奢侈之风。《武林旧事》记载皇帝与臣下争奇斗宝的情景: “有贵邸尝出新意,以细竹丝为之,加以彩饰,疏明可爱。穆陵喜之,令制百盏,期限既迫,势难卒成,而内苑诸珰,耻于不自己出,思所以胜之,遂以黄草布翦镂,加之点染,与竹无异,凡两日,百盏已进御矣。”[2]60-61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除了皇廷贵族流行奢侈之风外,就连民间坊里,竞奢攀比之风亦盛。酒楼业主之间“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歌管欢笑之盛,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2]160奢侈之风可见一斑。都人避暑时,“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2]84。甚至“有所谓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罗帛,雕饰为楼台故事之类,饰以珠翠,极其精致,一盘至直数万,然皆浮靡无用之物,不过资一玩耳”[2]75。商业气息的浓厚,滋长了投机取利的风气。“都民骄惰,凡卖买之物,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2]164倒卖货物,从中攫取利润,反映出当时临安商业的高度繁荣。对于民风骄惰形成的原因,周密在《武林旧事》“骄民”条中写道: “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环。诸务税息,亦多蠲放,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2]165生活于天子脚下,临安市民占尽天然优势,享受着经济的高度发达带来的各种福利,无怪乎周密长叹“何其幸欤”。
南宋后期笔记的作者,大都经历了末世的繁华,有的更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剧变。他们在客观记录临安城市经济的繁华和市民生活富庶的同时,也对市民过度奢侈的生活风习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梦粱录》卷一“正月”条: “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1]92指出了杭州的奢侈风气,历来有之。卷二“清明节”条: “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就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殢酒贪欢,不觉日晚。红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此时尚犹未绝。男跨雕鞍,女承花轿,次第入城又使童仆挑著木鱼、龙船、花篮、闹杆等物,归家以馈亲朋邻里。杭城风俗侈靡相尚,大抵如此。”[1]104在此,扫墓之俗竟演变成了游乐之习。卷三“五月”条: “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1]115卷十八“民俗”条: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269描写杭城的奢侈之风,慨叹市民风习不如旧时淳朴。
在记录和批评临安市民奢侈生活风习的同时,也记录和赞扬了临安市民济贫扶弱的善举。如《梦粱录》卷十八“恩霈军民”: “宋朝行都于杭,若军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恩。”[1]283不但朝廷对居民有济贫扶弱的措施,那些富家大户也对贫苦人家多有帮扶之举。卷十八“恤贫济老”条: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1]285反映了临安城社会风尚良好的一面。与此条记录相似,《繁胜录》也有类似的记录: “雪夜,贵家遣心腹人以银凿成一两、半两,用纸裹,夜深,拣贫家囱内或门缝内送入济人。”[5]
二、汴京与临安的双城叠韵
南宋笔记对临安城市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抒写,意在人事,而非风景。风景逐渐隐入到幕后,成为背景。在抒写中,往往以北宋都城汴京作为对照,时时出现汴京印象。在这对比的背后,隐寓着对北宋故都的追忆和对南宋君臣苟安江南一隅的不满。汴京和临安的双城抒写,贯穿了整个南宋的笔记发展史。
耐得翁《都城纪胜》称杭州为“都城”“杭”“行都”“都下”“都会”,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为“都人”; 称汴京为“东京”“京师”“旧京”[6]等,暗喻临安非正统之首都。日常生活中,南宋人时常追忆汴京风物。周煇《清波别志》云:“ 绍兴初, 故老闲坐, 必谈京师风物, 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一小阕, 听之感慨, 有流涕者。”[7]135
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序中云: “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且《洛阳名园记》后论有云‘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况中兴行都,东南之盛,为今日四方之标准;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绳厚,市井骈集,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仆遭遇明时,寓游京国,目睹耳闻,殆非一日,不得不为之集录。”[6]5在序中,耐得翁称北宋京城为“京师”,将其与临安做了对比,凸显出杭城的繁华与富庶。以园囿之兴废,映照洛阳之盛衰。而今杭城之繁华,则亦映衬圣朝之兴盛。但细细品味字里行间,仍能读出耐得翁在记录杭城繁华的同时,隐寓着对旧都之追忆,对南宋君臣苟安江南一隅的批评。除了序言,耐得翁也时常在正文中将今日之临安与旧时之汴京作比。如“食店”条: “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6]9“瓦舍众技”条: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教坊大使,在京师时有孟角毬曾撰杂剧本子。”“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6]12-13“舟船”条: “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龙舟争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之遗风。”[6]17金明池乃北宋皇家园林,位于东京汴梁城外。园林中建筑全为水上建筑,风景佳丽,池中可通大船,战时为水军演练场。这些东京元素,或直接称“京师”,或选取东京的自然景观,一方面是为了描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了在字里行间寄寓家国兴亡之慨。“市井”条记述杭城各色买卖人群时,补充说明这些买卖人群中“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圆子”[6]6。《四库全书总目》云: “是书作于端平二年,正文武恬嬉,苟且宴安之日,故竞趋靡丽,以至于斯。作是书者既欲以富盛相夸,又自知苟安可愧,故讳而自匿,不著其名。”“以其中旧迹遗闻,尚足以资考核,而宴安鸩毒,亦足以垂戒千秋。”[3]625道出了《都城纪胜》的著述背景及其中寄寓的兴衰之慨。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作于南宋初年,主要记载东京的风俗景象。孟元老早年经历了北宋的繁华盛景,而后遭遇北宋覆亡的剧变,来到杭州避乱。“情绪牢落,渐入桑榆。”追忆汴梁古都“节物风流”“人情和美”,恐故都风俗“失于事实”,遂“谨省记编次成集”[8]114,撰著此书。《武林旧事》是周密于南宋灭亡以后,回忆临安旧事而作。主要记载了南宋的典章制度、民俗风情、逸闻趣事等,此书与吴自牧的《梦粱录》并称,同为杭州地方文献掌故的重要图书。
孟元老经历了北宋覆亡之变,而周密则经历了南宋亡国之痛,二人经历相似。但北宋虽亡,南宋又立,仍为赵宋天下; 而临安城破,南宋覆亡,遂为异族统治。孟元老尚能避乱江左,而周密则唯有以一介遗民隐居于杭。时事不同,二人心境有别。但临安抒写,则是紧承汴京抒写而来。一朝二都,构成了南宋笔记中的双城抒写。孟元老的著述意旨对周密的笔记创作,当有一定影响。
三、临安意象的文化意蕴
通过南宋笔记的记述,地理上的都城临安,逐步转变为回忆中的故都临安,并最终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临安意象,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杭州、杭城、西湖、钱塘等意象,皆从南宋的临安意象化出。从南宋开始,临安意象更多地进入了文人的视野。每当江山易代之际,从临安意象化出的杭州、杭城、西湖、钱塘等意象就常常被摄入笔端,成为文人们表达家国之忧、寄托故国之思、抒发兴亡之慨的文学意象。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就是两个特殊的时期。
《武林旧事》是周密笔记作品的代表作。从创作主旨上看,此书不在于客观记录,而在于其中的情感意蕴,即寄寓了故国之思和兴衰之慨。《四库全书总目》称: “是书记宋南渡后都城杂事,盖密虽居于弁山,实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于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故迹,叙述尤详”。“其间逸文轶事,皆可以备参稽。而湖山歌舞,靡丽纷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遗老故臣,恻恻兴亡之隐,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3]626
《武林旧事》的版本源流比较驳杂,在元代就有六卷刊本和十卷抄本之别,并在周密好友中传抄流布。此外,书中的篇章还被单独裁出,作为单部笔记流传。石岩在《志雅堂杂钞·序》中云: “其(周密)著述之富,则有《绝妙好辞》《癸辛杂志》《武林旧事》……《乾淳起居注》《乾淳岁时记》《武林市肆记》《湖山胜概》若干种。”[8]5石岩写此序时为元至顺三年(1332),距离周密去世仅三十余年。可见当时就将《乾淳起居注》《乾淳岁时记》《武林市肆记》《湖山胜概》同《武林旧事》并列为书名并在世上流传。书中的篇章被单独裁出成书的原因,除了《武林旧事》的题材因素外,还有就是友人的传抄。周密在卷七的序中说: “此书丛脞无足言,然间有典章一二可观,故好事者或取之,然遗阙故不少也。”[2]195说明该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补充新材料,并加以修订而成,在此过程中,书就被“好事者”传抄出去。这里的“好事者”,主要就是周密的友人。版本系统的驳杂和书中文本被单篇裁出成书,与友人的传抄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宋诸多有关临安题材的笔记中,少有如《武林旧事》能如此动人心绪者。究其原因有三: 一为周密所处之特殊时代环境。周密亲身经历了时代的剧变,历之切,痛愈深,感人亦愈深。二是典雅优美的文风。此书文笔优美活泼而又委婉深曲。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皆深深地寄寓于文中,不尽言而情深味浓。三是周密的特殊身份。在宋末元初的江南文坛,周密是最为突出的一位,兼具词人、诗人、笔记大家、文物收藏家与鉴赏家等多重身份,俨然江南文坛的领袖。他交游众多,影响颇广,致使《武林旧事》在没有完全成书之时,就被好友借阅并传播。版本的复杂与流传的广泛,正说明了文中的临安抒写感染和打动着周密周围的友人。
在《武林旧事》问世约三百五十年后,时任明廷工部主事的朱廷焕采辑《西湖志》《鹤林玉露》《容斋随笔》《辍耕录》等书,补成《增补武林旧事》,共八卷,详述南宋临安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增补原书阙略。关于此书的撰述主旨,朱廷焕在序中云: “觉(杭州)湖山之美逾于昔闻,而繁侈之风竞胜未已。”“补入诗什,以存风流。末志灾伤,使知靡侈过甚,足招天谴。有汴京之乐,即有靖康之悲; 有武林之侈,即有厓山之变。运若循环,后人不昧此理。持以节俭,使武林常为乐邦可也。”[9]可知,此书乃补缀诸书而成。为其有感于明末杭人奢侈之风犹盛,遂作是书,存借古鉴今之意,表家国兴亡之忧。周密与朱廷焕的生活时代,一为宋末,一为明末,都曾在杭城生活,经历了末世繁华,对杭城风俗再熟悉不过。对奢侈世风的批评和对国运不济的忧虑,串起了他们共同的心绪。在朱廷焕的笔下,杭州也成了表达家国之忧的意象载体,体现了《武林旧事》对他的影响。
与朱廷焕同时的张岱,著有笔记小品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亦为追寻昔日繁华,寄寓故国之思。前者写南京,后者写杭州。南京为明朝首都,而杭州则是张岱长期生活的地方。两座城市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兵火战乱,生灵涂炭,到处是断垣残壁,成为张岱内心抹不去的伤痛。
张岱出身簪缨望族,前半生是在繁华、享乐中度过的。“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中年时,遭历了明亡之变。“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秩,缺砚一方而矣。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10]373国破家亡后,张岱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后来他也参加过抗清斗争,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遂隐姓埋名,以遗民自居。早年富贵、优雅的生活已如过眼烟云,经过血雨腥风的洗劫之后,只剩下了不堪回首的记忆。“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10]196晚年的张岱,醉情于追忆性笔记小品文的创作。“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虽间涉游戏三昧,而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恣,几令读者心目俱眩,亦异才也。”[10]503张岱创作笔记小品文,亦为寄寓身世之感,非为游记之类。“但张宗子(岱)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11]周密与张岱的生活经历相似,都出身书香门第,经历了繁华盛世,又遭遇了亡国之变,隐居于异族统治之下。晚年都专注于笔记的创作,尤其是以杭城为中心,记录故国文明。从这些方面看,周密的笔记对张岱笔记小品文的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南宋笔记中的临安意象,除了对后世笔记中的杭州意象有重要影响外,对后世小说中的西湖抒写也有着影响。以明末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为例,其中的不少故事即来源于南宋笔记。如第一卷吴越王事,取材于《钱塘遗事》卷一“梦吴越王取故地”条; 第二卷高宗游酒肆改《风入松》事,取材于《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 第三卷甄龙友两重遇圣事,取材于《齐东野语》卷十三“甄云卿”条; 第五卷李凤娘妒悍事,取材于《齐东野语》卷十一“慈懿李后”条; 第二十卷曹泳事,取材于《齐东野语》卷十一“曹泳”条。从这些故事来源即可看出南宋笔记对后世小说中西湖抒写的影响。
从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到明末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张岱《西湖梦寻》以及相关的西湖小说,对杭州的抒写成为贯穿其中的线索。在这些杭州抒写中,既有忆念中的故都临安,也有现实生活中的都市杭州。空间和时间的交织与融合、物象与意象的转换与更替,使临安意象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成为南宋及后世的文人们寄托家国之思、抒发兴衰之慨的重要载体,具有了政治寄寓的功能。同时,临安意象也成为杭州的都市文化影像,承载了一定的文化传播功能,因而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