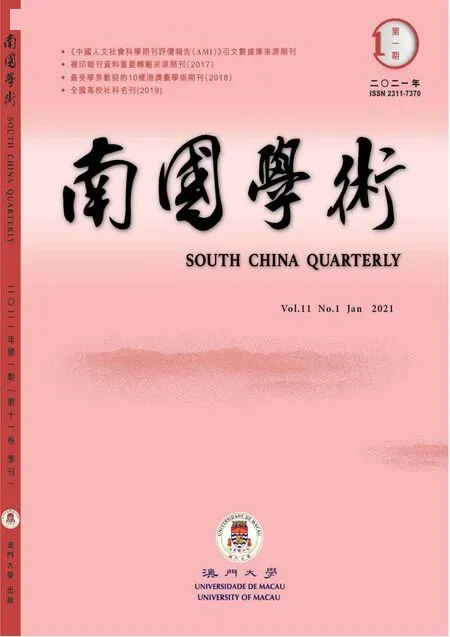詩人與考古:汲冢書對陶淵明新觀念的影
鍾書林
[關鍵詞] 汲冢書 陶淵明 《竹書紀年》 《讀〈山海經〉》
引言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此材料,以研求新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録序”,《陳寅恪集• 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266頁。陳先生從“古今學術發展之通義”的高度,強調每一個時代的學術進步,“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但是,對古代文士來說,因缺乏現代意義上的考古新發現,能夠預流者寥寥,而東晉的陶淵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潛,別號五柳先生)則是一個例外。由於他對西晉發現並整理出的“汲冢書”産生了濃厚興趣,不僅導致他的新政治觀和歷史觀的形成,也影響了其後的文學創作。
關於汲冢書的出土時間,大致有三說:一是房玄齡等《晉書• 武帝紀》記載,說是晉武帝咸寧五年(279);二是衛恒《四體書勢》、王隱《晉書• 束皙傳》、房玄齡等《晉書• 律曆志》的記載,說是晉武帝太康元年(280);三是房玄齡等《晉書• 束皙傳》又說,是太康二年(281)。今人朱希祖研究判定:“汲冢書之出土在咸寧五年(279)十月,藏於秘書監在太康元年(280)正月,命官校理在太康二年(281)春。”②朱希祖:《汲冢書考》(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37頁。經學者編次整理的“汲冢書”有十六部、七十五卷,影響最大的當數《紀年》十三篇和《穆天子傳》五篇。《紀年》又稱《汲冢竹書》《汲冢紀年》,一般稱爲《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五篇與《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由郭璞作註,形成了流傳至今的《穆天子傳》六篇。陶淵明辭官歸隱園田之後,閱讀的正是這批郭璞作註的《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汲冢書。
一 陶淵明閱讀汲冢書的緣
汲冢書從咸寧五年(279)發現出土,至永康元年(300)校理完工,前後經歷二十餘年,先後有荀勖、和嶠、華廙、摯虞、衛恒、賈謐、束皙等十七位重臣和博學之士,經由兩代帝王,雖然時值八王亂世動蕩,卻不減時人的參與熱忱。衛恒遇難後,束皙接手了他的工作,並對之前和嶠的整理提出異議,將《竹書紀年》重新整理校正,由此形成和嶠初定本與束皙重定本,後人將二本合校,形成《竹書異同》一卷。而當時的東萊太守王庭堅對束皙的整理成果也提出異議,由此兩人展開論辯,不幸王庭堅又亡逝,散騎侍郎潘滔便要求王接出面,解答王庭堅、束皙的論爭。王接詳辨兩家的得失,結論允當,得到摯虞、謝衡的認可。
和嶠、束皙等人的整理成果,不僅被當世的學者運用在學術研究之中,如司馬彪根據《竹書紀年》糾繆譙周《古史考》一百二十二事;而且持續向下延續,直至唐代,諸如,酈道元撰《水經註》稱引《竹書紀年》達九十三次,范曄直接將《竹書紀年》融入《後漢書》編撰中,裴駰《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均徵引了汲冢書的文獻。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下,身處東晉的陶淵明也頗受影響。根據與陶淵明同時代的王隱在其私撰的《晉書• 束皙傳》中記載:“《穆天子傳》,世間遍多。”陶淵明在《讀〈山海經〉》其一稱“泛覽周王傳”,周王傳即《穆天子傳》,反映出陶淵明對汲冢書的關注。
陶淵明關注汲冢書,還與他同束皙有着深厚的淵源有關。束皙是疎廣的後人,而疎廣正是陶淵明心儀的高士。日本學者上田武在比較束皙與陶淵明時說:“束皙是漢代疎廣的直系子孫,對於陶淵明來說衹不過是一種奇緣罷了。但是我們不能懷疑,這個奇緣成了陶淵明文學和思想迅速接近束皙的起動力。”③[日]上田武:“淵明和束皙”,《第二屆中日學者陶淵明學術研討會文集》(九江:《九江師專學報》編輯部,2001),第36頁。房玄齡等《晉書• 束皙傳》記載:“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而對於疎廣辭官隱居一事,陶淵明寄託了很深的情感,專門作有《詠二疎》詩以言志。清人邱嘉穗在《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評論說:“詠二疎去位,所以自況其辭彭澤而歸田也。……淵明仕彭澤而歸,亦與二疎同,故託以見意。”陶淵明筆下疎廣叔侄的“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與他的《歸去來兮辭》也頗有幾分相似。《詠二疎》開篇“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①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383頁。以下詩文不作註時,皆見此書。,讚譽他們功成身退,而希冀以功成身退的方式踐行“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功業正是陶淵明一生的理想。後世多將陶淵明與魯仲連、張良等功成身退的人物比附在一起,原因也即在此。
陶淵明、束皙性情相似,皆沉靜恬退,不慕榮利。房玄齡等《晉書• 束皙傳》稱其“性沉退,不慕榮利”,並創作《玄居釋》表達自己的志向。而陶淵明也愛靜,時常流露於詩文,如《時運》詩“我愛其靜”,《與子儼等疏》“偶愛閑靜”,被時人稱之爲“自況”的《五柳先生傳》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靖,通“靜”。清代宋大樽《茗香詩論》說:“顧晉有陶靖節之高趣,入宋終身不仕;又有束晳之沉退,張翰之慮禍,張協之屏居草澤。”即道出了陶淵明與束皙等人相似的性情。兩人皆好讀書,博學多聞。房玄齡等《晉書• 束皙傳》稱束皙“博學多聞”“才學博通”,“詳覽載籍,多識舊章”,並藉博士曹志之口說:“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陶淵明也好讀書,常在詩文中提及讀書的樂趣,如《五柳先生傳》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飲酒》詩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朱光潛稱他:“讀各家的書,和各人物接觸,在無形中受他們的影響,像蜂兒採花釀蜜,把所吸收的不同的東西融會成他的整個心靈。”②朱光潛:“陶淵明”,《詩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第237頁。所以,在博聞、好學上,他與束皙算得上是同趣味的。
束皙祖上自漢宣帝時疎廣隱居以來,歷世不顯;陶淵明祖上自漢景帝時陶青任宰相以至陶侃,亦歷世不顯,而陶侃,史稱“望非世族,俗異諸華”,雖然以軍功顯世,可仍然被望族戲稱“溪狗”。③東晉名臣溫嶠戲稱陶侃為“溪狗”。因陶侃出身不顯貴,故稱。語見《世說新語• 容止》:“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於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兩晉的社會現實,正如與束皙同時代的左思《詠史詩》所叱責:“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與左思一樣,束皙在《九品議》中尖銳地指出:“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若悉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鄉議則必有損。”陶淵明雖然沒有公開地向閥閱制度表態,但他“所有的田園詩,無不錐處囊中;其刺向虛僞門閥官場的鋒芒,無不脫穎而出。他是站在敵視喧囂官場的角度,描摹田園的寧靜;從厭惡上層社會的虛僞,讚美農夫的真淳”④魏耕原:《陶淵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69—70頁。。
在創作題材上,他們都創作了歌咏貧士的作品,託貧言志,反襯出追逐利祿的社會世風的醜態。束皙《貧家賦》以略帶誇張的筆法,敍述“余”之貧困生活的體驗。徐公持認爲,“余”雖“遭家之轗軻”,而“不以貧爲耻,顯示出在貧富問題上的坦然態度”;又言,“既有妻妾,當非真正貧家”。⑤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第318頁。若如此,則此篇當是作者想象虛構之詞。而陶淵明《自祭文》《擬挽歌詩三首》《形影神》等作品,亦多擅長想象虛構之景;在述貧上,更是行家裏手,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飲酒二十首》之十六“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都是表現“饑凍交至、日夜不寧的百般煎熬掙扎”很有名的句子。所幸的是,兩人雖然多感慨憂慮,但質性自然、樂天知命,“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成爲束皙、陶淵明一生的最好寫照。
此外,兩人都被朝廷聘爲佐著作郎,都有較高的作史才能。房玄齡等《晉書• 束皙傳》記載,束皙的才幹被張華所看重,“華召皙爲掾……轉佐著作郎,撰《晉書• 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又說:“皙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至於陶淵明,《宋書• 陶潛傳》記述:“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房玄齡等《晉書• 陶潛傳》也記載,陶淵明辭彭澤令後,“頃之,徵著作郎,不就”。
由上可以看出,無論是性情還是時人評價,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史學才華,陶淵明與束皙的相似點很多。正是兩人之間的淵源關係,促進了陶淵明與束皙及其“汲冢書”的密切關聯,剛出土不久的《穆天子傳》與郭璞註的《山海經》進入陶淵明的視野就成爲必然。
二 汲冢書對陶淵明新政治觀的影
(一)陶淵明《讀〈山海經〉》詩與汲冢書的關聯
陶淵明《讀〈山海經〉》其一云:“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云:“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之民發古冢所獲書也。”根據朱希祖的研究,《穆天子傳》分爲荀勖本和束皙本。荀勖的整理本,定名《穆天子傳》;束皙的整理本,遵從出土竹書內容,定名《周王遊行》。陶淵明此處不稱“穆天子”“穆王傳”,而稱“周王傳”,說明閱讀的是束皙整理本。“流觀山海圖”,則指郭璞撰《山海經註》及《圖贊》。《隋書• 經籍志》記載:“《穆天子傳》,六卷。”註云:“汲冢書,郭璞註。”可知陶淵明所讀的《山海經》《穆天子傳》,均爲郭璞所註。
不過,陶淵明此時所讀的不僅僅是《山海經》《穆天子傳》,還應有與《穆天子傳》同時出土的《竹書紀年》。衹是在《讀〈山海經〉》的標題、詩句中,無法將三者都體現出來。因爲,自“汲冢書”出土後,《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在南北朝時期,同在一起。酈道元《水經註• 昆侖山》云:“《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將三者置於一起論述。郭璞在《註山海經敍》中,多次提及《山海經》對《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的依賴關係。①〔晉〕郭璞,“註山海經敍”,袁珂《山海經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478—479頁。同時,郭璞註《山海經》《穆天子傳》時,多以《竹書紀年》爲證,形成三位一體的系統布局。對此,龔鵬程說道:“陶淵明所讀的《山海經》爲東晉郭璞所批註的。郭璞批註《山海經》時用《竹書紀年》印證周穆王西征的記載,並批評從前的儒者未能考及《竹書》,不能稱爲‘通識瑰儒’。”②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上冊,第140頁。他正是看到這一點,由此闡述了陶淵明對《竹書紀年》的重視程度。
《山海經》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一起流行傳播,在陶淵明《讀〈山海經〉》中也有一定的體現。例如,《讀〈山海經〉》第二首咏玉山、王母,“高酣發新謠”;第三首咏玄圃,“恨不及周穆”;第四首咏丹木,“見重我軒皇”;第五首咏青鳥,“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等等。這四首詩歌中涉及的內容,都可以在《竹書紀年》中找到確鑿的史料出處。
(二)陶淵明新政治觀在《讀〈山海經〉》中的體現
陶淵明的《讀〈山海經〉》創作很特別,不僅是詩本身的“好奇”,讀奇書,用奇光、奇鳥、奇山、奇木等瑰奇意象,而且關於這首詩的創作時間,多數學者認爲是在易代之後。明代黃文煥《陶詩析義》說:“愴然於易代之後,有不堪措足之悲焉。”所謂易代,是指公元420年,劉裕代晉自立,改國號爲宋、年號爲永初,時年陶淵明五十六歲。今人楊勇認爲,《讀〈山海經〉》第一首有“孟夏草木長”句,則詩當作於刘裕弑零陵王後一年,即永初三年(422)、陶淵明五十八歲時。③楊勇:“陶淵明年譜匯訂”,《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460頁。丁晏《陶靖節年譜》將該詩繫於永初二年(421)陶淵明五十七歲時作。他說:“是年,恭帝被弑。《述酒》詩‘山陽歸下國’,蓋以魏弑山陽公喻恭帝。……《讀〈山海經〉》詩‘巨猾肆威暴,欽駓違帝旨。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痛斥劉裕,以精衛、刑天自喻。”④丁晏:“陶靖節年譜”,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55頁。
在晉、宋易代之際,陶淵明的作品很少,自稱多年“不復爲文”,而忽然寫下《讀〈山海經〉》十三首,雖然不能肯定每一篇都有政治寄託,都作爲政治詩來解①例如,袁行霈針對《夸父》一首說:“余以爲,此篇乃耕種之餘,流觀之間,隨手記錄,敷衍成詩,未必有政治寄託。如作謎語觀之,求之愈深,離之愈遠矣。”(《陶渊明集笺註》,第410頁),但作爲組詩,它的整體寄意仍是值得關注的。從組詩的結構與創作意圖來看,這十三首詩歌主要流露出兩種政治情懷。
第一,超然塵外,欲逃離現實世界。黃文煥《陶詩析義》說:“十三首中,初首爲總冒,末爲總結,餘皆分詠‘玉臺’‘玄圃’‘丹木’,超然作俗外之想,與古帝之思。”針對組詩中一些流露心迹的重要詩句,吳瞻泰指出:“‘寧效俗中言’,是欲聽王母之謠。‘在世無所須’,是欲索王母之食。總是眼前苦遭俗物聒,頻爲出世之想,奇思異趣,超超玄著矣。”
所以,有不少前賢將組詩與屈原的《遠遊》相類比,強調陶淵明的悲憤之心。典型如王應麟說:“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心,可爲流涕也。”③〔宋〕王應麟:《困學紀聞• 評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917頁。陶淵明恨不得離開當世,仿效屈原“遠遊”,隨黃帝仙登,從周穆王西遊,通過青鳥見到身處世外的西王母。組詩由此流露出的情感,與《桃花源記》的“仙遊”塵外的境界頗爲相似。這種情感,與《宋書• 陶淵明傳》“(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是大體相一致的。自歸隱以後,陶淵明不再書晉氏年號,以“明眼人”洞察劉裕的野心。
第二,從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角度,提出“帝者慎用才”的忠告,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在《讀〈山海經〉》的十三首詩中,如果說其他幾首是否存在政治寄託還存有分歧的話,那麽,第十二、十三兩首暗寓寄託是毫無疑義的。以第十三首爲例,詩云:“岩岩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開篇即擺出觀點“帝者慎用才”,接着用兩個歷史典故加以闡述。其一是“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上下兩句,自問自答。大意是說,帝堯流放共工而殺鯀,是由於聽從舜(名重華)的言論。第二個典故“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詳見《管子• 小稱》。意思是說,管仲晚年曾經向齊桓公建言,讓他疏遠易牙等四人,結果反被桓公猜疑,但等桓公臨死醒悟時,一切都晚了,落得“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能得”的自絕地步。由此,“帝者慎用才”的論斷自然得出。
也有學者認爲,既然詩題曰“《讀〈山海經〉》”,那就肯定源自《山海經》。但是,《山海經• 海外北經》記載:“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溪。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山海經• 海內經》記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也就是說,其一,犯過失的是相柳氏,不是共工,何流放之有?其二,殺死鯀的是祝融,不是舜。可見,陶淵明此處運用的典故,不是從《山海經》中來的。由於陶淵明同步閱讀的是《山海經》《穆天子傳》《竹書紀年》三部書,那麽,衹有一種可能,是從《竹書紀年》來的。
細考《竹書紀年》,有兩點值得關注。
首先,《竹書紀年》記載,鯀爲顓頊之子。《山海經• 大荒西經》註引《竹書紀年》:“《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史記• 夏本紀》也說:“鯀之父,曰帝顓頊。”同時,《史記• 五帝本紀》又有讙兜、共工、鯀、三苗“四凶”說。即讙(歡)兜爲帝鴻氏之子,共工爲少皞氏之子,鯀爲顓頊氏之子,三苗爲縉云氏(炎帝之苗裔)之子。而據張守節《史記正義》,《史記》說法源自《左傳》。又,《尚書• 舜典》記載:“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其次,《竹書紀年》中關於舜的記載,與儒家宣傳的形象有別。《史記• 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廣弘明集》卷十一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引《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方詩銘、王修齡下案語云:“劉知幾《史通• 疑古》兩引‘舜放堯於平陽’,一云出《汲冢瑣語》,一云出《汲冢書》。其云出《汲冢書》者尚有‘益爲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三事,據《晉書• 束皙傳》及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此三事皆出《紀年》,則‘舜放堯於平陽’一條當亦爲《紀年》之文。”①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第64頁。由《竹書紀年》記載看,堯在晚年遭到舜的囚禁,並被奪取了帝位,導致父子不能相見。如此說來,被儒家經典美化的堯、舜禪讓制度,在《竹書紀年》中衹是血腥與暴力而已。正是受到《竹書紀年》記載的影響,陶淵明對儒家美化的堯、舜禪讓制度有了新的理解。
瞭解了《竹書紀年》中“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等相關記載後,也就明白陶淵明此詩的深意了:帝堯聽信舜的話,流放了共工,殺掉了鯀,最後自己晚年却被舜囚禁,連父子都不能相見;齊桓公聽信易牙等四人,晚年被他們囚禁,飲食困難,餓死病榻。帝堯、齊桓公,均是一代明君,最終都落得個囚禁自絕的下場。全詩末句“當復何及哉”,既是對齊桓公事的總結,也是對帝堯事的總結。黃文煥《陶詩析義》:“‘當復何及哉’一語,大聲哀號,哭世之淚無窮。”深得陶詩深意。陶詩運用的兩個典故,雖然對象不同,但得到的結論是一樣的:“帝者慎用才。”詩歌通過帝堯、齊桓公事“藉題刺世”,影射東晉被劉裕篡弑之事。
但是,詩歌似乎也不止於此。像帝堯、齊桓公這樣的一代英明之主,尚且不免遭寵臣囚禁而王祚移,遑論帝王中的平庸者了。所以,清人馬璞看破了這一點,他說:“此《讀〈山海經〉》十三首,十二首皆出第一首內‘俯仰終宇宙’一語,故十二首皆即以《山海》所載之事,慨慷後世之事,而晉、宋之事在其中,並不專言晉、宋也。淵明之詩豈易讀乎!”②〔清〕馬璞:“陶詩本義”,《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第310頁。這就是陶詩的深度。
三 陶淵明閱讀汲冢書後的新歷史觀
汲冢書特別是《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書的出土,大大豐富了古史的文獻記載與史學觀念,晉代學者臣瓚、徐廣、司馬彪等都利用《竹書紀年》來研究古史,而同處晉代的陶淵明對於《竹書紀年》的閱讀,則是結合晉、宋易代的殘酷現實和自身的感悟,形成了他的新歷史觀。
汲冢《竹書紀年》“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這一記載,與儒家典籍中堯、舜禪讓的仁政學說大相徑庭。這對飽受《詩》《書》熏陶的陶淵明來說,是很難接受的。面對同樣這一情形,有些人可能乾脆就不去相信它,或者竭力反對它,但生性好奇的陶淵明在驚訝好奇之後,隨之而來是他結合漢、晉以來的歷史和晉、宋易代的現實,與汲冢《竹書紀年》、儒家美化的堯、舜禪讓仁政學說等,相互碰撞、融合,進而一種新的歷史觀在他的頭腦中形成,並訴諸詩文表現出來。
在汲冢《竹書紀年》的記載中,儒家典籍中美化甚或誇飾的堯、舜、禹的事迹及其禪讓的仁政學說,都被徹底摧毀。除了上文所引外,還有其他記載,例如:《蘇鶚演義》引《汲冢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舜禪位後,爲禹王之。”《史記• 高祖本紀》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史通• 疑古》:“《汲冢書》云:益爲啓所誅。”《史通雜說》引《竹書紀年》:“后啓殺益。”《晉書• 束皙傳》:“(《紀年》)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③以上史例,參見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6—8頁;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第2、63—65頁。這些記載反映出,在權力的交接中,充滿了血腥的篡逆和殺戮。特別是“舜篡堯位”的一個“篡”字,將儒家美化的所謂的堯、舜禪讓仁政外衣剝去。
或許有讀者懷疑汲冢《竹書紀年》記載的真實性,但這些記載不是個別出現,而是多次地反復出現,更重要的是,汲冢《竹書紀年》的一些記載,與先秦的非儒家典籍也可以相互印證。例如,關於舜囚堯於平陽、逼堯讓帝位等事,《韓非子• 說疑》云:“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從陶淵明《命子詩》中“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來看,他是以堯、丹朱的後世子孫而自居的。因此,他對堯、丹朱的情感,不僅源於儒家經典的熏陶,還帶有濃厚的宗族血緣紐帶。而當他通過閱讀汲冢《竹書紀年》,知曉“舜篡堯位”等記載後,在心中將會激起怎樣的一種情感?可以想見,他對舜及其有關所謂堯、舜禪讓記載的反感。或許,他也感受到孟子以降儒家典籍記載的不實。加之,他又身處晉、宋易代的敏感時期,更能領悟到所謂“禪位”就是篡位的實質。置身於歷史與現實之間,陶淵明由此對古史有了新的認識。
放眼堯、舜、禹三代,所謂的禪位就是篡位,即對前代君王或囚或殺。往後,是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再往後,漢、晉所謂的禪位更是如此。西漢末年,王莽禪位;東漢末年,漢獻帝禪位於魏王曹丕,被廢爲山陽公;曹魏末年,少帝曹奂“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①〔晉〕陳壽:《三國志• 魏書• 三少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54頁。。到了晉代,篡臣紛起,禪位頻頻。先是桓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②〔唐〕房玄齡 等:《晉書• 桓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2579頁。,欲謀作亂。繼而桓溫之子桓玄終於篡位稱帝,“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③〔唐〕房玄齡 等:《晉書• 桓玄傳》,第2594頁。。最後是劉裕,晉代皇帝徹底禪位,走向終亡。房玄齡等《晉書• 恭帝紀》記載:
(元熙)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於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於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
一年後,晉恭帝即被劉裕弑殺。
縱觀漢、晉之間血腥的篡逆與弑殺,無一例外地以堯、舜禪位作爲他們的合理依據,並盡情地美化、頌揚。例如,《三國志• 魏書• 文帝紀》記述漢、魏禪位:
漢獻帝詔冊說:“諮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裴松之註引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魏王。”)
又如,《晉書• 武帝紀》記述魏、晉禪位: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於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於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於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
再如,《宋書• 武帝紀》記述晉、宋禪位:
晉帝禪位於王,詔曰:“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陶鈞三極,統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來尚矣。……予其遜位別宮,歸禪於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後來的宋禪位於齊,齊又禪位於梁,梁又禪位於陳,大體情形都是如此。由此,導致整個魏晉南北朝,一連幾個世紀,篡逆驟起,政權更替頻頻。身處漢、晉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陶淵明,對以堯、舜禪位爲幌子的篡逆者行徑,本已認識、感受頗深,而值此晉、宋易代之際,他閱讀了汲冢《竹書紀年》中舜囚堯逼位的記載後,讓他拋弃了“總角聞道”時的歷史觀,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歷史觀。
結語
陶淵明思想觀念的變化,以閱讀西晉出土的汲冢書爲分水嶺,呈現出前後的迥然不同。陶淵明早年對君主的看法,主要是受到儒家六經觀念的影響;晚年的變化,主要是受到《竹書紀年》等汲冢書的影響,對儒家樂道的堯、舜禪位之說産生懷疑,由此改變了所有之前對古史的看法,轉而追求一種迷戀上古、高蹈世外的理想。在陶淵明一些早期作品中,他接受儒家歷史觀的影響,對舜等古帝王充滿着一種頌讚與嚮往。而在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中,從傳說的上古帝王一直到唐堯,多所提及,表達嚮往之意,而對於虞舜以後的帝王一般極少提到。
他在《贈羊長史》中說:“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此處的“古人書”,即指汲冢書《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通過閱讀《竹書紀年》等“古人書”,讓他瞭解到漢、晉以來的名爲禪位實即篡逆的虛僞政治,並不僅僅起源於漢,而是發端於舜。被儒家美化的堯舜禪位,竟是舜囚堯而自篡的。堯舜禪讓的僞說,讓他感觸到自舜以降禪讓世風的虛僞。所以,他在《桃花源記》中着意強調“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否定漢、晉以來的歷史。在“淳風日盡”的世風之下,他效仿先賢隱逸成爲最希冀的人生快事。不管是《讀〈山海經〉》中的“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還是他筆下虛構的仙境世界“桃花源”,都成爲他新歷史觀的寫照,他的理想和寄託正由此而來。
其《桃花源詩》:“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按典籍記載,中國“紀曆志”始於舜,即堯禪位、舜監國時期。《尚書• 堯典》記載:“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帝曰:‘諮!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後世典籍多將其歸於唐堯時期,而按《尚書》記載可知,雖然仍是堯的年號,但當時堯将遜位,政由舜出。所以,“紀曆志”實際是始於舜的。“雖無紀曆志”,這也正是陶淵明所特意申明、表達否定的緣由。由此可知,其“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表達的歷史觀念與“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實質一樣,嚮往唐堯以前的上古帝王,在思想上否定自虞舜禪位以下的篡逆惡史,直至“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但這樣的思想絕不是所謂“無君論”,他自謂是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羲皇上人,嚮往風氣淳真的上古時代,也意在否定虞舜以降的禪讓虛僞之風。所有這些,實質上與他閱讀汲冢書後所産生的新觀念有莫大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