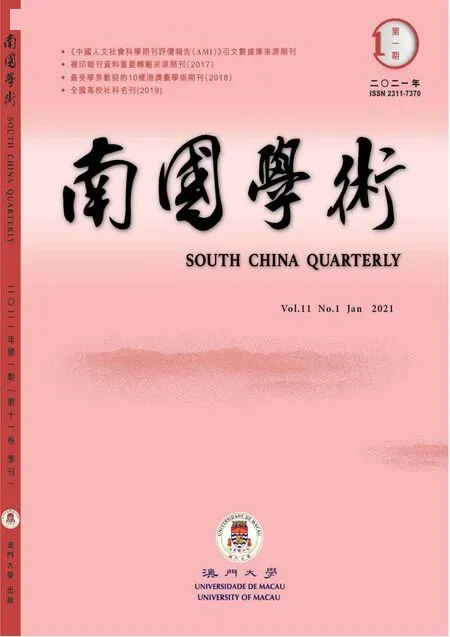“網絡生命體”視域下的網絡治理術
闕天舒
[關鍵詞] 虛擬生命 生命政治 網絡生命體 治理術
引言:網絡空間中的虛擬生命
看過科幻小說《三體》的讀者或許會記得雲天明,他在生命走向盡頭的時候參與了“階梯計劃”。經過程心的推薦,他通過了“行星防禦理事會戰略情報局”(PIA)的甄選和測試,同意其將自己的大腦送入宇宙。後來,三體艦隊捕獲到他的大腦並運用先進技術克隆出新的雲天明,繼而在與地球接觸中爲人類帶來三個隱藏重要情報的童話《王國的新畫師》《饕餮海》《深水王子》,這些童話故事裏面的信息讓人類對三體人和宇宙有了更多的認識和瞭解。而這個“階梯計劃”的過程,也就是人類在技術發展下帶來的生命主體延伸。因爲,在物理世界,人的行爲和其產生的影響都會局限在一定的時空,並且不能脫離個體的身體而存在。即在當下的這個具體空間中,“我”衹是實現了“我的”意志和行爲結果的統一。①藍江:“5G、數字在場與萬物互聯——通信技術變革的哲學效應”,《探索與爭鳴》9(2019):37—40。然而,在《三體》中,人類送出雲天明的大腦(相當於送出一個探測器),這個探測器進入三體世界後又變成一個具有身體的雲天明,他在另一端通過自身的行爲獲得三體人的信任,最終在與地球人的接觸中帶來至關重要的情報。小說中,人類在技術的加持下,思維和行爲在一定程度上脫離身體的限制,並對不同空間的現實世界產生影響(如傳送大腦、克隆生命、編童話故事、探測情報等),人們的行爲和意志在更大的範圍內得到延伸。卡普(E.Kapp,1808—1896)曾論證道:“人體的外形和功能總是作爲人類最理想的客觀存在,當成創造技術的外形和功能的尺度,投影到外部環境。”②喬瑞金、金煥森、管曉剛:《技術哲學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23頁。
在現實中,隨着互聯網和新媒體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身體在當下的言行同樣會對異時空事物產生深刻影響,主體性也得到極大的延伸。“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③[加]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何道寬 譯,第33頁。得益於新媒體的發展,人們可以通過短視頻與世界各地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同時也可以透過網絡“看見”並且感知更多人的生活現實;即使沒有親身經歷,但互聯網的發展讓人們實現了“網絡在場”,能夠跨越時空看見更多的人和事。有了互聯網之後,谷歌眼鏡就可以使用戶看到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這種基於電子版的賽柏格配件所到達的高度,是機械配件無法企及的。此外,新興的“靈境技術”(VR)、人工智能、可穿戴設備等技術正從不同的維度重塑人的身體,通過對人類與世界的相處經驗進行模擬,進行着一場重獲“身體在場”的“奧德賽”之旅。④譚雪芳:“圖形化身、數字孿生與具身性在場:身體——技術關係模式下的傳播新視野”,《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8(2019):64—70。
所以,我們既不能把網絡空間中的各種文字圖像、視頻、音樂、流行語等簡單地看作互聯網場域各種演算法的呈現,也不能僅僅將各種新現象、新事物當作虛擬世界豐富多彩的文化景觀,而是需要通過不同類型的數據和信息去理解互聯網背後“綫民”的生存關係和現實生活。“人們生活的社會空間,事實上是由現代科技所創造的兼具物質主義和虛擬意識流動特徵的雙重技術空間,亦即,人們不僅生活在依賴物質基礎而生存的物理空間,而且還生活在依賴信息傳播而活躍的網絡虛擬空間。”⑤楊嶸均:“論網絡空間國家主權存在的正當性、影響因素與治理策略”,《政治學研究》3(2016):36-53。“這意味着,信息成爲‘新的權力形而上學’。”⑥M.Dillon, J.Reid, “Global Liberal Governance:Biopolitics,Security and War”,Millenniu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2001):41-66.因而,這就需要從哲學存在的視角理解人們在網絡空間的生活狀態,從網絡生命體的內涵來探尋虛擬世界的運轉邏輯。法國思想家梅洛-龐蒂(M.Merleau-Ponty,1908—1961)在《知覺現象學》一書中指出:“我們的生存與世界的聯繫的關鍵就是我們的身體,我們是通過我們的身體行爲在世界上找到讓我們可以棲居的空間。從人類起源開始,人用身體製造了衣服和最簡單的工具,這些工具構成了所謂的文化世界。”⑦[法]莫里斯• 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姜志輝 譯,第194頁。現在,身體不再是人與世界的唯一聯繫,互聯網和新技術的發展使人們與不同時空的人或事發生着聯繫,可以棲居在網絡空間,變成一種特殊存在的網絡生命體。
一 網絡生命體:網絡研究的新議題
(一)理論源起:生命政治與治理術
1978年,福柯(M.Foucault,1926—1984)在法蘭西學院一次關於生命政治的演講中,闡釋了一系列對國家和治理的思考。他對於治理問題的討論,開啓了政治學領域對治理技術的理論與經驗研究,並且重燃了人們對“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研究興趣。①杜月:“製圖術:國家治理研究的一個新視角”,《社會學研究》5(2017):192—217。福柯將這種生命政治界定爲“一種新的權力技術”②米歇爾• 福柯:《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佘碧平 譯,第90頁。,即針對個體生命進行規制的治理術。進入新世紀以後,生命政治已然從政治哲學領域擴展到國家治理更廣泛的領域,其內涵和意蘊也發生了諸多流變,治理術也不再是對個體生命的規訓和懲罰,並且開啓了人們對網絡生態治理和網絡生命體的思辨性研究。
如果追根溯源的話,“生命政治”概念興起於19世紀末,由三股強大思潮交織而成,即以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爲代表的形而上學的生命哲學,以斯賓格勒(O.A.G.Spengler,1880—1936)爲代表的歷史哲學的生命哲學,以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爲代表的倫理性的生命哲學。③吳冠軍:“‘生命政治’論的隱秘綫索:一個思想史的考察”,《教學與研究》1(2015):53—62。受斯賓格勒思想的影響,科耶倫(R.Kjellen,1864—1922)把“生命體”概念引入國家領域,從一種生命的有機形態來理解國家的發展進程和運行邏輯。它“同個體一樣真實,衹是大得驚人,並且在其發展進程中遠比個體更爲強壯有力”④T.Lemke,M.Casper,L.Moor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然而,從譜系學來說,生命政治重新進入公衆視野並在政治領域產生巨大影響則要歸功於福柯。福柯指出,17—18世紀,隨着主權理論和統計技術的發展,個體生命日益變爲權力和治理的新對象,政治權力也是圍繞着生命出生、死亡、疾病、福利等一系列領域而展開和運轉,“一個‘生命權力’的時代開始”。⑤[意]吉奧喬• 阿甘本:《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趙文 譯,第90頁。基於此,福柯發展出一套與人口有關的“治理技藝”,以改善國家權力的配置和組織。因爲,人口現象具有一定的穩定性,有一定的規律可循,通過觀察可以識別出來,這就爲人口統計學等知識工具的出現打開了方便之門。⑥[法]米歇爾• 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錢翰、陳曉徑 譯,第56—60頁。然而,新媒介技術的高歌猛進又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管中窺豹的契機,周遭的媒介環境將議題觸角伸向了生命政治。⑦駱世查:“媒介環境即生命政治——數字時代的‘有機體’話語與主體追問”,《新聞界》6(2018):73—82。
生命政治在國家治理和網絡治理領域的演變新動向,就是“網絡生命體”。它是對傳統生命政治和當前國家治理場域的一種深層次隱喻,寓意了政府等公共主體將網絡場域虛擬的數字或存在具象爲現實社會的生命體,並以此爲參照系,構成治理網絡和日常社會生活的實踐。人們當前所處的社會,正是通過資本流動、信息流動、技術流動以及影像、聲音、象徵的流動而建構起來的。⑧楊嶸均:“網絡空間政治安全的國家責任與國家治理”,《政治學研究》4(2020):38—51。正如布爾迪厄(P.Bourdieu,1930—2002)的場域理論,“從分析角度看,一個場也許可以被定義爲由不同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構成的一個網絡”⑨[法]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包亞明 譯,第142頁。。從這個意義上看,網絡生命體可以廣泛被用來對網絡場域的各種現象和關係進行分析。進而言之,它是以現實生命體爲對象,以治理網絡空間爲目的,以政府爲代表構成公共主體,以現代化技術爲核心。作爲一種全新的網絡治理研究視角,它能夠讓人們更加深刻地認知和理解現階段國家進行網絡生態治理的邏輯轉變、系統思維、創新動力以及相應的治理效果。因爲,科學越發展,人類生存與環境的關係對立越需要二者之間進行深層對話,對話途徑最終會歸結到政治,而生命政治可能成爲一個很好的路徑。⑩劉華軍:“生命科學與政治學交叉研究的三個路徑”,《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017):45—48。
(二)對“網絡生命體”本質的理解
如果將互聯網看作是一個由技術、文化知識、自然秩序構成生態系統和生命體,那它必然是一個在不斷變化中前進的有機整體。而網絡生命體的意涵在於,將生物學、政治哲學、行政學的概念與生態系統的知識應用到國家治理、網絡治理領域,使得互聯網不再僅僅是抽象的虛擬空間,或是政治家眼中的政治權力和治理術不斷延展的規制範圍。將網絡生態和網絡生命體納入網絡治理的研究對象,能夠使公衆對網絡世界的認知提升到更廣闊的自然生態系統當中;而堅持以人爲本對網絡進行調節,纔能更好地保持網絡生態系統的有序運轉和可持續發展。與現實世界一脈相承,有機生命的某些特質在網絡世界無處不在,網絡生命體理論實際上是網絡世界宏觀體系與微觀治理的簡化以及虛擬與現實的互相滲透。
如今,網絡空間治理形勢日益複雜化,各種新理論、新視角層出不窮,但大多數理論和法規並沒有形成完整的網絡生態或網絡生命體理念,而是着眼於某一方面進行即時性表達,如數字生命、媒介環境等。這樣的後果是,對生命有機體和生態系統都會存在認知偏差和技術迷思。
德國思想家恩格斯(F.Engels,1820—1895)曾就“生命”概念從辯證唯物主義角度做過界定:“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本質上就在於這些蛋白體的化學組成部分的不斷的自我更新。”“從蛋白質的主要機能——通過攝食和排泄來進行的新陳代謝中,從蛋白質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導出所有其他最簡單的生命要素:刺激感應性……收縮性……成長的能力……內在的運動。”①[德]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卷,第422—423頁。他的觀點對於研究網絡生命體具有一定的啓發性:既要用微觀的視角來探索有機生命體發展的客觀規律,也要從宏觀層面來理解和觀察生命以及更高層面的生態系統。作爲互聯網來說,它是一種特殊的生命體,不僅需要應用先進的技術和體制機制來尋找網絡空間普通“綫民”日常社會生活的行動軌迹和作用規律(例如,通過大數據進行人群畫像,實現精準治理),還需要從宏觀整體的維度把握網絡世界,通過制度、文化、技術等不同措施實現網絡生態系統各要素之間的和諧共生、有序運作。
基於此,我們可以透過生命的本質來理解“網絡生命體”的內涵。第一,網絡生命體的核心是人。網絡空間的建設和治理要以人爲本,注意尊重人的生物性、社會性、精神性,不斷增強網絡的安全建設、文明建設來保障人的身心健康。衹有保持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的健康環境,纔能吸引更多人在這個空間從事正常的工作、學習、生活以及進行各種娛樂活動,進而提高公衆參與網絡建設的深度與廣度,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共同促進網絡生命體的生機與活力。第二,網絡生命體是一個社會生態系統。網絡空間內部不同民衆和要素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繫,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虛擬世界,但現實世界的“差序格局”同樣會投射到網絡世界中而發生作用。網絡的建設發展需要整體規劃,遵循客觀規律,對網絡空間任一要素或組織的忽視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譬如,網絡空間中存在不同類型的社會心態,這些社會心態背後折射出現實當中的問題難題,如果不注重對那些負面的社會心態及時疏導,就可能會生成更大範圍的危機,此類危機甚至會在物理世界、虛擬世界相互交織和風險疊加。第三,網絡生命體具有生物有機體的基本功能。一方面,網絡生命體在整個網絡生態系統中起着有機調節作用,其信息資源的更新代謝直接影響整個系統的正常運轉。一旦遭受病毒攻擊,網絡生命體就會與有機生命體一樣向外界發出警報;如果未得到有效治療和殺毒,網絡生命體就會“生病罷工”甚至危及系統運行。另一方面,生命的生長發育離不開自然,網絡生命體無論其硬件還是軟件都源自人們的勞動和自然界的物質能量供應,因此,網絡生命體在一定程度上屬於自然生態系統,與自然界相互依存。
總之,網絡生命體是互聯網作爲人類社會科技發展的產物,是在與自然生態系統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資源交換過程中,將人、關係網絡、外部環境都納入其中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統一的且充滿活力的整體。它既包括虛擬世界的個體生命關係存在,也包括圍繞互聯網而存在的複雜社會系統。網絡生命體是對虛擬世界的簡化,各種要素和系統最後作爲一種虛擬生命呈現在公衆面前,公共主體也可以圍繞這種網絡生命體對網絡進行治理和建設;同時,它又是現實社會在虛擬世界的投射,人們透過它可以看見、聽見、感知不同時空的日常生活狀態,也能夠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給更多的人,實現數據的傳輸和網絡在場。
(三)網絡生命體的“結構-功能”意義
從宏觀層面來說,由於網絡生命體是虛擬空間對現實事物的投射,因此,在互聯網當中,人們的一言一行就成爲參與虛擬世界的存在基礎,同時也是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的生命呈現。有學者指出:人們的身體及其行爲,揭示了世界的意義;同時,世界也展現爲屬於人們身體的世界。這是一種辯證的身體,既在做着有機生命的循環運動,也在展現屬於文化和精神層面的東西。①藍江:“數字身體、擬-生命與遊戲生態學——遊戲中的玩家-角色辯證法”,《探索與爭鳴》4(2019):75—83。就這個意義來看,互聯網和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爲人們構建了一個“萬物互聯”的環境。在這一環境中,虛擬與現實之間互相滲透、互爲鏡像。同時,網絡世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也構成了網絡生命體的基本景觀,在網絡建設中發揮着基礎性作用。這些網絡之網絡、系統之系統安穩無聲地運作着,構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超級結構,以一種複雜的、沒有被意識到的方式指揮着現代社會成員的生活。②張成崗:《技術與現代性研究——技術哲學發展的“相互建構論”詮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第49頁。人們可以從“結構—功能”視角來理解網絡生命體之於現實世界的意義。
網絡生命體的結構主要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個複雜系統,彼此間耦合發展。(1)網絡經濟系統。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以及快遞行業的發展爲網絡經濟的繁榮持續注入新的活力和增長點,經濟社會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人工智能、5G基站和工業互聯網等新基建的建設。(2)網絡政治系統。網絡治理和建設,政府公共主體不能缺席。雖然生命政治在網絡研究領域的意蘊已經不再是福柯的現代社會中“監獄”隱喻以及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眼中赤裸生命的“集中營”,但政治權力隨着國家治理現代化逐漸覆蓋到網絡空間。網絡治理乃至國家治理的重點是如何協調網絡空間中不同群體的利益關係,調度公衆參與網絡建設的積極性,保障人民群衆在網絡政治空間當家作主的權利,促進網絡生命體的和諧發展。(3)網絡文化系統。在英國社會學家湯普森(John B.Thompson)看來,文化是體現於象徵形式(包括行動、語言和各種意義的物品)中的意義形式,人們依靠它相互交流並共同具有一些經驗、概念和信仰。③轉引自劉玲:《城市生命體視角》(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第56頁。“綫民”在網絡空間的長期生活互動過程中,一起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網絡文化和精神產品,將網絡生命體的生存環境、狀態和網絡習俗綜合地呈現給現實社會。例如,國內知名的視頻彈幕網站B站,其背後就代表着一種青年群體的文化,展示出年輕人特有的文化活力、創造能力,一旦“破圈”,總會引來好奇和打量,也越發得到社會關注。④龔丹韻:“從B站破圈,看青年文化”,《解放日報》2020-04-20。(4)網絡社會系統。網絡社會可以看作是公衆在網絡經濟、政治、文化各系統互動交往過程中形成關係的總和。這種關係既有現實社會的延伸,如親朋好友之間互加微信、微博或抖音進行聯絡,也有通過娛樂遊戲、貼吧互動以及信息傳播而在虛擬空間重新建立的關係網絡,進而形成不同的圈層或聚集體。可以說,網絡社會構成網絡生命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生命都能在這樣的網絡生態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共同體。
網絡生命體由於不同系統相互聯動和相互依賴,從而形成四個不同的功能。(1)休閑娛樂功能。互聯網的發展給人們帶來豐富多彩的休閑娛樂活動:文化藝術類有電影、音樂、網絡展覽等;休閑設施類有網絡遊戲、“VR”景觀以及電視廣播中的各種娛樂節目等;媒體學習類有視頻課程、電子報紙雜誌、網上圖書館乃至遠端教學;至於輔助人們日常工作生活的硬件、軟件和演算法小程序等也層出不窮。這些既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要,也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2)互動交流功能。社交網絡的興起,將不同時空的人們都納入到一個公共交往空間;在此空間中,人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和利益訴求,可以與志趣相投的人進行互動溝通,現實當中的社會活動和交往在網絡當中同樣能夠有效進行。在網絡化時代,不同思想觀點相互衝擊交融,民衆思想觀念自然而然呈現出多樣化趨勢,不再容易被單一的意識形態影響。⑤闕天舒、方彪:“當前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評估與新型政黨制度的動能釋放”,《探索》5(2019):93—106。譬如,近年來不斷出現的網絡流行語,正是人們在互聯網觀點的表達與情感共振;它代表着某個網絡共同體的集體意見主張。(3)協調整合功能。網絡生命體是相互聯繫、和諧共生的整體,協調網絡生態系統中的不同生命體和要素就顯得尤爲重要。所謂協調整合,就是在網絡建設和網絡治理過程中,把一些分散的生命體通過某種機制措施有機地銜接到一起,從而實現整個網絡生態系統中信息資源共享和協同合作。最典型的例子是,《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正式施行後,各網站平臺認真梳理薄弱環節和漏洞短板,從機制、隊伍、產品、技術等不同維度發力,多措施並舉推動生態治理取得新進展。①倪弋:“《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施行以來——網站平臺自查自糾成效顯著”,《人民日報》2020-06-30。(4)吸收更新功能。網絡生命體是不斷健康成長的有機生命體,需要不斷吸收外界物質和能量來發展壯大自身。這些物質和能量,正是互聯網中常見的信息資源、知識和先進技術。它們如同有機體所需要的水、糧食、新鮮空氣一樣,爲網絡空間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生機和活力來維持其各項運轉,從而吸納更多的“綫民”參與進來。當然,網絡生命體當中的信息和技術等也需要不斷更新,其“新陳代謝”的進度越快,網絡生態中不同結構系統的發展愈加完善,不同要素之間也趨向更加平衡的狀態。這樣,人們在虛擬空間的生存狀態也更加舒適健康。
二 網絡生命體的治理範式
網絡生命體理論對網絡空間的重塑,同時還伴隨着對“治理術”的重新審視。在網絡生命體理論中,有機生命以一種系統性、關係性的客觀存在被嵌入到虛擬空間之中,成爲互聯網世界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質,並由此帶來網絡治理的變革。它不僅在理論層面引導人們以哲學的、動態的視角來理解網絡研究,更是從實踐層面推進一系列針對網絡生命體規制的新動向。首先,網絡治理術有明確的治理對象。有如福柯以具體的人口作爲“治理術”的對象,網絡治理術的對象則是網絡生命體,是圍繞網絡空間生命個體而生成的一系列關係屬性,包括“綫民”的利益訴求、情感心態、互動交往乃至虛擬財產等。其次,網絡治理術以網絡生態建設和秩序治理爲目的,旨在應對智能社會背景下的人與互聯網技術的關係問題:一是探究如何建立一套與網絡技術智能化與人際關係網絡化相配適的網絡治理模式;二是借鑒生命權力爲公共主體賦權,吸納更多的民衆參與網絡治理當中,共同營造一個良好的網絡生態空間和健康宜人的生命空間。再次,網絡治理術最重要的中介變量是技術。誠如統計技術進步會帶來國家對人口繁衍、生存質量、福利政策的關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繁榮同樣促使國家加強對民衆的精準治理,而網絡治理術既需要國家重視對生命個體的關懷,又需要國家加強對技術的價值引導和創新支持。因爲,它“衹是一種手段,對於自身來說,既沒有什麽善,也沒有什麽惡,一切取決於人”②[蘇]格• 姆• 達夫里揚:《技術• 文化• 人》(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薛啓亮、易傑雄 譯,第98頁。。
由於網絡治理變革是一個動態性、系統性的過程,不是對傳統網絡空間治理的徹底解構,而是重塑一個虛擬與現實相互貫通的生命空間,進而形成關注網絡生命體的治理範式,因此,具體而言,新的網絡治理範式——網絡治理術,應當遵循以下治理思路:
1.以開放的生態空間取代封閉的網絡空間。網絡生命體反對傳統治理過程中對網絡空間的假定,認爲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並不存在明確的象限和邊界,因而,網絡治理術應構建一種新型的行動框架,以開放式的生態系統來取代封閉式、場域式的網絡,並將“綫民”的日常生活與生命過程都置於網絡生命體當中。同時,治理主體以更加柔性和複雜性的治理方式來重新塑造網絡生命體的運行秩序。作爲治理單元的網絡生命體,其具有與外界不斷進行信息和能量交換的開放屬性,同時內在地嵌套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個混合的空間單元,顯示出不同的功能特徵和社會關係資源。爲了適應網絡生命體的開放性特點,網絡治理不僅需要通過追求情境性、動態性、協同性、多元性來建設並服務於網絡生命體的治理框架,還呼喚形成健康和諧的生命聯繫,強調將網絡治理術的治理重點聚焦於個體生命的內部、有機生命體之間以及生命體與網絡生態環境間的關係上。一方面,需要加強公共治理主體、參與者和他者之間的關係融合,通過技術提升和服務改善促進更多有機生命的主體延伸與網絡在場。另一方面,不斷消除數字鴻溝和信息孤島,促進信息資源在不同網絡生命體間的傳遞和整合,使更多的民衆接受知識和信息能量的滋養,從而更好地成長發育。這樣的網絡治理,不再是簡單地破除生命個體間的心理距離和時空距離,而是通過一整套的體制、機制、技術、人等要素建設良好的生態空間,打造運轉有序的生態系統,使網絡空間如同綠水青山一樣適宜生命體存在。
2.將“和合共生”確立爲網絡治理的價值追求。任何一種治理模式都內在地蘊涵着人們對現實的思考和對價值的追求,公衆“不可能僅僅呼喚一種政治秩序而放棄對這種政治秩序正當性的價值追求”①戴木才:“政治的價值基礎及其維度”,《哲學動態》8(2005):9—13。。既然互聯網將不同地區、不同時區、不同民族的人匯聚到同一個開放的生態空間,那麽,網絡生命體在理想狀態上就是一種“和合共生”的關係。由於網絡空間是一個兼具開放性、包容性的交往領域,其治理就應秉持開放共享的理念。②闕天舒、李虹:“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全球網絡治理新秩序的中國方案”,《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3(2019):172—179。此外,隨着網絡生態系統的多元化、複雜化發展,網絡技術在拉近人們距離的同時,也帶來各種網絡詐騙、網絡駭客、網絡民粹主義等諸多違法犯罪行爲,這使以往高度依賴官僚體制的治理模式陷入了失靈困境。因而,網絡治理術亟需以“和合共生”作爲價值追求,既強調網絡生命體和生態系統間的和諧有序,也重視新興技術應用的公平正義。網絡治理術並不否定政府、市場、社會等主體在網絡秩序穩定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它改變了人們對網絡生命體、網絡技術、生態系統的關係認知,“網絡是一種既非市場也非科層制的獨特‘組織形式’或‘治理類型’,它強調多元主體的平等性”③[美]W.E.哈拉爾:《新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馮韻文、黄育馥 譯,第314頁。。所以,網絡治理術應將人、技術與環境和諧相處的理念作爲一種實踐行動和價值追求,強調不同生命主體通過包容合作、和諧共生和共同參與來實現網絡生命空間的有序發展。一方面,和合共生被視爲一種網絡生命體關係性的存在,需要在治理過程中得到遵循和發展。另一方面,網絡治理術批判性地反思技術治理的限度及其規制,通過理念的更新和多元主體的參與來創造網絡生態環境的包容。
3.創造新的生命聯繫反向適配治理。與傳統網絡治理片面追求網絡場域的穩定性和規範性不同,網絡治理術在目標上應導向“和合共生”的關係創造,其治理重點是思考如何在網絡生態系統中實現“輸入—輸出”的平衡,包括吸納民衆多元的利益訴求與合理的意見,建設不同主體間協商和妥協機制,完善政策議程設置和公共資源配置機制等等。網絡治理術所強調的關係創造和系統平衡,將激勵多元的行動者參與到良好網絡生態建設和治理中來,進而在更大的生態系統中塑造網絡生命體中不同主體的角色和他們彼此間的聯繫。因爲,民衆不僅僅是被動的可被治理的客體,他們作爲網絡生命體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於能夠根據自己的位置和作用在網絡生命體中扮演着關鍵角色。一是網絡生命體的“細胞”。生命個體在龐大的網絡空間中微小得如同有機生命體中的細胞,但他們每一位都是網絡生命體不可忽視的個體,構成網絡生態系統最基本的單元,並不斷進行信息資源的更新和傳遞,實現網絡生命體的新陳代謝和能量交換。二是網絡生態體的“組織”。不同“綫民”根據各自的興趣愛好或意見主張等逐漸形成一個個朋友圈和小團體,類似於生命體內部的細胞群。這些網絡空間中的組織將“綫民”在互聯網當中聯繫起來,進而爲達到相應目標而採取一致行動,如“粉絲”群體在網絡平臺爲偶像打榜、慈善團體爲救災發起網絡籌款、網絡執法部門爲淨化網絡環境進行的專項行動等等。無論是生物學上還是管理學上,這些組織都將很好地執行相關生命體的行動,在更高層次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網絡生命體的“器官”或“系統”。不同組織按相應的規制和功能組合起來,就會構成更高層次的結構。從網絡生命體來看,這些結構相當於網絡空間的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社會系統、文化系統;從生命個體來看,這些結構的地位和功能類似人體中不同的“器官”或“系統”。由於“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人的本性是要過一種公共生活”④[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吳壽彭 譯,第7頁。,因而網絡生命個體同樣需要融入更大的共同體中過美好生活,正如“綫民”作爲行動者加入不同層級結構發揮自身作用,從而反向適配網絡治理。
4.基於多元行動者協同的雙向參與。對於網絡治理術來說,公衆積極有效的參與是網絡生命體得以運行的基礎和保障。網絡參與可以被視爲一個價值追求和治理適配的過程,它在具體實踐中強調不局限於網絡象限和邊界約束,使網絡生命體成爲一種開放性的生態系統。當然,這種網絡參與對網絡空間治理、網絡生態建設的有效性和積極性,一方面取決於多元主體的協商合作與行動網絡,另一方面取決於網絡生命體本身爲不同行動者提供的參與機制和平臺空間。因爲,網絡生命體是由不同的利益群體和複雜系統組成的關聯式結構,網絡範圍內出現的公共問題和難題既可能涉及大多數“綫民”和利益集團,又可能與現實社會生活相互交織,其治理難度呈現指數級增長。這就要求在網絡治理術中拓展多元的認知思維,培養開放包容的治理格局,通過吸納“細胞”“組織”“器官”等不同層級主體,推動更大時空範圍內的協商合作,進而在不同情境中更爲有效地解決公共問題。與此同時,網絡生命體的運行邏輯又涉及國家權力、政府行政、市場經濟、社會生活、網絡文化建設,需要公共主體作爲強有力的推動者來對社會組織和普通民衆進行賦權,加強法律和機制建設來整合社會資源和利益訴求,藉助先進技術開拓網絡參與渠道和機會空間,最終成爲共建、共治、共享的網絡治理格局。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基於網絡治理術的網絡參與,實際上是一種雙向的參與:一方面,是公衆對網絡生命體的建設和治理進行深度的民主參與;另一方面,是政府作爲公共主體的代表,創設各種各樣的參與機制和平臺,把國家治理覆蓋到網絡生態系統,形成一種反向的參與。
結語:網絡生命體治理研究的延展
縱觀學界對有機生命體的研究,廣泛分佈於哲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城市管理學等各個領域,然而,在網絡治理甚至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當中,並沒有將它們聯繫在一起。這裏借鑒“治理術”概念,意在探究面向網絡生命體的治理研究。與於傳統的網絡治理模式相比,基於網絡生命體的治理術,旨在將有機生命體與網絡生態系統相銜接。在網絡研究理論的變革中,網絡空間已被全面賦予開放包容的屬性,成爲一個與外界進行能量交換並且生生不息的網絡生態系統。一方面,網絡空間中的文字、圖像、視頻等符號或流行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現實社會生活狀況,人們透過網絡生命體可以感知大衆的日常生活,生命的深度和廣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延伸;另一方面,現實當中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系統滲透到虛擬空間當中,商品、權力、人口、服務等所能涉及的生命場域同樣覆蓋到網絡世界。
當然,邁向生命空間的治理,並不是網絡治理視角上的簡單轉換,更是涉及網絡研究整體理論和實踐的變革,如何建立起適應網絡生命體的網絡治理模式,仍需要作進一步思考和探究。以理論層面爲例:一是在現實世界與虛擬空間複雜的關係中,是否應當重新界定網絡治理術的作用範圍,反思當前網絡治理和國家治理的生成機理,系統探索網絡治理術如何有效回應開放性、動態性、整體性的場域概念。因爲,網絡治理不僅要在空間維度,而且還要在時間維度、觀念維度實現網絡生命體的統一性。二是網絡生命體如何纔能實現治理的常態化、制度化、現代化。一方面,國家治理在網絡空間無處不在但有時治理效果又不盡如人意,政府等公共主體怎樣能夠進行有效治理並有足夠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和個體的相對自治性不足,導致公共部門被賦予“無限責任”。因此,在網絡治理術當中,需要通過反思技術、制度來吸納更多的主體參與到治理當中,爲不同行動者賦能和賦責。總之,網絡生命體不僅指引着網絡研究理論和網絡治理的變遷,在更宏觀的研究視野中,它正在逐漸走向國家治理和城市治理的討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