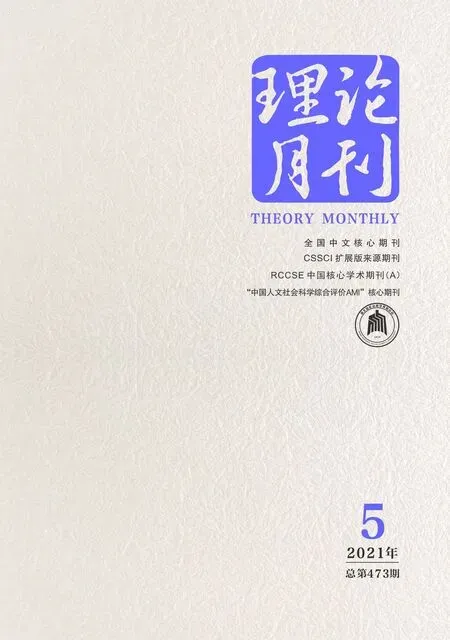现实性·形式感·多因论
——艺术起源的三个维度
庞 弘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610068)
人类自诞生伊始,便对“起源”(origins)问题保持着浓厚兴趣。从广为流传的各色创世神话到科学家对宇宙之肇始的猜想,再到高更(Paul Gauguin)那幅含义隽永的名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皆体现出这种追本溯源的热切冲动。在美学和艺术研究中,对起源的关注同样有集中体现。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无不从各自的方法论视域出发,就“艺术的起源”(the origin of art)做出形形色色的追问、思索与探究。
初看起来,艺术起源是一个很容易“进入”并“发声”的论域,但同时,艺术起源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甚至可能有“无穷解”的议题。这样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原初历史情境的难以企及。如卢卡契(Georg Luacs)便强调,当代人对艺术的真实起源几乎一无所知,“在许多重要的艺术门类中,如诗歌、音乐、舞蹈等,从来就不可能找到‘起源’的文献”[1](p204)。朱狄进一步指出,在围绕艺术起源的林林总总的解释中,不存在一个绝对令人信服的答案:“原始艺术家留下的唯一心理记录也就是他们的艺术品,而能代替他们回答问题的人只可能是和他们已经相隔了几万年之久的后代人,所以……即使是那些看来有相当说服力的理论(例如巫术论),它本身也还是猜测性的”[2](序言p3-4)。正是基于这种“回到历史现场”的不可能性,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才会不无激进地宣称:“对艺术来讲,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是靠否定其起源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3](p5)
现在,不少人意识到,“艺术起源”实际上同“何为艺术”关系紧密,古往今来关于“艺术从何而来”的假说,如最经典的“模仿说”“表现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实际上是人们依照自己对艺术本质的理解,对艺术起源所做出的“观念先行”式解读。既然艺术的定义必将随时代、地域、文化群体的改变而各有所异,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起源便大可怀疑[4](p46)。然而,起源问题的扑朔迷离,并不妨碍人们怀着浓厚兴趣参与到围绕艺术起源的讨论之中。倘若抛开传统“起源说”的既定模式,研究者或许可以另辟蹊径,从如下几个向度对艺术起源予以勘探:其一,是作为艺术起源之动因的现实需求;其二,是彰显艺术起源之独特性的形式自觉;其三,是艺术起源在“单因论”和“多因论”之间的微妙张力。
一、现实生存关切:艺术起源的内在动因
综观当前最流行的诸种起源理论,不难发现,尽管它们的思想渊源和关注重心颇有不同,但均在相当程度上将艺术与吃穿用度、生育繁衍、战争劳作、祭祀礼仪等现实生存关切联系起来。劳动说自不待言,其拥护者相信,人类的生存需求驱动了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而正是劳动催生了主体对艺术的欲求,赋予了主体操持艺术的身心素养,并从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向度对艺术加以塑造。即使是看似同物质现实较为疏远的游戏说和巫术说,其实同样与生存问题休戚相关。如游戏说便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投身游戏的自发冲动,只有在生存需要得以满足,拥有闲暇时间和剩余精力的前提下,人们才能以游戏的心态沉潜于艺术王国,为自己开辟一片自由的精神疆域。巫术说的要旨则是,艺术发端于原始人类的巫术仪式,其目的在于驾驭自然以使自身获利。巫术一方面具有现实指涉性,即主体借助形象化手段,间接作用于外在的物质现实;另一方面,巫术形象要发挥渲染气氛、激发情感的作用,又必须做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的意涵和属性。以上种种,无不在不同程度上触及艺术起源的内在动因——对种族繁衍、生命延续的迫切需求。
诚然,生存是人类立身处世的第一要义。在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远古时代,人们唯有努力存活下去,方有机会享受自然的丰富馈赠,并创造出灿烂的文化精神产品。李斯托威尔(William Listowel)对此深信不疑,他说:“原始艺术看来在每一个地方,都严格地和个人或集体的实用动机,热衷于保存和延续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的种族的激情混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并受它的支配。游戏、性欲、饥渴、战争、魔术仪式、日常劳动、生活方式、思想和事件的传达和纪念,这一切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艺术活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对它的产品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5](p203)朱狄进一步指出:“原始人耐心地磨光他的石斧,主要目的绝非出于对什么形式美的追求,而是想使它更加实用。同样,原始人用指甲纹去弄粗糙陶器的表面,在开始时也绝非出于装饰的目的,而是为了使它便于移动。……山顶洞人不惜花几倍制造工具的时间去创造那些被我们称为‘装饰品’的骨质项链,也一定有某种原因使他们相信它比普通的工具具有一种更大、更神秘的实用价值。”[2](序言p2-3)足见,人类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感绝非与生俱来,而是首先附着于现实的功利诉求,在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渐得以显现。
格罗塞(Ernst Grosse)对艺术的实用功利性做出了更详尽阐发。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他提出,艺术并非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应当被置于人类文化精神的总体构架中加以解析。通过对布须曼人、澳洲土著等原始部落居民的考察发现,任何民族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艺术活动,“就是最粗野的和最穷困的部落也把他们的许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艺术上”[6](p238)。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境遇下,依然倾注心力去从事看似无关痛痒的艺术创作,是令人惊愕的。格罗塞由此推断,在原始部族成员的心目中,艺术并非单纯的“美观”“宜人”之物,而是蕴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诉求。如原始装潢能训练人的手工制作技能;人体装饰可以震慑敌人,亦可以凸显个体的刚健、威猛,影响部落成员的配偶选择;诗歌、舞蹈和音乐则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使人们热情高涨、无所畏惧地投入战斗;等等。可见,早在其萌发阶段,艺术便绝非超越现实需要的自由游戏,而更莫过于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职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鉴于此,格罗塞得出结论:“原始民族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而是同时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的,而且后者往往还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6](p234)蔡元培的观点与格罗塞不谋而合,在《美术的起源》一文中,他同样强调了艺术在初始阶段所蕴含的实用功效:“初民美术的开始,差不多都含有一种实际上的目的,例如图案是应用的便利;装饰与舞蹈,是两性的媒介;诗歌舞蹈与音乐,是激起奋斗精神的作用;犹如家族的徽志,平和会的歌舞,与社会结合,有重要的关系。……总之,美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无论何等时代,都是显著的了。”[7](p104)
格罗塞等人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当前流行的“审美主义”(aestheticism)风尚。自19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开始推崇艺术的非功利性和纯粹性(purity)。他们坚信,艺术是与世俗功利无关、自成一格的存在,它将带来永恒而神圣的审美快感,总是与人类的内在精神相沟通。王尔德(Os⁃car Wilde)坦言:“艺术除了自己以外从不表达任何东西。它过着一种独立的生活,正如思想那样,纯正地沿着自己的谱系延续。”[8](p50)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强调,一旦关涉现实需求,美便不复存在:“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表现的是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是龌龊和令人作呕的,如同他孱弱可怜的天性一样。”[9](序言p22)艺术史家埃尼施(Nathalie Heinich)注意到,艺术活动的“职业体制”已日渐为一种新兴的“使命体制”所替代。艺术家不再受各种习俗、惯例、规约所迫,而是将创作尊奉为一项需要用灵魂操持的崇高使命:“从严格意义上说,有使命感,就是感觉被召唤从事某种活动,从此不再为了计算利益得失或服从礼节或者义务而生存,而是为了发自内心的个人的强烈爱好去生存。就是全身心投入一种事业,感觉自己生存的目的就是这一事业,感觉是上天注定的。”[10](p64)这些言论一方面凸显了艺术的自主性(autonomy)和独立价值,另一方面亦可能将艺术引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导致某些难以忽视的问题或症候①如美国学者埃德曼(Irwin Edman)便指出,“美”和“实用性”在当下的分道扬镳,一方面将助长“一种讲究实际的文化,对于感官的魅力或想象中的美丝毫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又极有可能带来“一些琐琐碎碎、微不足道的装饰性小玩意儿,以及唯美主义者的奢华,他们精美的创造及享受与生活毫无联系”。故而,一种孤芳自赏式的艺术观无助于营造健康、积极的精神生活。参见[美]欧文·埃德曼.艺术与人[M].任和,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3-24.。通过对艺术之起源的审视不难发现,艺术绝非“纯而又纯”的审美对象。自它诞生伊始,便同生存与死亡、战争与灾难、生产与饮食、劳作与休憩、祭祀与崇拜等人类生活中的重大议题紧密关联。反之,人们在今天所津津乐道的“美的艺术”(fine arts),其实只是现代性分化的晚近产物,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弹指一瞬。在“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口号愈发响亮的当下,上述认识无疑将体现出补偏救弊的重要意义。
二、形式感:艺术起源的关键环节
虽然艺术的明确起点无从考证,但纵观前人研究,不难提炼出形式感(formal sense)这一与起源难舍难分的重要维度。形式(form)是一个与个体生存密不可分的问题。人类自孩提时代便沉迷其中的“说故事”,即是在强烈形式化(formaliza⁃tion)冲动的驱使下,将自然形态的事件统摄到一个完整、自洽的逻辑体系中。在西方思想史上,形式同样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议题。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先验理式”,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以及贺拉斯的“合理合式”便从不同向度出发,对形式的本质与特性做出了深入思考[11](p162)。在20世纪以来的美学—艺术研究中,形式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卡西尔(Ernst Cassirer)强调,不同于科学家对法则或规律的揭示,艺术家的禀赋在于发现隐匿于现象世界的诸种形式。故而,“在艺术中我们是生活在纯粹形式的王国中而不是生活在对感性对象的分析解剖或对它们的效果进行研究的王国中”[12](p199)。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试图从形式出发对艺术加以定义:“艺术往往被界定为一种意在创造出具有愉悦性形式的东西。这些形式可以满足我们的美感。而美感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要求我们具备相应的鉴赏力,即一种对存在于诸形式关系中的整一性或和谐的感知能力。”[13](p2)真正从本体论高度审视形式的,是法国艺术史家福西永(Henri Focillon)。在他看来,形式绝非一般化的载体、躯壳或外部形态,而是与主体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并昭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在场:“那么,形式只是虚无吗?它只是游荡于空间的一个零,永远在追踪着某个总是在逃避它的数字吗?绝不是的。形式有一种含义——但这完全是它本身的含义,一种私下的、特殊的价值,不可与我们强加给它的那些属性相混淆。”[14](p40)
在原始人的思维体系中,形式感同样有生动体现。有学者通过对史前洞穴中动物遗骸化石的考察,发现远古先民热衷于刻画的动物其实并非他们在当时最常食用的物种。如阿尔塔米拉人主要吃的是赤鹿,但绘制在岩壁上的却大多是野牛;拉斯科人的主要食物是驯鹿,但在岩壁上却几乎没有留下明显的驯鹿形象;等等[15](p3)。由此不难推断,远古艺术并非直接与口腹之欲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容易入画之物反倒更有机会成为描绘的对象。而所谓入画的一个重要标准,则在于形象能否满足原始人独特的审美感触与形式期待。这种对形式感的追求在原始艺术中屡见不鲜。布洛克(Gene Blocker)发现,远古雕像具有三个形式特征:一是正面性,即雕像始终以正面示人,似乎总是在凝视观者;二是对称性,即形象的左右两侧呈镜像关系,使整件艺术品保持静止不变的理想形态;三是构图的外形准则,即制作者依循既定程式,对人体各部分加以恰当安排,使其结合为一个有稳定风格的整体[16](p83-85)。莫里斯(Desmond Morris)基于对史前遗迹与部落文明的综合分析,总结出原始艺术在形象表现上的八条形式法则:(1)夸张法则,即对人体特定部位(常常是性器官)的夸大处理;(2)纯化法则,即忽略细节和不必要之处,将复杂的形体简化为单纯、平滑、优雅的轮廓;(3)组合法则,即依照特定方式组织各部分,使形象处于大致的平衡状态;(4)多样性法则,即形象的线条日益烦琐,细节不断增加,但在复杂中亦可见出某些规律;(5)精致法则,即形象逐渐由粗糙变得精致,不同要素之间的间隔愈发清晰;(6)主题变换法则,即同一主题通过不同载体或中介而得以表现;(7)尚新法则,即原始艺术在总体上处于形式革新的缓慢进程中;(8)语境法则,即刻意为之的形式常常被安置于精心选择的场所,以彰显其作为(准)艺术的独特之处[17](p302)。以上种种,无疑印证了形式感在艺术发轫阶段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原始艺术中,形式感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抽象架构或赋形能力,具体表现有二:一是“秩序感”,即主体赋予世界以秩序,将纷乱、驳杂的自然现象整合为有序整体。如原始人在将粗糙的石块打磨为平滑的尖状物时,便体现出以既定秩序来规范并塑造对象的尝试。二是“空间想象力”,即主体依照在头脑中先行设定的空间图谱,对不同事物加以妥善安置,使之呈现出恰如其分的比例关系。如早期(准)艺术家必须对野牛在三维空间中的动作、姿态、躯体构造有所把握,方能在岩壁上绘制出大致准确的野牛形象。放眼艺术史的漫长历程,这种抽象的形式把握得到了反复的强调。
达·芬奇曾这样比较雕塑与绘画的区别:“雕塑家总是把材料往下削,画家则总是把材料往上添,并且雕塑家总削一种材料,而画家则添上不同的材料。”[18](p34)但无论是“往上添”还是“往下削”,其用意皆在于使对象由混乱转向有序,由无形转向有形,由分散转向整一。埃德曼宣称,艺术家的毕生使命,在于赋予经验以形式。在他看来,经验(experi⁃ence)虽充满活力,却往往杂乱无章、混沌不清,只有在具备一定形式的前提下,经验才可能脱离根深蒂固的混乱性,彰显其独具一格的诗性魅力:“无论什么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形式,无论什么运动都具有一定的方向,无论什么样的生活似乎都有一定的条理和章法。从中我们获得智慧,并把一个混沌的世界改造成为我们所期望的、可取的、有条理的世界,对此人们称之为艺术。脱离艺术和智慧的经验是紊乱无序的,是一种不具形式、没有目的的活动。”[19](p3)贡布里希(E.H.Gombrich)则试图用形式感来解释原始艺术生成的动力机制。他指出,艺术家的创作并非“所见即所得”式的复制,而总是在特定“图式”(schema)的支配下进行。所谓图式,即主体基于现实经验而形成的风格定向与心理预期,它为人们对周遭世界的把握提供了前提性的形式框架。如古人之所以发现了“天鹅”或“狮子”星座,是因为他们将心中关于天鹅或狮子的图式投射(pro⁃jection)到了漫漫星河之中。贡布里希由此猜测,原始洞穴中的图案很可能不完全出自模仿,而是岩壁上的纹理与先民脑海中的特定图式形成了呼应,进而驱使他们用染上颜色的泥土,将自己眼中所见的形象一点点勾勒出来[20](p123-129)。美学家塔塔尔凯维奇(Wladyslaw Tatarkiewicz)对贡布里希深表认同,在他看来,“形式”不只是一个与“内容”相区分的范畴,不只是创作者对不同要素的组织、安排、规划,同时亦涉及“吾人心灵对其知觉到的对象所作之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ind to the perceived ob⁃ject)”[21](p228)。
形式感虽是一个主体性(subjectivity)范畴,其根源却在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生产工具的制作中,随着对线条、形体、节奏的日益谙熟,以及知觉、感受、体验能力的不断提升,主体逐渐形成了对形式的敏感与自觉。当这种觉醒后的形式感被倾注于原生态的物质材料时,一种包含着丰富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亦将应运而生。“工具的制造培养了人的一种新的心理能力,即预先在心里形成加工对象形式的模式,以它指导加工的方向,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正是在几万年的工具制造中,人获得了对形式感的巨大敏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技巧,才使得某些艺术,尤其是造型艺术的产生成为可能。”[2](p187)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才会假设,人类的第一件艺术品与第一件手工制品或许是同步的:“当人类制造出第一件工具的时候,人类的第一件艺术品诞生了。一根用树枝做成的木棍,或者用砾石打制的砍斫石器,虽极其简陋,却是造型艺术的开端。”[22](p13)虽然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ayake)等学者从遗传学和进化论出发,将形式感指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①美国学者迪萨纳亚克相信,人类天生便有着追求“良好感觉”的内在倾向,正是这样的倾向决定了他们在进化中的选择与行动。如不断锻炼自己的味蕾,使果实尝起来有甘甜感,使毒物有苦涩感;再如训练自己的感觉器官,使之对黑暗、蜘蛛、蛇等产生本然的畏惧,对光明与温暖产生舒适和愉快之感;又如在配偶的选择中,逐渐趋向于厌恶歪斜的嘴脸,而偏好相对匀称、均衡的五官;等等。因此,在她看来,对“美的形式”的倾慕并非后天的文化建构,而是从一开始就被镌刻在主体的基因链上。参见[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艺术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M].户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但毫无疑问,作为本然“物种需求”的形式体验,同样必须在现实经验的不断拷问下,在与对象世界的磨合中逐渐产生。倘若缺少物质实践的“询唤”作用,形式感至多只是潜藏在人类机体中的某种可能性,无法得到直观、明确的映现与彰显。
三、艺术起源的单因论与多因论
在围绕艺术起源的讨论中,还存在着单因论(singularism)与多因论(multiplism)的复杂纠葛。单因论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哲学理念,其倡导者相信,在错综复杂的表象背后潜藏着普遍、永恒、绝对的唯一本原,只要发掘出这一本原,便能够把握世界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全部真相。柏拉图对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之理式的捍卫,黑格尔对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之“绝对理念”的阐发,是单因论哲学的典型范例。自20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发现,对单一本原的过度执着,将掩盖本应拥有的丰富可能,使认识踏上一条危险的不归之途。故而,一种新的多因论哲学开始崭露头角,它拒斥单因论所隐含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倾向,试图从不同侧面出发,揭示某一社会文化现象得以生成的多重依据和多重线索。法国学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是多因论的忠实拥趸。基于对马克思原典的重读,阿尔都塞提出了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这一颇具阐释力的命题。在他看来,任何历史事件都并非由单一因素塑造,而总是处于由无数微观事件所编织的网络之中,通过不同意志的组合与冲突而逐渐浮现:“有多少单个的意志就有多少股力量;在简单的情形下是两个力量相对抗,它们的合力是与原来的两个力量既不同又共同的第三个力量,原来的两个力量在第三个力量里都认不出自己,虽然它们是第三个力量的组成力。”[23](p98)正是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建构,为多因论渗入包括艺术起源在内的更广阔论域做出了铺垫。
长久以来,单因论是解释艺术起源的主导模式。人们耳熟能详的模仿说、表现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理论主张,无不将某一特定因素指认为艺术生成的唯一必要条件。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单因论的缺陷,并试图从多因论视域出发,对艺术的来龙去脉加以深入解析。美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发现,“由考古学家们所提出的任何一种单独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多样而复杂的艺术和符号的起源和意义”[2](p170)。李斯托威尔承认,在原始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贯穿着诸如“严格的功利主义”,以及“游戏、仪式、饥渴和性欲”等一系列共同因素,同时又强调,“我们不能接受某一种单独的理论解说”,因为它“排斥了对艺术的起源具有同样贡献的其他的实用活动和功能”[5](p198-199)。有学者指出,正如大江大河由千百条支流汇聚,艺术绝非发轫于单一起源,而是在多重动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不论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起源’一词,艺术的源头是否只有一个?任何一条大江、大河,都有众多的支流,除了主流的发源地以外,还有众多的支流的发源地,艺术有如一条河,它显然是由有如河流支流的各艺术要素以及非艺术要素汇集而成。……当我们考证艺术的发源地时,除了考证主流的发源地以外,还应不应该考证各支流,特别是主要支流的发源地呢?”[24](p53)
大体上看,艺术起源的多因论从如下两个向度得以展现。
从地缘上考察,艺术并非发端于某一中心点,而是以离心化的姿态在多个空间中同时涌现。科学家早已发现,包括亚洲、欧洲、东非在内的广阔领域,都曾留下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故而,欧洲(尤其是西欧)并非人类的唯一发祥地。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理论则证明,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先驱”或“领跑者”,相反,不同地域文明(主要指中国、印度、西方)在大致相近的时间内(公元前600—前300年)曾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25](p8-13)。在作为人类文明之精髓的艺术中,上述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向同样有生动表现。在很长一段时间,艺术史家将欧洲视为洞穴壁画等远古(准)艺术的源头。但在2014年,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七座洞穴中发现的大量形象(包括鹿、猪以及人手的轮廓等)则雄辩式地证明,大约在四万年前,全球范围内的智人便已不约而同地展开(准)艺术活动,其描摹对象和表现技法亦具有惊人的相似性[26](p223-227)。这种“多点开花”的局面对应了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观点。在德勒兹看来,传统知识呈现出“树状”形态,其中,无数思想脉络依托一个主轴而存在;后现代知识则具有鲜明的“根茎”(rhizome)气质,它不再由某一本质或中心所统摄,而是以无规则的方式不断扩张、延展:“根茎是一种反—谱系。它是一种短时记忆,甚或一种反记忆。根茎通过变化、拓张、征服、捕获、旁生而运作。……根茎是一个去中心化、非等级化和非示意的系统,它没有一位将军,也没有组织性的记忆或中心性的自动机制,相反,它仅仅为一种状态的流通所界定。”[27](p28)这种无规则的游移、蔓生、弥散,极为贴切地描述了艺术在诞生伊始的空间形态。
艺术亦是在多重力量的平行四边形结构中应运而生。虽然“艺术”在最初是一个极为驳杂的范畴①在前现代语境下,艺术并非今人眼中的“美的艺术”,而是与实用性的“技艺”水乳交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主要指“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等贵族子弟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技能。英国文化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同样谈道:“自从13世纪art这个词就一直在英文中被使用,它最接近的词源是中古法语里的art,可追溯的最早词源是拉丁文artem——意指skill(技术)。一直到17世纪末art这个词都没有专门的定义,它被广泛地应用在很多地方,譬如数学、医学、钓鱼等领域都会使用到这个词。”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7.,但必须承认,各门类艺术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与不同因素产生更紧密的关系,即不同艺术形态可能各有其独特起源。芬兰学者希尔恩(Yrj Hirn)提出,“艺术的不同形式促使我们去假定,存在着不止一种艺术冲动,而是几种艺术冲动”[28](p702)。他认为,在原始文化中,主要存在着如下六种冲动,它们分别催生了不同的艺术形态:(1)“知识传达冲动”使人们以图像、模仿和文字的方式,将思想和知识转化为可交流的符号,成为戏剧和造型艺术的起源;(2)“记忆保存冲动”使人们将重要事件记录于可见的物质载体中,成为叙事诗和造型艺术的起源;(3)“恋爱冲动”使原始人借装饰、舞蹈、歌咏等方式来取悦异性,成为装饰艺术、舞蹈和歌唱的起源;(4)“劳动冲动”使原始人依照一定节奏行动,以减轻重负并引发快感,成为音乐艺术的起源;(5)“战争冲动”使人们为恐吓敌人或提升士气,编排以战斗为主题的哑剧或集体舞,成为舞蹈和戏剧的起源;(6)“巫术冲动”使人们为施行诅咒而制作大量视觉文本,成为雕塑或绘画的重要来源[28](p693-727)。更进一步,即使在同一类艺术的形成中,亦充斥着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常任侠在《关于我国音乐舞蹈与戏剧起源的一考察》中指出,早期人类的歌舞艺术至少涉及“对于劳动成功的庆祝”“对于自然的崇拜”“对于祖先的祭祀”“对于两性的诱惑”难分难解的四重动因[29](p23-25)。卢卡契相信,模仿为视觉艺术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时不忘强调,“产生模仿艺术形象的最初冲动只是由巫术操演活动中产生的,这种巫术操演是要通过模仿来影响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1](p295-320)。德索(Max Dessoir)观察到,原始舞蹈一方面植根于劳动所培养的节奏感,另一方面又“似乎是由狂欢运动组成的,其中压倒一切的情感力图表达出来,使舞蹈者进入更大的疯狂”[30](p246)。诚然,一件艺术品绝非同质化的存在,而是包含着语言符码、形象体系、哲理意蕴、情感体验等丰富的构成要素,它们或是来自远古仪式,或是来自日益纯熟的手工技能,或是来自主体的表现欲和创造冲动,而无法用单一因由来轻易涵盖。这种多元生成的包孕性和混杂性,显然是艺术最令人神往的特质所在。
结语
综上,现实性、形式感和多因论构成了窥探艺术起源的三个重要视角。现实性聚焦于艺术在发轫阶段的实用功利属性,形式感凸显了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对形体、方位和空间构造的敏感,多因论使起源问题摆脱相对单一的本质主义模式,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与可能性。三重视角紧密交织,在种种近乎陈词滥调的起源学说之外,为人们接近艺术起源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依循上述三条思路,研究者将更清晰地感受到,艺术起源其实是一个不会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或许可以在特定情境下显露出冰山一角,但始终无法得到绝对精确的还原与重构。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艺术起源命题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在艺术史的总体谱系中,“起源”无疑是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人们或许能否认起源的可复原性(reducibility),却断然无法否认起源在漫漫时间之流中的真切存在,无法否认其在艺术发展的线性历程中所居的不容忽视的奠基性位置。同时,较之艺术理论的其他领域,艺术起源研究具有更鲜明的纯粹性和自主性,鲜少受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场外”因素的干扰[31](p16)。因此,围绕起源问题,研究者往往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而一方面形成了巴赫金(M.M.Bakhtin)意义上多声部“共鸣”的生动景观,另一方面又恰如其分地折射了主体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艺术的认知、理解与想象性建构。更进一步,不同于追求“阶梯式上升”的自然科学,艺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沉淀、累积、叠加的过程,故而,艺术在今日的种种构造方式、表现形态和精神取向,其实都可以在艺术的发轫阶段找到某些征兆或端倪。这样,对起源问题的关注,也便有助于研究者鉴往知来,从历史残留物的罅隙中窥探艺术在未来的可能走向①日本艺术家杉本博司(Sugimoto Hiroshi)对此有清晰认识:“人类的想象力一直是通过艺术来加以表现的。现在,为了理解那个无法预知的未来,我们到了必须回溯历史的时候。为了追溯人类的想象力,我们就必须探寻人类意识的起源。现在,艺术所能够做的,也许就是回忆,就是找回人成为人那个时候的记忆。”参见[日]杉本博司.艺术的起源[M].林叶,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凡此种种,无不使艺术起源成为一个值得当代人倾注心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