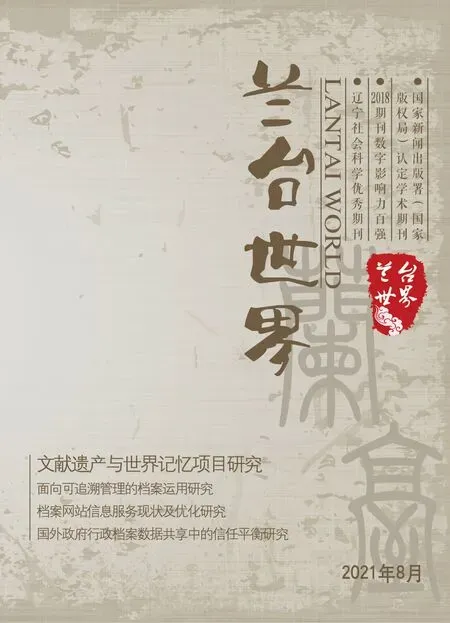困难遗产视角下的档案正义与世界记忆项目建设研究
王倩媛 王玉珏
世界记忆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 年创建,其初衷是为了加强全球范围内文献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避免集体遗忘。2021 年5 月,新的世界记忆项目审查制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Executive Board)第211 届会议上正式审议通过。此前,因我国《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日本政府以停止会费等手段为要挟[1],要求教科文组织对“世界记忆项目”进行法律框架的重塑。在数次会议与“全面审核”之后,原本应于2019 年进行的新一轮《世界记忆名录》评审被暂停,直接导致世界记忆项目发展受阻、进入停滞阶段。尽管世界记忆项目的创建,并非为阐述历史中的是非对错,但是现在由于政治影响,该项目的发展受到了重创。
日本对遗产的歪曲和政治干扰,并不只《南京大屠杀档案》一例。2020 年6 月,韩国对日本背弃“讲述整体历史”的承诺,在新建成的工业遗产信息中心否认强征劳工的历史,并展出部分歪曲、篡改过的历史资料的行为表示谴责。这一消息将2015 年引起中日韩三国遗产矛盾的《明治工业革命遗产》带入公众的视野,引发对于历史和解与世界遗产的讨论,也让学者与社会公众关注起此类困难遗产(Difficult Heritage)。
困难遗产常与战争、奴役、疾病等灾难相关,往往承载着创伤记忆或屈辱历史,成为遗产保护中被“忽略”的部分。尽管黑暗的过往会重新唤起过去苦难、屈辱的记忆,延续悲痛的情感,但是其作为真实历史记录的证据价值与教育意义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除了上述提及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等与战争、奴役相关的遗产,世界遗产项目中还出现了例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根除天花病的档案》、挪威的《卑尔根麻风病档案》等医学类记忆遗产。这些遗产见证了医患故事,也给未来医学研究提供了参考。通过困难遗产中真实的记录将历史记忆铭刻于文献载体之上,从而建立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以构建集体记忆的方式帮助树立身份认同,同时实现对未来的警示教育与应对参考。本文将以困难遗产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产生争议与矛盾的原因,剖析对其进行保护与利用的难点,并对如何以困难遗产构建世界共同记忆提出思考。
一、困难遗产的概念引入
遗产一般被认为是国家或集体记忆构建和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20 世纪90 年代,人们开始直面历史与记忆中的黑暗部分,学者们也逐渐将研究的目光放置在“困难遗产”之上,人们逐渐认识到那些看似不堪或是令人不安、自卑、羞愧的历史记忆也是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学界对于困难遗产的定义并未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在遗产研究领域出现过“不和谐遗产”“有争议遗产”“负面遗产”等概念与困难遗产相交叉,用来指代蕴含消极情绪或具有负面作用的遗产。第一次提出与创伤、伤痛相关的历史事件、遗址使用的是1996 年由唐布里奇(Tunbridge, J.E)和阿什沃思(G.J.Ashworth)提出的“不和谐遗产”(Dissonant Heritage),他们认为“不和谐是遗产的本质”[2]。阿什沃思进一步解释,不和谐遗产是人与其遗产在时间或空间上缺乏一致性的一种情况。1997年,唐布里奇提出“有争议遗产”(Contested Heritage)的概念来强调不同利益者间、不同阶段下遗产的争议与矛盾。1998 年,大卫·乌兹尔(David Uzzell)和罗伊·百伦泰(Roy Ballantyne)则是用“伤痛遗产”(Heritage that Hurts)来指代在发生过死亡、灾难和暴行等伤痛之后得到纪念和认可的遗产[3]。2000 年,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马尔科姆·福利(Malcom Foley)创造了“黑色遗产”(Dark Heritage)的说法,随后学界还就遗产的利用发散到旅游行业,对遗址的开发与记忆的承载进行研究。2002 年,美国学者林恩·梅斯凯(Lynn Meskell)则提出“负面遗产”(Negative Heritage)这一概念,认为遗产保护与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是相悖的[4]。而国内虽没有直接提出如困难遗产一样的术语,却也在相似含义的主题中使用过负面遗产、棘手遗产等说法,如张影舒在《如何书写“棘手的遗产”——以德国博物馆实践为例》中认为棘手的遗产是写满社会的冷漠与荒诞、人性的丑恶与苦情,更多的人们不愿触碰的历史与伤痛[5]。
2009 年,英国约克大学教授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在对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位于德国纽伦堡的纳粹遗产。由于纽伦堡与纳粹密切相关,人们在谈及纽伦堡时总会将其与暴行、审判、集会相联系,这对纽伦堡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德国在战后处理“困难遗产”的策略与方法吸引了麦夏兰教授的注意。在对纳粹遗产实行半毁灭、闲置或是用途转化等处理都无果之后,德国终于意识到要公开承认纳粹历史,解决棘手问题。以“人权之城”为构想,为纽伦堡市塑造新的国际形象,加之文献中心的建立、在纳粹集会场地上展览、导游工作的开展,使得纽伦堡逐渐转变为和平与人权的中心,也将属于纽伦堡市的纳粹记忆上升为世界性的人权记忆[6]。
在《困难遗产: 纽伦堡等地对纳粹历史的协定》(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一书中,麦夏兰教授对困难遗产的概念进行了定义与阐释,认为困难遗产是指国家或集体公开纪念他们过去犯下的、为之感到羞耻的暴行的历史,一般在当下被认为有意义,但也存在争议,且很难与一个“积极的、自我肯定的当代身份”相协调[7]。不同于威廉·洛根(William Logan)和基尔·里夫斯(Keir Reeves)在定义中强调遗址带来的痛苦和羞愧,麦夏兰在阐释中更加强调遗产的“麻烦”“难以解决”以及国家身份与公众和解。她认为,公开承认一方的历史罪行正在日益普及并成为一种国际做法,应当被视为当代身份认同的积极进展[8]。面对困难遗产中令人不安的历史,应该用不断变化和持续推行的协商策略来应对其未来的挑战与发展。麦夏兰教授对于困难遗产的定义不局限于死亡、灾难等历史事件,更具有普遍性与概括性,也因此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可。
二、档案正义视角下的困难遗产价值挖掘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人们对于民主、权利的意识觉醒,想要参与管理的渴望不断增强,社会正义与公平也逐渐成为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特里·库克(Terry Cook)在其档案学范式研究中就指出,档案正从支撑学术精英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服务于认同和正义的社会资源[9]。档案正义论主张“以档案追寻公平与正义”,充分发挥了档案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给弱势群体、边缘声音以表达的机会和途径,是对档案职业责任的明确,也是对档案工作中维护正义与公平的指导。鉴于困难遗产目前仍存在因争议而产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档案文献以证据的形式帮助实现记忆与认同的构建,守护公民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同时促进社会正义与民族团结。
1.构建记忆,避免集体遗忘的发生。记忆与遗忘总是相伴相生。记忆不是自发的,记忆的凝聚不是自然的行动,档案作为“构建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代替的要素”[10],承担了记忆塑造与传承的主要责任。南非档案学家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曾提出“为正义而记忆”的观点,并提倡社会积极参与争取平等、公平的正义斗争,通过档案的保存与利用增强认同感,凝聚群体,创造和谐友好的新公众[11]。然而,人们时常会有选择性地去遗忘伤痛与耻辱,只保存需要的记忆,造成“记忆安全”的隐患。
在面对边缘化、不受重视甚至是被排斥的记忆时,困难遗产的出现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不是彰显仇恨或是追诉罪行,而是寻求理解、宽恕与和平,通过构建记忆于未来起到警示与启迪的作用。尽管困难遗产中涉及大量战争、奴役、疾病、天灾等创伤记忆,是人类不愿再揭开的“伤疤”,记录在载体上的事实却可以通过复刻、展演的形式重现历史真相,削弱身份焦虑感,为弱势群体、边缘声音提供表达的机会和途径,避免集体遗忘症的发生。
2.还原历史,守护了解真相的权利。“档案责任与职业伦理就是恪守诚实、公平、真实、专业的原则,在档案和记忆的实际工作中,档案工作者和文件管理员必须立场坚定,勇于为社会和未来负责,保护文件和文件保管体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12]面对可能出现的不公或威胁,档案可以成为揭露真相的证据,成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守护者。困难遗产因为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因此时常被质疑内容真实性。而档案作为历史内容的承载者可以帮助还原历史事实,捍卫公民了解真相的权利,避免遗产沦为权力争夺的工具。
对于同一遗产的解读可能是多样的。各种团体寻求被公众认可的认同政治,借助承载记忆的遗产来塑造自我叙事,宣告权威性、正统性[13]。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的出现更是让文明之间的天平倾斜加剧,阻碍了文明之间的尊重、沟通与理解,其他被忽视的非主流遗产也在加速消亡。至此,部分历史就会随时间流逝而被刻意掩埋,部分群体的记忆也将难以找回。关注困难遗产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与保护,以困难遗产为基础,将历史事实以丰富的形式再现,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时代背景,了解事件始末。时刻铭记困难遗产对历史正义的特殊意义,也能够避免在多元化叙事之下对于历史事实的模糊化,帮助真实记忆的延续。
3.坚持正义,促进认同与民族团结。从认同角度而言,困难遗产帮助完善身份信息,增进文化归属感和安全感。认同的建构是在特定的话语中展开的,“国家身份是以特定的叙事手段制造出来的”[14]。完成文化认同除了要认同共性之外,也要认同差异,即将自身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区别开,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认知。一方面,困难遗产可以弥补过去身份塑造中缺失的部分历史背景,创造更加生动、全面的集体形象,从而赢得国家内部的认同;另一方面,困难遗产可以帮助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完成文化展示,宣扬民族精神,在实现沟通与理解的同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而从情感与正义角度而言,困难遗产促进问责与和解,完成消极因素的正向转化。记忆是鲜活且生动的,它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易于引发群体共鸣。于个人而言,记忆以叙事构建情感纽带连接起过去与现在,在接纳困难遗产的过程中可以完成对历史事实的体悟,将从中提取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根植心中,成为内在精神的动力与源泉。于国家而言,困难遗产以档案文献为材料构建集体记忆,凝聚民族力量,同时推动国家间的沟通与和解,用坦诚的方式减少负面因素的影响,实现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互鉴互赏。
三、世界记忆项目中的困难遗产问题
困难遗产的“棘手”,主要在于遗产带来的不安感与失控感。遗产中所涉及的历史时常与创伤、痛苦相关,但被认为在当下是有意义的,然而对于记忆的展演和复刻可能会扰乱一个积极的自我身份认同,因而遗产变得难以处理,需要谨慎对待。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与所处的位置不同,对棘手遗产的解读往往会存在差异和争议,导致政治冲突和记忆矛盾,从而影响群体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形成[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了三大遗产旗舰项目,近年来在保证遗产普遍价值的基础上更加关注遗产的多元价值,鼓励相互的理解与欣赏,在尊重文化多样性背景之下进行遗产保护。世界记忆项目就曾明确表达出对文献遗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接纳可能还未得到广泛认可的负面记忆。尽管部分国家对困难遗产抱着消极和逃避的态度,但困难遗产一直并会长期存在,保护困难遗产面临着政治、权力、叙事等多方的挑战。要想调和困难遗产中的矛盾,需先从剖析其面临的问题开始。
1.政治对历史正义的干预。遗产的话语表征与建构中充满了当代人的知识、想象、价值观、文化思维、利益诉求、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因而它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文化政治总是与之如影随形,国际学界将这称为“遗产政治”[16]。从困难遗产本身的性质来看,国家以建设积极的身份和形象为由介入项目是可以被理解的,出于对本体安全的维护,国家会采用一些手段来消除遗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各种团体寻求公共承认的认同政治或承认政治的结果,他们借助刻记为遗迹的记忆,来雕刻自我叙事,宣告正统性[17]。
然而,以特殊政治手段干涉遗产项目的评定会对遗产的内容价值造成伤害,既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正义的忽视。2015 年,俄罗斯曾对日本“生还回舞鹤——被拘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归国记录(1945—1956)”入选世界记忆遗产而提出抗议,认为日方是在“政治利用教科文组织”。日方却辩解称“是与俄罗斯合作推进申遗”,否认指责并拒绝撤回申请[18]。而同年,日本政府在我国为《南京大屠杀档案》与《“慰安妇”档案》申遗时进行了各种干扰与施压,一边要求遗产项目“去政治化”,一边又使用政治手段干涉对于遗产的保护,通过操纵叙事等方式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使各国对于历史与遗产的争议逐渐扩大,矛盾难以调和。政治立场的天然不同导致了各国对于记忆叙事的不同态度,这直接影响到了对于遗产的处理,同时也违背了对于历史事实的尊重与社会正义的坚守之心。而从遗产本身来看,这让本就可能具有争议的困难遗产陷入了一个不适合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困难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受政治干扰严重,进而历史正义得不到维护,世界记忆项目的发展也因此受阻。
2.遗产话语的权力争夺。随着人们对于“遗产”概念的深入理解,对于遗产研究的视角也逐渐开始多元化。世界遗产价值的普遍性与地方独特性、多样性的冲突在实践过程中越发凸显。从世界遗产认定过程上分析,政治化趋势逐渐上升,“权威遗产话语”出现,“申遗”趋于一种缔约国之间竞争国家实力的政治过程[19],遗产背后也反映出“专家——遗产——访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20]。出于对国际身份和文化输出的渴求,文化遗产项目成为了各国寻求文化认可、争取尊重与理解的平台。
困难遗产作为战争、灾害等的历史遗留不受重视,任何的不和谐、争议与矛盾都会影响国家在国际平台上的形象。基于此,在必须面对困难遗产时,各国会选择把握其保护与叙事的主动权,更多地以本国为中心完成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构建。而这种被政治与权力干预的遗产会削弱原先关于历史、情感、认同与记忆的价值,直接影响其保护和利用,从而引发记忆安全问题。2015 年,在《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同时,我国另一项遗产《“慰安妇”档案》的申遗之路却受尽阻挠。日本政府多次派出专家或官员,企图干涉项目评审,并以停止缴纳会费为要挟,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记忆项目”进行法律框架的重塑,试图通过施压加大对遗产项目的话语权,以实现对困难遗产,更是对“遗产评审”更多的掌控权。此举直接导致《“慰安妇”档案》申遗受挫,同时也影响了世界记忆遗产随后几年的评审,阻碍了遗产项目的稳定、健康发展。
3.历史叙事影响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相反,它“被持续地生产着,并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不断变迁”[21]。因此,对国家认同连续性的追求,进而对其身份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叙事。当他们在本体上不安全时,叙事凭借其记载作用与动员能力成为重要角色。历史叙事可以看作是对于遗产与档案文献资源的挖掘与开发,一方面,遗产资源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内容再现,使其得到了有价值的、超越时空的利用;另一方面,文献资源与各类媒介进行结合有助于历史记忆的展演,扩大了历史的传播范围,也促进了记忆的国际认同。然而由于立场不同,历史事实与历史叙事的矛盾难以实现调和,并逐渐从历史、遗产领域延伸到了教育、文化之中。“遮羞性叙事”成为日本等国面对棘手遗产的直接解决办法。有选择性地擦除或删改一些内容,只呈现出需要的部分,实则是试图挑战历史真实性,维护自身政治利益。
历史叙事是存在主观性的、可建构的,但是它是受历史事实约束的,“戴着镣铐”的叙述,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靠着想象力去创作[22]。以战争记忆为例,倘若“加害国”只是引导人民关注战争中的伤亡与痛苦,而不愿承认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则会造成国家与个人对战争责任的淡化。久而久之,其构建的集体记忆会与“受害国”的创伤记忆发生碰撞,对历史真相产生严重冲击。加害者不再企图逃避或篡改历史,受害者不再寻求报复,第三方也能从战争记忆中反思并汲取教育意义,这才是未来世界发展中最为需要的格局。
目前,部分学者提出“多元化叙事”的方式,鼓励更多的声音参与困难遗产与历史问题的表达,试图以更大范围地覆盖和梳理来解决国家间的记忆安全问题。然而,部分“多元化”观点的提出并未以保护历史记忆为目的,只是为了“选择性遗忘”,将真相隐于各类加工之中。长此以往,努力建立起的国家形象会受到消极影响,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历史正义的构建也会遭受冲击,身份认同将会在冗杂的信息中被动摇,困难遗产的保护也将难以推进。
四、对困难遗产问题的思考与展望
1.呼吁困难遗产申遗,参与世界记忆项目。世界记忆项目被视为“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旗舰项目的新生同胞,属于同一个大家庭,但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色”[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17 版《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方针》强调:“世界记忆项目关注的重心是文献遗产的保存与获取,而非其阐释或历史争端的解决。这应该是历史学家、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参与历史事件的争端,也不偏袒任何一方,更不一定赞同正在接受评估或已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中表达的任何观点。”[24]由此观之,从官方的角度而言,世界记忆项目保存困难遗产的初衷就是,希望人们能通过档案文献所展示出的历史真相,以极具情感共鸣的记忆,警示人们永远不要再制造苦难,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在一些遗产研究中,遗产被理解为根据当代社会的政治和社会需求,通过不同的记忆冲突而构建的社会过程,“遗产化”赋予遗产加深集体记忆和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作用。而困难遗产的特殊性导致它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价值,为了完成价值实现,国家可能会采用政治、外交手段表达自己强硬的态度,由此引发遗产、记忆层面上的冲突与矛盾,这是在世界记忆项目的困难遗产保护中频频发生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2.依托档案文献展演,构建世界共同记忆。困难遗产往往被认为与伤痛、苦难相关,其中包含了复杂的遗产化过程。面对国家间不同立场形成的不同解读,从唤起创伤性集体记忆和带有情感的原始事件,到后来不同利益集体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冲突[25],困难遗产往往不可避免争议。而此时档案文献则成为其中最有力的证明。对于同一段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而其背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正义不能被隐藏和遗忘。无论是二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还是我国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文献都在以记录的方式留下历史的印痕,成为记忆展演与固化的原材料。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而言,档案文献并不是为维护正义而生,但是它记录社会生活,蛰伏于社会常态时期,其真实性为调解社会矛盾、维护历史正义奠定了证据基础[26]。
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emoires)理论中,他将档案馆等记忆机构看作“记忆之场”,鼓励原始史料的使用,强调了档案文献在集体记忆与民族意志构建中的象征作用与认同价值[27]。从记忆展演与复刻的角度来看,历史事件在脱离了它所发生的场所之后,重新被人们用文字、声音、影像等媒介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历史叙事的手段,也是记忆被不断筛选和重塑的过程。正是记忆不断凝聚,历史对现有的记忆不断“转变、塑造和固化”,才使得历史和记忆不断往复,形成“记忆的堡垒”。困难遗产中因为立场而产生的争议可以通过档案文献来调和矛盾,以真实的叙事实现历史真相的还原,维护历史正义与记忆安全,以最初原料的复刻、展演完成人类共同记忆的构建,将“民族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避免集体遗忘症的发生。
3.正确处理困难遗产,推动国家和平共建。困难遗产作为带有一定负面情绪的遗产,时常成为遗产保护中各国争论的焦点。作为真实的记录,困难遗产可以较快地建立起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唤起群体对于当时历史事件的情感共鸣,加深现在与未来的凝聚团结。而从社会公平与历史正义的角度而言,正确处理困难遗产也可以促进“加害国”对于错误行为的改正与承担,寻求理解与沟通。以善于自省的德国为例,建造柏林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保护魏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遗址并建造纪念馆,都是在利用困难遗产达成“以史为鉴”的目的,通过博物馆、纪念馆、展览、影片等形式把参观者带入情境,将观者与被观者融合起来,帮助理解战争历史,创造原谅与和解的条件。就此可以得出,面对困难遗产的处理,将一些苦痛的历史坦然地置于公共文化场所之中,在认真保存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同时,也可以引发人类的思考,为“加害国”承担责任提供了途径,也为国家间互相理解、共建和平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除此之外,困难遗产也可以帮助建立各国面对自然灾难的合作。1665—1666 年伦敦大瘟疫中,亚姆村的抗疫故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其瘟疫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对于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策略、疫情后的记忆构建和产业发展,颇有值得借鉴和深思之处。对于此类困难遗产的保护,一方面可以借助前人总结的经验帮助我们应对现阶段的难题,实现各国准确高效的互帮互助;另一方面也能为未来可能的突发事件做好储备,以备不时之需。由此可见,尽管困难遗产代表残酷的历史真相,包含着受害者的苦痛与创伤,但是正确处理困难遗产可以帮助推动和平合作,减少政治障碍。
以促进文献遗产的保护与获取为首要目标,世界记忆项目的建立其实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想——找寻逝去的记忆。随着文献遗产揭示出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公之于世,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知情权得到保障,而历史记忆中展现出的正义、自由、和平与抗争也将成为鼓舞各族人民不断前行的动力[28]。困难遗产警示人们永远不要再制造这些苦难,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这一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人之思想中共筑和平”的想法不谋而合。倘若为了私欲企图篡改历史,将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遗产“政治化”,那么国家间的关系也将变得更加难以调和,共建和平的愿望也将只是一句“口号”。
“总有记忆不能也不应该被忘却。”在重视文化认同与国家身份的今天,我们既要关注困难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要时刻警惕日本这种矫饰欺瞒的叙事态度。我们应当正视历史,坚持维护历史记忆正义,排除世界记忆项目中的政治干扰,为记忆遗产的保护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也为实现“以史为鉴、共建和平”的初衷贡献国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