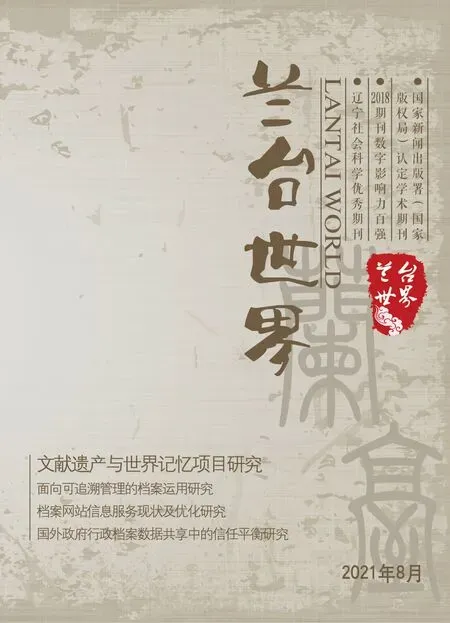记忆遗产的历史正义与政治挑战——世界记忆项目发展中的变革与重塑
朱传宇 施玥馨 王玉珏
记忆遗产是人类集体记忆的精华,其通常以文献为载体,凝结着人类历史文化、思想智慧的结晶。为保护与传承人类的共同记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于1992 年创立世界记忆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也称“世界记忆工程”“世界记忆遗产”)。该项目与世界遗产项目(World Heritage)、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共称为教科文组织的“三大遗产旗舰项目”。
经过近30 年的发展,世界记忆项目在确立记忆遗产政策法规、举办多样记忆遗产活动、提升公众记忆遗产认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获得广泛认可的全球性遗产项目。目前,世界记忆项目已建立亚太、非洲、拉美及加勒比等三个地区委员会,并在中国(1995)、波兰(1996)、澳大利亚(2000)、巴西(2004)等92 个国家建立国家委员会[1]。截至2017 年(最后一次评审),全球共432 项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我国入选13 项,排在德国、英国、波兰、荷兰、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之后,居第八位[2]。此外,在世界记忆项目的推动下,各国纷纷建立国家级名录,如《澳大利亚世界记忆名录》(Australian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2001)、《英 国 世 界 记 忆名 录》(UK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2010)和《加拿大世界记忆名录》(Canada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2017)等。我国于2002 年建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此后又建立《浙江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四川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等地方名录。各级各类文献遗产名录的建立,盘点了不同级别记忆遗产的“家底”,有效推动了世界各地记忆遗产的保护工作。
然而,在推动记忆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世界记忆项目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例如,在当前“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评选体系下,《世界记忆名录》入选情况与项目发展状况极不均衡:欧洲入选项目占比超过50%,而非洲地区和阿拉伯地区仅占7%。近年来,《切·格瓦拉的生活与作品》《巴勒斯坦解放海报集》等“争议遗产”(Difficult /Dissonant Heritage)的入选,造成“记忆正义”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矛盾与争议[3]75-76。2015 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后,日本政府以会费为要挟向教科文组织施压,并以透明性、公正性不足为由,要求该项目重塑法律框架、进行全面审查(Comprehensive Review)。由专家主导(Expert-led)的遗产项目有被进一步政治化的危险[3]91。
一、世界记忆项目发展面临困境
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致力于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保护,践行“在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这一基本理念。然而,由于世界记忆项目设立于“通信司”(有别于世界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设立于“文化司”)等顶层设计、治理模式层面因素的影响,世界记忆项目与其他两项遗产项目在组织管理、资金和影响力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部分争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教科文组织被迫卷入政治历史纷争。这些问题使世界记忆项目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
1.组织机构松散,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与运行。与世界遗产项目、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比,世界记忆项目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支持。在政策层面,世界记忆项目以“指导方针”(Guideline)和“建议书”(Recommendation)为执行依据,而世界遗产项目、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则以“公约”(Convention)为执行依据。执行依据的不同影响了遗产项目实施的过程与结果。公约是教科文组织最具法律效力的文件形式,缔约国必须承诺遵守公约内容。建议书无须国家批准,仅推荐成员国适用其规则。指导方针则为参考性文件,对国家不具有法律效力,约束力低。因此,世界遗产项目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缔约国参与、协商并实施,而世界记忆项目则是由专家领导的国际非政府项目,对国家的约束力和号召力不高。
在人员管理层面,世界遗产项目有许多全职工作人员,而世界记忆项目则完全依靠遗产专家“志愿”开展工作。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雷·埃德蒙森(Ray Edmondson)于2011 年教科文组织第四届大会上表示,世界遗产项目有数百名工作人员,而世界记忆项目甚至没有一位全职工作人员,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4]。与世界遗产项目数量庞大的人员体系相比,世界记忆项目仅有“兼职志愿者”,必然会造成人手不足、人员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下等组织管理问题。
在组织架构层面,世界遗产项目以缔约国为基础,共同构成缔约国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并从缔约国中选出代表,构成负责具体事务的世界遗产委员会(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5]。各缔约国与管理机构联系紧密。世界记忆项目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由遗产专家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IAC),最终决策权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教科文组织大会掌控。组织架构为“世界——区域——国家”三级管理体制,各级都由委员会及其附属支持机构组成。三级管理机构之间彼此独立,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且世界和地区两级机构工作人员由仅代表个人的专家任职,不代表国家[6]。这种相对松散的组织架构,优势在于专业性强、灵活度高,但也导致了缺乏有效推动机制的劣势,可能会出现各级委员会间联系不紧密、工作效率低等问题。
2.获得资助较少,缺乏足够的运行资金支持。世界记忆项目在资金方面也存在一定困难。世界遗产项目资金较为充足,《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规定成立“世界遗产基金”(World Heritage Fund)用于项目开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多家机构积极为保护文化遗产提供资金支持,部分发达国家也纷纷慷慨解囊,支援别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7]。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仅有“世界非物质遗产基金”(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nd)的支持,还有日本、欧盟、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等18 个国家、组织或机构建立信托基金,对项目运行及人员管理进行资金援助[8]。两个项目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强制缴纳和自愿捐款。依照公约规定,缔约国需要每年缴纳部分费用作为项目基金。此外,为支持世界遗产保护,也有部分国家和组织会对基金进行捐款。
尽管世界记忆项目也建立了“世界记忆基金”(The Memory of the World Fund),但是该基金主要来源于教科文组织的常规项目预算和其他组织或政府的捐赠[9]。与其余两个项目相比,既缺乏其他国际组织与机构的关注,也没有相关国家或政府对其进行支持,可获得的资金较少且不稳定。此外,韩国与世界记忆项目于2004年联合设立“‘直指’世界记忆遗产奖”(UNESCO/Jikji Memory of the World Prize)。由韩国每两年出资3 万美元,用以奖励为保护和获取记忆遗产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或机构[10]。然而,用于世界记忆项目自身运营的经费仍面临着资金数量少、来源不稳定等问题。
3.政府与公众关注不足,缺乏应有的社会影响力。世界记忆项目相关报道、新闻或者宣传材料匮乏,导致公众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有限。就国内的传播情况而言,采用搜索引擎检索有关于世界记忆项目的网页。以“世界记忆项目”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共得到与世界记忆项目相关的82900 个结果。以“世界遗产项目——(文化)”为检索式,得到292000 个结果,约为世界记忆项目的三倍。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9470000 个结果,文件和网页数量为世界记忆项目的百余倍,足见世界记忆项目在国内的传播力度和范围远不及另外两个遗产项目。
就国外传播情况而言,在YouTube 视频平台上分别对世界记忆项目、世界遗产项目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中英文检索,截至2021 年5 月11 日,观看数在1 万次及以上的视频数量分别为4 个、170 个、36 个。可以看出,相较于其他遗产项目,世界记忆项目的视频数量和传播力较低。
在世界记忆项目的有关视频中,播放数量最多的视频为介绍韩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白云和尚抄录的《佛祖直指心体要节》(Buljo jikji simche yojeol),且韩国另一个介绍《东医宝鉴》(DongUiBoGam)的视频观看量破万,可见韩国更加注重对外宣传本国记忆遗产。在YouTube 平台上,中国参与世界记忆项目的相关视频共10 个,均为《南京大屠杀档案》这一争议遗产,视频主题主要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价值、日本对《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不满和中国外交部对日本态度的回击。《黄帝内经》等记忆遗产的视频较多,但更加专注于记忆遗产自身内容和价值,极少对其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进行宣传。总体来看,中国对本国记忆遗产和参与世界记忆项目宣传较少。
4.争议遗产的入选,引发遗产话语的政治争夺。世界记忆项目旨在保护记忆遗产,以避免人类集体记忆的消失。部分在政治、历史等方面具有一定争议的记忆遗产,往往承载着集体语境下的历史性“创伤记忆”。特别是由战争等因素导致的文化创伤[11],应当与其他记忆遗产受到同样公平公正的保护。目前已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记忆遗产中,就包括“战争与外交记忆”“奴隶制记忆”“殖民记忆”等与精神创伤密切相关的记忆主题[12]。增强对“创伤记忆”的保护和国际认同,能够让世界记住伤痛,提升全人类对创伤危害的认知,以达到警示教育的效果。
承载着“创伤记忆”的记忆遗产在申报时极有可能引发争议,甚至引起政治矛盾。《法兰克福·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涵盖1963 年至1965 年间法兰克福·奥斯维辛集中营历时183 天的审判文件,引发了世界对种族、政治屠杀的关注和批判。在申报过程中,由于世界遗产委员会部分成员认为世界遗产的标准是为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但奥斯维辛集中营却笼罩了创伤、大屠杀等悲剧色彩,因此将其推迟一年审议[13]。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的申遗过程也充满了政治博弈。1993 年,美国为宣传其在核领域的科学成就,提议将广岛原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但是引发了民众的反核情绪,美国退出申报。此后,日本以受害者视角将原爆遗址论述为受害者苦难记忆的象征,此举引发了美国和中国的反对,这不仅给太平洋战争中受侵略的美国贴上侵略者标签,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造成伤害。但如今二者均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争议遗产”中的“创伤记忆”越来越受到国际重视,各国也更加注重通过遗产展现国家形象。
近几年来,某些国家企图通过经济与政治影响,将《世界记忆名录》评审规则政治化,这一行为造成了世界记忆项目的暂时停摆,并引起项目内部改革。
5.《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激化矛盾。《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时遭遇了重重障碍,日本采取一系列行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影响该项记忆遗产的评审。2015 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后,引发了日本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强烈反对。水间政宪等人撰文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真实性,对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进行“批判”[14]。
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作出了一系列行动,并采取外交手段封锁了这项入选遗产。地区历史战争逐渐扩大为国际舞台上的博弈,世界记忆项目也被卷入纷争的旋涡。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的后任者驰浩在与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会谈时提出,要改善世界记忆项目评审制度,推进评审过程透明化,并暗示日本将停止缴纳会费和其他特定项目的专项资金[15]。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也曾表示,“日本已敦促教科文组织改进遗产项目审查程序,并决定拒绝向其缴纳今年的会费”[16]。
面对日本撤出资金的威胁,教科文组织不得不推迟名录申请提交时间,原应公开于网站上的候选名单也在发布后不久被删除。2017 年,这场冲突达到高潮,世界记忆项目受到重创。教科文组织宣布暂停申报并冻结《世界记忆名录》,同时将改革世界记忆项目[3]103。世界记忆项目接近停摆这一现实,究其本质是政治力量对世界记忆项目的介入,使一直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国家间的矛盾下日益激化。
二、世界记忆项目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议题
在现实困境面前,世界记忆项目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发展问题。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其地域发展极为不平衡:欧美文化导向严重,非洲和阿拉伯等地区国家入选遗产数量较少。同时,由于世界记忆项目缺乏公约性文件,导致项目约束性与强制力较弱。
是否“公约化”,以及如何解决公约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化”问题;如何对项目进行法律框架重塑,且坚守其“寻求世界共同记忆”的初衷,避免过度政治化可能对项目造成的损害;如何对待争议遗产入选可能会带来的政治阻挠与维护历史正义之剑的平衡等问题,均成为世界记忆项目发展的制约性、关键性因素。
1.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遗产的地区不均衡性。世界记忆项目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同一地区不同国家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截至目前,《世界记忆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欧洲及北美地区入选记忆遗产274 项,数量居于首位,占总数的52%;亚太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分别入选116、93 项,占22%、18%;然而,非洲地区与阿拉伯地区仅分别入选13、7 项,占总数的5%、2%。从入选《名录》的数量可以明显看出,欧美国家占据主要席位,《名录》更多是西方遗产话语的产物。
从项目评审专家的分布来看,国际咨询委员会相对比较注重地域的平衡性,历届均有分别来自五大地区的成员。本届(第13 届)国际咨询委员会的14 名成员中,包括欧美地区5 名,阿拉伯地区3 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2 名,亚太地区2 名,非洲地区2 名。尽管各地区均有分布,但欧美地区专家人数最多,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纵观历届国际咨询委员会专家分布,始终为欧美地区的成员居多,总体占到成员总数的35%。评审专家仍为欧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在项目评审时受西方话语体系和西方评判观念影响更为深刻。
同一地区不同国家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益凸显。欧洲和北美地区国家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记忆遗产数量从1 项到23 项不等,不同国家间数量差距较大。非洲地区共计入选24 项记忆遗产,涉及14 个提名国家。其分布呈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英语区、法语区国家申请数量较多,分别占比50%和28%。主要申报国有:南非入选5 项,塞内加尔、马里分别入选3 项,占全非洲总数量的三分之一。可见在非洲地区国家之间发展不均衡。
地区、语言分布的不均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文化多样性”理念不相符合。世界遗产专家布雷塔·鲁道夫(Britta Rudolff)在2011 年第四届世界记忆国际大会上提出,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记忆遗产似乎“反映了19 世纪全球权力结构的记忆,而不是21 世纪的世界记忆”[17]。这种西方权威遗产话语体系(Au 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18]预设了遗产的意义和本质,实际上是在权威话语框定的语境中重新对遗产进行定义、命名、评判与管理[19]。从根本上而言,权威遗产话语是一种文化强权话语,会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加速标准之外其他遗产的消亡[20]。在看似公正科学的评价标准背后,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和专家话语的知识体系和审美取向[21]。因此,在欧洲中心话语体系导向下的评审,不仅会严重影响文化公平,甚至可能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记忆安全。
2.《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的建议书》是否“公约化”,教科文组织的法律文件形式主要分为公约(Convention)、建议(Recommendation)和宣言(Declaration)三个级别,其法律效力与约束力依次减弱[22]。作为最高等级的政策文件,公约不仅能够为名录带来更加坚实的地位和有力的支持,还有利于提升全世界的遗产保护意识。
1972 年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3 年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目前,二者分别有194 和180 个缔约国。公约的颁布一方面形成了世界层面的遗产保护原则与宗旨;另一方面也增进了缔约国对项目评审的支持及相关遗产的保护。
指导方针并非强制性条例,仅对各国实施记忆遗产保护项目进行指导。在现实中,世界记忆项目的纲领性文件——《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方针》作用和影响力较弱。因此,是否将世界记忆项目的指导方针转换成公约成为亟待解决的议题。世界记忆项目建立公约有利于提升项目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强调记忆遗产的重要地位。在世界记忆项目不断拓宽深度和广度的同时,理应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框架与指导政策。
在2012 年世界记忆专家会议上,与会者就“世界记忆项目是否应该建立公约”产生分歧。以雷·埃德蒙森为代表的专家认为,世界记忆项目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对记忆遗产的保护优先级较低。与建筑遗产、自然遗产或非物质遗产等文化遗产相比,记忆遗产对人类社会同等重要,但在地位上却远低于前者。然而,以林德尔·普洛特(Lyndell Prott)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公约必然会带来沉重的外交和政治负担,尤其对部分小国而言[3]60-66。
此外,公约也会使世界记忆项目的专家导向机制受到冲击,为记忆遗产活动增添更多政治牵制。与公约相比,出台“建议”似乎更为适当。建议具有迅速调整的灵活性,能够快速适应现代记忆遗产载体的技术演变,也同样能提高成员国对世界记忆项目的认知。就当时的结果而言,反对建立公约的意见占据上风,因此会议作出了出台《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的决定。但建立公约的声音并没有因此而绝迹,2022 年世界记忆项目建立30 周年将会是又一个关键讨论时期,届时《建议书》是否会升级为公约,还有待继续关注。
3.是否沿袭“专家型”项目评审机制。世界记忆项目是由专家领导的国际非政府项目。《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方针》提出,国际咨询委员会是世界记忆项目的最高机构,由14 名国际专家组成。专家为非政府机构成员,以个人身份任职。其遴选应以其在保护记忆遗产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依据,并适当考虑地域和性别代表性。该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规范世界记忆项目运作、管理《世界记忆名录》、加强世界记忆基金管理、促进世界记忆项目宣传、推进记忆遗产数字化保存和地区委员会及国家委员会建设等工作。
在项目评审机制方面,世界记忆不同于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其他遗产项目。这些项目采取“政府导向”,由缔约国政府指派代表构成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和评审项目的委员会成员均代表各自国家身份,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世界记忆项目道德准则》(the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Code of Ethics)则明确要求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必须是以个人身份任职的专家,而不是国家、政府或其他实体的代表。在行使其职责时,他们不寻求或接受政府、机构或其他外部机构的指示[23]。
现有的“专家型”项目运行机制在保证客观性方面存在优势。专家以个人身份任职,不代表国家、不接受政府指示。且每位成员任期为4 年,仅可连任一次。国际咨询委员会每两年进行一次成员更替,每次更换半数成员。用任职周期等条件对专家进行约束,在评审过程中以记忆遗产自身价值为依据进行去政治化评判,保证评审的客观性。
但这一项目运行机制也存在部分缺陷。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多为档案馆、图书馆等记忆机构工作人员或记忆遗产专家学者,也存在政府顾问、法学学者等,从事的研究复杂多样,对其专业性的判断较为困难。委员会13 届人员构成中,来自欧洲的专家学者有6届人数达到5 人及以上,占比较大,存在欧美国家的文化垄断风险。因此,“专家型”项目运行机制还需要注重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度,通过法规、条约等要求对专家进行政治上的约束,尽量摒除因国家利益带来的审查偏见。同时建立监督机制,对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进行警示。
4.如何解决“争议遗产”入选引发的政治矛盾。世界记忆项目始终保持自身开放性,欢迎可能未被主流政治与意识形态认可的“负面记忆”(negative memory)。这类承载负面记忆的记忆遗产能够使人超越史学家视角,重新审视、认识和阐明历史事件,从而缅怀那些在传统史学中缺乏关注的弱势群体和受压迫者[3]95。这种对负面记忆、创伤记忆的支持体现了世界记忆项目宏大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和倡导。
然而,“负面”也往往伴随着争议与矛盾。创伤记忆产生的一项重要因素就是人为导致的战争。在剧烈的冲突面前,战争双方必然有不同的立场,这就导致不同立场的族群面对同一项记忆遗产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与记忆,久而久之形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尽管存在争议,但这些记忆遗产同样可能具有世界价值,具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条件。有时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并不会平息纷争,反而会放大争议,甚至为教科文组织带来棘手之事。
面对争议遗产,教科文组织的态度更倾向于“不予置评”。世界记忆项目仅关注记忆遗产本身,在纷争中始终秉持中立态度,没有立场倾向。世界记忆专家的义务在于鉴定记忆遗产的世界价值,解决历史争议的任务应由历史学家来承担。正如《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方针》中所言:“世界记忆项目关注的重心是记忆遗产的保存与获取,而非其阐释或历史争端的解决。这应该是历史学家、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职责。”[24]
尽管主观中立,但在客观层面上,教科文组织仍然会被迫卷入历史争端之中。目前面对争议遗产,教科文组织仅表明中立态度,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对争议事件进行处理。如果因遗产有争议就将其排除于《世界记忆名录》之外,与世界记忆项目倡导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理念不符。但若争议事件多发且难以解决,严重影响到世界记忆项目自身发展,未来世界记忆项目在面对争议遗产时可能会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5.如何重塑世界记忆项目法律框架。在以《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引发的争议中,日本以透明性、公正性不足为借口,要求重塑世界记忆项目法律框架。世界记忆项目受到透明性、公正性不足的指责,固然有日本反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的政治因素作祟,实际上也反映出在评选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国际咨询委员会议事规定》中明确指出,《世界记忆名录》和“‘直指’世界记忆遗产奖”的评选投票过程应非公开进行,投票过程拒绝媒体与游说团体出席[25]。这一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界因素对专家投票过程的干扰,但同时也将最为重要的投票环节封闭起来。缺乏第三方监督的流程很难让公众对其透明性与公正性认可。雷·埃德蒙森也认为,世界记忆项目中“存在着有害的权力斗争、隐瞒信息、判断失误、沟通不畅和缺乏透明度等问题”[3]86。
随着世界记忆项目在流程和管理上的缺陷日渐显现,教科文组织执行局(Executive Board)表示有必要“让世界记忆项目重回正轨”[26]。因此,世界记忆法律框架将在保持“专家型”项目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针对“透明性、公正性不足”这一问题重点实现重塑。如,可能会倾向于进一步细化《世界记忆名录》评审过程,增强评审过程的公开性监督;明确专家评选与推荐机制,对专家进行更多约束,以减少失范行为等。在法律框架中强化《世界记忆名录》评审的公正性与透明性,从而在程序层面最大限度减少争议性事件的发生,推动世界记忆项目平稳运行。
三、世界记忆项目转型中的中国参与
在世界记忆项目面临现实困境、实现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记忆遗产大国理应积极参与,为项目发展和记忆遗产保护提供多方面支持,既推动国内记忆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也提升我国在国际记忆遗产领域的参与度与话语权。同时,我国始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世界记忆项目运行,也是保护人类共同记忆、促进文化多样繁荣的体现。
1.支持对创伤记忆的纪念,维护历史记忆安全与正义。世界记忆项目致力于保护全人类共同的记忆,既包括辉煌灿烂的文化记忆,也包括痛苦的创伤记忆。目前,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创伤记忆遗产涉及战争、种族隔离、殖民统治等多个主题。《南非自由斗争档案集》(Liberation Struggle Living Archive Collection)以视听档案的形式揭示种族隔离统治下的南非历史[27],其中关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视频资料详细记录了其获罪原因、获释过程以及就职典礼、演讲等活动,能够帮助南非乃至世界人民更深入和细致地了解种族隔离带给社会的危害;《安妮日记》是德籍犹太人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于躲避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时所写的日记,其在揭露二战时期纳粹党罪恶的同时,也象征着人类对和平的向往与渴望;《贝宁殖民地档案》《加勒比地区17—19 世纪奴役非洲奴隶的档案》及《黑人和奴隶档案》等都揭示着殖民统治与贩卖黑奴的黑暗历史。随着纳粹的倒台,殖民统治、奴隶贸易等落后思想的改变,如果不加以记忆,曾经黑暗的历史真相将逐渐被后世所遗忘。社会可能重蹈覆辙,只有记住、留下这些记忆,才能从中学习、反思,构建更和谐的国际社会,更好地维护世界民族的平等。
中国支持对创伤记忆的纪念,铭记创伤是对受害人民最基本的尊重。唯有记住伤痛,才可从中探寻正确的价值观,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才能在战争记忆中看到和平的不易和美好,真正“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因此,中国积极推送《南京大屠杀档案》《“慰安妇”档案》和《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力图将民族记忆构建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获得国际认同,从思想上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2.维护遗产项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真实性是记忆遗产的重要特征,具体指遗产项目应保持原始状态,是真实的、未经篡改的原件,而非复制品、伪造品或篡改品。真实的档案一方面是指档案本体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是指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即历史的真实[28]。世界遗产项目、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世界记忆项目的审核标准中均包含真实性与完整性。文化遗产类型多样、数量繁多,在进行评判和保护的过程中坚持真实性原则,不仅要求我们尽量争取获得第一手资料、找准找对收集对象,而且对于收集到的资料还要通过查寻史料追本溯源式地全方位考证[29]。世界记忆项目关注的是原始资料的保存和获取,而不是其解释或历史争端的解决。中国坚持维护遗产项目的真实性,用真实的记忆遗产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
客观性是在申报、评判记忆遗产等过程中参与主体保持客观的立场,使用客观的标准,不受国家利益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不掺杂个人情感和自身好恶。在世界记忆项目中,为确保评审客观性,名录小组委员会以及国际咨询委员会应与申报者保持距离,免受利益诱惑与不当游说的困扰。
中国维护遗产项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从评选流程的客观真实,维护项目的权威性和公信度,用入选遗产客观真实记录历史,保障公民对人类历史与过去的知情权,让世界窥见真实的历史、了解文明的进程。
3.维护世界文化与记忆的多样性。教科文组织通过公布《多元文化主义——应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政策》(1995)、《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 年)等多部文件向世界宣告:文化多样性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对人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多样性指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30]。世界文化与记忆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丰富的体现,世界遗产项目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理念与价值取向中均明确说明重视文化多样性与保护整体性。世界记忆项目的使命之一即为以最适当的技术促进保存世界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记忆遗产,这一使命要求世界记忆项目鼓励广泛、无限制地获取所有记忆遗产。
《世界记忆名录》入选记忆遗产主题多样、载体丰富。入选的记忆遗产时间跨度长、地域广泛,特别是非洲地区多数入选记忆遗产主题呈现出多元性、综合性等特征,集中反映某一时期社会的整体面貌。中国坚决维护世界文化与记忆的多样性,支持世界遗产项目中对多样文化的平等对待和尊重。
4.积极推动世界记忆项目的健康发展。在参与世界记忆项目具体事务方面,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其一,参与《建议书》的修订。《建议书》是教科文组织首个全面涉及记忆遗产领域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成员国需定期报告执行情况,为世界记忆项目提供了立法基础。其实施对象是教科文组织的全体成员国,是对各国政府发出的建议与倡导,相较于原来的指导方针具有更强的号召性和执行力。《建议书》还存在是否应该出台“公约”性文件、在多大程度上强调与保存数字文件、适用范围等问题有待解决和明确。中国作为文化强国,应始终支持世界记忆项目的顺利运行,积极参与《建议书》的修订,在国际舞台传达出中国声音和中国想法。
其二,对数字记忆遗产保护提出建议。《建议书》将“数字遗产”专门写入标题,表明世界对数字遗产的重视。中国各界学者已经对数字遗产保护和记忆遗产数字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探究,如建设数字敦煌数据库、“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字研究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等。在学术研究与实践项目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总结数字遗产保护经验,并据此为国际数字遗产保护提供建议。
其三,完善中国记忆遗产项目体系。中国在2000年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形成了一个世界、亚太地区和中国的连贯的记忆工程链。在国内,各省份也开展了地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使文献遗产名录覆盖到“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各个层面,并通过开展中国记忆项目、城市记忆项目、乡村记忆项目等多个记忆项目,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中国记忆遗产项目体系不断充实完善,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均形成了记忆遗产项目保护方针和计划,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和地方经验的保护政策和遗产名录。
其四,加强四个世界记忆学术中心的工作。目前,世界记忆项目在全球共建立五个学术中心,中国即占据四个,分别为世界记忆项目澳门学术中心、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世界记忆项目福建学术中心和世界记忆项目苏州学术中心。这四个学术中心通过召开专家主题研讨会议、开展世界记忆项目进校园、开发档案文献遗产相关课程等活动,对世界记忆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进行讨论和研究,促进世界记忆项目的宣传,提升公众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意识。四个学术中心仍需不断拓展活动边界、创新活动形式,更好地为世界记忆项目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我国作为记忆遗产大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力量的坚定支持者,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理应运用中国智慧、发挥中国力量,多举办积极、务实、可行的各类记忆遗产保护活动,为世界记忆遗产保护贡献新的活力。作为记忆遗产保护的倡导方,中国理应积极入局,推动世界记忆项目转型,以实际行动支持对创伤记忆的纪念,铭记苦难历史,将和平理念根植于人们心中;维护世界记忆遗产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确保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推动文化与记忆的多样性发展,尊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参与世界记忆国际政策的制定与修改,完善中国记忆遗产项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