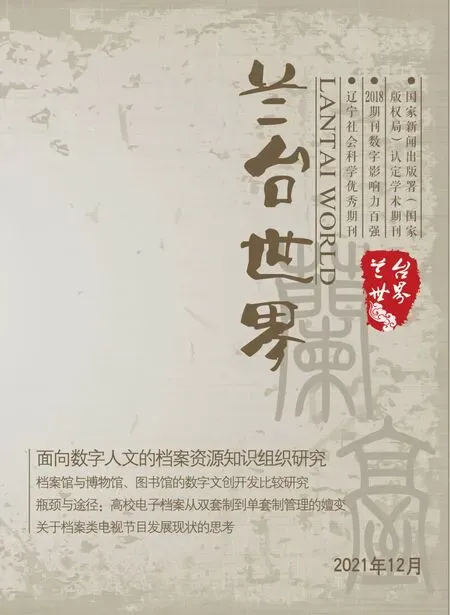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研究
罗应梅 姚 红 黄 凯 赵财霞 张 婷
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曾经入藏着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文献集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由乾隆皇帝钦定,纪晓岚主持编撰,成书后抄成七部分藏于北京文渊阁、文源阁及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文津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七处。七部《四库全书》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炮火硝烟和颠沛流离,现仅存世四部。文澜阁《四库全书》便是其中之一,也是存世库书中经历最为坎坷的一部。自1861年太平军二度攻占杭州阁书被毁到民国末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先后被补抄4次,即清光绪年丁丙补抄3103种、1915年钱恂补抄33种、1923年张宗祥补抄211种、1934年陈训慈补抄1种。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七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其价值远高于现存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成为“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七七事变后,文澜阁《四库全书》又为避寇而西迁,从1937年8月4日《四库全书》装箱离馆,到1946年7月5日重回杭州,经历了长达8年零11个月的“抗战苦旅”,涌现出很多“文军护书”的典型故事,展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人文精神和保护文物、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一、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始末
1.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1]。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便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以便有计划地掠夺中国图书文献和珍贵文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将搜集各种中国古籍作为其主要任务;1937年12月成立的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和操纵的所谓“民众团体”——“新民会”,除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外,还负责搜集沦陷区的图书文献;南京沦陷后,日军更是明目张胆地成立了“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运输劫掠的图书,编纂劫掠图书的目录。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的组织,部分日本军人、学者自发地或有组织地掠夺中国图书典籍,配合和支持对中国的侵略。纵观近代日本的对华战争,除了进行军事打击、经济掠夺外,他们入侵中国的固定内容之一就是劫掠书籍,他们从来不忘对中华文化瑰宝、图书文献的掠夺。1937年杭州沦陷前陈训慈在日记中写道:“今战事遍及江南浙西,即图书之浩劫已为空前所未有。”[2]如今,这些图书散藏在日本各图书馆,成为研究亚洲文化和历史最好的资料宝库,人们在这些图书馆中可以找到很多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图书。
七七事变后,沪凇会战打响。上海、杭州屡遭敌机轰炸,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随时有被毁或被掠夺的危险。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意识到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被掠夺的危险,深感保护库书责任之重大,果断决定采取转移的办法来保护《四库全书》。他一面向浙江省教育厅报告情况,要求调拨阁书迁移经费,一面动员全体馆员赶制木箱,将库书装箱转移。1937年8月4日阁书顺利运出,开始了西迁旅程。据日本学者记载,1938年2月22日,“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好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幸而库书已经转移,免去了痛失国宝之虞。
2.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与回归。文澜阁《四库全书》于1937年8月4日运出后,经历了首迁富阳渔山,再迁建德松阳坞,三迁浙南龙泉。随后教育部议定阁书迁贵阳,并派浙大协助运书,于1938年4月30日运抵贵阳,点交贵州省立图书馆保管。而在贵阳的藏地也经历了三次变化,先是藏贵州省立图书馆,旋又秘藏张家祠堂,后又转移到北郊地母洞。1944年“黔南事变”爆发,阁书紧急迁运至重庆青木关,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旁的瓦房中,抗战胜利后,才回归杭城。
库书的首迁地点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系该馆编纂夏定域向赵坤良先生请求,用赵家弃置未用之旧宅庋藏库书。负责押运及保管阁书的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中这样记载:“8月1日,全馆职员麇集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3日深夜装竣。计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共228箱。4日晨阁书离馆,运往江干装一大船,余奉命随书出发,负责保管之责。”[3]毛春翔向馆长陈训慈报告阁书藏地情形,“谓地处群山围绕中,旧屋不显,可望不致遭损”[4]147,同时“渔山镇赵姓屋,在山丛中,颇宽敞僻静。主人赵坤珊相遇亦厚,不收凭值”[5]148。但是,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杭州危在旦夕,在渔山都可以清楚地听到爆炸声。11月23日,陈训慈赴富阳查看,与乡民谈及富阳城乡情形,“谓城民多迁乡,乡间亦皇皇。军队过境颇多,已掘长壕,拟将退杭守富也”[6]149。于是,阁书被迫辗转运到建德。
在富阳转运建德途中,因船重水急不得已滞留桐庐,多方寻求帮助皆无果,后幸得浙江大学帮助才将书分批运至建德北乡松阳坞暂存。后又因战事日急,杭城沦陷,建德震动,阁书再一次辗转迁移。先是雇佣民船运书至金华,再觅车转运至龙泉,暂存于县城中心学校。后教育部决定阁书“拟迁贵阳,由浙大协同运迁”,“谓西南僻远,战事不至波及,迁书斯土,可高枕无忧,浙人士亦以为然”[7]。随后,阁书从浙江龙泉再出发,经福建,入江西,再入湖南,由湖南入贵州,于1938年4月30日抵达贵州省立图书馆,9月29日,转藏威清门外张家祠堂,1939年4月8日又搬迁到北郊地母洞。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地母洞秘藏了5年零8个月,1944年底又因日军大举进攻贵州而紧急转运到重庆青木关。抗战胜利后,文澜阁《四库全书》随浙江大学一起,于1946年7月5日回到杭州。竺可桢校长谈到此次库书回归时说:“此次自渝由汽车六辆载运东来,5月7日出发,昨、今始到。原定运费四千万元,现超出已多,押运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长,夏朴山等等。”[8]而回杭过程中的艰辛也是不一般的,毛春翔曾写到“途中麻烦之事,困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
3.历经十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历经沧桑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历次浩劫中几乎陷于毁灭,幸得浙江几代人的侠肝义胆,以及他们在抗战期间与众多国人一道,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保护和捍卫了《四库全书》的安全。但是经历了200多年的洗礼和磨难,库书已有许多封面硬化,书线脱落,部分书页发霉、破损或残缺的问题。为使文化瑰宝得以传承,宝贵精神得以弘扬,库书价值得以延续,杭州出版社与浙江图书馆共同决定影印再造文澜阁《四库全书》,签署了共同合作整理出版协议。经过一年多的翻拍和图像处理,形成了全套精美的影印件。2006年2月22日,库书的经部开机印刷,但因经费不足几经曲折,历经十年的努力,耗资4300余万元,集合政府部门、出版界和民间的力量,才于2015年最终完成。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再一次续写了几代浙江文化人为保存它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起到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积极抢救、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和有效管理”的作用。影印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共1559册,约10亿字,重约5吨,全书篇幅采用大16开本,选用优质木浆纸印制,兼具美观与存真。
二、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详情
1.贵阳秘藏地点三次转移。经过数千里辗转,文澜阁《四库全书》运抵贵阳后,先是藏于贵州省立图书馆内。根据贵州省立图书馆向浙江省立图书馆开具的存书收据显示,寄存于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书籍共计3467部、42536册,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等。由于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是由旧粮道署修缮改造而成,馆藏条件很差,不仅面积狭小,房屋结构也不适合图书馆的业务开展。为改善藏书条件,该馆立即着手新建藏书室,并向贵州省政府和教育厅呈报了《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等,试图赶建书库。但因时局所限,经费困难,贵州省立图书馆新建书库未能建成,只能采用购买现成房屋的方式来解决藏书的问题。经过多次考察筛选,最后决定购买贵阳威清门外张家祠堂作为藏书楼。张家祠堂有大小房屋数十间,房屋结构和质量也都基本符合藏书的要求,只需稍加修缮便可使用。1938年9月28日,库书顺利转入张家祠堂,同时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父子随书入驻张家祠堂着手清点库书,并对在迁移途中翻车落水的3000余册书进行细心曝晒。但是仅仅过了半年,库书又一次被紧急转移到贵阳北郊的地母洞。1939年2月4日,日机轮番轰炸贵阳大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段,房屋损毁无数,火光满天,而秘藏《四库全书》的张家祠堂距离大十字仅2公里,库书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必须再觅安全之藏所。经过多方考察,最终决定将之转移到贵阳城外的许官溪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从此库书在地母洞秘藏了5年零8个月,直到1944年秋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11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贵阳震动,各机关、团体开始组织疏散撤离。教育部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紧急转移,12月8日,库书再次装箱起运,直奔重庆青木关,直至抗战胜利。
2.揭秘文澜阁《四库全书》保存完好之法。阁书西迁与东还,前后历时8年11个月,跨越6省,往返数千里,经历了在转运途中翻车,11箱3000余册书落水事故,以及贵州山洞的潮湿环境及多雨少晴的气候条件,但最后返回杭州时却完好无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通过档案记载和当事人回忆大致可以揭秘一二。
阁书在转运途中,曾在福建浦城至浙江江山的途中,因“险路甚多,运输车中有一辆在离江山峡口不远处倾覆,十一箱翻落池中”,幸有附近村民帮助“入池起箱,另雇他车星夜运达江山县城”,翌日便借城隍庙天井曝晒,但是“书浸水中久,晒两日,水滢如故”,但因“运输时间紧迫,不容久延,即命装箱”,待阁书抵达贵阳转藏于张家祠堂时,保管员夏定域再次“重加曝晒始干,三千余册书,每册每页须细心揭开,夏君竭数月之力,始完成此艰巨工作”。转入北郊地母洞后,面临山洞潮湿的环境,可谓竭尽办法。贵州省政府、教育厅派人亲自考察藏洞,教育部多次派人视察,要求切实改善阁书的洞藏条件,连蒋介石也曾致电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谓“地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但经考察,未见霉坏之书,因此没有再迁。
据档案记载:“为防潮起见,在洞内筑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9]1940年冬,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地母洞书库视察,又提议将洞里的木棚进行改建,盖上瓦,并另建一堵砖墙以确保安全。为进一步改善藏书条件,又将藏书的木台“三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圆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启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积蓄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10]。另外,为了保证库书保持干燥不发霉,还专门制定了春秋两次晒书的惯例,教育部拨专款予以支持,浙大派专人予以指导,严格规范晒书操作流程。从开箱清点、装箱送指定晒书处、晾晒库书、收书捆扎,详点无误后加樟脑粉或樟脑丸,然后用油纸或牛皮纸包盖完善,最后装箱后再用洋钉加固封箱,每一个环节都做得一丝不苟,待下一个晒书季节往复循环。每一项护书的行动,每一个晒书的环节都保证了阁书在艰难的环境下仍能完好无损。
3.还原贵州大学传抄《四库全书》轶事。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州期间,许多当地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使用此书,完善有关贵州的文献典籍,提出了传抄《四库全书》的建议,但因其工程过于浩大,加之经费支拙以及战乱干扰,传抄四库整部改为传抄与西南相关文献珍本。此桩传抄轶事在相关档案中得到还原。1942年9月3日,国立贵州大学张廷休呈函教育部,指出:“查四库全书国学总汇,不仅珍本、孤本坊间颇少流传,即普通典籍书肆刊行讹误百出,鲁鱼亥豕,面目多非。前者钧部计划全部影印,发扬国故,嘉惠士林,举国色忻,跂足仰望,嗣以工程过大,改印珍本。讵抗战军兴,影本复罹浩劫,治国学者莫不同声痛惜。本校办立伊始,图书设备亟待充实,兹拟就浙馆文澜阁四库全书整部在黔之便,抽借传抄,俾秘府瑯环流播黔地。”[11]并拟具了《〈四库全书〉迁移、建库、传抄计划》,拟将库书迁移到花溪。但张廷休的提议很快被教育部驳回,陈训慈也在致张廷休的信函中指出,“若移至邑镇平地,人烟较密之地,即不免有空袭之虞”[12]。随后,张廷休又多次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教育部、浙江省立图书馆等进行沟通和协商抄书事宜。最后教育部提出了折中建议:“查本案前据该校长一再呈请到部,当经慎重考虑,以该书如全部传抄极为不易,且有散失之虞。为应地方人士需要提高西南文化计,权宜办法只能就该书中有关西南文献为外间未经刊印之孤本抽借传抄,抄写工作亦不能离开藏书场所,以免散失”[13]。此后,《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珍本计划》《国立贵州大学、浙江省立图书馆传抄四库全书珍本办法》相继得到核准实施。起初,传抄经费预算46万元,贵州大学希望教育部能够出资60%,其余40%从学校经费中匀支,不足再向社会募捐,但后因传抄范围的变化,1943年6月3日,教育部社字第26375号指令,将“所呈经费概算书表,传抄经费核减为85000元”,并随令拨发传抄经费。传抄《四库全书》的范围“以有关西南文献为限”,国立贵州大学第六次校务会议决定推举柳翼谋、崔萍村、全受仲三先生拟定传抄办法,并分函广西省政府及贵阳文通书局商洽联合进行。文通书局亦“推请谢六逸、张永立、华仲麐三先生会同贵校商讨合作进行各事宜”[14],最终选择的书目共103种3999卷。抄书工作由贵州大学教授、国学大师柳贻徵具体办理,并准予在地母洞口修建茅屋,作保管员工居所,并兼作抄书之用。
三、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的当代意义及价值
1.滋养贵州文化工程,树立贵州文化自信。文澜阁《四库全书》迁黔最直接的价值便是滋养了当时贵州的一大文化工程——民国《贵州通志》,该志始修于1919年,完成于1948年,约800万字,是贵州省志中卷帙最为浩繁、史料最为丰富的一部。该志书编撰耗时30年,数十人参与编辑、校录和采访,纂修该志书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除时局动荡外,史料的收集是其中一大难题,该志经数次增补,最终于1948年正式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迁黔正好弥补了修纂该志的部分资料空缺,为其提供了难得的珍贵史料。已故著名学者李独清教授讲道:“浙江图书馆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贵阳地母洞,教育部有邀请各大学派人校勘是书之意,馆中同人以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府转教育部将趁校勘之便,抄录有关贵州史料,馆中委托我到地母洞翻阅文澜阁图书,将其中涉及黔中的资料钞出。……除有传本者,如陈法《易笺》、乾隆《贵州通志》不钞外,其余片语只字,皆钞录下来,以供修志之用。如任可澄编前事志,于张岳《小山类稿》,每感不足。传世虽有两个刻本,一称选集,全无奏稿,一称全集,奏稿极少,全未涉及贵州。而四库本奏稿中征香炉山的详细奏报,达十余篇。任可澄因得改正某些材料不实的记载。他为宋元人文集中,就有不少涉及贵州山川风土之作,以前均未见过。”[15]民国《贵州通志》的成书,改变了自1771年乾隆《贵州通志》问世以后,一个半世纪以来贵州省志失修的状态,为修志所做的准备工作,可说是贵州建省以来一次较具规模、较有系统的征集贵州文史资料的宏伟工程,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迁黔,填补了诸多贵州史料的空白,鼓舞了每一个贵州学人,极大地增强了贵州人民的文化自信,遗惠后世,功不可没。
2.《四库全书》西迁秘藏是一种文军长征精神。文澜阁《四库全书》从西迁到东还时隔近9年,辗转数千里,无论是起初决定西迁而多方筹措,还是辗转秘藏中精心保护,都表现出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中华儿女保护民族文化瑰宝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展示出他们对国家文化瑰宝的深深热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个人生存尚且不易,更别提像竺可桢校长带领下的浙大师生,陈训慈馆长带领下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同仁,以及黔浙两省为护书而不断努力的人民,他们顶着巨大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保护着中华文化瑰宝。这种精神和行为,正是一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先辈不易,后辈当倍加珍惜,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肩负起传扬库书经典的责任,唯有自强自信才不负前辈重托,才是真正地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3.挖掘西迁秘藏历史,彰显优秀文化品格。文澜阁《四库全书》为避寇远徙数千里,数载秘藏边陲,复又完璧归杭,可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的战斗,是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先有陈训慈馆长未雨绸缪、多方筹措将书运出,后有浙大派车救书于危难,再有黔浙教育厅之经费支持及高度关注,还有库书保管员毛春翔、夏定域等数年如一日精心晒书、护书,改善藏书条件,等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图书馆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华民族万分危难的历史时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已经升华为至高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数千里的库书迁藏路线也承载着宝贵的民族精神,可以说“重建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2000公里抗战苦旅线,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是爱国主义教育难得的好教材”,“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16]。因此,在和平年代,对《四库全书》的迁移秘藏历史进行挖掘和宣传,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重,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更是对优秀文化品格的大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