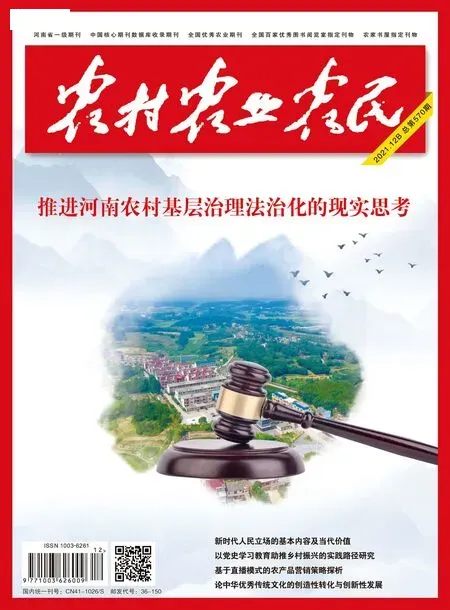精准帮扶与农民的“不精准”舆论
陈小锋
精准的帮扶政策作为精准扶贫策略在过渡时期的延续,应当继续注意“精准”的意义。不过,无论是脱贫攻坚的精准扶贫,还是衔接过渡期的精准帮扶,精准的政策设计都可能遭遇“不精准”的舆论评价。梳理和解释脱贫攻坚时期与衔接过渡阶段“不精准”舆论的生成语境和机制,有助于理解“不精准”舆论的实质,继而改进当下的精准帮扶措施。
一、程度与性质语境中的“不精准”
在脱贫攻坚时期,不少地方采取由贫困发生率而确定贫困名额的操作方法,其结果有时与实际贫困人口数额不完全一致。一般农村社会,个别农户因生活困难而被确定为贫困户,多数农民对此并没有太大疑义,争议经常出现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贫困户的资质问题上。贫困线是一个确切的数字,数字线附近的农民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但是,分化程度不高的人群因为名额配给和硬性的贫困识别线而被分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活水平上模糊的程度差异转化为明显的“是”与“不是”的问题。由此,近乎同质化的人群里因一个数字而有了质的不同。
在另一层意义上,日常生活中的农民与国家直接互动的机会并不多,甚至没有直接互动。扶贫资源是国家的象征,获取扶贫资源对一些农民来讲意味着与国家发生了联系,或许得到资源多少并不重要。
事实上,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各家户的生计方式和经济状况都相互知晓。很多时候,农民或许在意的不是贫困户与否,而是为什么被“区别对待”,“我们都一样,为什么他有,而我却没有?”身份上的差异决定了农民的斤斤计较,从而引起了“不精准”的舆论。
二、科学与经验语境中的“不精准”
过渡时期的精准帮扶除了使低收入或边缘人群摆脱物质贫困,还应包括正向的激励效果,即被帮扶者更加积极地朝着富裕生活的目标而努力。然而,无论是在脱贫攻坚时期,还是当下的过渡时期,从激励效果层面来评估帮扶工作的机制尚未正式形成。
即便是那些被列为低收入农户的评价也可能会有“不精准”的表达,因为给予型的帮扶政策能让农民短时期内困难在一定程度得到缓解。但是物资救助对受助者而言,只会产生“没有不满意”的感觉,而不会收到“满意”的效果,也就是说没有激励效果。那么,在此意义上讲,单一的物资扶持无论力度多大,也不会让农民感觉到被激励。甚至对一些地区或农民而言,不仅没有产生保障作用,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忧虑。特别是在一些帮扶产业的推广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农民的质疑,纵使产业帮扶政策具有良好的初衷,其实践效果被打折扣的现象屡见不鲜。
现实是,反复的科学实验使新技术、新品种有了充分依据。然而,无论农业专家和政府部门如何宣扬新技术、新品种的美好前景,农民都更倾向于认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土地的习性和时令的意义”。新的改变意味着农民要丢弃原有的农业经验,更新自身的知识系统甚至价值理念,而在追求稳定、安全的农业社会里,新的东西还意味着秩序的动荡和风险。在没有看到切实因为更新技术和物种获得明显收益之前,农民不但不会主动去尝试,而且一般都会持有自己的看法,甚至会传出一些谣言。所以,对产业帮扶的“不精准”舆论实际上是基于农民对新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而发生的。
三、客体与主体语境中的“不精准”
一些“客体化”语境中的农业是社会发展的短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拖后腿”的角色,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更是农村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所以,农业是现代社会的附属品,而农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这类认识可能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然而,历史上每一时期的农民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展示其主体性和创造性。斯科特的研究也表明,弱势群体表达意见的方式是谨慎小心的,公开场合会表现出“话语缺失”,私下的讨论里往往会以“诽谤”“诋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一般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如同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弱势的一方学会感知“意见气候”,可能因为发现持有相同意见人数较少而选择沉默,也可能因为意识到意见持有的多数性而大胆表达。
当前防止返贫工作中,类似的主体性问题并不少见。然而,人们的表达已不完全是那样的被动与沉默,不少案例显示农民正在由间接性表达转为直接性表达,表达也由隐蔽的私下领域走向公开场合。特别是一些没有被列入帮扶名单的农民可能走得更远,比如,陕西某县农妇为了获取贫困户资格喝农药威胁基层干部,河北一老人因没有被列为帮扶对象而直接掀翻了乡镇干部的餐桌。
整体而言,处于被动地位的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农民的权利意识开始逐步形成。那么,无论是隐匿的议论,还是公开的抗议,都源于一种主体性视角对“精准”问题的认识。因此,如果不考虑农民的主体性,无论精准扶贫多么精准,农民对此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微词。因此而产生的农民的“不精准”舆论,实质上并不一定是客观的“不精准”,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他们的主体性。
四、国家与地方语境中的“不精准”
农民历来被认为是勤劳善良的代名词,然而,也不乏好逸恶劳之人。这类人的贫困根源在于缺乏主动作为。乡村社会中,人们一般会通过民间舆论对此现象予以谴责,以警示其他人引以为戒。然而,帮扶政策的介入使那一部分精神贫困、好吃懒做的人不但未受惩戒,反而获得变相的“奖赏”,而自食其力的农民可能会感到略有所失,这样一来,乡村社会原有的舆论和道德标准就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可见,新的介入不仅使农民在物质层面的得失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人们坚守的价值体系开始受到挑战,不少人会感到无所适从,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不公平感在乡村社会传播和蔓延。此时的“不精准”舆论,既是对那些精神贫困而被列为帮扶对象的政策安排的质疑,也是对不劳而获者的斥责。也就是说,此时的舆论具有道德评价作用,它是地方价值体系的表现。
不少案例显示,一些基层干部在确定扶持对象时也难免会陷入地方社会网络之中,尽管这种做法不合规,但在地方社会却是“合理”的。事实上,人们争夺帮扶资源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表面上争的是社会帮扶资源,实际上争的是“面子”,体现的是人际关系网和社会地位,因而也形成一种被帮扶就意味着优势感的怪象。
五、结 语
由是观之,农民的“不精准”舆论并不是一些琐碎事实的分歧,它的实质是不同语境中不同认识标准建构的结果。舆论所说的“不精准”不是绝对标准的不合理,在特殊的农村社会里,地方社会情境、农民特质与思维惯习决定了“不精准”的舆论。实践中,农民针对一些问题表面上很少公开质疑,但这并不是农民缺乏主体性意识,而是主体性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基层社会极为复杂,再完善的政策设计,执行过程中都可能在“最后一公里”遭遇质疑的声音。质疑集中在帮扶效果的各种议论,由此产生了“不精准”的舆论。人们表达的直接对象是帮扶资源,然而,其背后隐喻的是地方文化权力。在此意义上的“不精准”舆论可能在所难免,它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毕竟,乡土中国的色彩并没有彻底褪去,理解农民问题需要本土视角与文化自觉。故而,不能因为“不精准”的舆论而盲目否定精准帮扶的成效与基层干部的努力,重要的是要体会农民表达方式、表达机制以及表达语境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完善帮扶工作机制和实践方法,使精准帮扶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