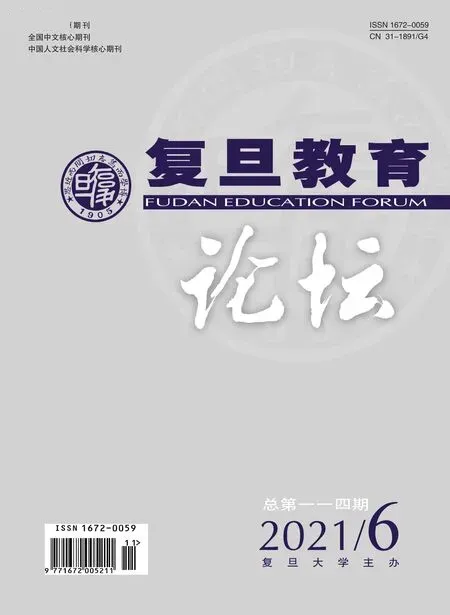疫情折射下日本高等教育的问题与归因
——基于线上教学的视角
蒋 妍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综合研究中心,日本 东京 1698050)
2020 年的新冠疫情迫使全球的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对线下教学转线上教学、留学生不能入境等一系列挑战。疫情暴发时正值日本大学的学年转换时期①,大学要面对的有高考活动、毕业典礼、开学典礼、新教职员工入职说明会等组织层面的运营问题,还有与每位学生、教师个体相关的线上教学转换问题。加上疫情期间公众外出行为受到限制,每个人(从学生到家长)在家的时间增多,使得线上教学受到了学生、家长、大学相关者乃至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在这一年多与新冠疫情共存的生活中,从文部科学省②到各个大学再到教师及学生个人,大家都在努力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与此同时,疫情也让一些日本大学教育改革中的沉疴逐渐浮现出来。
本文将以这次新冠疫情开始到2020-2021学年结束(2021 年3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以及各大学针对线上教学所做的应急措施作为切入点,结合疫情期间日本各大学关于线上教学的调研报告,探讨日本多年来大学教育改革的成果以及一直存在于日本大学教育中的问题以及深层原因。
一、疫情开始前日本开展线上教学的基本局面
日本和中国虽然仅一海之隔,但在大学的基本制度方面却跟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比如日本大多以4 月为新学年的开始,日本的大学中很少提供宿舍。日本的状况自有其特点,以下简要从三个方面概观疫情开始前日本开展线上教学的基本局面。
(一)日本对线上教学的学分认定和教学形式有基本的规定
在日本,除了放送大学③这种主要开展线上教学(包括音频、视频以及网络等形式)的大学以外,也允许一般的全日制大学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即所修的部分学分作为毕业正式学分是被承认的。关于线上教学的学分,基于《大学设置基准》④中的相关条款,同时结合文部科学省2007年修订的告示,其要点如下:
(1)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所需的124个学分中,最多有60个学分可以通过线上教学修得;硕士研究生毕业所需学分则没有此限制。
(2)所修习学分依然遵循学分制的规定,即1学分需对应45小时的学时(包括课内和课外预习复习的时间)。
(3)线上教学形式可以包括实时双向互动形式和非实时双向互动形式。前者指使用一些直播平台进行教学,课堂中需加入小组活动,有跟学生的互动等。后者包括录播课(视频教学)或者是上传学习用的教材到校内的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简称LMS)上,配合适当答疑、反馈完成教学。
这样一来,对于全日制大学本科学生来说,在现有制度且无法预期疫情结束时间的情况下,他们会对自己无法修满毕业所需学分有所担忧。
(二)在疫情开始的时候,适逢日本正在进行有关著作权法的修正
日本学术界一直都很重视学术伦理和著作权,尤其是在2014 年震惊世界的小保方晴子涉嫌学术造假事件之后,对于学术过程中的学术伦理和著作权,比如学术引用规范包括图片、照片的使用就更加重视。线上教学的开展自然会涉及教学中使用的资料、教材、视频、音频资源的传播,以及相关著作权归属问题。疫情开始前,为了推进教育的信息化,文部科学省的关联机构文化厅在2017 年就开始推进著作权法的修正,并成立了一站式处理著作权相关事情的机构“教学目的公众传播补偿金管理协会”(简称SARTRAS)。简单来讲,就是通过网络进行教学活动时,不再需要教师自己去执行烦琐的著作权申请以及确认手续,只需要向该机构交纳补偿金(费用)。但到疫情开始前,关于执行细节,尤其是费用的金额问题一直处在僵持阶段。
(三)在疫情开始前,日本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大学教育改革
日本的大学在政府的指导下从20 世纪90 年代就开始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多,以及少子化的影响,日本的四年制大学在2009年进入了马丁·特罗所分类的“普及化”阶段后,改革的相关举措就更受关注。日本高等教育学者金子元久感叹道:“日本大学教育在20 世纪的关键词就是大学教育改革。”[1]这些改革主要是在《大学设置基准》以及日本文部科学省下设的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日语原文为“答申”)指导下进行的。尤其是2008 年、2012 年以及2018 年咨询报告的发布,确实在日本的高等教育界掀起了波澜。比如:2008 年咨询报告的发布后伴随着《大学设置基准》中对教师发展(FD)的义务化,努力鼓励甚至半强制大学教师进行提高教学技能的活动[2];2012 年的咨询报告强调推进主动型课堂教学(active learning);2018 年的报告强调学习成果的可视化。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一些国立综合性大学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各个大学也不得不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师发展活动。
二、新冠疫情下文部科学省的应对措施
虽然日本的大学总数中,私立大学特别多⑤,但和中国一样,日本的教育也深受政府政策部门的影响。在疫情当中,日本文部科学省是通过一系列通知的方式督促日本各阶段的教育机构进行应对的。根据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企划科科长牛尾则文在2020 年10 月的总结,日本疫情中针对大学教育的具体应对举措可以分为以下5个方面[3]:
(1)承认线上教学所修习学分。前文提到原本毕业所需的124 个学分内只有60 个线上学习学分是被承认的,此规则得到了放宽,同时要求各大学以及教育机构灵活应对医疗实习、教育实习、实验课等实践科目的施行形式。
(2)对线上教学提供资金支持。具体包括系统服务器的维护,线上教学用摄像头以及音频设备的购买,学生移动通信装置的租借,专业人才的配置等。
(3)确保学生的学习机会。通过一系列通知,指导和要求大学开展线上教学。
(4)为留学生提供支援。对象包括日本在海外的留学生以及来日本留学的外国学生,内容涉及奖学金、补助金等。
(5)探讨和制定高考相关手续等方面的灵活应对方案。
从这些对策中,可以看出文部科学省对于线上教学尤为重视。表1 列举了2020 年1 月份疫情开始到2021年3月学年结束这一段时期的疫情发展状况以及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有关教学的文件。

表1 2020学年日本疫情发展状况以及文部科学省关于教学的通知文件
(一)文部科学省针对大学教学发布的通知文件
这些通知文件的内容随着疫情的发展,在主导线上教学开展形式上的侧重上也不同。在新学期开始前的3月24日文部科学省发布了“关于2020年度大学教学的开始”的通知,要求各大学有弹性地使用大学校历、安排教学进度。因疫情的持续发展,4月7日,政府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要求减少外出,实际上多所大学采取了封校措施。因此,许多大学开始将开学时间推迟到4 月底或者5 月初,同时决定开始进行线上教学。
在2020 年4 月疫情严重且各个大学面临开学时,文部科学省的通知内容主要侧重于对线上教学所修习学分的承认。在6 月疫情稍有缓解时,文部科学省发布了“大学应对新冠肺炎的指南”,有意鼓励开展线上加线下的混合形式。只是这时各个大学都疲于应对线上教学,似乎该指南并没有得到有效传达[4]。之后文部科学省的通知也倾向于线下教学的推进,甚至在10月,对媒体宣称要公布线下教学开设率低的大学名单,招来了大学的强烈反对,后不了了之。但在12月23 日公布的大学下半学期教学开展状况的调研报告中,间接公布了这一数据⑥。
(二)大学教学实际状况调研报告以及疫情应对中做得优秀的大学实践案例
表1 中的阴影部分是文部科学省文件中的第二类,即大学开展教学的实际状况调研报告以及疫情应对中做得优秀的大学实践案例。调研报告的具体内容包括教学的开展形式,以及选择各种形式的大学数量、开展的基本情况等。大学实践案例则侧重介绍在推进线下教学中有特色的大学实践,比如同志社大学分阶段性地开展线上教学,宫城大学对教室进行了改造包括撤换固定桌椅等。
除了上述文件方面的支援措施以外,文部科学省在著作权的交涉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与各学会团体等的共同努力和交涉,促使和推进了线上教学相关著作权法的及早修订[5],使线上教学得以顺利进行。
三、新冠疫情下大学的应对措施
如上所示,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主要以发布通知文件的形式对各个大学在疫情中的应对尤其是线上教学的开展进行了基本指导,但落实到大学的一线,应对方式多种多样。现任京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推进中心主任饭吉透[6]用了一个比喻描述当时的情况:有的大学“仅仅给一个游泳圈就让下水”,有的大学“某种程度上对游泳的方法进行指导,并装备好救生工具再让下水”。以下就日本的大学层面所进行的应对措施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构建线上教学环境
疫情的突然到来以及持续时间之久是各大学没有预料到的。因为要转线上教学,一些大学不得不临时去扩充服务器,来构建线上的基础教学环境,或者通过开展校内LMS 使用培训活动来构建线上教学的软环境;另外还有一些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通过给学生发放补助金或者租借给学生无线上网设备等方式来帮助学生构建线上学习的基本环境。在疫情稍微有所好转后,一些大学对教室进行整修,安装通风设备,在教室内放置酒精等消毒品,或者在公共区域搭设塑料隔板,为学生参与线上教学提供物理环境保障。
(二)随疫情发展不断调整教学方针
日本各大学线上教学开展形式也严格遵守前文中提到的《大学设置基准》和文部科学省的告示要求。一线教学中主要采用的线上教学形式有3种:直播课,即使用直播工具(如zoom 等)的实时双向互动教学形式;录播课,即使用幻灯片软件或摄像设备录制的视频形式;资料提示型,即把学习材料上传到学校的LMS系统供学生自行下载(如表2所示)。

表2 文部科学省对线上教学的规定及大学的对应形式
在一年多的具体实践中,各所大学所采用的教学形式根据疫情变化、学生的学习环境以及本校的信息技术资源不断调整。比如2020年4月和5月的疫情初期,日本刚刚展开线上教学,各大学采用的主要教学形式为录播课,主要原因是学生的网络学习环境存在限制,如学生不能进入校园,且有手机流量限制[4]。
到2020 年6 月1 日为止,日本线上教学的开展比例为94.4%;随着疫情的缓解,到2020 年7 月时,开始有部分大学恢复线下教学,出现了线下与线上教学混用的方式[7]。文部科学省在疫情稍微缓解后,也开始倡导大学开展线下教学,且在12 月23 日间接“点名”了线下教学开展比例较低的377 所大学,其中包括国人熟知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但这些大学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表明了线下教学难以展开的理由[7]。
在2020学年末期即2021年3月底的调研中,日本97.4% 的大学计划在2021 学年,将一半以上的教学恢复为线下[7]。实际在进入2021 学年后,日本各地的疫情在不停反复,各个大学的对应也多种多样,有的跟据疫情状况在调整,有的一直保持不变。从教学方式上来讲,大多数学校已经恢复线下教学,采用的是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混合的方式。
(三)开展线上教学相关的各种支援和培训活动
疫情期间如何进行线上教学成了每个大学以及每位教师必须面对的挑战。各个大学纷纷以各种形式展开对线上教学组织运营方式的支援和培训活动,即所谓的教师发展活动。有教师发展中心的大学主要是借助此中心的力量,以及与信息部门的合作,对校内师生进行支援活动。支援和培训活动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层面的,比如如何制作视频,各种直播或课堂交互工具的使用方法等;另外一种是教学方法方面的,比如如何进行线上教学的评价,课堂中如何进行互动。这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校的对应方式也基本一样[8]。
在具体的活动内容上,各个大学开展的活动侧重点不同。如大阪大学在对教师开展教师发展活动的同时,非常注意对新生的支援活动,特别成立了“欢迎频道”的制作小组,采用视频形式对大一新生进行支援,内容包括大学新生入门,大学学习所需要的基本学术技能等学习类活动,顺应疫情也加入了有关体育锻炼的视频陪练内容,包括体操和拳法等[9]。此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将重点放在对教师教学方式的支援上,且在其中重视发挥助教的作用(详见各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相关的网页)。
四、线上教学的开展对大学教学的促进
日本的疫情还在持续中,一年多的线上教学给日本的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整体上,关于线上教学,现在备受瞩目的线上教学中的互动、虚拟空间中的临场感等话题在20 世纪90 年代都已经被讨论过[10]。只是90 年代之后,日本就开始落后,在2009 年OECD 的测评中处于最低水平,甚至处于停滞状态[10]。除个别大学,比如早稻田大学人类学院下设的线上大学(e-school)、熊本大学教育学院的专业学位项目等,很早以前就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之外,日本的全日制大学很少有开设以及运营线上教学的经验,学生们也鲜有相关线上学习经历。对此,近年来在大学教育领域比较有名的日本社会学者吉见俊哉认为,这20 多年停滞以及落后的原因在于“多媒体教育是先进技术主导的实验性探索,而在线教育需要社会组织的变革,日本具有接近世界顶级的多媒体技术,但是在改变教育组织的机构时,日本社会就暴露了其微弱的组织变革力”[10]。饭吉透也批判大学中的管理层以及大学里的教职员工在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缺乏领导力,知识与经验等[11]。金子元久则比较乐观,认为在两个月内大学教师们顺利接受线上教学这一方式,并在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开展了起来,这表示“必要的话大学教师是有行动以及适应能力的,反之,没有必要的就不会动”[12]。具体到线上教学方面,可以发现以下的改变:
(一)促进LMS使用率的提升
这次疫情直接促使了大学里原有LMS 使用率的提升。日本的大学对学生学习信息的基本管理一般都会用到LMS。可是在疫情开始前,日本的大学里LMS的使用率相对较低。据日本ICT推进协议会2020年的调查,在2018 年日本4 年制大学的LMS 导入率为69.2%,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的科目教学LMS 使用率分别为20.5%、28.4%、31.3%[11]。有日本学者比较了同时期美国大学的LMS 利用率,称日本比美国至少落后了15 年以上[11]。就连诺贝尔奖辈出的京都大学,疫情开始前的LMS 使用率也仅仅只有不到20%,但是在疫情的外部压力下,2020 年度上学期科目教学的LMS使用率达到了90%[11]。
(二)促进了教师发展活动的开展
大阪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佐藤浩章[13]撰文指出,在突然从线下转线上教学的过程中,实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教师发展,他自己所在的大阪大学所组织的培训活动,每次参加人数都是过去教师发展活动中所没有的。据他称,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是同样的状况。早稻田大学也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教师发展活动,包括大型“线上教学的第一步”网络研讨会,每个月一次的教员咖啡等活动,还有不定期的广播形式的午餐会活动,数量和频度都很大。根据公布的统计数字[14],仅仅是4 月举办的“线上教学的第一步”主题活动,参加者累计达到2827人次⑦。
在日本,大多数的国立大学和部分大型私立大学都设立有本校的教师发展中心,常备有教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但很多年都处于在校内不被认可的位置,有的多次面临解散与合并危机⑧。在疫情期间,这些中心对本校的线上教学开展发挥了重要的带领作用,也有因其卓越表现得到校长嘉奖的(如东京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栗田佳代子等人)。这些国立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在贡献本校线上教学设计的同时,及时将涉及教学课堂设计的信息在网页上公开,与没有此机构的大学教师实现了信息共享。比如大阪大学的“课堂教学10条”资料公开于网络,因其简洁性和易读性,疫情期间受到一线教师和其他各大学网课支援人员的好评。此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相关教师发展中心的网页也是及时公开,并将大部分信息与外界共享。私立大学中关西大学的教师发展中心除了信息公开,还举办了一些面向校外的有关在线教育的论坛。
除了设有教师发展中心的大学通过网络研讨会形式进行培训和信息传达以外,全国层面,“国立信息学研究所”从2020 年3 月底开始组织有关线上教学的分享活动,现在每周五定期以视频和资料的形式为日本的一线大学教师提供信息。还有一个“大学教师应该做什么的信息与洞见共有小组”,截至2020 年8 月30 日这个脸书(Facebook)小组登录人员数为20335名[13]。此外,在没有教师发展中心的大学或学院,则主要由精通信息技术的教师组织学习会,进行同事间的相互支持。
(三)推进了著作权的修订
日本的著作权法相关条例中,线下教学对应的著作权条例与线上教学适用的条例不同,以及以教学为目的与以培训为目的所适用的著作权条例也不同。比如:学习资料在线下教学中是可以复印发给学习者的,通过邮件形式发给学习者则不被允许,此外还有许多细节规定限制。大多数日本人尤其是学者对著作权有较高的认识,版权意识也较强,所以著作权法的修订讨论直接影响到线上教学的开展。疫情背景下对线上教学的依赖,使得著作权法修订问题的紧急程度升级。在文部科学省以及各方团体的多方斡旋交涉下,在2020 年4 月28 日相关条例得到放宽,保证了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
五、线上教学折射出的日本大学教育问题
新冠疫情迫使全球的大学都不得不采用线上教学这种方式,给大学、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很多挑战和课题。有些挑战是全世界共通的,具有普遍性,如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教师之间缺乏深度合作等[8]。有些挑战表面上具有普遍性,背后却有日本独特的原因。2020年,在经过4 月和5 月准备阶段的混乱后,有一些研究者和大学开始对线上教学的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以下根据金子元久团队、东京大学、九州大学、大阪大学、关西大学、早稻田大学及庆应义塾大学等公布的调研报告,结合这些年日本的大学教育改革举措,深度解析疫情下线上教学折射出的日本大学教育问题。
(一)缺少可共享的丰富慕课资源以及共享意识
2012 年全球掀起慕课浪潮,日本也参与其中。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与早稻田大学等带头在几个国际化的平台(如edX、Coursera)上开设了课程,但数量并不多,比如京都大学到现在为止只有14门(含过去开设的),且这些课程都是英语课程。此外,日本有独自运营的日语慕课平台(JMOOC),但该平台提供的科目数量有限,截至2020 年5 月30 日,仅有37 所大学参与,开设了425 门课,且听讲者多限于终身学习者[15]。这些科目大多并没有在大学内得到推广使用或者是跟大学课堂教学取得很好的联动。所以,在疫情中,对于大学或一线教师而言,客观上并没有充足的慕课资源可以使用。此外,在上述几所大学的调研报告中并没有利用慕课进行教学的相关调研选项设置,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日本的大学教育界还是倾向于让教师们自己制作视频,没有共享意识。
(二)重科研轻教学的传统以及近些年来经济衰退、预算削减间接导致大学学术环境恶化
其表现方式就是,学生在问卷中纷纷反应课业负担重,以及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对于“兼职教师”的依赖。日本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传统由来已久,教师的研究倾向非常强,且普遍缺少教学设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大学重科研,在晋升评价或大学老师更换大学时只有研究成果会被评价。而且,日本的大学教师们自身也十分重视并热爱科研。这在90 年代初对14 个国家大学教师的调查结果中也得到了印证:“日本大学教师重视科研胜过教学的比例为72%,仅次于荷兰,这个比例与接近最低位(37%)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16]。因为大多数老师作为研究者的意识很强,没有受过基本教学方法或教学技能的训练,在课堂教学中会有教师仅仅通过讲讲自己的研究或杂谈就混过去的情况,并没有设定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的意识[12]。虽然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FD 被义务化,即每位老师都有要提高教学技能的义务,但并没有相关的激励政策或手段,所以落实到大学以及个人层面时,执行程度并不理想。同时,日本经济衰退,科研教育经费的减少也导致了学术职位的减少与不稳定,给年轻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教学不被重视导致多数大学教师不会主动去提高教学技能。所以,突然转变为线上教学时,大多教师不知如何进行教学,纷纷采用了增加作业或学生学习任务的形式,自然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感。
与此相关,在调研报告中发现,一些大学的教学非常依赖于兼职教师。比如,私立名校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对兼职教师的依存度都在50% 以上。截至2020 年5 月1 日,早稻田大学全部教研人数为5394 人,兼职教职人员为3381 人,约占62.7%;庆应义塾大学全部教师人数为6262人,兼职教职人员为3471人,约占55.4%。在日本,非正式被雇佣、只承担教学任务的被称为“非常勤”,即只承担某科目或某几门科目的教师,只拿课时费⑨。兼职教师实际身份也多种多样,有的是大学教师在自己本校以外的兼职,有的是博士生或博士后,有的是拥有实际业务经验的人,如企业的人受邀兼职,有的则是博士毕业后暂时找不到正式学术之位只能以此为生计等。所以,任课教师的教育信息技术、教学技能水平参差不齐。近年来许多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的教学都在大量依赖于这些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的大量存在也间接反映了学术科研环境的恶化。日本普遍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较长,且在读博期间大多不像中国和美国一样有奖助学金方面的经济支持,拿到博士学位后也未必能有安定的科研教学职位,这是当下日本年轻人远离学术科研的原因之一。这已经引起日本在读博士人数的下降,以及日本科研水平的连年下降,因此疫情前就有几位知名大学的校长提出要重视此问题[17-19],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三)强行导入美国大学制度水土不服,学分制就是其中一个
调研结果反应的学生抱怨作业多、课业负担加重问题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这一问题既与前面提到的日本重科研轻教学相关,也与学分制相关。
根据日本现行的学分制,要获取1学分,需要对应45个学时(包括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学分制”是日本战后在美国CIE(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指导下引入的,初衷是为了克服日本大学里的“灌输式”授课形式,保证学生能有更多自由安排大学学习科目的同时,有更多的机会成长[20]。根据学分制的规定,教师是需要把课内教学和课外学生作业作为整体进行设计,科目之间需要有联系,需要体系化。但学分制在引入时,这些内容没有被认真解读和理解,只是按照“1 学分对应45学时”的规定在强硬执行。再加上日本原来走的是德国模式,且日本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极其严重,因此就出现并持续了很多年的教授不布置作业、大学生课外不学习、轻松拿学分毕业的所谓“双赢”现象,也就是一直被诟病的“大学生课外不学习问题”[20]。这些年文部科学省主要是通过一些政策和制度改革来促使学生增加课外学习时间,包括设置每个学期可以修习的学分上限、引入GPA(Grade Point Average)制度、采用美式教学大纲等等。此外文部科学省还将FD 法制化,希望通过提高大学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来间接督促学生的课外学习[20]。但根据金子元久发布的疫情前进行的后续调查[1],发现学生们的学习时间并没有增加。这次疫情使得学生的学习时间问题又得到了关注,与之相关的学分制度以及背后的教学设计、学习成果的评估等问题正在引起讨论。
六、小结
通过对文部科学省在疫情中的应对措施的分析,同时结合日本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发现教师发展中心在这次疫情中对线上教学的展开起到积极作用,这可以算是改革的一项成果。此外,文部科学省在认可在线学习学分、学生的经济支援方面,尤其是在著作权交涉方面起到了一定正向的引领作用。
通过对日本各大学针对线上教学所做的应急措施以及调研报告的分析探讨,发现日本在改革过程中,片面或者生硬照搬了美国的一些制度或做法,导致了水土不服。比如,造成学生作业负担的背后,除了有日本重研究轻教学的传统的影响,其制度根源在于学分制的强硬执行。再比如在学术科研环境恶化的环境中推行FD 活动,却没有相关的晋升评价方面的鼓励政策,以致虽然推行改革20 多年,且有先进多媒体技术的情况下,日本大学在面对疫情需要线上教学时依然不能从容应对。
日本的大学教育改革先于中国,且以美国为模版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实践。这次疫情使日本教学改革中的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了出来。这些问题以及背后的原因也许可以给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一些启示,例如,政策引领要基于一线的情况或问题,不能简单照搬形式,尤其是在学习外国制度或做法时,一定要看到某条制度之后的大学或者国家的相应情境,因地制宜才能使政策或者制度落地、真正惠及大多数大学人。
注释
①日本4 月1 日为新一年度的开始,从幼儿园到公司都一样。大学的教学日历中,通常1 月到2 月为高考时期(除了全国统考以外,考生还需要到所报大学去考试),3 月底通常会安排毕业典礼,进入4 月,会安排新学年的各种事宜。日本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感染者是在2020年的1月16日,对教育界产生影响的是2月27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发的一则声明,要求日本全国中小学、高中以及特别支援学校临时封校。因为此声明的发布,许多大学将原定于3月中举行的毕业典礼停止或者缩减规模。
②日本统管教育的政府机构,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
③类似国内的广播电视大学。
④日本所有大学的基本运营都需要依据《大学设置基准》。
⑤根据文部科学省网页上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5月1日,日本的大学共有795所,其中,国立大学86所,公立大学98所和私立大学619所。
⑥该报告主要是针对9 月15 日的调研报告中计划线下教学开设少于50% 的377 所高校。报告中公布了这377 所高校的回答内容,特别重要的一项是“线下教学的比率”,其余的几个选项主旨是解释线下教学比率低的理由。
⑦早稻田大学该年度的教职员员工总人数为5469人。
⑧笔者曾在日本的国立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两大教师发展中心工作过,此为个人经历。
⑨课时费标准因校而异,可以简单理解为家庭教师的按小时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