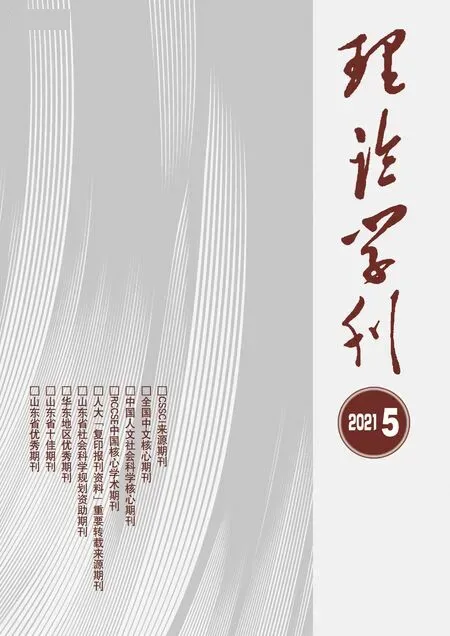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考察
赵纪萍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103)
从费正清时代起,美国就是海外中共研究的重镇,而中共党史研究一直是美国中共研究的重要分支。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迄今产生了大批研究成果,成为美国乃至海外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渠道。对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进行历史考察,了解和把握其发展演进、研究领域以及立场方法等,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他塑”及其国际影响,从而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中更加有效地增强话语权,进而促使美国乃至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抛弃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论”和意识形态偏见,向着更加客观、真实的方向发展。
一、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演进
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大致经历了早期探索、勃兴发展、转型调整以及延续深化四个阶段。
(一)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萌芽探索时期
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与同时期日本、苏联的中共党史研究相比,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表现并不亮眼。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上都表现出早期探索的特点——研究成果不多,研究人员背景复杂,研究缺乏系统性。
说起来,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初发轫,还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直接有关。据记载,1922年,曾出席中共一大上海会议的陈公博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陈公博用英文写作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具体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创建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发展。当然,这篇关于中共党史的硕士论文,严格说来不能归入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之列。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向美国政府报送的《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红色根据地的早期历史;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伦敦出版的《远东前线》,通过对国民党政权的实地观察和间接收集到的材料,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为西方了解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信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早期作品,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瑞士籍传教士薄复礼的《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1936年)。该书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长途跋涉过程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丰富细节和感人事迹,尤其是对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在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间的战斗生活和历程中的重大活动作了详细的记录,是中外学者进行红军长征研究的极为宝贵的原始材料。总的看来,直到抗战爆发前,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背景比较复杂而且缺乏相关专业训练,研究成果零星稀少且不够系统,表现出早期探索的特点。
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影响的扩大,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武装及其抗日斗争兴趣渐浓,有大批美国记者和学者突破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前往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实地考察、战地观察、访谈等形式,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活动。一方面,这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美国记者和学者收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党史文献资料,为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积累了奠基性的基础材料;另一方面,他们完成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通讯报道和著作,通过发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以及在美国、英国等出版的记录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根据地人民生活、抗战政策、抗战活动、抗战精神等的著作,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尼姆·韦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1939年)、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1939年)、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1940年)、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1943年)、哈里森·富尔曼的《北行漫记》(1945年)等,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活动进行报道,把中共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散布的所谓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谣言,成为美国乃至海外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英勇抗日这段历史的鲜活资料。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发表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很大一部分文章,由于受信息不对称、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存在不少误说,这对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无疑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勃兴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勃兴发展时期。1955年,在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者的大力推动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成立伊始,即全面推动对于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仅为美国培养和储备了一支颇为庞大的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队伍,而且为世界各国培养输送了为数不少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并以此向全世界辐射影响力,带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进入勃兴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中共党史研究项目、文献档案原始资料汇编和研究论著,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费正清及其领导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是推动美国乃至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勃兴发展、兴盛繁荣的重要力量。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是费正清带领史华慈、布兰特等年轻学者积极推动成立的,其目的是通过全面推动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研究,引导美国政府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对美国政府如何制定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对华政策提供政策咨询。一方面,费正清领导下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通过设立研究项目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他们广泛搜求和汇集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积极创办学术期刊和出版研究论著,不仅是美国学界、政界、社会各界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渠道,而且影响着中国及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国际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影响带动下,美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教学研究机构以及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有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中国项目、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
无论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构成和水平,还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来看,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共党史研究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美国涌现出了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除了费正清,还有史华慈、派伊、鲍大可、施拉姆、麦克法夸尔、傅高义、莫里斯·迈斯纳、马克·赛尔登、哈里·哈丁等。从真正意义上可以说,这些专家学者开创了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先河,并推动着这一研究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美国整理汇编了大量的中共党史研究原始资料,研究资料的收集表现出系统化的特点。据统计,美国95家图书馆当时的中文藏书超过4亿册,重点收藏中共党史资料的哈佛大学所藏中文资料达40万册,重点收藏中共党史资料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几乎收集了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所出版的全部重要的中共党史资料(1)梁怡、李向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评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这一时期推出的大批研究成果,以学术性研究和应用对策性研究居多,研究内容涉及中共党史的通史性研究、阶段史研究,以及党史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多给予了客观正面的评价。例如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就给予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以高度的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伟大创造性的成就”(2)[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但是,其中也不乏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误读,甚至还存在有意为之的抹黑和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论著。这都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要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进而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三)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转型调整时期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进入转型调整阶段。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曾一度陷入低谷,出现消退沉寂的趋势。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一批党史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不久即进入理性的转型和调整阶段,“西方中心论”和基于“冷战”思维的官方研究模式不再“一统天下”,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更加客观的模式来研究中共党史及中国问题。
虽然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略有减少,但是研究深度却有所增强,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这一时期的通史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最有影响力的是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1987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1987年),不过,在个案研究、阶段史研究、差别性研究等微观研究领域,此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涌现了一批得到较普遍认可的论著,例如罗杰·费利哥特与雷米·考弗合著的《康生的秘密使命》(1987年)、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1987年)、贺康玲与戈迪温合著的《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1989年)、斯特拉纳汉的《媒介:中国共产党和〈解放日报〉》(1991年)、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1995年)、卡罗尔·卡特的《在延安的考察团(1944—1947)》(1997年),等等。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新出版的研究成果较之前期有所减少,尤其是大部头的著作为数不多,不过实效性、现实针对性强的论著则有所增加,并且更加注重使用微观研究的方法,更加着力于细节研究,这就使此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理性思考和微观研究相对而言也更加成熟。犹有可言者,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更加有研究针对性的专家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者队伍方面为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夯实了基础。
(四)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延续深化时期
在经过20世纪末的转型和调整后,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在21世纪进入到了延续深化的新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一方面吸引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多个角度关注、解读始终不渝领导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学者深入中国社会、获取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的机会大大增加,这就使得美国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研究,无论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深度都能够得以大幅推进。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进入了延续深化的新阶段。
21世纪以来的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出以下新情况:其一,由于研究条件、研究手段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使得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者能够更加快捷、方便甚至即时地获取研究资料和研究资源,从而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开阔了研究视野,也拓宽了研究范围。其二,研究队伍实现了新老交替,并且越来越壮大。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日益认识到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加大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投入,不断加大对相关研究者队伍的培养和支持力度,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学术机构、智库乃至网络媒体加入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行列,其中基辛格、傅高义、沈大伟、裴宜理、伊维德、亚历山大·库克等最具代表性;另一方面,美国中共党史研究队伍中华人研究者的数量和影响日益凸显,一些出生于中国、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华人学者,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越来越受到美国学界和政府的重视,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三,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对重视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转向了更加注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类中国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的新的研究格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当下”,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当下”进行更加微观、细致的研究,例如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原因的考察研究,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跟进研究,对改革开放的持续研究等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并没抛弃对中国共产党既往历史的研究,而是将中共党史作为研究“当下”的历史背景来加以关注,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中共党史研究透彻了,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当下”。
二、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回顾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其研究的重要领域及其重要观点。概括说来,重点研究领域包括对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汇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身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及重大问题等的研究。
(一)对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汇编
收集中共党史文献资料是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美国作为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镇,在收集原始文献资料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政府、军方、基金会、历史协会、大学图书馆以及档案馆都收藏有丰富的中共党史文献资料。早在19世纪,在美国中国学的草创阶段,美国的政府、基金会就依托并大力资助相关协会、大学里的中国学教研机构、图书馆、档案馆等,收集整理汇编中国相关资料,比如1927年成立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在政府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的大力资助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经拥有了135000册的中文藏书,成为美国收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3)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3页。。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促使美国中国研究的重心逐步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且促进了对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汇编。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研究协会、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收集整理汇编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原始文献资料和研究资料,例如哈佛大学通过香港收集到的《红卫兵资料》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哈佛大学豪顿图书馆收藏的“李大钊档案(1914—1915年)”(4)桑月鹏、俞晓秋主编:《新时代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213页。、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刊《向导》、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编印的《密执安中国研究集刊》和《密执安中国史著作摘译》、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八七紧急会议议决案》、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编辑的《有关中国共产党运动史等的中文资料》(5)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4、82页。、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诺思整理的《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物》(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4、82页。、俄勒冈大学数字化处理收藏的“福尔曼档案(1931—1974)”(7)桑月鹏、俞晓秋主编:《新时代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213页。等,都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美国收集整理的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中,有一部分被学界称作“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的文献特别值得关注。这部分档案文献是以斯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人士(后期主要是美军观察组),在冲破国民党和日军封锁到达延安以及华北敌后根据地之后,基于实地考察而写成的有关中共敌后抗日斗争的文章、图书和报道。它们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的观察文献,分散收藏于美国各档案馆、图书馆等文献资料收藏机构。显而易见,这批文献对于开展中共敌后抗战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一方面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批中共党史文献资料,例如美国国务院出版的90年代以来国务院、白宫、参众两院解密的中国相关档案材料;另一方面编译出版了大量毛泽东文集,例如麦克法夸尔、齐慕石和吴文津编译的《毛泽东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1989年)、汤姆森·罗格翻译的《寻乌调查报告》(1990年),以及施拉姆主持编译的《通向权利的道路——毛泽东革命文稿(1912—1949年)》1—5卷(8)梁怡、张强、李向前:《近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管窥》,《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虽然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汇编出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绝大部分散落的中共党史相关文献资料已经整理出版,而且近年来美国在中共党史研究文献资料数据化方面也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美国收集整理的很多文献资料存在着真伪难辨的问题,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和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期从中国庞大的中共党史资料库中寻求更为丰富和可信的文献资料支撑。
(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身的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身的研究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宏观整体性的通史研究,也有对中国共产党某一阶段历史的研究。
在宏观性研究方面,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属于通史性研究。通史性研究成果是海外学者和政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基本依据,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1987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1987年)等。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还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或早期历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改革开放史等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不同侧重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在中共创建史或早期中共党史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影响也不太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学者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而且颇具影响。举其要者,尼姆·韦尔斯的《红色中国的内幕》、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论著,都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整体性研究成果。此外,抗日根据地研究的相关论著中,还有一部分是对根据地某一问题,如干部问题、群众运动、教育等的深入研究。除此之外,还有战时社会经济史、抗战中的中外关系等的专题性研究。美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表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内容丰富的特点。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是比较早的。早在抗战时期,随着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等突破封锁进入延安或深入战地考察,便出现了很多抗日战争史方面的相关论著,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相关研究的比较优势,并延续至抗战胜利。之后受“冷战”影响,美国学者的抗战史研究有所低落,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复苏,相关研究再次勃兴,到21世纪则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及至2015年也即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美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拥有稳定的研究力量、充足的研究项目及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抗战史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9)刘本森:《英国学术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趋势》,《国际汉学》2019年第3期。。
美国学者解放战争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是相关论著视角比较独特,研究比较深入透彻,思考也颇深刻。例如罗其韬所著《中国不可避免的革命:对美国输给共产党的再思考》(2007年),该书以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为切入点,探讨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三大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变化与力量消长,指出处于对立两极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谁就面临孤立,直至最后失败(10)翟亚柳、乔君、陈鹤:《2007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克里斯托弗·卢所著《1945—1949年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主义的策略与领导》(2009年),则“从军事战略史角度分析中共如何发动和最终赢得战争从而赢得政权,分析了中共军事力量的转变与中共领导人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11)陈鹤、翟亚柳、乔君:《2009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而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中国人征服中国》(1949年),是她在1946—1947年间对延安等几个解放区进行采访后,以所见所闻为基本素材写成的,该书在总体回顾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的基础上,着重记述了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同得到美国支持和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美国学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重点关注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的形成、中国的“一化三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外交关系等问题。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国人民公社的兴起》(1964年)、埃德加·斯诺的《漫长的革命》(1971年),歌颂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12)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4页。。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者普遍认为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解密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因此格外重视改革开放史研究,“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或宏观或微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与相关问题,追溯改革的历史轨迹,试图从不同层面解读中国的发展、中国所取得的经验和未来发展的方向”(13)陈鹤:《新世纪以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其中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被看作是“第一本全面考察中国改革的起源、围绕它所产生的争论,以及它的困难与成就”(14)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的著作。该书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提出质疑,其研究动机和所持立场应予批判。此外,美国学者裴宜理发表在《中国研究》第57期上的《研究中国政治:告别革命?》一文及由他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层政治改革》一书,还有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所著《今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把真实客观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故事视为己任的罗伯特·库恩所撰《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等,都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共党史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及重大问题研究
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及重大问题一直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而且结出了累累硕果,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美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历来重视对中共党史重要人物进行研究。他们普遍认为对中共党史重要人物进行研究是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实践和治国理政实践的一把钥匙,因此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深耕,不仅著述颇丰,而且影响广泛。一方面,美国学者聚焦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研究,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领袖人物进行不同视角和层面的研究,研究成果丰富多元且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相比较而言,对毛泽东相关研究的成果数量最多、传播影响范围也最广,对邓小平的研究有趋于弱化之势,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研究间或有之,对习近平的研究则呈现出愈益重视的走势。在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研究方面,20世纪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1952年)、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派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1976年)(15)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8、82、90、93、79页。,以及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罗伯特·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论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习近平总书记,他们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成长背景、人格魅力、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等持续进行的深入研究,相继推出不少成果,比如大卫·兰普顿的《跟着领袖走: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伊丽莎白·伊科诺米的《第三次革命:习近平和中国新一届政府》、罗伯特·库恩的《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等等,这些成果高度评价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美国学者也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进行了相关研究。史华慈的《陈独秀与对现代西方的接受》(1951年)是专门研究陈独秀的一篇论文,此外,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诺思的《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物》(1952年)、《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1953年)(1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8、82、90、93、79页。,以及华盛顿大学兴登教授的《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物》(17)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8、82、90、93、79页。、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吴文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领导人——胡佛图书馆藏中国传记书目选注》(1956年)(18)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8、82、90、93、79页。,是对中共重要领导人进行介绍的文集。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物传记辞典(1921—1965)》(两卷本,1971年),对中共党史上的340多人正式立传,进行介绍的更是多达1700多人。《近代中国革命领导人物》(1971年)一书也收录了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等多个中共党史人物的传记。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研究中共党史人物,不管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凡是有名气的,他们都写传记。例如,1971年出版的《近代中国革命领导人物》,不仅收录了前述李大钊等人的传记,也为后来背叛共产党的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作了传(19)胡华、林代昭:《台湾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其次,美国学者对中共党史重要事件及重大问题的研究也极为重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南京大屠杀”、三大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右倾”、群众路线、知识分子问题、妇女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法治问题、对外关系,以及党史上的一些重要思想、重要理论、重大政策等,都是研究的重点所在。美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这些重要事件、重大问题进行解读和分析,形成了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麦克法夸尔长期专注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裴宜理则重点研究工人运动,贺亨则对农民运动给予高度关注(20)何俊、卢睿蓉:《薛龙著〈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五十年〉》,《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加利福尼亚大学布兰特的《1924—1927年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21)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8、82、90、93、79页。,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惠廷的《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动态》(1958年)、《中苏同盟的矛盾转化》(1960年)、《中国和美国——下一步怎么办?》(1976年)(22)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6、87、82、86、87、86页。,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专家鲍大可与赖肖尔合编的《美国与中国:下一个十年》(1970年)(23)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6、87、82、86、87、86页。、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科恩的《中国外交关系的动力》(1970年)(24)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6、87、82、86、87、86页。等,是研究中外关系方面的重要成果。密执安大学雷麦的《共产党中国的煤炭生产:一篇关于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论文》(1956年)、艾克斯坦的《共产党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前景》(1954年)和《共产党中国的国民收入》(1961年)(25)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6、87、82、86、87、86页。、布鲁金斯学会鲍大可的《共产主义经济战略:大陆中国的兴起》(1959年)(2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6、87、82、86、87、86页。等,是中国经济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被称为“全世界研究有关中国的法律问题的第一流权威之一”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科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1949—1963)》(1968年)、《现代中国的法律》(1970年)、《人民共和国和国际法》(1970年)(27)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6、87、82、86、87、86页。等,则是中国法律研究方面的重要作品。此外,傅高义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69年)、鲍大可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治权力》(1967年)和《中共执行的政治方针》(1970年)(28)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6、87、82、86、87、86页。等,系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执政方针、党的建设、执政实践等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越来越以分析研判中国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为目的,越来越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其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研究背景来对待,带有强烈的时政研究色彩,研究成果则带有越来越强的实用性。
三、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通过对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进行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有其显著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并回应的问题。
(一)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在研究动力、研究主体、研究取向、研究领域、学科地位等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表现出很多新趋势。
第一,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动力持续增强。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智库、专家学者乃至媒体相继加入到了中共党史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在经历了萌芽探索、勃兴发展、转型调整阶段之后,在新世纪已经进入到延续深化阶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就是相关学者想要在理论和现实层面破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这些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世界减贫事业的巨大贡献者,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积极持续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伟大战略性胜利,更是引起了美国从政要到学者各个层面人士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他们不仅关注中国现实以便从中寻求答案,同时也纷纷回到历史中去探寻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奇迹的经验和秘诀。
第二,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回顾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演进过程,这一特点几乎贯穿始终且日益明显。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地,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多元化的特点非常明显,析而言之,有美国的权力机构,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有受福特基金会等私人资本资助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如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等;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诸多大学所设的研究机构;有私人资本资助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亚洲研究协会等;还有数量众多的记者、外交官,如斯诺、斯特朗等,可以说,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政府机构、智库和高等教育机构三足鼎立的局面。就研究者来说,可谓是学派众多。在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中,有以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有以鲍大可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派,有以沈大伟为代表的华盛顿大学学派,还有以哈里·哈丁为代表的布鲁金斯学会学派等。而且不同学派之间经常展开激烈的学术论战。20世纪60—70年代,哈佛学派同华盛顿学派曾形成学术对立,华盛顿学派曾有人公开批评费正清的“亲共”立场(29)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美国中共党史研究队伍近一个时期出现了新老交替的情况。随着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傅高义等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方面领军人物的相继离世,老一辈中共党史研究者只有沈大伟、裴宜理等人还比较活跃。中生代、新生代学者,如“中国通”罗伯特·库恩、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哥伦比亚大学的蔡欣怡、美国廉政研究专家魏德安等,成为新时代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有生力量。总之,研究主体的日益多元化,突破了美国中共党史传统的研究范式,促成了美国中共党史研究主题以及研究取向的多元化。
第三,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主题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主题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从萌芽时期主要关注党的早期创建、早期历史和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的比较单一的研究主题,发展到新世纪的既重视通史性研究、阶段史研究,也关注党史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大问题的研究,还重视中国共产党现状的研究,并且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程度日益加深。此外,新世纪以来的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还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当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反腐败斗争、环境治理,以及党的代表大会、脱贫攻坚工程等问题,进行更加微观细致的研究,推出了大量相关论著。这反映了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和队伍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视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转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类中国现实问题为重点的新的研究格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共党史越来越被视作当下现实问题的一个历史背景来加以关注和研究,毕竟“以史鉴今”已经成为国内外广大研究者的共识。美国学者裴宜理就曾指出:“中国革命遗产中的某些要素事实上推动了市场改革中正确决策的实施。”(30)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2007.
第四,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存在多元化取向。研究主体多元化的背后是研究取向的多元化,不同的研究主体的研究取向存在明显差异。概括来说,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为学术性研究、应用对策性研究以及意识形态丑化性研究。其一,学术性研究。学术性研究主要来自美国各大高校以及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其特点是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进行研究,力求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等,都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机构。其二,应用对策性研究。应用对策性研究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最初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取向。例如,美国中国党史研究的开拓者费正清,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应用对策的鲜明印记。费正清在分析中国革命时就强调,“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为了自己的恰当利益而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施加影响,使它不致于为国家牺牲个人,不致于使中国从属于某个大国,或被铁幕围住,断绝与外界的来往”(31)《费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这一类型研究的主力集中于美国各大智库,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他们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大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下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在理论上对中共党史重大问题追根溯源,而且重视在实践上深入思考如何发挥中共党史研究“以史鉴今”的实用功效,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性研究人员流向各大智库,比如李侃如、沈大伟、裴敏欣等目前都在美国的智库担任要职,这说明应用对策性研究也需要有坚实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其三,意识形态丑化性研究。意识形态丑化性研究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的噪音,其特点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进行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歪曲丑化。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类型的所谓研究不应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然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搞污名化的所谓研究在美国一直不断出现,而且其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所谓研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积极思考应对之策。
(二)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在其发展历程中获得了巨大进展,对国际社会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治下的中国具有重要影响,但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并积极作出回应。
首先,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文献资料在收集和整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此外也还存在部分档案资料失真失实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费正清、费维恺、齐慕实等人都提过,冷战时期,研究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材料奇缺,只能以从港台转手的材料为主,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准确度”(32)梁怡:《重视海外中国史研究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1日。。因此,在考察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他们的研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来源是否可靠、内容是否真实。对于土地改革、“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中共党史上相对敏感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的论著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国内学者,如果不注重考察其文献资料的可信度,有些真相就会被遮蔽。
其次,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存在明显的话语霸权现象。话语霸权现象是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但在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不足为奇,毕竟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映射的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动向以及西方所主导的国际舆论的总体形势。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美国关注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根本目的是要服务于本国的对华政策并以此来影响国际舆论,由此,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势必反映其对华政策的动向和国际舆论风向。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共党史相关研究的动向正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反映:1969年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以《七十年代的任务》为题所作的演说中尖锐指出,美国之所以在亚洲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就是因为它不了解中国,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因此,在演说中他强烈呼吁美国改变对华政策(33)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1页。。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一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更是挖空心思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情况同样非常突出。2018年,沈大伟、黎安友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应当对华采取强硬态度”(34)Larry Diamond. Chinese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ese-influence-american-interests-promoting-constructive-vigilance. 2018-11-29.,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此外,美国学者往往以自己的视角和立场研究中共党史和解读中国,并且凭借其对国际舆论的控制造成话语权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分配极不平衡,“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治下的中国的论调,使得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真相被遮蔽,而这往往会使得各国不明真相的人们不自觉地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误判。
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和深化对美国乃至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再研究,正确把握我国所处的真实舆论环境,有的放矢地提升中国在世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话语权,积极主动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者抛弃意识形态偏见,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