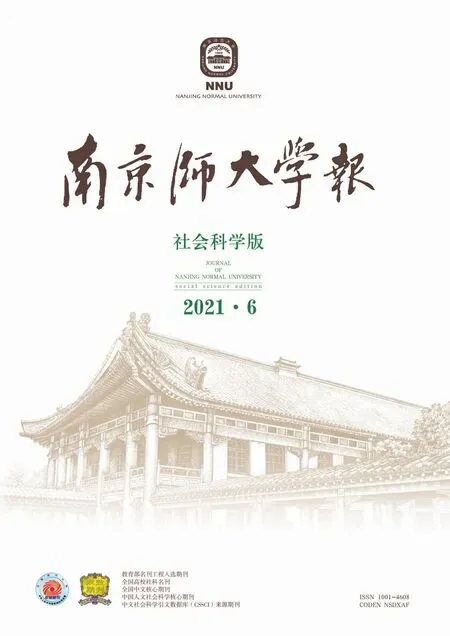麦金太尔的“启蒙计划”批判之批判
陈 真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是当代颇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在美德伦理学领域里,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西方近代以来主流道德哲学的批判和对美德伦理学复兴的推动。他的代表作《追寻美德》一书对近代以来的西方道德哲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种抨击主要集中在对所谓“启蒙计划”(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的批判上,尤其集中在西方理性概念的批判上。弗兰肯纳认为在同时期现代西方文化和道德哲学的批判者中,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的批判无疑是“最为坚决、持续和包罗万象的”。(1)W.K.Frankena,“MacIntyre and Modern Morality”,Ethics,Vol.93,No.3,1983,pp.579-587.然而,麦金太尔的批判包含了许多似是而非之议,所讨论的内容涉及到理性在伦理学的研究中是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终极的价值原则是否可以进行理性的反思与评价,根本的价值分歧能否通过理性和客观的方法加以解决等等,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和澄清。本文对这些问题均给出了与麦金太尔相反的答案。我们希望本文的讨论有助于澄清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些模糊的,甚至是有害的认识。
由于麦金太尔在对近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中所提出的概念和论证并不严谨,十分杂乱,也不是他所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值得讨论,我们只是选取他有价值的主要论证加以重构,尽可能清晰,也尽可能有力地表达他关键性论据的核心思想。(2)本文主要依据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一书来重构其核心的论证。麦金太尔断言“启蒙计划”——寻求道德问题上的理性共识并为道德进行辩护的工作是失败的。其论据主要有三。其一,启蒙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实际上成功过。”(3)A.MacIntypre,After Virtue(3rded.),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7,p.21;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6页。我们引用该书时将同时注明英文本和中译本的页码。如对中译本译文有所修改,将在译本前加上“参见”二字。其二,启蒙计划导致现代西方根本的道德分歧是无解的,无解的原因是因为分歧的各方所诉诸的根本价值原则是不可公度的(incommensurable,又译“不可通约的”)。其三,启蒙计划导致现代西方道德或道德语言概念的“严重的无序状态”,这一无序状态是由于启蒙计划的道德合理性论证与历史语境的分离所造成的。本文将分别讨论这三个论据,试图说明它们为何难以成立,并力证启蒙时期以来的理性的方法依然是我们解决道德问题的无可取代的方法。
一、 启蒙时代思想家的代表性理论是否已经失败?
麦金太尔认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从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到德国,如休谟、边沁、狄德罗和康德,都打算用一种世俗的道德取代传统的、迷信的(宗教的)、失去价值的道德,这种入世的道德自认为可以得到任何理性人的赞同。启蒙思想家力图阐述任何充分反思的、理性的行为者都无法拒绝遵守的道德规则。麦金太尔断言,这样的尝试都失败了,如果他们的论证不成功,麦金太尔声称,那就强有力地证明了整个启蒙计划也不会成功。启蒙思想家留下的只是互相敌对的立场,每一个主张都声称取得了理性人的赞同,得到了理性人的辩护,但每一个主张都受到对立的、同样声称得到理性人赞同和辩护的主张的反驳。麦金太尔认为康德式的道德哲学家和功利主义者彼此间的无休止的冲突说明理性解决道德冲突的失败,从这种失败中,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理性在解决道德冲突方面是无能为力的。(4)麦金太尔后来重申了他在《追寻美德》中的上述主张,参见A.MacIntypre,“The Claims of After Virtue”,in K.Knight(ed.),The MacIntyre Reader,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8,p.70。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分析麦金太尔对每位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并一一评析。我们拟选取他对康德、休谟和功利主义的批判来说明,他断言启蒙思想家代表性理论全都失败的说法难以成立。
按照麦金太尔的解释,康德反对以幸福等后果来决定一个行为或事情道德与否,也反对援引上帝启示来为道德辩护,他主张实践理性自身——无需诉诸任何来自经验的内容就可以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就可以判定一个行为或事情是否道德,就可以为道德行为提供辩护。(5)参见A.MacIntypre,After Virtue,pp.43-46;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55-58页;I.Kant,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trans.by H.J.Paton,New York:Harper & Row,1964,pp.57,65,70,88,89,91,98,108。“理性的本质就在于制定普遍的、无条件的、内在一致的原则。因此,一种合理的道德所规定的原则,能够也应该为一切人所信奉且独立于各种环境和条件,亦能够始终一致地为每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任何场合下所遵守。这样,对于所提出的准则的检测也就不难设计了:我们能否始终一致地要求每个人都总是按照这一准则行事?”(6)A.MacIntypre,After Virtue,p.45;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58页。麦金太尔提出了一系列的反例来反驳康德的学说。他说:“人们不难看到,许多不道德的和琐碎的非道德的准则,都可以被康德的检测证明为正确的原则,甚至和他所极欲坚持的道德准则的证明一样有说服力,在某些情形中,甚至更有说服力。譬如‘除一种诺言外终生信守所有诺言’、‘迫害一切持虚假宗教信念的人’以及‘总是在三月的星期一食用贻贝’等都会通过康德的检测,因为它们都能够始终一致地被普遍化。”(7)A.MacIntypre,After Virtue,pp.45-46;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58页。将这些通过检测的准则视为道德准则显然是荒谬的。这些都是针对康德学说常见的批评。麦金太尔运用康德绝对命令的第一种公式,即普遍化的原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一步反驳了康德的另一个公式,即“不论对己还是对人,总是将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8)麦金太尔对康德公式的表达并不准确。准确的表达应当是:总是将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他认为“‘除我之外把每个人都当作手段’可能是不道德的,但它并不自相矛盾,甚至要求一个根据这一准则而生活的利己主义者组成的世界,也不会有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如果每个人都照此准则生活,可能都不太方便,但这并非绝无可能,而且考虑‘方便’就不得不诉诸对幸福的慎思,而这正是康德力求从全部道德思考中完全排除的东西。”(9)A.MacIntypre,After Virtue,p.46;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59-60页。
麦金太尔对康德的反驳是西方教科书或大学课堂上对康德学说常见的批评,但站在康德的立场上则未必无法回应。我们试从康德的立场,提出两点反驳意见。首先,康德确实主张理性自身可以先天地(apriori)发现道德法则或为道德提供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者的判断是“独立于各种环境和条件”的,也不意味着无需任何经验的感受。康德的本意是:如果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判断此时此景的条件下采取某一行为是正确的,那么,对于任何一位相似的理性的行为者来说,在相似的条件下,该行为也同样是正确的——而非“独立于各种环境和条件”。康德强调道德法则的先天性,他的意思只是说道德法则无法通过经验归纳得到证明,但却可以通过理性的人发现。比如,“将无辜婴儿折磨至死以从中取乐是错误的”,这一原则不是,也无法通过经验归纳而获得,但任何一位理性的行为者都无法否认这一原则或判断是正确的。康德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完全无需身处经验的世界就可以发现道德规则。他明确说过,“无可否认,这些先天法则还需要通过经验把判断力磨练得更加敏锐,以便一方面能够区分这些法则应用的不同情景,另一方面则是使这些法则为人的意志所接受,并对其实践运用产生影响”。(10)I.Kant,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p.57.
其次,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必须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如果我们对康德的学说给予合理的解释,那么他所说的逻辑的一致性只是道德原则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康德看来,任何准则要成为一个道德原则,还必须是任何一位理性的人在相似的条件下都不得不接受的准则。而麦金太尔所举的反例无法为理性的人所接受,因此,这些反例无法成为真正的反例。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常常将康德所主张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视为毫无例外的原则(麦金太尔似乎就这样认为),而任何道德原则似乎都是允许有例外的。因此,这是康德学说的一个重要缺陷。但所谓例外的情形往往是因为有其他的道德原则与之冲突。以遵守承诺为例,当出现例外时,往往是因为有更重要的道德义务,比如,拯救无辜者的生命或者其他比当时遵守承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遵守承诺就不是一条道德义务,或者说,此时就无效了。遵守承诺是道德所要求的,是因为行为者曾认真地做出过承诺。当出现例外时,当为其他更为重要的道德原则所压倒时,遵守承诺依然是一条有效的道德原则,因为行为者或者感到需要对被承诺者做出解释,或者会为违背承诺而感到不安或内疚。如果遵守承诺的原则在此时真的完全失效,行为者就不会有诸如此类的感受了。这正如牛顿力学的惯性定律的情形一样,按照惯性定律,一个物体沿着作用力的方向可以保持匀速直线前进。可当在具体情景中,一个物体受地心引力的影响没有保持匀速直线前进,我们并不会因此而断言惯性定律失效了。对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普遍性也应当做类似的理解。
我们这里并不是想证明康德的学说没有问题或没有缺陷。退一步说,即使康德学说存在缺陷,也不能说明我们就无法依靠理性去解决自身与康德义务论之间的分歧。事实上,麦金太尔提出的反驳意见依靠的依然是他有意无意加以贬斥的理性。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康德学说的缺陷。这方面,后来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如罗斯、罗尔斯、斯坎伦、达沃尔等人,已经做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工作,这些工作本质上是康德义务论思想的继续。因此,我们很难轻言康德伦理思想的失败。尤其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普遍化”的概念上,而是讨论实质性的道德问题,比如,一个不随地吐痰的社会是否优于一个随地吐痰的社会,我们获得的答案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等,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同等条件下,一个不随地吐痰的社会优于一个随地吐痰的社会。引入任何所谓喜欢随地吐痰的“传统”或“历史”都无法否认这一判断的真理性。
麦金太尔认为休谟主张“道德必须基于激情和欲望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来予以理解、说明和辩护”,(11)A.MacIntypre,After Virtue,p.49;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63页。最终通过诉诸同情心来为道德提供辩护。他认为休谟提出同情心,显然是想在无条件地遵守普遍和绝对的道德规则的理由和由于具体环境刺激所产生的欲望或情感反应而生的理由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可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搭建桥梁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休谟……所使用的‘同情心’只不过是一种哲学虚构的名称罢了。”(12)A.MacIntypre,After Virtue,p.49;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63页。然而,麦金太尔的断言似乎显得有些草率。首先,休谟所说的“同情心”,或者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移情心”(empathy),确实是我们道德思想的情感来源之一,这已为当代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所承认,而不是所谓主观任意的虚构。(13)参见M.L.Hoffman,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10。斯洛特(Michael Slote)等当代西方伦理学家利用这些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休谟的思想。(14)关于斯洛特的工作,参见陈真:《论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其次,在康德的理性道德原则和休谟的情感之间未必就不可能搭建一座桥梁,因为理性行为者的道德直觉背后起作用的很有可能就是理性行为者不由自主的移情反应。
麦金太尔认为西方伦理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论,而边沁等人所主张的功利主义则根据行为的后果为伦理学研究确定了一种新的目的论——一种以追求“快乐”或追求“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功利”为行为终极目的的目的论,即当我们必须在不同的行为或政策之间进行决策时,总是应当选择可以产生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快乐的行为或政策。在功利主义那里,“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功利”这两个概念是同等的概念,可以互相置换。麦金太尔认为功利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它的“功利”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因为“功利”概念中所包含的“幸福”概念无法测度。经典功利主义的“幸福”是通过“快乐”和“痛苦”来定义的,然而,不同行为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是不同质的,如游泳和喝啤酒所带来的快乐,它们之间如何测量比较?即使是同一种质量的快乐也有强弱之别,如何换算恐怕也是一个难题。麦金太尔认为,由于不同的快乐或痛苦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公度的,因此,当面临多种行为或政策之间的选择时,我们无法根据功利原则进行选择。这样,“功利”或“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概念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清楚内容的概念。它至多只是各种意识形态所利用的一个“伪概念”。(15)参见A.MacIntypre,After Virtue,pp.64,70;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81-82、89页。对于麦金太尔的批评,我们提出两点反对意见:第一,“功利”一词的英文为“utility”,在当代博弈论和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通常译为“效用”,通过这一概念,人们可以在不同质的比较、选择和决策之间建立可公度、可量化的基础,因此,绝不是一个主观任意的虚构概念,而是一个在经济学和博弈论中可以发挥实际作用的概念。尽管经济学和博弈论中这一概念的内涵不能完全等同于功利主义的“功利”,但其量化的方法原则上依然可以用于功利主义“功利”的测度与分析。第二,麦金太尔指责“功利”是一个虚构概念的主要理由是不同快乐或痛苦之间的不可公度性,然而,如果这种不可公度性的意思是指不可精确地量化的话,那么精确的量化并非是我们依据功利主义原则进行行为或政策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并非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精确地测量和比较不同的快乐或痛苦才能决定两种行为或政策中哪一个的后果更好。许多思想实验,如“电车难题”“器官移植”等著名的反驳功利主义的案例中,我们都无需精确地测量不同的痛苦与快乐,我们凭借常识就可以做出判断与决策。
人们常常认为康德主义义务论所难以解释的道德案例,功利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而功利主义难以解释的道德难题,康德主义义务论又可以很好地解释。麦金太尔认为这恰恰说明启蒙思想家代表性理论是失败的:这些思想家每种观点的合理化论证的关键部分都建立在其他观点失败的基础上,它们彼此间的有效的批评最终也使彼此的观点都失败了。“因此,为道德提供一种合理化论证的计划也就决定性地失败了;从此往后,我们前辈的文化(以及随后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道德不再具有任何公共的、人所共有的合理性或可证明性。”(16)A.MacIntypre,After Virtue,p.50;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64页。然而,其一,对一个理论的质疑或理论间的相互质疑是认知真理的手段,这种质疑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被质疑理论的失败。真理往往是越辩越明。在人类科学史上,人们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关于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的争论,都推动了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如果仅仅因为人们之间认识有分歧,就认定他们工作是失败的或无意义的,那么,麦金太尔的理论从提出之初,就遭到其他哲学家的强烈反对,这是否就说明他的理论也是失败的呢?他的理论即使事实上是有缺陷的或失败的,也不是因为由于有人反对或他与他人有争论和分歧,而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其二,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缺陷或不足并不必然等于它们的失败,它们之间的互补恰恰说明了它们分别反映了道德规范性特征的某一方面,而不是所有的方面,因此,它们在决定一个行为是否是道德时是互补的,而不是失败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道德的本质,共同推进了人们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其三,断言西方哲学家所讨论的道德“不再具有任何公共的、人所共有的合理性或可证明性”并不符合西方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当代西方哲学家依然在寻求道德合理性或客观性的证明,而合理性或客观性本质上就是普遍的、公共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麦金太尔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与否定显得有些草率和任意,如同弗兰肯纳所说的那样,他在批判中常常看不到所批评对象可能的反驳。(17)参见W.K.Frankena,“MacIntyre and Modern Morality”。因此,他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既缺少对批判对象的充分理解,也缺少充分的理据。
二、 根本的道德分歧是否不可公度?
麦金太尔断言启蒙时期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为道德合理性的辩护是失败的,因为他们“自身在道德合理性的特征问题上或者在理应以此合理性为基础的道德实质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这颇能说明问题。……这就等于再一次提出了一个初始的证据(primafacieevidence),证明他们的计划已经失败,……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乃是其各自建构工作归于失败的明证。”(18)A.MacIntypre,After Virtue,p.21;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26页。这导致他们争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无休无止性。……这类争论不仅没完没了(尽管它们的确如此),而且显然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没有任何理性的方法可以确保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意见一致。”(19)A.MacIntypre,After Virtue,p.6;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7页。这里所谈到的道德分歧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根本的道德分歧,即争论双方不可能通过达成相关的非规范性事实的共识而可以消除的道德分歧。(20)参见R.Brandt,“Ethical Relativism”,in D.M.Borchert(ed.),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nd ed.),Vol.3,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6,p.368。然而,将这种道德分歧归咎于启蒙计划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根本的道德分歧古已有之,并非启蒙时期以后才产生的。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中,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关于究竟应当做一个正义之人,还是不正义之人的争论,苏格拉底和塞拉西马柯关于正义是否就是强者利益的争论,都可以视为一种根本的道德分歧。(21)参见Plato,Republic,in E.Hamilton & H.Cairns(eds.),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1961,Book II(359d ff.)and Book I(336b ff.)。这种根本的道德分歧不仅在西方古代,在中国古代也同样存在。比如,农民起义“均贫富”的主张和统治阶级“三纲五常”的主张也是一种根本的道德分歧。恰恰是因为存在着这样根本的道德分歧,启蒙以来的哲学家才努力寻求答案。我们并不能因为哲学家寻求这种答案而倒因为果,认为是哲学家造成了根本的道德分歧。因此,将根本的道德分歧归咎于启蒙计划是犯了“假原因”的逻辑谬误(fallacy of false cause)。
麦金太尔也许是想说,西方现有的、源于启蒙计划的理性框架无法解决这种根本的道德分歧,因为争论双方根本对立的观点在现有的理性框架之下是不可公度的。他说道,西方道德争论的双方“所援引的概念五花八门并且明显地不可公度”(22)A.MacIntypre,After Virtue,p.35;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45页。。由于国内不少学者有意无意地认为哲学的第一原则或道德的终极原则是无法进行辩护的,且对立的终极的或根本的价值原则之间是无法比较合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可公度的,这种观点对于伦理学研究最终能否建立在理性和客观的基础上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麦金太尔的不可公度性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与讨论。
那么,为何不可公度?在麦金太尔看来,西方道德分歧的双方在进行道德争论时,都可以根据演绎推理有效性的要求,构造一个支持自己结论的逻辑上有效的论证,即当其前提为真时,其结论一定为真。但这些有效论证的结论却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真。从这些对立、矛盾的结论,我们最终会推溯到论证者各自所诉诸的互相矛盾的行为目的或价值原则。麦金太尔认为,由于这些价值原则是不可公度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比较两条原则合理性程度或力度的统一的量化单位,以便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决定哪一条原则更为合理,因此这样的道德争论是无法合理解决的。他说:“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任何既定的方式可以在这些主张之间进行抉择,道德论证看上去才会必然无休无止。从这些对立的结论,我们可以反推到其对立的前提;可是,一旦我们找到这些前提,论证也就停止了,从而援引一个前提反对另一个就变成了一件纯粹断言与反断言的事情。或许这就是道德争论中尖叫之声嘶哑嘈杂的缘由。”(23)A.MacIntypre,After Virtue,p.8.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9-10页。
然而,这种无休无止的道德争论所涉及的根本道德原则或最终行为目的真的就不可公度了吗?当一个价值原则和另一价值原则发生冲突之时,当一个行为目的和另一个行为目的发生冲突时,我们真的就没有理性的方式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真的无法合理解决由于这种分歧所造成的具体的道德分歧或政策分歧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区别两种不同的可公度性概念:一种是以基数标度(cardinal scales)为单位的量化的可公度性,一种是以次序标度(ordinal scales)为标准的非量化的可公度性。假定有两个比较的对象,A和B,它们可以是事物、事态、欲望、行动目的等等,那么建立在基数标度上的“可公度性”可以定义如下:
A和B的价值或重要性是可公度的,当且仅当它们的价值或重要性可以通过量化的单位精确地衡量或相互换算。
比如,一位大学毕业生有两个单位愿意录用。一个单位给的月薪是5000元,另一个单位给的月薪是6000元。如果收入是这位大学毕业生选择的唯一考量,那么这两种选择的价值或优先性可以通过人民币单位精确地加以衡量,故两者是可公度的。
在缺少量化的基数标度来衡量和比较两个对象的价值或重要性时,我们可以采用次序标度来决定比较对象的价值和重要性或选择的优先性,次序标度的可公度性可以定义如下:
A和B的价值或重要性是可公度的,当且仅当存在着一个价值或重要性的次序标度或价值排序,按照这一次序标度或价值排序我们可以决定A和B价值的优劣或重要性的程度。(24)关于上述两种可公度性概念,参见R.Chang,“Introduction”,in R.Chang(ed.),Incommensurability,Incomparability,and Practical Reas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34;J.Griffin,“Incommensurability:What’s the Problem?”,in R.Chang(ed.),Incommensurability,Incomparability,and Practical Reas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35-51;陈真:《论道德和精明理性的不可通约性》,《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
比如,如果我们必须在守约和救人之间做出选择,尽管它们之间不存在基数标度的可公度性,我们还是可以决定哪一种选择更合理,更有价值。这时我们选择的标准不是根据价值的量,而是根据价值的质,即根据次序标度来进行选择。按照一般的情况,人的生命比守约更重要、更有价值,因此,救人的行为更有价值、更重要。
麦金太尔的主要问题是,他只考虑了一种意义上的可公度性,即可量化的基数标度意义上的可公度性,而没有考虑到非量化的次序标度意义上的可公度性,因此,得出根本价值原则不可公度的结论。然而,按照非量化的次序标度意义上的可公度性,几乎所有的价值原则或比较的对象,如果不是全部,原则上都是可公度的。麦金太尔可能会质疑:其一,并不存在着一个一成不变的并且可以应用于任何具体情形的次序标度的价值排序。对于任何一种次序标度的价值排序,我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否认这一排序的具体反例。其二,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一个价值排序,当不同的人们提出不同的价值排序时,我们应当如何决定谁的排序客观上是“正确的”?麦金太尔显然认为按照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的理性概念,西方哲学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客观的方法来判定谁的排序是正确的。
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首先,虽然我们并不能找到一成不变的、适用于任何具体情况下的价值排序,但我们总是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找到一个适用于该情景的具体的、客观的价值排序。其次,由于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是先天的(apriori),关于价值或重要性排序的判断也是先天的,其正确性不可能建立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但我们只要充分理解了相关事实和条件,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何种价值排序客观上是正确的,就像我们理解了1+1=2的命题意义,我们就知道该命题客观上是正确的一样。这一决定客观上正确的价值排序的思路本质上是康德思想的延续。这种客观的价值排序或优先性排序对于理性的人们而言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一个不随地吐痰的社会优于一个随地吐痰的社会”,这一判断所预设的价值排序是:在正常条件下(如不妨碍行动者根本利益的条件下),保持公共场所清洁的原则优先于个人自由的原则。在是否可以随地吐痰的问题上,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这一判断,包括这一判断所预设的价值排序,是客观的,独立于任何人主观意志和愿望要求的,也独立于麦金太尔所说的所谓“传统”。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有随地吐痰的“传统”而认为随地吐痰是合理的,或者认为随地吐痰社会优于不随地吐痰的社会。
当然,并非任何价值排序的正确性都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在麦金太尔所提到的关于流产的道德争议和关于分配正义和私人财产权的争议中,双方所预设的价值原则似乎就没有一个一目了然的客观的价值排序。(25)参见A.MacIntypre,After Virtue,Chapter 1。前者预设了妇女自主生育权与婴儿生存权的冲突,后者预设了平等原则和个人自由原则的冲突,我们并没有一个一目了然的对立原则的价值排序或重要性排序。但某个具体问题或具体情景中没有一目了然的价值排序,并不等于没有客观的价值排序。问题是如何发现和找到这样的客观价值排序。当代西方哲学家沿着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传统,提出了初始(primafacie)义务论、理想观察者理论、反思平衡的方法和理由根本主义(Reasons Fundamentalism)等,为具体情景下找到客观的价值排序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思路。按照罗斯的初始义务论,当不同的行动目的或价值原则在具体情形下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最终可以诉诸我们的理性直觉解决这种冲突。(26)参见W.D.Ross,The Right and the Good,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pp.16-47。按照费斯(Roderick Firth)和布兰特(Richard Brandt)等人提出的理想观察者理论,当行动者处于理想的认知条件下,在掌握了所有相关的事实问题时,理想行动者对具体情形下对对立原则的选择就是客观上正确的选择,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排序就是客观上正确的价值排序。(27)参见R.M.Firth,“Ethical Absolutism and the Ideal Observer”,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12,1952,pp.317-345;R.B.Brandt,“The Status of Empirical Assertion Theories in Ethics”,Mind,Vol.61,1952,pp.458-479。按照罗尔斯反思平衡的方法,人们可以从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considered moral judgments)——一种新的道德直觉——出发,通过反复的辩论以消除道德思维中的各种潜在的矛盾与不一致,达到某种反思平衡的状态,从而解决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道德分歧,包括根本的道德分歧。(28)参见J.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Sections 4 and 9 in Chapter 1。按照斯坎伦的理由根本主义,具体的理由为根本价值原则的判定与抉择,包括根本道德分歧的解决,提供了最终的根据。(29)参见T.Scanlon,“Contract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in A.Sen and B.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3-1228;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Chapter 1;Being Realistic about Reas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Lecture 1。我们这里拟提出一个进一步解决根本价值分歧和冲突的理性原则。由于通常情况下诉诸武力或丛林法则不符合争论双方的利益,因此,只要道德争论双方不希望通过武力或丛林法则解决彼此的冲突,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客观的、理性的方法来解决价值排序问题并进而解决彼此的冲突。这个解决价值排序的理性原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关于流产问题的争论一直是一个西方社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既希望尊重妇女的生育权,同时也希望承认胎儿的生存权。当二者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我们如何解决这种冲突,如何解决它们的价值排序?在流产问题的争论中,贯彻任何一种原则,都必然会导致根据另一个原则所不希望发生的后果。尊重妇女的生育权会导致无辜胎儿——人类胎儿——的死亡,然而,如果无条件地强调胎儿的生存权并从法律上禁止流产,则会在现实中造成大量的不安全的流产,给孕妇的健康,甚至生命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两种后果都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如果能够避免,我们应当尽可能避免其中任何一种。但万一出现怀孕,而孕妇本人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希望流产,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有条件地(即尽可能早地采取流产措施,而不是等待3个月以上)选择允许妇女流产。那么,当我们运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时,怎样判断两害孰轻孰重常常是一个需要通过社会长期争论,甚至长期观察(以解决孰轻孰重的问题),才能解决的问题,但原则上,这种争论并非永远无休无止。当我们决定选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时,我们原则上就已经确定价值排序或解决了价值排序的问题,剩下的争论往往是事实问题的争论,而事实问题无论多么复杂,原则上总是能够解决的。正如流产问题,究竟道德上是否允许,有人也许不同意我们的结论,但只要赞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我们之间的分歧原则上都是可以解决的。关于平等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的争论也是一样,我们最终是通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解决它们的排序和冲突。这些根本价值原则的冲突与争论往往涉及非常复杂的事实问题,往往需要具体情形具体分析,比如,是否实行社保体系,建立怎样程度的社保体系,往往涉及各方利益和博弈,涉及各种事实的变量,往往需要各方充分讨论和辩论才能达成共识。而且,每一种具体情形都各不相同,因此,平等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的排序不可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一样的。然而,我们之所以对达成共识抱有希望并且这种希望是合理的,正是因为我们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上能够达成共识。这就是无论所争论的问题看上去是多么难以解决,我们始终愿意去争论,去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总是越辩越明,事实总是能够澄清,问题总是能够解决。
总之,即使我们无法找到量化的可公度的方法来解决根本的价值原则的冲突问题,我们依然可以诉诸非量化的可公度的方法,即具体情景下的价值排序的方法来理性地解决根本的价值分歧。即使具体情景下的价值排序不是一目了然,我们依然可以有理性的方法来解决或认识客观上正确的价值排序。因此,根本的价值分歧也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加以解决的。这些方法本质上是启蒙思想家理性思想的延续。因此,不仅麦金太尔以不可公度性来否认启蒙思想家的理性方法是难以成立的,而且他认为根本的道德分歧是无解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 启蒙计划的道德合理性论证真的是与历史、语境相分离的吗?
麦金太尔认为启蒙计划不仅造成了西方道德分歧的无解,而且也造成了西方道德或道德语言的无序状态。他设想了一场自然科学的浩劫。在他的想象中,一系列环境的灾难导致公众将原因归咎于自然科学家。一场规模巨大的骚乱将实验室摧毁、科学家处死、科学书籍和仪器焚毁,与骚乱接踵而至的一场政治运动废除了学校里的科学教育,监禁并处死了留下的科学家。当曲终人散,人们终于从混乱中清醒过来而试图恢复自然科学时,只剩下残片断句。人们开始恢复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并凭借残篇断句开始研究,“中微子”“质量”“比重”“原子量”等术语虽然还在使用,然而由于其预设的科学信念已不复存在,因而人们围绕科学理论,如相对论、进化论等所展开的争论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完全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麦金太尔断言,西方道德正处于一场类似的浩劫之中。他说:“我要提出的假设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道德语言,同我所描绘的这个想象世界的自然科学的语言一样,处于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30)A.MacIntyre,After Virtue,p.2;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2页。“道德的完整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碎片且部分被毁”。(31)A.MacIntyre,After Virtue,p.5;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6页。
在麦金太尔看来,启蒙计划的道德合理性的论证,包括道德语义的分析,与历史情景和相关语境分割开来既是造成西方道德和道德语言无序状态的主要原因,也是无序状态的具体表现。为何将道德问题与历史情景和相关语境分割开来会造成道德的无序和无解?麦金太尔认为道德之所以能够发挥实际的效力,恰恰因为都是个人的、历史的和具体情景依赖的。他认为当代西方道德论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争论的双方“无一不是旨在提出一种非个人的合理性论证,从而通常都以一种适合于非个人的模式出现。”(32)A.MacIntyre,After Virtue,p.8;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10页。但是道德断言的力量或效力,在历史上实际上都是依赖于其具体语境的,特别是依赖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当一个人说“请如此这般地去做”(道德律令通常可以表达为祈使句),另一个人凭什么,或者有何理由去遵照该命令行事,往往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上下级关系。“在这类情况下,我的话是否给了你一个理由,取决于你听话时所具有的特定情状或你对我的话的领会。在这一方面,这一命令具有什么样的说服力取决于话语的个人语境。”(33)A.MacIntyre,After Virtue,p.9;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10-11页。然而,当代西方道德争论双方却以某种非个人的方式提出他们的论证,这样就割裂了道德话语与其可以发挥效力的语境,脱离了双方道德断言可以发生效力,可以统一双方认识的语境,“言说的语境与表达个人爱好和欲望时不可或缺的说服力之间的特殊联系,在道德以及其他评价性言说那里被割裂开来了”,(34)A.MacIntyre,After Virtue,p.9;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11页。道德争论的双方“从那些对立的立场所做出的断言,由于离开了其理论和社会的语境(断言中概念的最初阐述和理性辩护就是依据的这些语境),典型地并且普遍地变成了仅仅是态度和感受的表达。”(35)A.MacIntyre,“The Claims of After Virtue”,p.70.这是造成当代西方道德语言处于分离无序状态的重要原因。如何评价麦金太尔的上述指责?
首先,是否应当以一个理论实际上发挥效力来评价一个道德理论的正确与否?麦金太尔显然认为是,然而实际上不是,道理很简单:因为实际发挥效力的理论未必都是正确、合理的。比如,印度的寡妇殉夫制(suttee)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一千四百多年的实际效力,但却未必是正确的,未必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实际发挥效力并非是一个道德理论正确性的充分条件。能否实际发挥效力甚至也不是一个理论正确性的必要条件,因为一个合理的道德理论或道德要求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发挥实际效力,比如,对一个理性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未必就能够发挥实际效力,但这并不能证明该理论或要求是错误的。所以,以是否发挥实际效力来评价一个道德理论或道德辩护的正确性是难以成立的。如果“实际效力”主要指可以打动一个行为者,那么一个合理的、正确的道德理论或道德要求的必要条件只能是:可以打动完全理性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或部分理性的人。西方哲学家自启蒙时期以来一直试图为道德合理性进行辩护,为道德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这种工作逻辑上、概念上就蕴含可以打动理性的人,也就是说,这种工作,如果成功,确实具有可以打动人意义上的“实际效力”。
其次,当代西方哲学家为道德合理性所做的辩护是否脱离了历史的语境?其一,并非所有的历史语境都是与道德合理性的辩护相关,比如,历史上三从四德的语境就与现代道德的合理性辩护无关。而麦金太尔显然认为启蒙时期以前的西方道德、西方伦理或伦理学都是相关的,但这需要说理,而麦金太尔显然缺少这样的说理。其二,在麦金太尔的表述中,仿佛以前的道德或理论都是与历史语境完整的结合在一起,都是很好的,但经过启蒙时期思想家用理性代替上帝或神学以后,就将本来“那些构成人类诸多文化之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体”弄得支离破碎了,麦金太尔这种厚古薄今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也不符合实际事实。历史语境应当是相关的历史语境,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变革的相关语境,一方面是当代的语境。从这两个方面,启蒙时期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为道德合理性所做的论证并没有脱离其历史和相关的语境。众所周知,在启蒙思想家之前,西方社会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约14世纪到17世纪)的洗礼,在这场长达数世纪之久的运动中,人们以人性反抗神性、以人权反抗神权、以理性反抗盲从,中世纪的神权早已开始动摇。正是由于西方社会自身的这一深刻的变化,启蒙思想家提出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以取代以上帝为基础的神旨论,他们的哲学反思将上帝、神学从道德中分割出去,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不仅为失去上帝权威之后的西方道德提供了新的权威——理性,也为后来的道德哲学家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展示了新的研究进路,为后来世俗社会里的法治奠定了道德理性的基础,无论从历史还是思想史的角度,都是积极的、与时俱进的、值得肯定的。而当代西方元伦理学家,无论是认知主义者还是非认知主义者,都是从西方日常道德语言的实际使用去分析道德语言的含义并进而为道德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样的辩护看不出是如何脱离了必要的当代的历史语境。而当代西方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则与当代的历史语境和日常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一些道德案例直接取自法庭判决的案例。
再次,道德合理性论证应当是个人的,还是非个人的?麦金太尔认为西方哲学家道德合理性论证的问题之一是:这种论证是非个人的(impersonal),而非个人的辩护由于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因而缺少实际的效力,这是导致无休无止的争论,从而导致启蒙计划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道德或道德要求本身就是非个人的,因而其合理性的论证当然也是非个人的。道德合理性论证的非个人特征恰恰是道德或道德义务所要求的。任何合理的、客观的道德要求一定是普遍的、非个人的,独立于个人欲求和要求的,无论个人是否有意愿遵守,都必须遵从。这并不是说道德要求或道德义务与个人毫无关系,道德义务通常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不可能不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孝顺的义务涉及子女与父母的关系,遵守承诺的义务涉及承诺与被承诺者的关系,还钱的义务涉及借者与贷者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论,道德义务是行动者相关的(agent-relative),但这种义务并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欲求,比如,子女不愿意尽孝,借钱者不愿意还钱,但依然应当遵守相关的道德义务,因此道德义务必须是非个人的。道德义务的这种普遍性和公共性似乎也为麦金太尔所承认,因为他指责当代西方道德的理由之一就是它“不再具有任何公共的、人所共有的合理性或可证明性”。(36)A.MacIntyre,After Virtue,p.50;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64页。麦金太尔这种前后立场的不一致反映出他批判启蒙计划的思考确实不严谨、不缜密。
综上所述,麦金太尔指责启蒙计划将道德与历史语境分割开来,造成了西方道德的无序状态,其理由要么难以成立,要么缺少事实依据。
麦金太尔主张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去研究道德问题和道德理论,因为他认为“不属于任何特定社会道德的道德是不存在的。”(37)After Virtue,pp.265-266;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338页。他称他所捍卫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38)After Virtue,p.266;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338页。。按照这种历史主义,我们应当从“那些构成人类诸多文化之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体中”(39)参见After Virtue,p.10;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12页。,从道德论说的各种概念原本都借以发挥作用的那些“更大的理论与实践总体”(40)参见After Virtue,p.10;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第12页。的语境中,去寻找其理论的力度和说服力。然而,由于他拒绝用启蒙时期以来的理性作为解决道德分歧的基本方法,又由于实际发生的历史传统和历史上的复合体未必就是合理的,在《追寻美德》之后,他最后诉诸的是神学目的论、托马斯主义和上帝的权威。(41)参见麦金太尔为2007年版的《追寻美德》所写的序,After Virtue,pp.x-xi;陈真:《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吗?——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批判》,《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从人类思想发展史来看,这似乎是一种倒退,而非进步。因此,启蒙时期以来的理性方法,亦即讲求概念清晰、逻辑论证和经验证据的方法,依然是我们解决根本道德分歧,解决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难以取代的方法。麦金太尔对启蒙计划的批判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