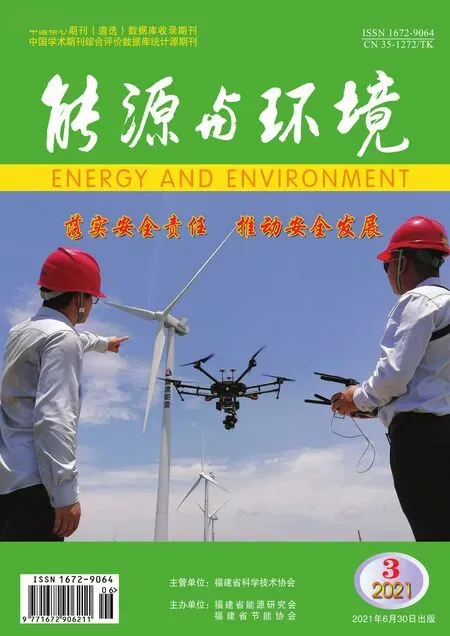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开展健康风险源头控制
刘晓曦
(吉林省正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长春 130000)
为了更好地预防因为规划不合理而导致的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的负面影响,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协调化发展,其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属于环境风险评估的重要方式。从我国的环境相关保护法律角度来看,国家目前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善的环境、健康监测体系,同时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调理当中明确提出,应当从分析、预测以及评价的内容,涉及到规划实施可能对于环境、人群健康的直接影响[1]。目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环境健康的相关内容以及技术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对此,探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开展健康风险源头控制显得格外重要。
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问题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区等快速发展,并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成为了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近些年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加重,关于多人群的环境污染事件也在不断增多,这和产业规划布局之间的不合理有着密切关联性。纵观当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现状,因为规划健康风险评估方式方面的欠缺,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将人群健康防护等因素考虑到其中。在当前的规划环评时间,期间只能够单纯参照环境质量标准的权衡区域排放控制,实际上有许多的化工园区排放的特殊污染物并不在环境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当中,导致人群活动空间和企业之间的局部缺乏合理性。同时许多污染事件也衍生出了关于规划源头健康风险防护的重要性意义,但是规划健康评估却因为技术、职能部门的模糊性导致无法出台。从当前的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角度来看,健康风险的评估技术仍然存在缺陷,实践期间并不能将人群健康防护的多方面因素加入其中[2]。在当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导致无法按照当前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开展人群健康的风险评估。例如,某石化园区中,如果单纯以大气环境的角度进行考量,其中大多数指标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实际上周边群众仍然会经常遭受刺激性气味影响,所以这一些指标并不能直接作为大气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
2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特征
自从20 世纪开始,国家对于战略性环境保护评价的理论方式就开始了研究,同时在不断地总结和创新,这也为我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许多的理论基础。但是,当前来看仍然存在现状落后的情况,停留在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以及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的层面。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并没有一个相应的理论方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约束条件指标仅仅是停留在资源环境的承担方面,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人群健康的影响指标。在技术导则方面,虽然规范了具体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流程,但是对于风险评价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只有指导性条款,在具体技术导则方面,并没有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规范,只是提出了预测与评估的内容,在规划实施方面对于人群健康的影响并不突出,技术方面究竟如何实现仍然缺少规划健康风险的评估技术导则,导致具体实施效果不理想。
当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发展滞后主要是由规划健康风险评估自身的特性而决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特征主要在于下面4 点:①系统性。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一性主体评价相比,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价主要目标属于多生产、生活等主体,带有突出的风险源识别功能,叠加和人群活动预测的耦合性特征;②情景性。在规划构成的不同要素分析期间,无论是生产排放还是突发性的事故概率,在现实分析方面都带有叠加、后果估算以及风险预测等特性;③反向约束。和传统的健康风险评估方式相比,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最终目的是借助风险承担力的评估,提出具体的约束指标,从而实现对风险源的调整。这一约束性指标可以为整个规划进行布局,其主要目标在于规划的绿色、环保以及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④规划互动性。规划健康的风险评估应当贯穿在整个规划期间,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具备和规划的互动特性,同时对于整个规划过程可以形成指导性支持。上述4 个特征也决定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复杂性,同时对于技术融合的要求也相对较高。
3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难点和发展趋势
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现状来看,技术难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空间尺度上情境暴露的模型。核心在于空间方面多风险叠加和人群实际暴露的耦合关系。从单个的行业微观排放以及区域内环境尺度范围内的污染物分布特征角度来看,对于个体、群体平均暴露水平的估算方式,可以应用定性结合定量的方式进行分析,并构建相应的情境暴露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健康风险的承受力对于规划期间不同排放源的方向制约性存在作用。规划健康风险的评估期间最为关键的健康承受力阈值在于明确技术方面的健康风险评估水平,并在这一基础上完成健康约束性指标的延伸。
国际上传统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应用了约40 年,其中的“四步法”理论也比较成熟,技术从以往单一性的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估转变为了多因子、多暴露途径的叠加风险评估,同时对于情境的应用也在不断的成熟化。结合空间分析的技术特征,对于不同污染源的叠加处理方式,可以实现优化风险控制的规划。借助分析总结方式可以更好地评价评估发展趋势,并在规划环境评价中应用,补充规划环境评估中风险健康风险承担估算的参考指标。规划健康的风险评估中,健康风险承担力属于约束性的指标,其主要是指环境系统中所能够承担的污染物数量和可支撑性经济规模、人口局部[3]。其关键在于分析和识别规划发展期间的健康风险承担能力,并协调不同环境介质下的环境容量发展对于健康的影响,同时基于健康承载能力实现对区域污染物排放量、浓度的控制与约束。在具体的约束指标方面,借助源强分析方式,情境排放的环境影响属于定量化的评价,制定具体的环境准入条件并实现对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与此同时,借助评估发展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明确关键健康损益性的指标,并借助有偿分配、产业结构优化等思路进行改进。如何将健康风险的约束指标应用在规划当中的约束性指标当中,并分配到不同排放源属于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4 推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发展的有效策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破坏问题越发严重和普遍。从我国的环境保护技术现状来看,规划健康风险评估的技术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导致当前在规划方面的源头保护人体健康的能力与作用相对落后。为了更好地展现环境保护当中人本化的基础理念,从而预防因为规划不合理而导致的群体健康负面危害。目前来看,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于做好健康风险评估技术的研究,并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法律,对健康相关内容进行完善与补充,这不仅是贯彻环境保护理念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环境保护法律的重要落实环节。下面从2 个方面探讨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的发展策略。
(1)及时开展重点区域的规划健康风险评估技术的研究,针对性的推进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规范和导则。一方面需要注重情境暴露水平的关注,在对规划实施预测分析同时,不仅需要注重多风险叠加的复杂空间分布情况,同时还需要注重规划空间中人群的不确定性特征,提出规划健康风险评估的具体方式。另一方面提供关于健康风险评价的相关指标,注重空间地理单位方面的健康风险指数,注重不同环境尺度之下健康风险承担力实现对约定产业调整的动态化评价指标。在充分探究的基础上,可以将研究成果构建成为技术规范和导则,从而支撑相关的环境管理制度需求,提高整体建设效益[4]。
(2)需要注重重点区域的规划健康风险评估作为重点工作环节,针对性的完善制度体系与设计体系,并从根本上注重区域健康的风险防控。在深入开展基础研究期间,需要及时组织并开展重点区域的规划,并基于健康风险评估作为试点开展。借助试点不断的完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方式以及技术体系,同时提高整体科学性以及可操作特性。目前来看,建议先针对相对发达的城市着手,基于发达产业与人口密集区域,针对性的开展规划健康防护和产业的合理性布局。按照国家的发展战略,开展预期实施后的健康风险评估,同时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人群健康风险防护性的支持。逐渐构建形成管理应用和科技支撑性的融合发展,并逐渐构建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从而将污染健康的风险真正控制在源头。
5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显得越发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整体水平并不理想,健康风险源头控制非常重要。健康风险源头控制属于环境保护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风向标。健康风险源头控制工作应当有效贯穿在整个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做好基础性技术支持。与此同时,健康风险源头控制工作还需要突出监督性功能,推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持续发展,为环境保护工作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