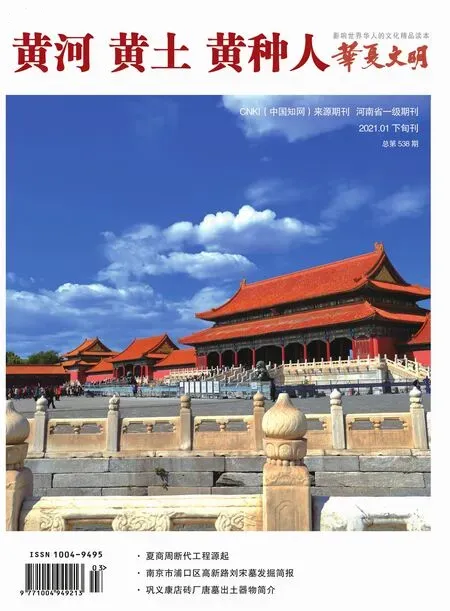夏商周断代工程源起
朱学文口述 苏喜成记录整理
1995 年,我国两位国务委员,主管文教、社科的李铁映和主管科技的宋健,推动我国历史考古学界做了一件大事,他们共同组织了200 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专家联合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年代缺失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事情虽然过去20多年了,但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却仍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现谨对往事略作记述,既是一种追忆,亦祈对来者有所启迪。
1995 年,那是我先生刘光宁在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办公室工作的第三年。 同年7 月下旬,宋健同志要到北戴河休养,他邀请刘光宁偕家眷一起前往。我毫无思想准备地随同一行人登上了去北戴河的列车。 刚一进入车厢放下行李,刘光宁就招呼我到客厅去见宋健主任。我担心跟宋健主任没什么可说的,有点忐忑。 刘光宁说,放心吧,宋健主任惜时如金,不喜欢闲聊,这次只是礼节性的见面而已。
进了客厅,两三句寒暄之后,宋健主任问我学什么专业,哪个学校毕业的,现在从事什么工作,我一一作了回答。 宋健主任又问,你对于中国的历史纪年从什么时间开始的注意过吗? 我说,中国的历史纪年是从公元前841 年开始的,那是西周共和元年,司马迁定的点。说到这里,宋健主任话匣子打开了。 他说,他正想找一位学历史的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像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早期历史年代的缺失已是既成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在陈列或者展现历史过程时,怎么表达那一大段缺失历史年代的时间概念。 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有关公元前841 年以前的部分实物丰富,而年代表达一律是“约公元前××世纪—约公元前××世纪”, 这几乎是不变的表达方式。 这个“约”字太笼统、太模糊,反映出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宋健主任说,他经常看到报纸上、电视上报道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数量相当大,看得出考古学家的自豪和乐此不疲。 而他总在想,考古学家怎样才能把他们的成果让普通人分享,分享这些成果的意义,分享他们的快乐。 这里就有一个成果量化的问题,这一点做得显然不够。
宋健主任说,最近他访问埃及,参观埃及的国家历史博物馆。 他们对古代历史的陈列不仅实物丰富,而且年代表达清晰、完整、成系列。 每一个古代王国的年代都有数字表达, 使人不由得肃然起敬。要知道,今天的埃及人和古代文明时代的埃及人不是同一个种族。 古文明时代的埃及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四散了,今天的埃及人是后来的定居者,这个国家的历史曾经有过断裂。 今天的埃及人对他们这块土地上的古代文明历史有如此详细的研究和表达,是非常不容易的。
宋健主任接着说,当然,对埃及古代历史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西方学者。早在拿破仑出征埃及的时候,他随舰带了几位科学家,带回去一块刻有古代文字符号的石碑,从此,开启了法国人释读石碑文字的研究,这就是埃及学的发端。 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投身到对埃及古文明的研究中,他们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 对埃及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手段也越来越先进,经过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成果。 两河流域的历史研究大致也是这样的过程。
宋健主任说,年代学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他一直在想,西方学者研究埃及学采用过的各种技术手段,今天我们都具备。我们在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面也已经有一百年的积累,眼下20 世纪还剩几年,在这个时间点,综合总结一下以往的研究,完全有必要。 当然,要有一个新的目标、新的高度。他的想法是,让自然科学参与进来,联合攻关。 尝试解决一个最终必须由我们自己解决的、公元前841 年以前的年代学问题。 解决年代学问题,用中国学术界习惯的说法,叫“断代”,我们就叫它“夏商周断代”吧。
宋健主任又开始向我提问:中国史学界有没有人提出过开展对公元前841 年以前的年代学研究的议题? 我说,我的见闻有限,没有听说过这个议题。宋健主任问:历史学家为什么不提?考古学家为什么不提?我无法回答,在那种场合又不得不回答,只好把学科细分之后自己的感想拿来作答。 我说,提出如此重大的议题, 需要有相当宽广的宏观视野,而现实是我们的学科越分越细。我们上学时,历史与考古专业并存于一个系,彼此都觉得是用不同的手段研究历史问题。 现在分成两个系,彼此隔膜了。 现在的历史系出来的人,不少学近代史的人不关心古代史, 研究古代史的人不关心现代问题,这几乎是常态了。研究的细化、深入化,就像挖井人一样,当他见到水的时候,终于成功了,可他面前,目力所及,只有他亲手挖出来的井口大的一块天。 在这种条件下,宏观视野很难建立起来。
宋健主任说,他想找几位研究先秦史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讨论一下能不能组织起一支队伍来做这件事情。中国历史的年代学问题总不能等外国人来做吧!趁他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推动这件事,离开了就推动不了了。听他说得这样直白、真诚,我很感动。他又问我:“你认识不认识先秦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 ”我说:“认识倒是认识的,但是久不来往,可以试试。 ”他说:“这件事就请你帮忙,我可是认真的。 ”我说:“我理解。 ”
他又提到,他很想参观一下考古研究所的陈列室,但是不便提出,怕人家说他手伸得太长。当时我完全不懂,作为国务委员,怎么连参观考古研究所陈列室还要有所顾忌呢? 比这个疑问更重要的是,那天与宋健主任的一席谈话从此成为我和一大批朋友二十多年探索不歇的话题。我原以为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不料听了洋洋洒洒一堂生动而立意高远的历史课,很是震撼。 时间过去了25 年,宋健主任和我对话的具体内容可能记得不十分准确了,但对其中的要点,我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 回到包厢后刘光宁向我感慨了一句,最近几个月不断地听宋健主任念叨“埃及学,埃及学”,周围所有搞科学技术的工作人员都不解其意,今天听了宋健主任和你的谈话才恍然大悟。
一餐饭之后,宋健主任又叫住我说:“我想请你介绍认识先秦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你说可以试试,我现在想落实一下,你到底是有这样的朋友,还是只想试试?”我说:“历史学家只要他人在北京,您回去就可以见到,考古学家过去有过师生之谊,要见到他们也不会太难。”宋健主任说:“那好,我就等你的消息。 ”宋健主任的急切心情又一次溢于言表。
那时是1995 年,我还没有手机,身在北戴河要和北京的朋友联系还多有不便,只有等回到北京才能去联系寻访想找的师友。 那几天,我整天都在想该把谁介绍给宋健主任。 想来想去,我把目标定在李学勤和俞伟超二人身上。 我对李学勤的了解,主要来自侯外庐先生。侯外庐先生每当谈及他钟爱的学生们,除了为逝者哀伤外,从他嘴里流露出来的全是对学生们的赞美。其中对李学勤的赞赏之辞最多。 我记得侯外庐先生对他的夸赞常挂在嘴边的是:少年成才,异常勤奋,对史料的熟悉同代人难以比肩。 李学勤更大的优势是在掌握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之外,简帛也已经进入他的研究之列。侯外庐先生在李学勤提出从思想史研究室调到先秦史研究室的想法时立刻批准,当时我很是不解,侯外庐先生怎么这么轻易地放走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呢?后来侯外庐先生跟我说,李学勤有大抱负,应该成全他。 侯外庐先生的评价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下的人看法有没有变化呢? 我还想做一些了解。
“文化大革命”前,俞伟超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中口碑很好,大家几乎公认他有才。 “文化大革命”后,俞伟超先生出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新一代有思想的考古学家。
一周后回到北京, 我立刻打电话找李学勤,不巧李学勤去香港了,只有再耐心等他回来。 接着我又去中国历史博物馆, 直接找馆长俞伟超先生,不料俞伟超先生也出差了,归期不定,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吴岱封先生接待了我。吴岱封先生送了我一件当天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的恐龙展览的宣传品——印有黑色恐龙的白色T 恤衫作为见面礼物。我请吴岱封先生尽快转告俞伟超先生,就说朱学文有急事找他。
既然李、俞二位先生都一时联系不到,我只好再联系一位我很敬重的历史学家——黄宣民先生。他是专攻中国思想史的,古史功底很好,视野宽广,看问题往往比一般人多一个学术史的角度,所以见地比较深刻。相识十余年来,我们彼此信任,谈话无须设防,我相信找黄宣民先生是很合适的。
接通电话以后,我就把宋健主任的那番话告诉了黄宣民先生,并且说宋健主任有一个意图,想组织我们的人文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起联合攻关中国公元前841 年以前的年代学研究,具体说就是“夏商周断代”研究,把西方人在埃及学上做好的方法借用过来,在20 世纪之末,21 世纪到来之前,我们最好能拿出一张最近一百年来自己的科学研究答卷。 这一百年我们做了那么多事,要总结出一些东西来,也算是对大家辛苦付出的一个交代。 我跟黄宣民先生这么一说,黄宣民先生表示,这是天大的好事啊,有这样的好事,那可要抓紧啊,要抓住这次机会。他有点感慨,但是也不激动。我说:“宋健主任要我找几位有水平的古代史专家和考古学家,跟他们商议一下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条件开展,怎么开展、怎么组合比较好,我回来了就赶紧行动。 ”黄宣民先生问我要他做什么,我说:“你觉得古代史专家谁最合适,考古学家谁最合适? ”黄宣民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史专家中李学勤是不二人选,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随即就一一列举了李学勤的学术成就。 我说:“这些我都知道,这些都是十年前侯外庐先生对他的评价,我就想知道,经过了十年,历史学界有没有更加新锐的人才出现。 ”黄宣民先生让我不用考虑别的人了,李学勤是不二人选。 黄宣民先生又一次用了“不二人选”这个词。听了黄宣民先生的这番话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想的最佳人选就是李学勤,黄宣民先生跟我不谋而合。
我说:“这么讲的话,这些年起来的年轻教授们暂时都可以不考虑了。 不过,听说李学勤这个人不太爱管事, 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会铺多大的摊子,但我觉得肯定不会小。”黄宣民先生认为那是我不了解李学勤,他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不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 我说:“这好像跟我听到的别人的议论有点不同。如果遇到重要问题需要决断的时候,李学勤能不能当机立断、驾驭局面呢? ”黄宣民先生明确指出:这就是你还不太了解李学勤的地方,李学勤这个人是不会多管闲事的人,不会和别人发生重大的冲突,是个很安静的人。 但是放心好了,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李学勤是个很有魄力的人,敢于决断、敢于担当。学术界一些很前沿的见解恰恰都是这个不大爱多说话的李学勤提出来的。我听黄宣民先生这么说就放心了,我要推荐给宋健主任的人应该是一个有担当、敢说话的人。这时,黄宣民先生突然话锋一转讲道:有一个问题倒是想提醒你,这个工作一旦开展起来,很快就会有人打出一面大旗来反对,反对的队伍一定还不小,阵势会很大。我说:“什么人呢?”黄宣民先生说就是这一百年来被肯定的一种新的思潮——古史辩学派,顾颉刚的古史辩学派现在已经成为正统。而中国有一个特点,凡是在做学问的问题上,哪一种见解变成正统的时候, 大家都会把它举起来当成一面革命的旗,凡是反对这个见解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帽子给他扣上去,说他保守、复古,很不堪的话都会说出来。我说:“那可怎么办?李学勤会不会害怕啊?”黄宣民先生却说是要提醒我有思想准备,不用担心李学勤,要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李学勤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想:那挺不错的,给我原来想推荐李学勤的理由又加了一条。黄宣民先生又提到这件事肯定会有人反对,而且阵势很大,提醒我到时候不要惊慌失措。
这个电话就这样结束了。黄宣民先生没有说更多话,也没有出去跟人家传播,甚至于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跟我通过电话。当“夏商周断代工程”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 大报小报上登满了相关的消息,黄宣民先生连问都没问。他大概看到了谁在主持这个工作,觉得很放心吧。 过去黄宣民先生跟我联系还比较频密,后来他家里出了一点事,直到他后来去世,原先提醒我的话渐渐被证实,黄宣民先生却再也没有提过一句相关的话题。这也说明了他对李学勤是多么的放心。
跟黄宣民先生通话之后,我又找了一个学考古的大学同学——孙关根, 上学时我们同系不同专业。 孙关根毕业后分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如今已经认识了几十年,他非常正派。我们彼此很坦诚,却也没有十分密切的交往。我跟孙关根简明扼要地讲了宋健主任的意思,说宋健主任希望找几个水平比较高的、精通先秦史学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要跟他们探讨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开展。孙关根毫不犹豫地说:“史学只有找李学勤,非李学勤不可。”我说:“是吗? 有这么严重吗? ”他说:“有这么严重,你知道学者之间有时候吵起架来是会脸红脖子粗的,大家都是有名望的人, 可是有时候就是谁也不能说服谁。李学勤是我做编辑以来,我所接触到的那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最有教养、最干净的一个,身上一点不好的风气都没有。李学勤干净到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甚至觉得李学勤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年轻的文史专家里唯一的一位绅士。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跟别人争吵, 从来没见过他和别人脸红,交锋的时候他非常隐忍,彬彬有礼,永远如此,非常冷静。 找这样的人讨论问题是最好的,李学勤不会把场面弄得乱哄哄的,不可收拾。 有很多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会把矛盾激化, 弄得场面不可收拾,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我们需要这样非常冷静的人,对是非的判断很有立场。 ” 我追问:“觉得他这么好?”孙关根肯定答道:“他就是这么好,这就是他的特点, 你总不能给宋健主任推荐一个火药筒子,说不上三句话就跟人吵起来。研究这个课题必须要有一个识大体、冷静、控制得住局面的人。 ”
我又问:“考古学家呢? ”孙关根说:“考古学家人才太多,具体参与过挖掘的、亲历发掘几十年的人有的是,他们都很有见解、很有水平,但是他们脾气不一定好。 我不是说让你找个小绵羊去,但是这个人必须要有教养,这是做大事。”我认为孙关根说得很有道理。 孙关根这么一判断,我清楚了要找的一定不能是那种几句话不合就上火的人。孙关根还说道:“而且要办这种事的人还要有公心,不能私心太重。 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就是一个口碑极佳的教授。 北京大学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考古学家实在是太多了,搞各个段的都有,先秦这一段,严文明是我现在想到的最佳人选。 他的教养、品格、性格、为人各个方面口碑都极好。你可千万别去找那些炮筒子。 ”我赞同说:“好。 ”孙关根又说:“可惜严文明刚退休,不当系主任了,现在新的系主任叫李伯谦,那是很年轻的一位,这个人我感觉为人很好,你可以再去做一些了解。”电话就讲到这里。在以后的日子里, 跟 “夏商周断代工程” 接触最早的两位朋友——黄宣民、孙关根,从此都没来电话打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情况。这项工作开展以后,我也特别忙,没顾上跟他们讲这方面的事。
就这样一直等到李学勤回来给我通第一个电话,问我什么事情那么着急找他,我又转述了宋健主任的意思。 李学勤赞同地说这是个好事啊! 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亢奋,然后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大吃一惊。李学勤不谈这个了,而是直接提出:这个事儿要他做的话,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是我们自己选的,一个指派的都不要,一个二把刀也不许进。李学勤表态后,我一听就明白了,一旦碰到这种机会,他已经有舍我其谁的准备了,立刻就想到工作怎么做了,真是很有特点。 李学勤又问我下一步怎么做,我说那就等宋健主任的消息吧。 李学勤表示以后我们就通过电话联系。 我说那只有这样,就随口打听一下他家住在哪里,才发现原来我们两家住得很近。 李学勤还问我其他学科的人都找了谁,我说还不知道该找谁呢,正想跟你商量。李学勤指出,那没问题,这些人他都熟,可以给我开出个名单出来,天文学和碳-14 测年方面的专家也都由他来列名单。 李学勤开出的名单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我大喜过望,连说:“太好了,太好了……”
第二天李学勤就把名单给我了,随即我第一时间通过我先生刘光宁把这份名单转交给了宋健主任。宋健主任拿到名单,大喜过望,立刻拉着刘光宁跑到楼上去找李铁映,跟他商量。李铁映非常兴奋:“好啊!这事该做,好!义不容辞,我跟你联手推动这件事情。”刘光宁不知道他们二人之前是否就“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想法有过沟通交流,当宋健和李铁映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刘光宁看到了李铁映表现出的对这件事的超强的接受力、 领悟力。这件事本来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现在由自然科学家提出来, 李铁映丝毫没有领地受到侵犯的抵触感,并且极力支持,此种气度真是令人钦佩。
从此,两个人联袂登台,把这件事完美地推上去了。没有人阻拦,两个国务委员来推动这件事,又提出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这件事又是必须做的,我们不做,外国人也会抢着来做。而且我们一百年来大量的研究应该有个交代,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以及我们取得的成果有什么意义。
1995 年9 月中旬,李学勤在当时的历史研究所召集我们想到的可以参加断代工程的人开了一次会。会上,俞伟超提出:我们这次有必要把人类基因研究加进去,商代的墓葬里有很多外国人,外国人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当时的中西关系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宋健主任事后对我说:基因的问题肯定是要研究的,不过要放到后面,这次来不及了。
工作要开展,就需要资金,而我们这个临时决定的项目并没有预算,只能靠宋健主任来“化缘”。宋健主任把部分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请到了中南海,开诚布公地讲了我们要做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必要性,虽然这是一件在短期内决定的事情,但却是现在必须做、一刻也不能再拖的事情。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没有专项资金,目前已落实的仅有国家科委的300 万元,剩余部分就只能请大家支持一下了。当然,大家认领的时候不是太容易,中科院的路甬祥面露难色,不情愿地说出50 万元,别人也不好说太少。此时李铁映说:路院长,你到时候不要后悔啊,这么重大的国家课题,完成之后影响有多大你是知道的,堂堂中国科学院只出50 万元,你好意思吗? 路甬祥的表情丰富了起来,咬了咬牙说:“好吧,100 万元。 ”就这样,财政部400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300 万元, 国家文物局200 万元。这次会议一共筹集了1300 万元资金。到了1998年的时候,钱已经花光了,特别是重离子加速器改造、加装置,耗费了大笔资金。 还有发掘经费方面,采样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还不算,很多工作都是各个承担单位、研究所自己筹钱开展。 在宋健的要求下, 这一年财政部追加了专项经费200 万元,科技部追加了攻关经费100 万元。1999 年,科技部再次追加攻关经费300 万元,至此,国家拨款总额达到1900 万元, 并非外界传说的财政支持了几个亿。
为保障隶属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高校、研究单位、文博单位等相关机构协调配合,宋健建议成立一个机构来协调、落实各项事宜,支持组织七个部、委主要负责人成立强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 该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国家科委(后更名科技部)副主任(副部长)邓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佳洱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任院长)路甬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滕藤(继任江蓝生)
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继任张文彬)
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甘师俊(继任刘燕华)
邓楠、陈佳洱任正、副组长。
专家们内心略显不安,恐怕在研究过程中受领导小组各方面的想法影响,首席科学家由此提议并最终请宋健和李铁映两位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特别顾问,专家们到此刻才真正放心。
当时筹集资金的会议上我和严文明先生邻座,他悄悄地跟我说:你们通知说研究能不能开展这项工作,怎么给人的感觉今天突然就要开始了呢? 是不是太仓促了点?后来的工作中严文明先生的积极性就不高了。 重要的会议他虽然都来,可是不怎么多说话。 严文明先生表示断代工程领导是真的说到做到,只支持,不干预,完全由专家研究决定每一个年代的结论,这件事做得了不起。当然这里面包含了严文明对以往研究工作方法的不认可,也可以看出来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 严文明先生还说断代工程最大的缺点是这个团队没有竞争机制,考古有成就的人多的是,为什么就选这几个人呢?为什么不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呢?应该允许竞争,就像拍卖一样,公开透明。 严文明先生觉得这是个缺憾。
当时我无法回答严文明先生,现在我可以清楚地回答严文明先生:对于这件事情,宋健主任觉得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再不启动就来不及了,20 世纪就过完了,而且这种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里面的年代定位,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分歧意见,如果放任不同声音各抒己见,可能乱作一团,也不会有明确的结果出来,而我们要做的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量化的结论,立刻就得开始,一刻也不能再拖。就像宋健主任说的,一旦离开那个职位了,就推不动这件事了。 这是宋健主任的苦衷,他不是一个不民主的人,也不是一个不懂竞争的人, 宋健主任也想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得不说,宋健主任的运气还是很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20 世纪以来这一大批辛辛苦苦探索研究、历经苦难而矢志不移、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科学家都投身进来了。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批人可能就不在了,现在正是他们满腔热情无处挥洒之时,他们庆幸自己有生之年可以做此等大事, 定当全力以赴、不计得失。
1996 年5 月16 日,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会,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两位国务委员给每一位专家组成员颁发聘书,并合影留念。 专家组成员是怎么选定的呢?在我最初提交给宋健主任的推荐名单中,有李学勤、仇士华和蔡莲珍夫妇、俞伟超、严文明、席泽宗。宋健主任很满意,在这些人中选定了首席专家:李学勤、仇士华、席泽宗、李伯谦。李伯谦是宋健主任亲定的。宋健主任可能考虑到俞伟超已经不在北京大学,也不在研究机构了,领导这个工程不太合适。 李伯谦呢,宋健的考虑可能是北京大学在考古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必须要有北京大学的权威学者参与。然后由四位首席专家决定了专家组名单,很快就形成了一支由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的队伍。 在会上,李铁映郑重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是没有先验的结论的,科学研究是允许失败的。 你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得不出结论也没关系。 如果没有得出结论,就找到得不出结论的原因,以便于以后有针对性地开展下一步工作。 我们只帮忙,不插手、不干预,完全由专家组来决定最后的年代结论。所有的参会专家听了都觉得很受用、很感动。
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了,就开始打退堂鼓。 李学勤却不同意我退出,他要求我留下来继续为断代工程出力。 就这样,我变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主任,负责大家的信息传递、沟通。当信息纷至沓来的时候,我的先生刘光宁告诉我,你这个角色啊,就应该做一个筛子,把所有的信息都筛一筛,有价值的、必须要传递的东西准确地传递过去,情绪化的话都筛掉,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角色就是个是非婆。 就这样,我做筛子做了好几年,大家相互之间都很融洽,全是齐心协力在做事情。我们这个项目办公室的人一点功利都没有,只拿一点很少的津贴,说白了就是为大家服务。 自我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我经常有的一个体会就是管理人员对研究人员不够尊重,具体做工作的人很辛苦,管理人员看不到,也体会不到,也不懂其中艰辛,因此管理人员经常是颐指气使,好像自己多了不起似的,说话得当不得当都不知道。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就对项目办公室所有人说,我们对每一位专家组成员,不管多么年轻,甚至不是专家组成员,只要是参与课题研究的人,都要保持最高的尊重态度,要做最佳的服务,该做的事情一律不准推谢。我强调以后,大家都做得非常好,也都很愉快。
当宋健主任需要看可行性报告时, 李学勤一篇接一篇,提交报告之快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夏代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商代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西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脉络非常清晰。基本上隔两天他就有材料给我, 我们两个交接材料的地点是两家的中间点——114 路电车的终点站, 紫竹院站。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门脸的牛肉面馆,每次都是李学勤等我或者我等李学勤,交接完材料就走,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有一天我跟他开玩笑说:“李先生, 咱们两个这么交接材料的过程像不像做地下工作啊? ”李学勤呵呵一笑说“有点像”,就走开了。这样,我们的交接工作从我穿着单薄的秋装开始,一直到我穿着厚厚的冬装,持续了几个月,各个节点的可行性报告就全部出来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李学勤之所以出报告如此之快,是因为他在宋健主任还没有提出这个命题的时候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该怎么做了,而且已经非常成熟,成竹在胸了。 哪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怎么解决,哪些问题是可以通畅地走过去的,李学勤都了然于心,只是没有力量来推动,李学勤他不是司马迁,只是一个搞历史研究的。
我跟李学勤接触后才想明白了宋健主任那个问题的答案, 不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不出这个问题, 而是他们明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推动这件事。这也是宋健主任之于断代工程的重要性,正如他自己所说,趁他在位,可以把这件事推动下去,等他离开了这个岗位,就做不到了。的确如此,宋健主任的贡献可以说是厥功至伟,而且他是联合了李铁映一起做的,李铁映是管社会科学的,宋健是管自然科学的,两个国务委员同时提一个课题,“啪”一下子就推动了这个课题。
与此同时,宋健主任也做了几件大事。一件是他要跟中国历史学界打招呼, 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希望征求历史学界的最高权威周谷城的意见。 周谷城先生收到宋健主任的亲笔信后马上回信:“谷城坚决拥护! ”周谷城先生说,有你这样的推动,相信不久后就会有成果。另外一件事是宋健主任开始发表相关文章, 题目叫作 《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完全是他自己亲笔写的,洋洋洒洒,指出原先疑古的大旗就是革命的大旗,反对疑古就是复辟,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古史的年代定下来。 1996 年5 月21 日《光明日报》全版刊出,这篇文章一经刊出,好评如潮,好多报纸都是全版转载。 宋健主任还提前通过科技部外交参赞把文章转交给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张光直先生是古代中国研究专家,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商丘的殷商文明合作考古调查发掘, 他以美方专家领队的身份参与了, 投入得很深。张光直先生收到信后马上回信,对宋健主任评价很高:“这是我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里面所看到的文章中最有气魄的一篇, 宋博士这篇宏文正好说到我一生事业的核心, 我对这个主张举双手赞成。 这个题目如果照文章所述的广义的解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的。 它的解决只有依靠国家才能动员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所以,我相信这个计划如果有合适的学者, 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做,是应该会有突破性的新贡献的。”言辞恳切,令人感动。 当时他的帕金森病已经很重了,走路、说话都很困难,但他还是坚持给宋健主任回了信,助手打印完成后,他亲笔签了名。不久后张光直先生来华访问,宋健接待了他,把李学勤和几个考古学家找来跟张光直先生一起谈。 张光直先生提出和他一起在中美联合考古队发掘河南商丘的张长寿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宋健主任就很客气地告诉张光直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就是李学勤。 张光直先生表示很好, 李学勤是个合适的人选。那天的谈话也很愉快,得到了张光直先生的鼎力支持,但是他本人已经没有精力参加了。
到了1997 年,孙关根突然来了一个电话,他嗓子得了病,说话发声很困难,给我一种他随时会停止呼吸的感觉,所以他也不愿意多讲话。 孙关根很低沉地跟我说:朱学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特别特别重要的消息。 在全国考古学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邹衡异常活跃,很自豪地讲述了他如何表达不同意见,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断代工程,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断代工程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事情,又都是考古学家在开会,大家都想知道里面还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秘密。邹衡这么个大专家、大牌研究员、商代考古学的绝对权威,性格里又透出那种不可一世的张扬,谁也不敢得罪他。 邹衡要表现自己在断代工程里如何英雄豪杰、如何舌战群儒、如何跟人斗争的,大家当然很兴奋了,这是最重要的消息了。 当时场面非常热闹,大家议论纷纷。朱学文,我告诉你,邹衡先生那番激昂之词让我瞬间就对断代工程放心了,邹衡敢这么肆意地在断代工程会议上展开他的雄辩,就说明断代工程的研究过程很正常,李学勤没有搞一言堂,空气是民主的。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李学勤面对那么多权威的专家学者不可能把控得住局面,因为这里面大家太多了,都是顶尖的,所有的顶尖专家都碰到一起可不就针尖对麦芒嘛。 现在看李学勤是把控得住局面的,他根本不怕有人闹,有人喊叫,从来面不改色,他就是这么个人。
这个电话让我大喜过望,对外面闹哄哄地对断代工程的议论, 特别是考古学界对断代工程的议论,我是很不放心的,却也不好出去打听。孙关根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说,太好了。当时因为邹衡脾气很大, 对于是否邀请他进专家组时曾有过讨论,李学勤和李伯谦都非常坚决地认为邹衡必须请进专家组。 我说邹衡先生可是不会冷静的,我的意思是想要队伍纯洁一点、简单一点。 李学勤说不可能简单,邹衡先生是个纯正的学者,在专家组里他也吵不起来,何况在外面吵不是更麻烦吗?事实证明,李学勤这个决定完全正确,遴选的这么多专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是顶尖而卓有成就的,肩膀头一般齐的。 如黄宣民和孙关根两位所言,在首席科学家的人选上,当然要选学术成就突出的,而更重要的是要有格局、有气度。 点火就炸的脾气只能使场面变得混乱不堪,对于工作的开展毫无益处。 从开始一直到后来整个过程,黄宣民和孙关根的真诚令我不能忘怀。
接了孙关根电话的第二天,断代工程在远洋饭店开会,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所有的专家组成员都在座,邹衡先生就坐在我斜对面。我说,我昨天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邹衡先生在考古学界的大会上非常公开地告诉大家, 他是怎么反对断代工程的,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大家都很兴奋。那个朋友告诉我,邹衡先生这番话起到了两种作用,跟邹衡先生相同见解的人会欢欣鼓舞,客观的人一听就会觉得断代工程搞得不错,很民主,很好,不是一言堂,看来还有希望。 我说,邹衡先生,真感谢你的这番话。 在座的所有人掌声一片,给我叫好,邹衡先生也哈哈大笑。 邹衡先生抨击归抨击,但是他对断代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的研究成果都很上心。
断代工程一旦开展起来, 这一群人工作的动力都来自内心,是原动力,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给司马迁续笔,对于断代工程的工作责无旁贷。李铁映和宋健正好碰见这样一支队伍,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国家科委(科技部)也不插手我们的研究工作,只是了解一下工程进度,询问我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解决, 而且指定由科技部社会发展司的特派专员徐俊与我们保持直接联系,跟进整个项目,这个管理项目的创新方式由此被科技部沿用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王正也和项目办公室一直有密切的联系。 后来这个工程又得到了国家其他更高层领导的关注,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关注,并没有插手,这是对我们这个团队的信任、尊重。真正做到了政府推动而不干预, 完全由专家自己决定整个过程和最终结论。 实际上,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领导小组中没有任何一位提出意见来插手具体的研究成果,只听取汇报,为断代工程协调与各部委的联系及解决求助的问题。 领导小组对于断代工程的两次帮助让我印象深刻。 原先工程只是列入第九个五年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第二年科技部将它改为重中之重的科技攻关项目, 得到了国家更多的支持。 这是第一件事。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与公布结果的日程上,领导小组一直支持“夏商周断代工程” 专家组自行决定并公布年表,不通过官方形式。 2000 年结项时,科技部得知带字甲骨测年的工作仍未最后完成, 他们表示不要着急献礼,完成研究再说,都来得及。 这是第二件事。首席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断代工程年表的各个支持点都已定妥, 无须碳-14 方面的数据也可成立。 故在2000 年结项后,以专家组名义正式发布了夏商周年表。
在断代工程结束的时候,宋健主任写了一篇文章《酬“断代工程”初遂》(《光明日报》2000 年9 月22 日),向200 位专家致谢。 他说,每一个时代的人要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感谢大家!再一点呢,希望今后这种多学科的合作继续开展,还能做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