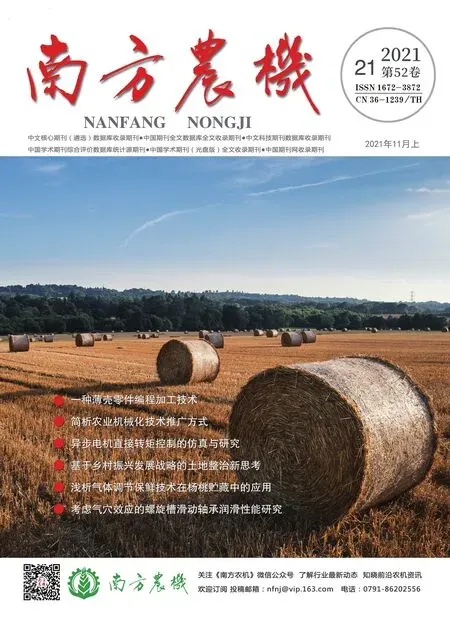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研究综述
宋 帅 , 郭 真 , 宋传洲
(1.海军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 430033;2.烟台警备区,山东 烟台 264000)
20世纪80年代伊始,世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步入信息化战争时代,世界各国均重视信息化联合作战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均把人才培养视为强国强军的基本战略。航母是国家展示综合国力的一大利器,拥有航母而又能控制海洋的国家才能成为海洋强国,才有资格成为世界强国,这个强国需要既能够建造航母,又有战斗力强的航母人才,因此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其中的关键之一。我国航母服役时间相对较短,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一项需要大量时间来推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深入研究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能力构成、成长规律、培养方法和途径,以及更为系统科学的培养模型和评估算法。
国外对联合作战人才或基于联合作战背景的人才研究非常多,而我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重视起来,并积极展开对其的探索和研究,研究的文献也相对较少,而其中我国对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研究文献就更少。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诸多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各国航母人才培养的有关文献,对比国内外人才培养和研究情况,得到启示,提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有关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未来研究方向。
2011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做了释义,是指能够有效组织实施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指挥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自然限定了航母这一约束条件,需与航母联合作战指挥职责相适应,概略上讲主要包括“指挥人才”“政治工作人才”“参谋人才”“管理人才”“勤务保障人才”“专业人才”等,根据担负的主要职能可分为高级作战指挥军官、中初级作战指挥军官、参谋军官、技术保障指挥军官、专职事务指挥军官等5类。
1 外国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情况
1.1 美国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情况
美国是最早发展航母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人员组成最多元的强大的航母部队,有着丰富的航母制造、管理和作战经验。因此,美国航母人才的选拔培养最具有借鉴意义。美国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美国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1920年,美国出台的《国防法》已经提出联合作战的概念,并对其开展研究,在1924年建立具有联合特征的陆军工业学院。直至1986年,美国历时40余年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1](Goldwater-Nichols Act of 1986)大幅提升美军联合作战能力,是美国制度改革的源泉性文件,为建立联合作战人才培养机制打下了基础。同时,美国还出台了《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并按照文件建构了联合职业军事教育的理论、概念、原则与框架体系[2],经历1990年《联合职务军官教育计划》和1997年《切尼报告》,随着对实战经验的探索和研究,美国联合作战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完善。2004年,美国又颁布了新的《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将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划分为预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单独阶段、将级军官等5个阶段。至此,美军逐渐形成“联合军官终身教育体系”,包括联合个体训练、联合职业军事教育、自我发展、联合作战经历4个方面的综合性培养方案,2007年美国相继出台《联合军官管理:联合资格制度实施计划》《国防部联合军官管理计划》,标志着美军联合职业军官培养进入新阶段,2018年,美国海军发布了美国海军军官、士官能力培养大纲,对军官、士官能力培养进行了规范,但仍未针对航母人才选拔培养进行特殊规范。
当前,美国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3]的培养、选拔、任用可简要概括为3个特点。一是注重联合作战指挥员的飞行背景。航母舰长、航空联队指挥官以及副舰长,都具备飞行员经历,且只有担任过航空联队长的军官,才有资格成为航母舰长候选人,美国航母上的指挥人员的选拔对飞行员履历、平均飞行时间、在航母起降次数、飞过的飞机型号、是否从事过飞行教官等都有明确要求。二是注重用不同岗位历练指挥协调能力。鉴于航母是海上编队核心和指挥枢纽,航母编队指挥员要求具备优秀的指挥能力和很强的协调能力。美军军官的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一方面靠院校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在平时训练和演习中锻炼积累,通过职务和岗位变动令他们变得见多识广,资历丰厚,经验丰富,具备多方面才干。三是注重先训后用、训用一致和终身学习培训原则。美国航母军官要参加飞行学院飞行学习,而后还要在任不同岗位期间参加多种相关培训,以航母舰长为例,在被任命为航母舰长之前,至少要在5所不同学校学习工作。
1.2 俄罗斯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情况
1963年苏联第一艘航母“莫斯科”号直升机航母动工建造,1967年入列黑海舰队,之后又相继出现基辅级航母、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瓦良格号等,直到俄罗斯时期,海军战略由远洋进攻转为近海防御,加上国内经济危机的困扰,所以不仅淘汰了所有的中型航母,而且也没有再发展中型航母,目前仅拥有“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俄罗斯军官培养的特点是重视军人社会价值,院校的课程设计逐步拓宽,将基础和任职教育在同一校区合训,俄军的军官培养走的是“军事专才”“指技合一”“新型通才”“复合型人才”的道路[4]。俄罗斯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特点可简要概括为:
一是在培养力量上注重资源整合。通常军队培养人才数量多、专业细、难度大、费用高,单靠有限的几个军队院校难以完成,所以俄军通过将专业化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嵌入到普通高校的学历教育进程中,既最大化发挥了地方教育资源的优势,又通过普及国防教育,提高了普通学生的军事素养,使普通高校培养的人才更贴近军队的需求。二是在培养模式上注重模拟训练与基地训练结合。俄军一直把模拟训练作为培养锻炼官兵、提高他们实际组织指挥以及专业技术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三是在培养手段上注重实战背景锤炼。通过实兵演习来检验部队、锻造联合作战人才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固定做法,而且演习锻炼的目的性、指向性越来越强。对于较大规模的演习计划,俄军一般都是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拟定,并逐渐形成例行性任务,通过让官兵真实参与重大演习训练任务、执行重大军事行动提高指挥打仗的能力。
1.3 英国、印度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情况
英国也是最早拥有航母的国家之一,且对航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任何一条航母上都可以找到英国人的“发明专利”。1912年英国海军对一艘老巡洋舰“竞技神”号进行了大规模改装,其成为世界上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英国发展航母不断推陈出新,首创排水量在2万t以下的轻型航母,后来有“无敌级卓越号”,以及近年来最大的军舰“海洋”号航母。印度独立后,购买英国、俄罗斯的航母,来自英国的“维克兰特”号和“维拉特”号,来自俄罗斯的“维克拉玛蒂亚”号,此外,印度科钦造船厂正在建造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并计划命名为“蓝天卫士”号。印度曾长期被英国殖民,在航母人才培养方面与英国类似,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整个培养过程是贵族培养模式。英印海军军官一般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接受教育为精英式、国际化培养模式,注重完善突出明显培养优势的各类保障机制,是一种以综合能力为目标、突出知识技能、融会贯通专业技能的一套完备的培养模式。英国2001年就成立了国防大学,专门设计了“高级指挥和参谋”课程培养联合作战指挥员和高级联合参谋。二是在培养初始阶段遵循“先泛后专”模式。英国、印度强调将航母军官培养成为着眼未来需要、具有复合知识结构、适应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既博又专的人才,初级阶段重视军官的基础素质和综合素质培养,除基础文化、科学技术、作战能力外,社会交际、管理能力、领导能力也是重点培训内容。英军、印军均规定学员经过初级基础教育后,必须要经过专业知识与技能训练才能任命为军官。三是在特定阶段让航母大国代为培养。2008年5月,印度委托俄罗斯开始训练米格-29航母舰载机飞行员,2008年6月,俄罗斯对印度飞行员进行理论培训,8月开始进行飞行训练,后续又培训印度官兵管理使用航母。2011年,根据英法两国协议,英国皇家海军派遣首批顶级飞行员前往法国接受培训,以使这些精英在英国联合攻击战斗机及新的航母开始服役前积累丰富的经验。英法两国经常联合培养人才,特别是英国在联合攻击战斗机交付和新航空母舰的建成期间,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的官兵先在法国巴黎三军防务学院学习法语,而后在航母上服役长达3年,期间要按要求参加法国航母出航和战斗机训练,期间穿着英军制服,同法国战士一样按等级享有对应待遇,同吃同住同训练。
2 我国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研究情况
2.1 我国有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情况
我国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起步较晚。文献[5]对我国联合作战指挥员培养制度进行了研究,文献[6-8]对全军联合指挥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前瞻性研究,文献[9-10]对作战指挥人员的能力素质和知识结构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研究,文献[11]则针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训提升能力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军人职业化教育的相关内容。文献[12-14]对联合作战中的参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方式方法进行了研究,文献[15-17]关注联合作战政治工作指挥人才,对其培养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联合作战指挥勤务保障人才培养方面,文献[18-20]分别对军事物流、后方保障、航空保障等方面的指挥人才培养进行了探析,而文献[21-22]则重点将联合作战人才培养放在信息化条件下进行了研讨。我国对军队进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文献[23-26]在新体制编制的背景下对联合作战指挥人员的能力素质进行了探讨,特别是文献[27]将信息作战和海军军种作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研究的重点,文献[28]探讨了战场需求与人才培养目标精准对接问题。
2.2 我国对国外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研究情况
我国对国外军队人才培养的研究,对美国的人才培养情况的研究较多,其次是俄罗斯。文献[29]系统介绍了美国联合作战参谋军官有关的制度、培养方式、选拔标准、自我提升途径等内容,文献[30]关注美国联合训练匹配人才建设的重要性,文献[31]关注美国人才培养的制度和途径。文献[32]关注美国对人才生长的阶段性发展规律和制度,文献[33-34]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美军联合职业军官培养制度,分析了我国联合军事人才培养制度的问题,并提出了方案和建议,文献[35-36]研究了美国联合作战人才的培养机制及其动态发展。大部分文献关注分析的是国外有关人才培养的优点,而文献[37]却是从美军联合职业军事教育体系建设逐渐完善的动因和尚存的不足视角出发,分析出培养周期长、福利式教育中的作弊现象、执行过程僵化等缺陷。文献[38-42]则研究分析了美国联合文化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类似的,文献[43]研究的是俄罗斯军事人才与联合文化的构建,文献[44]关注的是军事改革后俄罗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状况。文献[45-46]则对比研究了美国、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军事指挥人才培养状况,文献[47]是出访考察捷克和白俄罗斯后关于军事人才培养的思考。这些研究具备如下特点:一是学习国外从“联合作战需求”出发的思想理念,匹配与联合作战人才相关的制度方案、培养方法、训练模式等所有内容;二是分析借鉴外国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能力构成;三是学习外国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途径;四是呼吁形成中国特色的军事联合文化,实现 “联合文化”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从而以文化育人。
2.3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模型分析和算法应用
随着我国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向前推进,对联合作战指挥人员的培养的研究逐渐丰富和深入起来,但很多研究的内容大多是概念和思想的阐述,在人才研究中运用科学评估方法和模型理论方面并不多。文献[48]采用SWOT方法对我军联合指挥军官培养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献[49]针对初级指挥军官信息化素质能力的指标体系构建进行了研究,文献[50]构建能力素质模型对联合作战保障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文献[51]基于胜任特征理论对我军联合作战人才培养的素质和能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类似的,文献[52-53]构建胜任力理论研究该问题,文献[54]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密切值方法对联合作战参谋素质能力进行排序。文献[55]从联合岗位军事职业教育的培养特点出发,提出基于岗位需求的反向设计与正向实施和基于CDIO工程教育理念能力映射的岗位能力需求与分析模型。此外,在较早的对军队人才研究的文献中,文献[56]建立素质测评与选拔模型,采用选择组合赋权的TOPSIS方法作为预任参谋选拔排序,为联合作战人才研究提供参考,类似的,文献[57]在研究实现三军联勤军事医学人才培养时,提出整体W与部分之和∑Pi 的对比分析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而建立“综合一体化”培养模式。而文献[58]面向联合作战保障,针对仿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值得借鉴。
3 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研究现状分析
1)国内有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研究还不够多,对外国特别是美国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和研究相对滞后。这也反映出我国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尚在初期,而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更加任重道远。
2)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参与战争少,实战考验少,我国军事人才培养精确联合作战需求的研究不足,尤其在我军在演习演训演练未能贴近实战的情况下,与实战相链接的人才培养研究严重不足,甚至研究文章流于片面、空洞无物、脱离实际。
3)国内有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开展研究的切入点单一、重复,往往是蜻蜓点水缺乏深度,缺乏更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具有特色的新思路新方法。
4)国内的有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研究以理论研究概述为主,缺乏更为科学系统的算法评价和模型评估研究。
4 结束语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我国现代化军队建设和发展、国防力量稳步提升乃至实现建设“能打仗、打胜仗”世界一流军队目标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航空母舰作为海上有力的信息化作战平台,随着我国“辽宁”号“山东”号航母相继服役,对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队伍的建设已是必修课程和基本课题。本研究梳理诸多国内外包含航母人才在内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研究文献,为下一步开展航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相关研究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