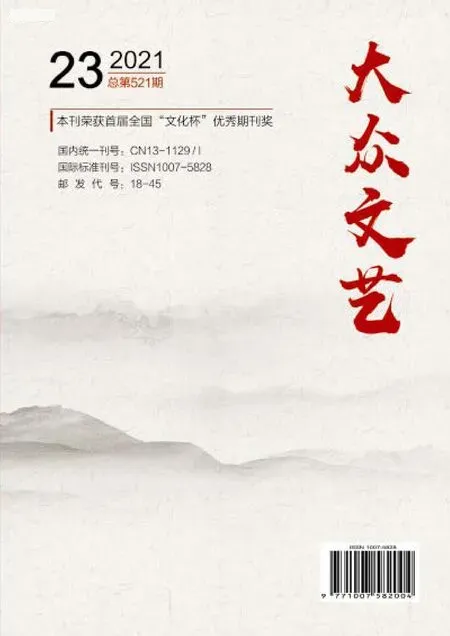从《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看王世贞乐府变创作
柴 东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西安 710021)
王世贞《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收录于《弇州续稿》,属于其《乐府变》创作之一。历代对王世贞《乐府变》诗歌评价颇高,如胡应麟便认为“乐府自晋失传,寥寥千载,拟者弥多,合者弥寡。……而元美诸作,不袭陈言,独絜心印,皆可超越唐人,追踪两汉,未可以时代论。”王世贞《乐府变》究竟有何独特之处?本文拟通过对《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的研究,探讨王世贞《乐府变》的创作特色。
根据前人统计,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共收录乐府386篇,含《乐府变》19篇,《弇州续稿》收录乐府58篇,含《乐府变》10篇,又因其中7篇为童谣,后人多不纳入《乐府变》范围之内,故仅以22篇论说。《乐府变》虽数量不多,但影响却颇深。正如朱彝尊所言:“乐府变,齐齐正正,易陈为新,远非于鳞生吞活剥者比。”在《乐府变》二十余篇中,《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独占风骚,被评为“整组《乐府变》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这不仅是因为其鸿篇巨制,更是因为此诗得变风变雅之遗意,兼具怨刺讽喻的特点。
一、《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文本细读
王世贞《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创作于严嵩革职,籍没家财,严世藩被诛之际。严嵩乃今江西分宜人,“袁江”“钤山”皆位于今江西境内,故以此代之。根据资料,汉代以来,以“县官”称天子,故诗中“县官”即指明世宗,即嘉靖皇帝。又明时称三公、三孤官为“相公”,严嵩曾任少师,属三孤官,故诗中以“相公”指代严嵩;宋代以来,以“司空”喻称工部,严嵩之子严世蕃曾任工部左侍郎,故诗中以“司空”指代严世蕃。“当”乃“代”之意,《庐江小吏行》又名《孔雀东南飞》,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
《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诗共三百一十九句,一千五百九十五字。第一部分共八百二十五字,讲述严嵩父子及其跋扈生活。全诗首句起兴,借“钤山自言高,袁江自言长”,嘲讽严嵩父子之张扬;而后以独火贪狼星作比,总叙严嵩之为人;又以“十五齿邑校,二十荐乡书”言明其仕途之平坦;再以“文丝织隐囊,细锦为床帷”状其骄奢;以“但卧不必出,称敕撰直词”道其傲慢。然而“相公别有心,县官不可寻……司空别有心,相公不得寻”,指明严嵩及严世蕃早有异心,以至于诸多官员“宁忤县官生,不忤相公死”,天下大事“不复问相公,但取司空旨”,严嵩父子权势滔天,追随者甚众,“义儿数百人”,甚至“老者相公儿,少者司空子。谓当操钧柄,天地俱长久。”第二部分共四百五十字,阐明严世蕃遭弹劾及其下场。忽以“御史上弹章,天眼忽一开。诏捕少司空,究粟诸赃罪”开篇,表明严世蕃被流放雷州之事,而后虽然“相公船头坐,谁敢问讥征”,得以暂时逃脱,但随着“御史再发之,天威不为恒”,最终还是迎来了御史“捕司空至京”的决定。诗中,严世蕃拜别其父,认为“今当长相别,儿不负阿父”,并劝诫诸姬妾“归者吾而配,不归而鬼妻”,告诫儿郎“(金银)不得铸爷身,及身身始知”。但却不知此时的自己已是众叛亲离,父亲严嵩心中发出了“阿父宁负汝!……汝父身不保,安能相救取”的感慨,姬妾及儿郎也均认为“司空(阿爷)何太痴!归者吾而配,不归人人妻……有金儿当死,无金儿自支”,通过对家人的心理描写,嘲讽了严世蕃被捕后的惨淡结局。被捕至京师的严世蕃“一依叛臣法,矺死大道边。有尸不得收,纵施群乌鸢。”“矺”即“磔”,乃车裂之刑,可谓下场凄惨。而其父严嵩则家财殆尽,“片瓦不盖头,一丝不着肩”,子孙“诸孙呼践更,夕受亭长鞭”,姬妾则“夜半一启门,诸姬鸟兽窜”。严氏一族土崩瓦解,严嵩晚景凄凉。第三部分共三百二十字,借旁人之口对严嵩展开严厉谴责。开篇处,“相公逼饥寒,时一仰天叹:‘我死不负国,奈何坐儿叛!’”读之似乎亦觉严嵩之凄。然而旁人却为之大笑:“唶汝一何愚!”并接连发出指责:“汝云不负国,国负汝老奴?谁令汝生儿?谁令汝纵臾?谁纳庶僚贿?谁朘诸边储?谁僇直谏臣?谁为开佞谀?谁仆国梁柱?谁剪国爪牙?土木求神仙,谁独称先驱?”一连九个诘问之后,再次历数严嵩“六十登亚辅,少保秩三孤……甲第连青云,冠盖罗道途”等恩赐殊荣,认为严嵩此生尚不如一娄猪、一羖䍽、鞲中鹘、鼠在厕对君王及世人有用。严嵩听后“相公寂无言,次且复傍徨。颊老不能赤,泪老不能眶”。诗文最后,王世贞发出“为子能负父,为臣能负君。遗臭污金石,所得皆浮云”的感慨,对严嵩的一生加以总结。
二、从《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看王世贞对乐府诗的继承
在文学史上,乐府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魏乐府,到唐代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李白“援古讽今”的古题歌行,和张王“语有经国隐忧”、元白“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创作,再到宋代张耒、苏轼等人“补乐府之遗”的“新题乐府”,直至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乐府”,乐府在诗歌发展史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正如王世贞《乐府变十九首序》所言,“拟者或舍调而取本意,或舍意而取本调,或舍意调而俱离之”,至明代,乐府的发展早已陷入窠臼。有感于此,王世贞创作《乐府变》,不同于唐人的“新题乐府”的另起炉灶和明人“拟古乐府”的竞相仿作,《乐府变》“因新事创名,度以古曲”,“发旧题之新意”,注重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充分发挥了美刺讽谏的社会功用,开创了明代乐府创作的新思路。
一是对“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叙事传统的继承。王世贞对《孔雀东南飞》推崇备至,认为“《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因而,在叙事上,《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亦对《孔雀东南飞》有所继承。一方面,《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承袭了《孔雀东南飞》以第三人称为主的叙事特点,以全知的诗人叙事者入手,对故事进行了全面的掌控,做到了“叙事如画”。不论是“汤汤袁江流,截嵲钤山冈”的首句起兴,还是司空被捕至京前,面对相公“再拜泣且絮”的动作描绘,抑或是对严嵩姬妾鸟兽窜后“里中轻薄子,媒妁在两腕”的事件描述,都似《孔雀东南飞》一般,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展现在了读者眼前。另一方面,《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亦承袭了《孔雀东南飞》随情节需要而转换人物叙述声音和观点的写作手法,做到了“叙情如诉”。如描绘严世蕃被捕辞别家人之时,分别以严世蕃、严嵩、姬妾、儿郎四者的声音展开对话,更加显现出了严世蕃被捕后的众叛亲离,加剧了全诗的讽刺意蕴。又如严嵩在饥寒交迫中,发出“我死不负国,奈何坐儿判”的自辩,其中“奈何”二字,出自严嵩之口,更表达了他自以为无辜的错误认知。
二是对赋比兴写作手法的承袭。全诗开篇即以“汤汤袁江流,截嵲钤山冈”起兴,而后以赋和比为盛。王世贞向来重视赋笔,认为“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更是以赋体为主,在总叙严嵩生平时,承袭了《孔雀东南飞》“十三能织素”之语,自“十五齿邑校,二十荐乡书”至“八十加殊礼,内殿敕肩舆”,反复运用了赋笔铺陈回旋的写作特点;在状其滔天权势时,以“甲第连青云,冠盖罗道途”等句阐述;在状其生活豪奢时,以“银床金丝帐,玉枕象牙席”等句铺排;在论及严世蕃死后,严氏一族下场时,又以“片瓦不盖头,一丝不着肩”等句展开;在篇末痛斥严嵩时,更是再次提道“六十登亚辅,少保秩三孤”等经历,借赋笔点明严嵩所为于国有负,并与前文呼应,更显严嵩之过。此外,全诗又以比法为辅。篇首总叙时,以“独火贪狼”星宿比其性情,以“鹳雀立”“鹤昂藏”比其外貌,在篇末斥责时,以“一娄猪、一羖䍽、鞲中鹘、鼠在厕”比其行径,更是令读者联想到《硕鼠》《鸱鸮》等诗。而王世贞在诗中直言严嵩“不如”这四种动物,则更能表现对其愤恨之情。
三是对怨刺讽喻传统的延续。汉乐府继承了“诗可以怨”的写作倾向,以《孔雀东南飞》控诉封建家长之专制,以《孤儿行》控诉社会家庭之冷漠,以《蒿里行》揭露战争民众之苦难……正如陈田《明诗纪事》所言:“(弇州)《古乐府变》犹得变风、变雅遗意。”王世贞在《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中亦延续了怨刺传统,借严嵩之故事,表讽喻之思想。如在第一部分,连用两次排比,叙说“县官与相公,两心共一心”,表达了皇帝对严嵩和严世蕃的宠信与依赖,而“相公别有心,县官不得寻”则言明了严嵩和其子的欺上瞒下。诗中,看似皇帝被严嵩所欺,严嵩亦被严世蕃所欺,皇帝与严嵩皆无过错。但若结合下文细细审之,当严嵩自言无辜时,旁人指责他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看似“坐儿叛”,实则于国有负。顺此理推之,皇帝亦有失察轻信之过,只是王世贞颇多顾及,未能在诗中言明,只能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而已。此外,王世贞对嘉靖帝颇有微词之事,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亦可佐证。又如严世蕃在被捕至京前,对姬妾和儿郎分别发出了“归家另配”和“不得为吾铸金身”的谆谆告诫,却未曾想姬妾和儿郎心中皆认为严世蕃“何太痴”,早已为自己谋好了出路,两相对照,更显世间亲情之冷漠。再如最末处,诗中描绘严嵩落魄凄惨至极,就连死后也只是“殓用六尺席,殡用七尺棺”,与之前“老者相公儿,少者司空子”的权倾一时相较,纵使认有“义儿数百人”,却无一人为其送葬,这更加讽刺了当时官场上趋炎附势,树倒猢狲散的社会现实。
三、从《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看王世贞对乐府诗的发展
一是“齐齐正正,易陈为新”。正如前文摘王世贞《乐府变十九首序》所言,“拟者或舍调而取本意,或舍意而取本调,或舍意调而俱离之,姑仍旧题而创出。”“调”指乐府之曲调,“意”则是指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时人的创作,有的只注重对诗题的承续,如杨维桢和李东阳的乐府创作,尽是咏史,与当下时事全然无接;有的又只注重“即事名篇”,甚至于自创乐府诗题,如皇甫汸《乐府十二首》,与古乐府毫无关联。王世贞则不同,他选择了延续旧题而申发新意。当然,“随代遣词,遂题命意”,与他宗杜不无关系。王世贞曾评李白拟古乐府,认为其“不如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也”,正表明了王世贞尊崇杜诗,认为拟古乐府当继承古乐府传统,以讽咏时事为旨归的创作倾向。但他亦指出杜诗仍有不足,如《乐府变十九首序》其“词取锻炼,旨求尔雅,若有乖于田畯红女之响者”。故而王世贞《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在学杜的基础上,以嬉笑怒骂之俗语入诗,如“唶汝一何愚!汝云不负国,国负汝老奴”等句,通过大量的对话描写,尽显语言的张力,使得全诗的叙事与抒情更显生动。
二是不吝塑造严嵩的立体化形象。在《世宗实录》、宗臣《报刘一丈书》等中,严嵩被塑造为一个作恶多端、陷害忠良的脸谱化人物。据陈田《明诗纪事·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按语:“元美父,蓟辽总督忬,以分宜陷死。……元美《钤山冈》诗,可以怨矣。”王世贞之父难祸起严嵩,他完全有理由在诗中极力丑化严氏父子。但在《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中,王世贞却对“司空辞相公,再拜泣且絮”与“相公寂无言,次且复傍徨。颊老不能赤,泪老不盈眶”两个场景进行了细致描述,通过对话和肖像描写,分别表现出了严世蕃孝敬父亲和严嵩尚知礼义的另一面。甚至于诗中较严世蕃的形象而言,其姬妾、儿郎和里中轻薄子则更为不堪。明人张夑《书黔山堂集后》曾言:“观其(严嵩)生平持论及与人书,较多温厚和平之气,犹未见有翻覆星辰、摧落一世手段。……王弇州作《袁江流钤山冈》,模拟分宜父子间,备极写照之致,然犹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自是确论。”从这一观点出发,王世贞在《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诗中,仍能以“不能掩文章”之语,对严嵩的才学加以肯定,并在诗末详细描绘严嵩遭斥责后无言以对,略做停顿后又彷徨无依,直至“颊老不能赤,泪老不盈眶”的细微表情,忠实于对历史侧面的描摹。
三是对史家笔法的化用。根据叶晔教授观点,王世贞在《乐府变》的创作中运用了史家“互见之法”,使得不同篇目中的意象相互映照,而更进一步证实了诗句中历史的真实性。除此之外,史家笔法在《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诗中更有诸多体现。首先,在叙事系统上,可谓有本有末。王世贞如传记文学一般,于开篇处言明了严嵩的籍贯、出身等信息,又以“十五齿邑校”等六十字集中介绍了其一生的履历,甚至在篇末亦不忘补上严嵩“殓用六尺席,殡用七尺棺”的结局,颇具传记文学之特色。其次,在叙述方式上,《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正叙为主,但“不知何星宿,独火或贪狼”“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等句,又兼有预叙的手法,对严嵩预先做出了“独火贪狼”及“孔雀有毒”的评判。再次,在语言艺术上,《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化用了史家的春秋笔法,为尊者讳,寓贬于褒,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如以“县官、相公、司空”指代“嘉靖帝、严嵩、严世蕃”,又如同前文所叙,王世贞虽对嘉靖帝颇有微词,却并不明言,而是将其寓于篇末旁人对严嵩的痛斥之中。看似怒骂严嵩,实则亦是指责皇帝的宠信偏听。最后,诗笔还体现在篇末“遗臭污金石,所得皆浮云”一句的规劝上,此句似“太史公言”一般,兼具佛家说教色彩和寓言意味,以严氏父子之事警醒世人切毋重蹈覆辙。
综上所述,王世贞《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历来为诸多诗评家所称赞。此诗不同于前人对汉魏的一味仿作,是王世贞“即事而命题”等诗歌创作主张的实践产物,不愧为其《乐府变》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