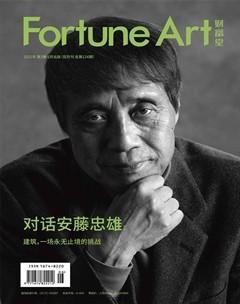不是句号,是问号?
邱敏

在上海,我们每年能接触到经典老大师展览机会不少,从数量、品质到展览规格都可圈可点。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对外文化交流的开放性和艺术机构自身的专业性,除此之外,门票回报、网红效应、传播力度、潜在赋能,让艺术机构在选择大师展览进场时,相互之间有种血拼到底的暗暗较劲。
在2021年西岸美术馆举办的这场康定斯基的个展之前,该馆的《时间的形态》一展中,已经有两件康定斯基的作品做了一个热身。当然,康定斯基在现代主义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学术悬念,但若论及这个展览对上海本地的艺术创作的意义,还是非常有咀嚼口感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既有北方的“理性绘画”,也有以西南艺术为代表的南方绘画,同时还有厦门达达喊出“无物而不是艺术”,浙江的艺术家们回应“无为而不是艺术”,观念艺术抛弃绘画本体的时候,上海的艺术家却羁留在画布上,执着于形式、色彩、肌理、材料的探索,构筑一个抽象画的世界。所以,康定斯基的个展不仅仅是满足中产阶级的怀旧趣味,它是给上海依然在进行抽象艺术实践的艺术家们打了一针强心剂。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康定斯基如何从印象派走向抽象的结果,这不只是一个将形式简单归纳为几何形体的过程,同时它也向我们昭示康定斯基个人身上自我抗争的精神力量:他既是一个严谨得近乎保守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果断放弃现实的安稳,大胆跨界,甚至积极介入革命的人。
多面的康定斯基:展厅中展出的康定斯基的照片,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模样,相反,他西装革履,架着金丝边眼镜,更像一名睿智的律师。这次展览可惜没有他工作室的照片,他的工作室井然有序,颜料罐收拾得像商店货架上的物品。而他作画时经常穿着白色的西装,作画的整个过程,手指缝干净,白色西装从头到尾纤尘不染。
康定斯基有一半东方血统,其曾祖母是蒙古的公主,他的父亲就出生在中国边境,而他1866年出生于莫斯科。最初在莫斯科大学学法律、经济学,26岁留校并成为教授。康定斯基30岁时在俄国旅行,在旅途中,他观看了大量的民间艺术,也接触到欧洲的现代主义艺术。在一次展览会上,他看到了莫奈的《干草堆》,他困惑于这些画就像未完成一样,没有细节的精细打磨,但这幅画紧紧抓住了他。回去之后不久,康定斯基毅然放弃了法学教授一职,跑去德国慕尼黑学艺术。他去慕尼黑开始波西米亚的艺术家闯荡生活时,成为妻子的表妹和他离婚,而他在慕尼黑美术学院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他们一起游历欧洲,对新艺术进行大胆探索。当时他师从于一位具有象征主义风格的老师,康定斯基并不感兴趣,他恋恋不忘的是莫奈创作中的自由开放性。康定斯基是一个学习能力超强的好手,他顺利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并取得了学位。他另一个爱好是提琴演奏,也近乎专业水平,古典音乐修养非常好。


革命的康定斯基: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他回到俄国,积极参加革命,受到重用,参与组建了苏维埃文化艺术宫,并担任馆长。在这次展览“俄罗斯:间奏岁月”这一板块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定斯基有几幅小画出现了非常清晰的具象形的绘画,同时有几幅迷你版的抽象作品,似乎觉得他不是那么自在地画那些抽象形式的作品。很快,他与俄国的左派艺术运动产生激烈的冲突,他的抽象艺术得不到理解。康定斯基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清高的俄国人,指的就是那些描绘具有宏大叙事、史诗性的左派艺术家。或许这可以解释他又回到了具象的物象以及迷你版抽象艺术的原因,他尝试着委曲求全,但发现这实在有违自己的天性,好在1922年他作为文化亲善大使去德国时被滞留到了德国,继而受聘包豪斯,教授包豪斯艺术基础课程,二战爆发前期,他又跑到法国去,最后在法国终老。

对音乐的吸纳:康定斯基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作曲家通过有限的曲式,就能创造出那么丰富的交响乐,他希望把点线面和颜色关系变成基本的内容。然后后世画家就可以用这些内容互相配合,像谱写音乐那样画出他们所需要的情感。他致力于赋予几何形式以情感,借助音乐的抽象性来沟通形、线、色的动感、力度和节奏性。但这是康定斯基一厢情愿的想法,后来理论家格林伯格倡导的抽象艺术发展方向之一,就是剔除康定斯基绘画中的抒情性和音乐性。
康定斯基的调色板:这次展览非常有意思的是展出了康定斯基的调色板。值得注意的是,这块调色板的意义不在于它是艺术家的创作工具展示,它对康定斯基最终在画面上取消客观物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康定斯基一直有一个疑惑,每次画完画都发现他的画不如调色板好。但调色板会成为画吗?后来他发现,调色板比画好的原因在于,客观物正在消失。而康定斯基之前的画受印象派风格影响很大,有大量可以辨析的形象存在。他终于意识到客观物没有意义,在这種灵感之下,他画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抽象画(《无题》1913年)。

东亚艺术以及神秘主义的影响:此次展览有机地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主义艺术史呈现,以一种对话和开放的方式,呈现康定斯基的个人艺术创作生涯的同时,也揭示出一条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艺术的发生所受到的东亚艺术影响的线索。尤其在展览入口的展厅,专门展示了康定斯基的日本浮世绘收藏,而结束展厅以中国青铜器的影响收尾。这个展览点出了康定斯基所受到的东亚文化影响,但遗漏了一点,就是康定斯基的绘画中还有一个神秘主义的背景。康定斯基从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中看出一种抒情性的体验,并将其用在点线面的造型因素之中;同时,他又把点线面看成是一种神性。在康定斯基学习法学的期间,他曾经到俄国的乡村考察东正教的各种教会的状况,对俄国的神秘主义的民间传说非常有兴趣,他的作品中一直有一个神秘主义的背景,后来有一些学者将其解释为“通灵论”,探讨其神智学的传统渊源。对于康定斯基来说,“点线面”作为一种造型因素,要同时具备抒情性和神性的统一。
无论对抽象艺术依然持有热情,还是已经放弃绘画本体的艺术界人士而言,尽管康定斯基的艺术成就已经盖棺论定,但它不是一个句号,它向我们提出了诸如东亚文化如何影响现代主义艺术革命,大胆跨界应该立足于什么,神秘主义与艺术创作有联系吗等等问题,而这些依然是我们在2021年艺术中一直在追问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