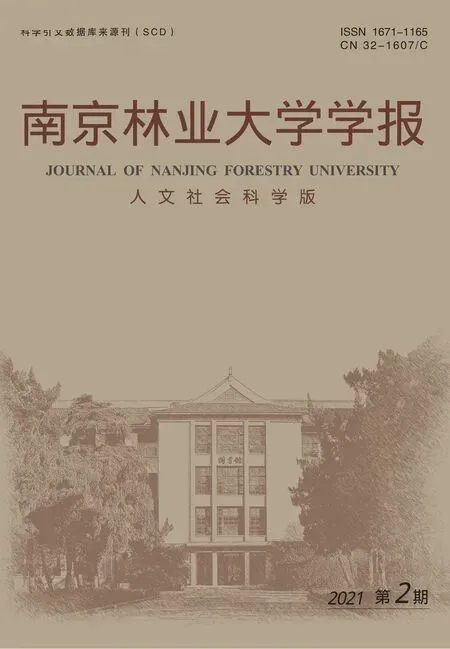蕾切尔·卡逊“海洋三部曲”中的生命审美观*
张红霞,李新德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是美国水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博物学家及自然保护主义者,被誉为“环保运动之母”。代表作有《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和“海洋三部曲”(Sea Trilogy)。其中,“海洋三部曲”包含《海风下》(Un‑der the Sea‑Wind,1941)、《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1951)和《海滨的生灵》(The Edgeof the Sea,1955)。①关于The Sea Around Us的中文译名有《我们周围的海洋》和《环绕我们的海洋》,前者更为多见。The Edgeof the Sea的中文译名主要有两种:《海之边缘》和《海滨的生灵》,前者直译,后者意译,因研究目的,笔者采用后者。《海风下》记录了北美东海沿岸、外海及其海底生物动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周围的海洋》描绘了古往今来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海洋的边缘》则激荡着濒海生物坚毅顽强的生命精神。“海洋三部曲”以“生命”为主线,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生命审美价值,更潜藏着卡逊对各类动植物生命之美独特的思考与感受。在卡逊看来,海洋孕育着一切,也主宰着一切。洋流运动不只是水的运动,更是一条生命的溪流。永恒的海洋承载着永恒的生命,沉淀着历史的印记,也预示着遥远的未来。灿烂多姿的海洋生命究竟传达着怎样的生命信息,又蕴藏怎样的宇宙真理,近在咫尺的滨海生物的生命意义却与我们遥不可及。当下,在人类唯我独尊的时代背景下,探寻其他生物的生命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拟结合环境美学中的“参与美学(participatory aesthetics)”与“从自然本身欣赏自然(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分析卡逊独特的生命审美观。
一、以敬畏之心审美生命
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敬畏生命(reverencefor life)的思想渗透在卡逊的每一部作品中,例如:苍凉无边的冬季海面实则到处隐藏着无数“生”的希望;黑暗沉寂的深海依然栖居着生命;一杯海水、一抔泥土都可能含有数百万个生物;深海生命承受着巨大的水压,极尽所有去适应无尽的黑暗,绽放着生命的奇迹;海葵必须依靠一点坚硬的基础生存,而在泥沙淤积的世界里,每一只找到家园的海葵背后都意味着数以千计以失败而终的海葵。洋流永无止息的迁移运动,淘汰了大多数的生命,筛选出百难之中依旧顽强的个体。我们不得不叹服于这巨大的生命浪费,敬畏生命的难能可贵。滨海的鸟群虽幸免于洋流运动,却也坚守着南迁的信念。《海风下》中的一种珩鸟,飞越两千多英里的大洋去追随南方的暖阳。纵有千难万险,珩鸟依然勇往直前。南迁的信念战胜了猎人枪支的威胁,即使耗尽生命中最后的力气也依然坚定地前行。猎人对生命的轻视与鸟儿勇往直前的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流露出令人敬畏的生命意志。卡逊也同样敬畏那历尽艰险却依旧力争上游去生育下一代的鲥鱼群,即使尸体垂悬在渔人残酷的网上,头也依旧无一例外地朝着上游的方向。
生物强烈的生存意志不仅仅局限于动物,植物亦是如此。卡逊告诉我们:“北极的植物必须抓住一年中仅有的几个星期中那阳光充盈的时机,穷尽其一生地绚烂。之后,它们便要将这仅存的生命余火包裹起来,熬过漫长的黑暗与寒冷。”[1]41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前,生命从未退缩。无论结局成败,每个生命都极尽所能,演绎“生”的意志。
二、以生态哲思审美生命
卡逊笔下的海景是一片自然全美的仙境。海洋生命的生死存亡不仅在美学上引人入胜,而且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思。生态探索既能趋近生命的奥秘,更能深化审美体验。因此,探索生态真理的过程,也是趋近生命意义的过程。
首先,最明显的是万物互利共生的和谐美。“海洋三部曲”无不揭示这样一个生态道理:海风牵系着陆地和海洋,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圈。在这里,万物生命组成一张错综复杂而又脆弱的生命网,形成一个生生与共的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卡逊痴迷于生命的这种和谐共生之美,有时直接表露。在《海滨的生灵》里,卡逊写道:“海滨连接着陆地和海洋,激荡着生生不息、不眠不休的生命能量。每次踏入这片世界,都会对生命的美妙与意义有更深的体悟,都能感受到那生命与生命,生命与其周围的环境彼此相连而织成的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2]2有时,她又以具体的例子揭示这种和谐共生之美。在《海滨的生灵》中,卡逊把佐治亚海滩上的洞穴比作地下城市,而久居于此的居民大多共生共居,其中蝼蛄虾为多达十个不同种类的动物提供庇护所。还有诸多美丽动人的群落,比如珊瑚礁和红树林吸引着众多生物,构筑出一片片热闹的社区;《海风下》中记录了一种名为潘东(Pandion)①鸟名,又叫鸬鹚,一种长翅的大鸟,因善捕鱼而有“鱼鹰”之称。的鸟,在它偌大的鸟巢别墅下寄居过麻雀、椋鸟、鹪鹩、猫头鹰及绿鹭等其他鸟类,潘东都对它们温和以待。甚至还有鲑鱼与海鸥共同捕食的策略,一方在水下疯狂追捕,另一方在水上助攻,被追捕者在这样的双重围剿下无处逃生,最后两方互利共赢。在卡逊笔下,母亲海洋是一个无缝隙的家园,在这里,没有谁能够独自生存,没有一个缺环,现在承接着过去和未来,每一个生物都与其周围的环境密不可分。大自然用它神秘的手掌滋养着万千子民,展示着“生”的神奇与美妙。
其次,生命本质的生死游戏之趣。海岸沙滩相对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是冷漠贫瘠的,而相对有心的观察者则是神奇美丽的。《海滨的生灵》中,卡逊用很多的笔墨讲述了渺小沙粒的广阔世界。正是在此,卡逊趋近了生命的实质。她说:“生命的实质几乎总是在于——觅食、避敌、捕猎、繁殖,所有这一切组成了沙滩群落的生与死,使之永存不朽。”[2]132《海风下》更是淋漓尽致地描述了食物链上的生死游戏循环规则。比如,其中一只淡水龟、一只野鼠与一只大蓝鹭之间的故事,幼龟慌乱地躲避上涨的海水,近旁的野鼠敏锐地察觉出了这一动静,越过沙地,涉过溪涧,咬住了幼龟。于是,野鼠兴奋地专注于它的美餐,全然忘记了身边袭来的潮水。恰巧,沿岸飞过的大蓝鹭灵机地察觉到了这一绝好的良机,果断地抓住了野鼠。而就在这永恒的生死游戏规则下实则隐藏着诸多审美之趣,如幼龟求生的意志、野鼠敏锐的听觉和大蓝鹭机灵的观察。正如罗尔斯顿所言,野生动物自发的“能动美”吸引着我们,它们的能动性和野性在审美上吸引着我们。[3]332
此外,在常人眼里看似毫无生机的景象实则都是假象,例如:光秃寂寥的树皮下包裹着棵棵嫩芽以及冬眠的昆虫;冰冷深厚的积雪底下其实埋藏着冬眠的种子与无数的虫卵。在《我们周围的海洋》中,卡逊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形象地告诉我们:“表层水域通过一系列微妙的、环环相扣的共生关系,将整个海洋中的生命联为一体……在海中,每样东西都能物尽其用,一丝一毫都被不断循环,先是为某个生物吸收,之后又被另一个生物所利用。”[4]在海洋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环环相扣,互为一体。积年累月的沉积降雪在四季轮回、海水交换中循环更迭,孕育新生。罗尔斯顿称之为“共同的生命之流”,即生命物质不断循环流动的动态过程,陆地流向海洋,死亡流向新生,过去流向现在。遗传物质在“自然的阻力”与“自然的助力”下取走生命,又重新组成生命。在自然神秘的法则下,新生与死亡,种子与生长,成功与失败,永恒与变化等一系列“自然的符号”投射成生命的信息,讲述着新生与死亡。罗尔斯顿将其比喻为“我们既是祖先遗嘱的执行者,也是受益者”[5]。而自然符号的这种生与死除了自然终结之外,还应包括幼龟、野鼠与大蓝鹭之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生死游戏。同样,卡逊将连接陆地与海洋的滨海生物看作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生命载体。生态学的视角是卡逊接近自然的桥梁之一,也是卡逊想借此传达给公众的宇宙生命真理。这种共同的生命之流哲理在《海风下》及《海滨的生灵》中不止一次地明确展现。卡逊常常站在生态学角度,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展现海洋生命动态平衡的神奇与壮美。
最后,生物生存适应的生命精神之美。大海之滨,作为海陆界限,此时属于陆地,彼时又成大海。只有最坚韧、适应力最强的生命才能在此生存。于是沙滩上的动物几乎都学会了深挖洞穴;在岩石区,即使脆如瓷器的动物都可钻入岩石。漫步于动荡多变的海滨时,卡逊常常被这种坚韧与顽强的生命精神所感动。正如她在沙质海滨一章结尾处总结的那样:“这几乎无一例外地向我表达着生命力的强力——强烈的、盲目的、无意识的要生存、抵抗和繁衍的意志。”[2]189
从了无生机的混沌期到如今热闹非凡的海底社会,生命遵循生态系统规律,适应自然从而生生不息。生命在精妙的自然法则下丰繁而有序,“海洋三部曲”揭示了数以千计的海洋生物如何依赖潮汐生存繁衍,生物活动如何精准地适应自然规律,陆地生命与海洋生命之间是多么休戚与共,幽禁于深海、北极以及海滨的生物如何适应恶劣的环境而绽放生命的奇迹,等等。同时,也用艺术的语言唤醒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正确定位。卡逊敏锐的自然感知力,使她不只看到大自然奥妙神奇的一面,也能察觉到大自然所遭受的破坏。伯林特称之为肯定审美价值和否定审美价值①伯林特在谈及环境美学的领域时,谈到城市美学必须思考否定的审美价值: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刺耳的信号声、公用事业管理线、脏乱的街道以及单调、陈腐或是压抑的建筑设计给知觉带来的妨碍或破坏。那么,同理,在自然鉴赏中,动物栖息地的破环、空气污染等也可以被看做否定的审美价值。参见:阿诺德·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M].陈盼,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7页。。当肯定审美价值到达一定深度时,否定审美价值便会逐渐清晰。美学价值是保护生命的根源所在,而生命之美是海洋之美的灵魂所在。卡逊从生态学的视角揭示了生命的宏观大美,这无疑是对现代环境美学的一个强有力的补充。
三、从生物本身审美生物
17世纪俳句创始人松尾芭蕉(Matsuo Basho)教导学生要“从一棵松树中了解松树,从一根竹子中了解竹子”[6]158。日本禅宗(Zen Buddhism)提倡我们身心全部“进入(enter into)”或“与之融为一体(become one with)”[6]158。同样,尼尔·埃文登(Neil Evernden)和安妮·狄拉德(Annie Dillard)在谈及自然时,都指出要回归事物本身(return to things themselves)。[6]158-159然而环境美学家齐藤百合子(Yuriko Saito)认为这三种模式虽可以摆脱人类意识,但并不能真正与自然事物达成共鸣。她的“从自然本身欣赏自然(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认为,要真正从自然本身欣赏自然,还需借助自然历史以接近自然之物的本质。[6]151-168那么,欣赏有生命的动植物更是如此。只有去除过去固有的人类意识,从它们的视角感受它们的生命,才能真正接近鉴赏对象的本真。而早在20世纪,自然的见证者①传记作者李尔称颂卡逊为“自然的见证者(witness for nature)”,参见:Linda Lear.Rachel Carson:witness for nature[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LLC,1997。——卡逊已为我们树立了行动的标准。
首先,卡逊以生物为中心审美生物。在创作“海洋三部曲”时,卡逊以动植物为主角,并为此感到欣喜:“我已成功地变成了夏天鹬、螃蟹、鲭鱼、美洲鳗和好多种别的海洋动物!”[7]卡逊站在它们的立场,想象它们的世界,从它们的视角探寻海洋生物各个维度的细节。埃米莉·布雷迪(Emily Brady)指出动物除了功能之美外,还有“表现属性(expressive quality)”和“情感反应(emotional reaction)”[8]。而卡逊的“海洋三部曲”展现了更为精彩纷呈的生命活动,有鲜为人知的海底大合唱、神秘诱人的潮汐规律,甚至微小沙粒所负载的历史信息等;更有燕鸥、黑脚兄、三趾鹬之间激动人心的战争,燕鸥一边留意水中鱼的活动,一边密切注视着三趾鹬,并且精明地知道对方的弱点,在黑脚兄口叼小蟹时,故意振翅威吓。这些动作和心理活动似乎是燕鸥的自我描述,卡逊将自己完全隐身,以鸟为叙述者,讲述它们自己的故事。传神的是,这种化身仿佛也把读者变换成了那只燕鸥。这种从动物视角展现生命的能动与灵机,是真正从生物本身欣赏生物。
其次,作者通过想象与海洋生物产生共鸣。约翰·杜威(John Dewey)指出,恰当地欣赏来自过去和异国文化的艺术都需要“通过想象”增强“共鸣”(sympathy through the imagination)。[9]齐藤百合子把这种共鸣沿用到自然鉴赏中。那么,动物鉴赏更须如此。在子夜前后,壮观的鸟群启程南飞,卡逊用一句“苔原上的每只鸟都听到了这呼唤”[1]48传达了候鸟内心对南飞的热切渴望。类似地,在三趾鹬离开孩子南迁时,卡逊化身三趾鹬母亲,想象着她离开孩子的焦虑。把鸟儿看作与人相似的主体,通过认知基础上的想象,拉近了鸟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进一步趋近了宇宙生命“生”的生命哲学。正如罗尔斯顿所言,鉴赏动物是一种生命感受另一种生命,这种跨价值的感受带来了审美的丰富性和创造性。[2]332卡逊通过想象,体会着动物世界里其他生物与人类相通但又异化的表达属性,通过想象产生共鸣,因而更能理解生物本身。
最后,卡逊从生物的视角客观地了解生物,尽可能摆脱人类的主观意识。齐藤百合子指出,“为了达到共鸣,我们需要一些关于其他生物的信息,比如外力如何影响它们,它们又是怎样做出回应,等等”[6]159。而这方面,卡逊显然知道得更多。当春潮大涨,暴风雨把候鸟从几英里外的大海上吹来,三趾鹬和其他滨鸟群为躲避暴风雨寻找栖息地,卡逊完全站在候鸟的立场,结合它们不同时期的生活场所,描写道:“陆地对它们来说是陌生的领域,除了每年往南极海域育雏时在一些小岛上做短暂停留外,它们的世界就是天空与翻腾的海水。”[1]30-31再如,《海风下》中一种名为三趾鹬的滨鸟,常常喜欢黄昏时候在伴侣面前炫耀自己的威武与霸权。当然,雄性三趾鹬的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与人类相似,所以容易被人类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只有深刻了解动物习性,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它们的世界。禅悟(Zen enlightenment)认为,“水”在不同的生物视角下代表着不同的物象,可能是“美丽的花朵”,可能是“珍物或宝石”,也可能是“烈火和脓血”,还可能是“宫殿和凉亭”,甚至还可能是“森林和墙壁”[10]。因此,相同的鉴赏对象投射到不同的鉴赏者意识中所代表的物象不尽相同。卡逊在审美海洋生物时,在某些场景下,她会选择性地抛弃一切已有观念,以初见大海的《惊奇之感》(The Senseof Wonder)①《惊奇之感》(The Sense of Wonder)是卡逊的另一本自然小册子。在该书中,卡逊把人与生俱来对自然的好奇、热爱、共情及敬畏等情感统称为对自然的“惊奇之感”。该书旨在启示父母如何保护并培养儿童终生对自然的这种“惊奇之感”。参见:Rachel Carson.The sense of wonder[M].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98。关于The Senseof Wonder的中文译名,国内学术界普遍翻译为《惊奇之心》,见:蕾切尔·卡逊.惊奇之心[M].王家湘,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4;但综合多方因素,笔者更倾向于采用《惊奇之感》的中文译名。可参见George Santayana.Thesenseof beaut[M].New York:Hansebooks,1896,其中文译名为《美感》,见乔治·桑塔耶拿.美感[M].杨向荣,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走进大海生灵,与之朝夕相处,观察记录它们的生命活动,尽可能地摆脱人类意识,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了解生物。因此,在审美生物时,不能完全依赖于科学知识。在某些场景下,切身观察生物习性、活动、栖息环境等,不以人的观念为主导,客观地了解生物本身,也是趋向恰当的生物鉴赏的必要前提。换言之,只有切身目睹过、感受过,才有权利评判一个对象的审美价值。间接的意识接受或转移都可能带来认识和审美评判的偏颇。在这一点上,卡逊给我们做了示范,例如,“月光在鱿鱼看来是心醉神迷的向往”“平原在三趾鹬听来是活的”以及“暖阳和绿波是候鸟的最爱”。她结合各类生物的生活习性、喜好规律、生态功能等信息,从生物本身认识生物,为我们展现了海洋生命纷繁多姿的美。也唯有如此,才能正确欣赏动物生命的灵性美,去除人类意识,真正做到从生物本身欣赏生命。“海洋三部曲”并不是专业科学知识的堆砌,多数故事都是由卡逊亲身观察记录所得。因此,“海洋三部曲”可以说是一部生物“纪实片”。她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海洋,因为海洋生命那灵动的美与无穷的奥秘令她痴迷。为此,她这个海洋常客与海洋精灵相知相熟,因而能够较为准确地从生物自身揭示它们生命的客观真理。
四、以参与模式审美生命
在环境美学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鉴赏者究竟应以何种身份鉴赏自然?参与者、静观者、外来者、内在者抑或是其他身份?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艾伦·卡尔松(Allen Carson)、罗尔斯顿认为鉴赏者应以“参与者”的身份走进自然、融入自然。卡尔松强调“自然语境的多元维度以及我们对它的多元感性体验”,鉴赏者与鉴赏对象及周围的一切是一个“融合”的整体。因此,鉴赏者应尽可能地缩短自身与自然间的距离,全身心地沉浸到自然中。[11]而伯林特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无利害”、静观美的束缚,以建筑艺术为例提出“参与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ngagement)”[12],试图构建一种可以在鉴赏艺术、建筑、自然景观中通用的普适方法。之后,罗尔斯顿将其延伸到了对野生动物的美学鉴赏中,进一步丰富了“参与美学(Participatory Aesthetics)”。
“参与”一词的主要意思是:使自己参与或专注于某项事物,或使自己对此肩负某种承诺或责任。对于伯林特和卡尔松提出的参与美学而言,其中的“参与”就是要使自身融入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环境或生态整体之中。[13]这种鉴赏模式呼吁一种全身心、多感官的融入体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层的视觉欣赏,更不是在图片、视频里的间接参与或者在森林之外的远距离欣赏。简而言之,“参与美学”试图突破传统美学的审美视野,要求各种感觉经验联合投入自身在内的环境整体中,形成一种审美参与者、审美对象和审美体验相融合的审美情境,建立一种“参与”的多元体验审美观。而这种审美体验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自然的见证者卡逊已经完美地展现了先例。作为一名从小与自然为友的海洋生物专家、博物学家及作家,卡逊的审美视角比当代环境美学家探寻到的更为丰富。
要体会古老神秘的海洋生命所承载的生命意义,需要我们以一种“内在者”的状态,完全置身于整个海洋景观,敞开所有感官,与海洋促膝长谈。在欣赏海洋生物时,卡逊常常或静坐海边,或漫步沙滩,或趟入海滨,或潜入海下,与海滨生灵密切相处,聆听它们的声音,体会它们的世界,与之融为一体,用生命感受生命。比如:深海的“星星”①指深海会发光的动物。;夜间沙蚕的烟花表演②沙蚕会呈现色彩斑斓的颜色,夜晚常常聚群活动,因而,卡逊把这比喻为美轮美奂的烟花表演。;海底植物筑成的海洋花园;夜间的虫鸟合唱队;海底生物的大合唱;淡水龟和新生龟蛋的气味,潮水的气味;精细柔软的海沙,轻如羽毛的螺壳,褐壳藻丝绒质的外壳,角叉菜铁丝般的质感;等等。卡逊诗意般的语言和那超乎常人的自然感知力为读者呈现了一场感官盛宴。
品读“海洋三部曲”,似乎能听到潮水不眠的翻滚声、鸟儿动听的歌声与海洋精灵那悦耳的大合唱。不同的是,卡逊能捕捉到它们背后更为深刻的意义和鲜为人知的海洋之语。“踢——呀——呀!”“啊”“哈”“叽”“魁——咿——呀!”“咕——阿——喜”“踢——呀——呀!”“凄!凄兮!”卡逊把它们喻为夜间合唱队,有时她能从叫声中辨认出鸟的类别,甚至有时候能读懂它们的语言。她似乎真的变身为三趾鹬,从这平原微妙的沙沙声中辨识出那是金珩集结队伍以待次日南迁,从而见证了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珩鸟队伍壮观的南飞表演;鸟的叫声众所周知,但幽暗的深海下群鱼的语言却鲜为人知,比如:幽暗的深海下的“呜咽声”“尖叫声”“幽灵般的呻吟声”“噼啪声”“嘶嘶声”“嗡嗡声”“唧唧声”,等等,对此卡逊也虔诚聆听,而后把它们喻为“海底大合唱”。有时候,卡逊打开小蜂孔海绵倾听枪虾的警告声,仰卧海滨倾听海滨生物的敲击声。
在齐藤百合子看来,自然语言丰富多样,需要我们调动各个感官去识别。[3]154卡逊正是这样,她把自我与周遭环境完全融为一体,多种感官相通交融,探寻大自然那些鲜为人知的美。夏末初秋的夜晚,常人印象中凄凉乏味的沼泽在卡逊眼中却别有一番景致,她深情地赞美道:
九月,沙丘上燕麦圆锥形花序变成了金黄色。沼泽慵懒地躺在阳光下,闪耀成了五彩的天地,有盐碱地草地的褐黄与柔绿,灯芯草的暖紫,还有海篷子的猩红。橡胶树红得好似河岸上映红的火光。夜晚,秋天浓郁的气味弥漫着温暖的沼泽地,披上了一层浓雾。掩护了破晓时伫立草丛中的大蓝鹭,也使得匆忙穿越沼泽的草甸田鼠躲过了群鹰的法眼,好似早就预料到了这场危险,田鼠事先铺好了秘道,它们在数以千计又杂乱无章的沼泽草丛中耐着性子顺藤摸瓜找寻出路。[1]51
在这段描述中,多重感官相融并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命绚丽多姿的美与奥妙。其中有触觉味道的视觉描写——盐碱草地的柔绿,灯芯草的暖紫;有视觉色彩的嗅觉描写——秋天浓郁的气味;更有触觉和视觉相融的双重感官——夜晚遮蔽大蓝鹭、田鼠的薄雾,以及隐秘处草甸田鼠凭着对沼泽根茎的感觉铺出的密道;还有潜在的听觉描写——草甸田鼠逃窜的沙沙声。卡逊正是先验性地将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想象全部融入这番体验,忘我地感受着生命的缤纷与奥妙。
诚然,只有身临其境地融入,才会激发全面纯粹的感官通道。相同的自然景观投射到不同的鉴赏群体时,美学价值才会大不相同。不同的感官参与的自然审美体验,升华到的美学价值亦不尽相同。
五、结语
自然的灵魂在于生命,而生命的灵魂在其“生”的活力。环境美学家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详尽论述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命对自然的价值。罗尔斯顿将生命看作是自然的投射,是一条源自过去并通向未来的动态之河。同样,卡逊笔下的海洋亦是一条连接古今的生命之河。保护环境终归是保护大自然中各种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尤为如此。因此,未触及生命美学的环境美学不能称之为成功的环境美学。同理,未重视生命美学价值的环境美学亦难以走向环境保护论。从环境美学角度解读卡逊“海洋三部曲”中的生命审美观,我们认识到:这种生命审美观总能使她不断地从大海母亲那里看到新的意义与价值,也启发我们从生命本身敬畏生命、欣赏生命、追寻生命的意义。她以海洋生物为主角,记录了鲜活真实的海洋世界,既抒发了她对生命无尽的爱与赞美,也树立了行动的标准,发出了向善的感召。在海洋之母温暖的臂弯里,交融着生命的美与善,卡逊以其自身的审美态度与审美方式启发我们如何让生命美走向生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