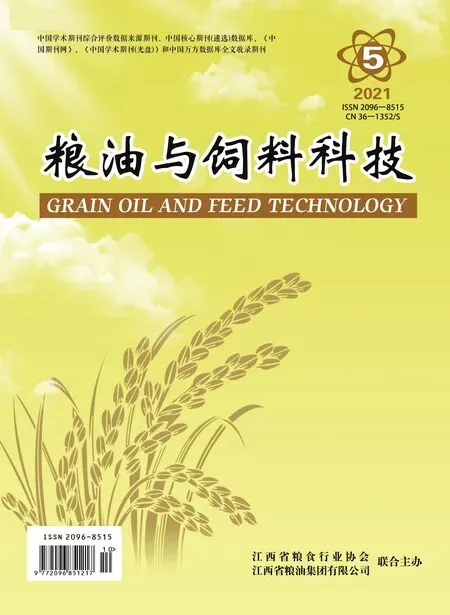悠悠岁月,逝去的苏桥老粮站
汤章涛
一
前段时间,我回了一趟老家,一个养育了我二十多年的故乡,赣东北一个偏远而又静谧的热土。
故乡的山水很亲很热很熟,闭着眼也能走一上午。那天上午,父亲邀我去苏桥老街上走一走。苏桥乡与坦下乡已经合并为一个乡,合并后的乡仍然命名为苏桥乡,但政府所在地迁到了原来的坦下乡。老苏桥街上的乡政府便撤了,成了居委会。昔日的繁华与热闹逐渐消退,但依然能见到当年的街貌和旧式城楼,苏桥粮库便是其中的一角。
粮库,乡亲们叫它粮管所,有的后生叫它粮站,实际上门框边的牌匾印着:“中央储备粮苏桥收储站”。这个地方是当年全乡老百姓生产生活中最需要涉足的地方,它牵动着父老乡亲的神经,魂牵梦萦,昼思夜想,惺惺相惜。
二
粮站,在我岀生几十年前就建成了,具体什么时候开建的,我也不知道。与粮站相连的是粮票,粮票,我见过。父亲是个文化人,小的时候,父亲把粮票锁在柜子里,当命根子。粮票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便稀稀疏疏地不再用了。一般的乡亲们手头有棉票、肉票、布票,甚至点灯的油票,但是很少有粮票。粮票只有吃商品粮的城里人或者公务人员才有,普通的社员岀门做点生意要些粮票路上用,也只能通过村里开证明拿米去兑换,那都是少之又少。
乡亲们平时的口粮只有通过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生产队里给你分口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生产小队是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单位。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生产大队的会计,只记得父亲管了大队里的很多账本,父亲打算盘非常厉害,左手右手能够同时拨动算盘珠子,算出十多位的数字,嘴里时不时地念出一两句口诀,让人着迷。
生产队一直延续到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民公社便解体了,生产队便成了现在的村民小组。
三
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先要上交公粮,也就是上交国家粮,后要上交定购粮,也就是集体粮,剩下的就是社员的口粮。“大锅饭”时代,粮食产量低,全年粮食亩产只有三四百斤,这还要雨水好,如果雨水不好,亩产一二百斤也是常有的事,一年下来,乡亲们口粮都成问题。所以,每年在夏收和秋收后,县里和公社就组织干部下到公社和生产大队,包点抓粮食征购。大队的广播喇叭几乎二十四小时地响,播放干部动员讲话,粮食征购好人好事和进度表,场面轰轰烈烈、声势浩大。
生产队在完成上交公粮、留足种子和牲畜饲料,除去公积金、公益金,剩余的粮食便作为社员的口粮进行分配。有谷粮也有杂粮,要按当时的标准计价,那时稻谷每斤0.11元、红薯0.03元。杂粮也要进行分配,四斤红薯抵一斤谷粮,一斤芋头抵一斤谷粮,一斤小麦、豆子也可以抵一斤谷粮。谷粮与杂粮一起进行分配。
1958年之前,社员的工分也用来计算口粮,也就是工分粮。大队会计计算岀总口粮的总金额,然后计算出工分的分值,得出每户的金额。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口粮,一般是六四开。总口粮的60%按人头分配,也就是人头粮;剩下的40%按工分分配,也就是工分粮。每户的人头粮加上工分粮,便是该户全年的口粮。一般情况下,一等劳动力能分到640斤口粮,三等劳动力也有600斤口粮。
七十年代以后,生产队里社员的工分不再计算工分粮。为了公平起见,每户的粮食、红薯、大豆分别计价,计算出每户口粮应付的金额。每户工分应得的金额减去口粮应付的金额,是负数的农户要出钱给生产队,是正数的农户等着领钱。一般来说,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农户要拨钱,壮劳动力多小孩少的农户要得钱。
听父亲讲,他读初中的时候,家里除了我爷爷奶奶,就没有其他劳动力了。加上小孩多,劳动力少,得出钱交口粮钱,因而家里粮食非常吃紧。每次吃饭,爷爷让孩子们先吃,最后剩的锅巴饭粒菜汤菜泥,一起倒在碗里,勉强吃个半饱。由于长期体力透支,营养不良,不惑之年,爷爷就因饥饿生病而死去了,那年,父亲才十八岁。
四
八十年代初,我已开始上小学了,虽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已实施,但统购统销的政策仍未废除。农民耕田种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同样按规定给国家交征粮。尽管有的农民打的粮食不够吃,但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每逢夏秋两季收割完稻谷,都坚持到粮站送征粮。
夏季“双抢”完成后,每天清晨,在粮站大铁门还没打开的时候,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已经推着独轮土车来交征粮了。那时,大多数村到苏桥街上很少车辆,有的地方还不通公路,运粮必须靠独轮土车推。独轮土车左右板上可以放两麻袋谷子,有的叠加放四个蛇皮袋谷子,一车下来有近三百斤。乡亲们力气都不错,他们用手扶起车子,肩上韋拉着垫绳,两头垂下套着车把,两臂一起用力,推起来要掌握车子的平衡,持续发力往前走。遇到沟沟坎坎,跟随的母亲们,弓着背帮着拽拽车。一路下来,骄阳如火,挥汗如雨,汗透衣裳。
有时候送粮的人很多,一车车、一担担稻谷排到了粮站的大门口。乡亲们一边聊聊家常,一边伸着脖子往前看,眼巴巴地等着粮站工作人员收粮食、评级、装仓。等轮到自己,便赶忙拎起麻袋去过秤。
粮站的工作人员脾气可不怎么好,很容易就生气了。他们的心情不好掌握,譬如来交粮的是他们的熟人或朋友,他们能高兴地和熟人说上几句:“肥猪长得好不好?红薯儿是不是都挖完了呀?”碰到他们不认识的农民,工作人员就不一定高兴了,査拉着一张脸,冷冷地倪着眼前这个交纳粮食的人。等着评级的老农民,脸上流露岀迫切、焦急、怯懦的神色,就像小学生站在严厉的老师面前一样,忐忑不安地等待。工作人员的手里总拿着一杆长长的探粮枪,往谷袋里一戳,取出粮食一嚼,看谷子是否晒干。工作人员的脸色稍微松弛一些,老农民的气便可舒缓一些。老农民巴不得粮食能评个好点的等级,给个好点的价格,可以抵更多的提留款。
有时,粮站工作人员会对那些不合格的粮食让交粮者就地翻晒,用风车扬尘,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农民尽管心里有些怨言,但是看看这里交的都是爱国粮,也会老实照办。每次送粮,孩子们总喜欢跟大人去玩,跑到粮站的仓库里,看粮食堆成山样的形状。
五
粮站的院墙就像城墙一样厚实,一样巍峨。墙角长着青苔,墙缝里露出几束野草,墙顶上插满了尖尖的碎玻璃,显得更加森严。站在空落落的水泥院坝往上看,可以看见宽阔的蓝天和蓝天下粮站的灰黑色屋顶。来来往往运粮的农民们在宽宽大大的走廊里奔走忙碌,他们在风车旁清理着粮食,在大秤旁秤着粮食的重量。
每次卖完粮,父母亲拿到钱后,常会顺手给孩子们一点零钱。孩子们会跑到苏桥街上买几根冰棒,坐在阴凉处美美地吸着,吸完了冰棒的棒子,孩子们也舍不得丢掉,叼在嘴里舔很久。
粮站,就是这样一个热热闹闹、生机勃勃的地方。
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兴起,物质越来越丰富,市场供应越来越充裕,国家开始放开统购统销政策,允许粮食自由买卖了;存在半世纪之久的苏桥粮站逐渐没落了。到了2000年,全国开始农业税费改革试点,部分省市的粮站取消征收公粮,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粮站的仓库里储藏的粮食都已清空了,粮站已经退岀了历史的舞台。
如今,公粮和“交公粮”的时代,已成为一种记忆,一种怀想。在记忆和怀想中,回味和咀嚼那个时代的酸甜苦辣。
时光飞逝,四十年转瞬而过。曾经年轻的父母垂垂老矣,曾经的小屁孩已进入中年,曾经稀缺的猪肉也变成家常便饭,但曾经的艰难和余香,了无痕迹,唯有记忆留存心里。
●汤章涛:南昌二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