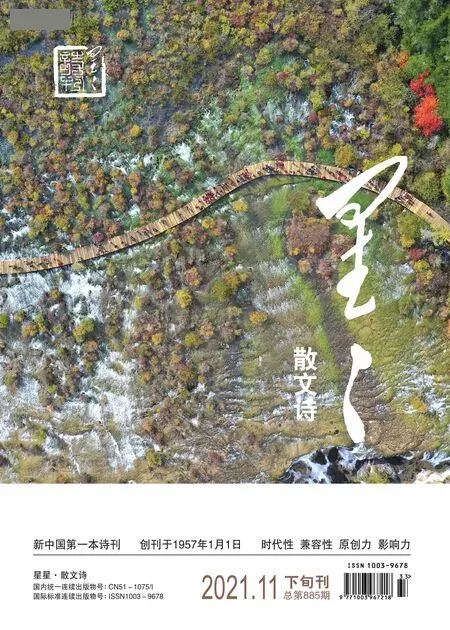触觉(组章)
‖皇 泯(湖南)
定格后,时间不再是时间
这是新世纪初的春天,时间定格在三月。
一座现代钢筋混凝土高楼,坚如磐石;
一间传统装饰的雕花房,纸糊的窗,舌尖一舔,即穿。
漏掉了两点水的姓氏,一马当先。
蹄风,轻轻抚过山林,拂过平原,就是草原了。
嘘,小心!
悬崖勒马,草原有水汪汪的草,草丛里也有潜水的蛇。
这是春天的创世纪,大胆的定格后,时间不再是时间。
我握住了月光
这个并不很特殊的夜晚,我握住了月光。水一样清澈的月光,又水一样漏过我的指缝。
幸福来得快,去得更快。
有如梦幻,跨过醒前与醒后的门槛。
那一瞬间,惊艳般的灿烂凋零成小白花,除了娇嫩,略显忧郁的苍白。
十五之夜,只要有月亮,天空就有一个句号。
就这样,水一样的月光流过来,又流走了。
圆满的是天象,残缺的是人间。
陈年黑茶,泡开鲜嫩的故事
不是法兰西岛的Fontainebleau,也不是拿破仑钟情的“美丽的泉水”。
这是家乡的枫丹白露,一个茶台两张椅,上世纪的陈年黑茶,泡开鲜嫩的故事。
秀峰湖的秋天,萧瑟得只剩下几根枯枝了,从桥南方向掠过柳树梢的翅膀,却扇出一片春意盎然。
温暖在窄小的包厢,幸福膨胀。
仅仅只是啜饮传统的黑茶,已无法为现代生活解渴。
来一杯,雀巢或蓝山,星巴克或麦斯威尔,加点砂糖或方糖,还可加奶,只要是咖啡,便会有西式的回味。
敞开了心扉,顽皮的脚丫,自然就溜过了门槛。
海平线,再也不可能平静
过完今天,就是明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年末的时间结点。
年初,浪漫的三级跳远,两步就跌倒在沙坑,传统已深陷至腰身,脚印,怎能逃离?
关于时间的算计,细如沙漏。我们在潮汐的起落中,看到了水丰富的表情。
起起伏伏,是生命的常态,海平线,再也不想平静。
腾跃浪尖的欢畅,与跌入漩涡的痛苦,殊途同归。
那是升起的帆,扇开了白云的翅膀;
那是撒开的网,收不拢鳞状的波光。
那是触礁后的鱼翔浅底,隐入了潜流;
那是归航的港湾,没有抛锚的锁链。
一孔牧笛,横槊赋诗
这是生命肆意疯长的季节,自由,开放在草原,草原,茂盛在天边。
激情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日子,一孔牧笛,横槊赋诗。
天空湛蓝得有一点假,云朵洁白得不是很真实。
天堂的幸福,离地狱仅隔一层纸,只要舌尖有味觉,一舔就穿。
沿着一条覆满嫩草的黄皮肤小路,深入腹地,深入天边。
不怕车轱辘辗压的伤筋动骨,何惧鞭影如飞蚊,大道当空,就对应一路赤裸裸的脚印。
妹妹也放声歌唱,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
再细微的水滴,石也穿
和一块石头有了亲密接触,大山就浓缩在那里。
旁门左道的小草,尽管呈现树木生长的态势,仅仅只是生机勃勃而已。
这使人们有了还原森林的想法,原生态的故事,持续哑剧的形式。
嘘!不说话,当然无须字幕的对白,肢体,是表达真情实感的最佳语言。
并非短暂的时空,翔飞着小鸟不知道疲倦的歌声,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和一块石头亲密无间了,浓缩的大山返回到石头。
再细微的水滴,石也穿。
想睡遍呼伦贝尔,那一片大草原
想把星城宾馆那一朵血色的玫瑰花,淡忘。
因为,那是一朵不带刺的浪漫,理智成无花果;
想把杭州小吃街那一夜美味,饱食。
因为,那是一次巧妙的可口可乐,无法重新品尝;
想畅游喀拉斯湖,那一泓碧水。
因为,那是一汪神秘的圣洁,由不得你的世俗;
想睡遍呼伦贝尔,那一片大草原。
因为,那是一张铺天盖地的温柔,淹没了你的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