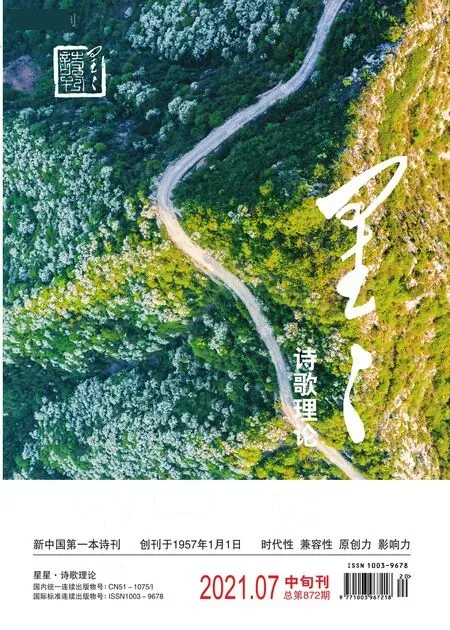当代汉诗的零写作
>>>余 退
谈当代汉诗,不得不追溯其起源,就像人类精神的还乡,总是想确认并回到某个出生地。从现象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当代汉诗的缘起开始于胡适的《尝试集》,也有说成熟于郭沫若的《女神》,或者如张枣所分析的其真正的有效性发端于鲁迅的《野草》。
但还乡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从与当代汉诗的紧密关联角度而言,几乎不再会有当下的写作者会以民国时期的诗歌文本直接作为自己的写作参照坐标,其实这也就意味着起源的失效。臧棣说“如果从新诗与现代审美的关联来看,不必讳言,新诗的传统是一个零传统”。开端与后代的联系并未有推演中的那样紧密,乃至绝大部分联系早已经失效,这在中国新诗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起源所起到的奠基作用不等于是实质的推进作用,两个作用之中显然存在着巨大的落差,甚至我们应该脱离开端,重新从“零”开始辨析当代汉诗。
“零写作”并非故意引导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当代汉诗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当代汉诗其本身存在着几对非常显著的“互否”关系:第一个是古典继承与反古典的关系。一方面,当代汉诗暗中保留了古体诗的精神基因。中国古典诗歌从古诗十九首到《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清诗这样一路发展下来,铸就了汉民族强大的诗性基因,其背后所依托的是中国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古典精神,这些精神不同程度在当代汉诗身上透露出来,而且不可去除。但同时,中国新诗又天然具有对古典诗歌的对抗和焦虑,从诞生之日起,新诗就具有了颠覆、抵抗的性格,建立在对传统古典诗歌的反叛上,要追求“诗体的大解放”。第二是对西方文明及西方诗歌体系的艰难吸收。无可置疑,西方文明和西方诗歌,特别是现当代西方诗歌对当代汉诗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撬动作用。这方面的影响是直接的,翻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条汇入的河流,裹挟着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在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兴起的阶段,往往是谁先接触了最新的国外诗歌文本,谁就能第一时间震动诗坛。但是,因为文化根脉、文化背景、时代特点及历史事件等差异的影响,中国当代诗人要消化西方诗歌存在着内在的天然阻力,其融入要经历艰难的吸收和重构过程,但又因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特殊张力,这种张力成为造就当代汉诗差异化和独特性的一个特定因素。第三是文化的异化和断裂,特别是当代商业、现代科技和集体意识对经典思维的左右和冲击,导致大众思维的苍白和统一化。进入到网络时代后一切都在高速翻新,很多领域的认知都在重新打破,从而产生语言和思维上的断裂及再认、焦虑与新奇、对抗和兴奋,这些都会第一时间反馈到最为敏感的当代汉诗上。
当代汉诗既古老又是全新的,将在自身的前进中成就当代汉诗的传统和性格。在这异常激荡的发展过程中,旧的传统被消解、打碎,转化为因子成为新诗的原料,由复杂的内外环境而造就出新诗复合型的内在肌理,使得当代汉诗表现出有别于古体诗、西方诗歌及其他文体的复杂性。身处当代中国,诗人所面临的是看似寂静的文化生态,实则是处于很强烈的地震带,当代汉诗写作者必定会面对种种困扰,这时候更需要反思当代汉诗的构成。目前对于中西经典诗歌的态度,很难做到直接摒弃、否定,或者直接直承式地接受,而是正在吸收、重新发现、重构,而形成一种新的自觉,仿佛在重新开始。
当代汉诗的发展和汉语的高速更新、翻新紧密相关。当代汉诗的创作和现代汉语之间不是简单的依赖或者原材料与构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相互交融、互存互动的。一方面,经过百年的发展,现代汉语已不只是简单的“白话”,不仅具有口语功能,而且已经建构出了属于现代汉语特属的语言体系,而产生了新的“文言”。当代汉诗必须依赖现代汉语的逐步成熟而成立,同时也正因为现代汉语的未成熟,让当代汉诗具有了青年的、未完成的气质。另一方面,诗歌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超前性,始终会走在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山脊上,为锻造现代汉语的精神气质而提供高度,在文本的角度引领现代汉语的前进。当代汉诗的“先锋性”特点也一直是现代汉语高速翻新的一种表现。
“零”意味着“自我重审”。“自我重审”在写作的起笔时就已经开始,新诗写作者永远面临着一种“空白”。这种“空白”非“清零”,更像是随时准备着从零出发,回到诗意的本体之内,像是要通过诗歌重新学习进入世界,处于自我的持续更新之中,而且这种更新的速度在“第三代诗歌”之后,显然是加快了。取消写作的姿态,取消对传统田园及个人小我的迷恋,回到生存和语言的现场,以进行式的方式重新确定自身,在写作方式、写作倾向及意义上的不断“归零”之后再次出发,这个和当代汉诗所具有的“自我重审”属性息息相关。
当然,这里的“自我”是需要讨论的。当代汉诗的“自我”表现和经典文本里的“自我”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当代汉诗里的“自我”更加具体、低沉、碎片化,更能直面真实之境,其表现空间更加自由和巨大,也更加无序、苦楚,是正在进行的过程。这与人所处的维度有关,在面对商品经济、科技发展、人工智能等场景时,自我何在?智慧为何物?家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正面解答的艰难问题。通过新诗的写作,我们在断裂的现实中不断回到人的自身上来,开始存疑、感慨、迷惑、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同表现。然后又不得不以这样一个“未定义完成”的“自我”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当代汉诗的“自我重审”属性显现为“时间的重审”,海量的当代汉诗能否历经时间的考验是个严峻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因为但凡是真正的作品,其本身具有的“超越”性质会带着作品穿越时间。但是新诗的失效问题,却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个问题的产生应该作为诗人的一种自我警示。似乎和药品一样,诗歌具有一定的“保质期”,这看上去非常的可悲而残酷。以朦胧诗为例,朦胧诗重启了新诗的发展,但是才过去四十年,很多当时确定为经典的文本,现在看来几乎失效了,面对更迭的观念和诗艺的探索,其文本的可读性、价值变得非常之弱,更多剩下的是历史维度的价值,这肯定是值得深思的。
诗的发展主动见证了更多预设的诗意的快速失效。1990年代盛极一时的喷涌的各种诗歌主义,其“主义方面”的意义绝大多数已经失效了或者正在面临更大程度上的失效。现在,你很难听到诗人会坚持其“莽汉”“整体”“英雄写作”“下半身”“非非”“女性”等诗歌流派特征,目前尚有个别人在坚持的“口语写作”显然也已经乏力。当然,“第三代诗歌”优秀文本的成立却是显而易见的,和其对个体精神的表达、对语言丰富度的探索、对不同世界的触摸都有很深的关系,但其所张扬的各类“主义”的意义已经归零。
目前,要对诗歌进行分类已经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和当代汉诗的高速“失效”有关。比较多见的分类,是按照70后、80后、90后等年龄段来划分,这个当然显得粗暴,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同属于一个时代,从50后到00后都是“同代人”,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简单的客观性。按照学院派写作、民间写作进行分类,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中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界线,也过于笼统。从“实用”角度而言,绝大数参赛诗因其具有的强烈的“虚伪”和意义的“预设”,将被作者本人及时代快速放弃。还有一些即兴小札、抒情诗、农业诗,因其仅显示单向度的世界,而显然没有多大的价值。这些消解都和当代汉诗的“自我重审”属性有着莫大的关联。
难度写作不属于分类,而属于诗人的一种自我追求,“难度写作”也存在“零”的问题。诗人以个人过往成熟作品和整个诗歌体系而建立起一个参照系,驱动自我写作,一方面是需要的,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艰难的,这也会迫使成熟的写作者产生一定的深度焦虑。真正的难度,可能是在于我们疑惑自我并在疑惑中确认自身的悖论的难度。如何让“难度”归零,产生“零”和“一”的互动,由简至繁,从单一再变现出复杂性,其实更加让人期待。
诗依旧是神秘的,诗是什么很难说清楚。沃尔科特说“我从来没有把写诗和祈祷分别开来”,他几乎把写诗等同于祈祷。从我的理解而言,诗更像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一座空中之城、一扇窄门、一条地下通道、一艘潜艇。诗人通过文字连接那些不能连接之物,让各种存在碰撞在一处,将发生和尚未发生的事件都可以折叠到一首诗的狭小空间内,诗意就显现在那里,像重新进入胎盘,回到了“零”,这是一种温和的创造。
其实“零”也是假定的,它只能是心灵的度量衡,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状态,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它在,又不在。它在这个世界的具象显现之一是“孩童”,另外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诗人”。“零”出现在诗人的内心世界,而通过其敏感、直觉、理悟、自我视角、时空意识、实践,体现出对生命察觉,对内部外部世界的认知。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单一的,不是单向度的,有无数隐秘的世界同时并存着。写作也绝对不是单一心灵世界的显现、投射,诗人看到了无限的世界,而通过诗歌重新构建出其空无的形体。诗意封闭在诗人的精神之中,通过语言而逐渐成形,外立于诗人之外,而和诗人又成为一体。
人因为有自由意志,富有创造性,让写作具有了自我赋予的属性。但是当代汉诗的特殊表现是自我赋予是一种“零赋予”。诗人通过文字能够赋予出的仅仅是“本真”,也就是摘掉眼镜用裸眼看世界,通过诗性的重临,深度还原已经被异化的自我、他人,显示生存的真相,并不能在实用的角度添加什么,也并不能改变什么。陈超说“现代诗不是众人皆宜的审美遣兴,而是有意于探讨生存真相的人们的对话与沟通”。这个世界需要文学的心灵去确认。通过诗歌,诗人带着人们重新看见世界,重新确认自我,穿越现实之境直抵精神之境。现代汉诗的完成,对于人本身的生存真相有着强烈的自证味道,人本身的定义在每一次对话和自证过程中都将被一次次改写,这个是诗的属性所决定的。
“零”其实也表现为“超越”。当代汉诗的“超越”是诗歌所共有的,这种“超越”是亘古不变的,不分古今中外的,又具有时代的特点。“超越”赋予诗人一种特权,替万物重新命名,以语言重构出本真的世界。“超越”不可“神化”,但让诗人可以无视很多局限,包括肉体的局限、语言的局限、思维的局限,同时又站在大地之上。
通过“零”,诗人与传统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既是在生成、固化传统,同时也是在解构、推翻传统,既是在生成“现世”,又是在超越“现世”。诗的主体在语言变动、诗性传递中得以确立,命名是一个动态流动的过程,类似于诗意的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