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个人的孤舟与时代的长河
庄莹 张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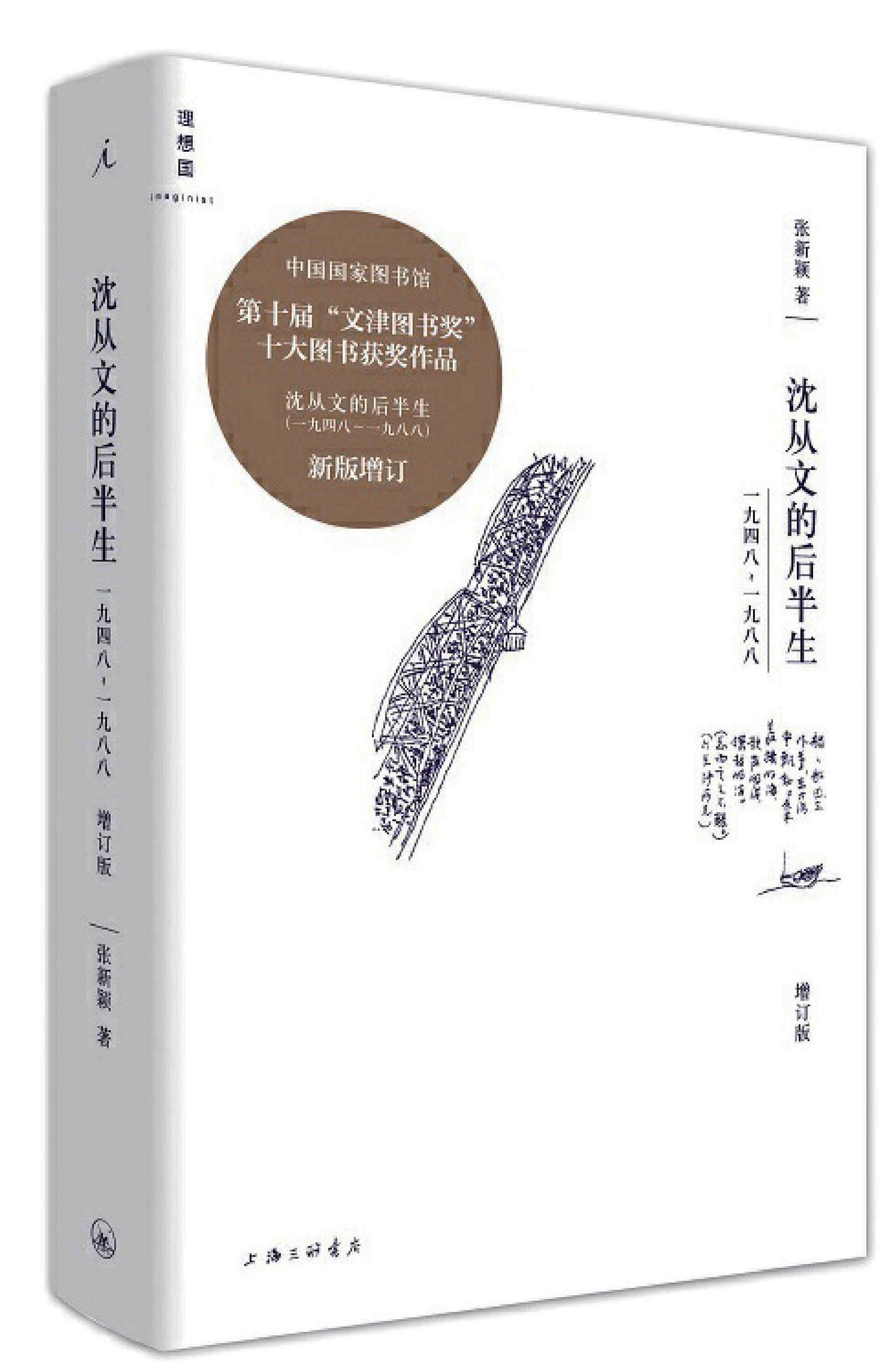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从文在文学史中从被遮蔽的“旧作家”转而被学界发现,甚至成为研究热点。但相关研究较多关注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用“世外桃源”和“风情画”来阐释沈从文小说的风格和特征,他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语意阐释之中,被提炼、缩小、定型、标签化,反而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遮蔽。近十年来,“沈从文热”又从学界扩散到日常读者层面,沈从文带着他的故事和情事出现在各类市场书选题中,成为在媒介环境中传播的“沈从文”。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市场行为,在公众视野中获得充分关注的沈从文,只是前半生的沈从文。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自1997年写出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随后便发表了诸多论文和论著,自认为是“一个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的人”。2014年,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获得第十届文津图书奖。2018年,《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增订版)》于上海三联书店再版增订。
《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出版,将对沈从文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空间,并在社会媒介环境中为公众还原了一个更立体、多元和丰富的沈从文。张新颖并未将沈从文囿于作家、个体、个人经验等传记写作的固有模式,而是通过多层次故事的累加、叠合、融汇,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
时间的开始:个人与时代的张力
《沈从文的后半生》起笔于1948年,落笔在沈从文去世的1988年,这40年时间构成了“沈从文的后半生”。著作没有以常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为界,而是选取了更带有个人性的1948年。时间逻辑的确定,也构成了一如沈从文画作中所描绘的大海中飘摇的艒艒船与不远处歌声的海、锣鼓的海之间呼应又间隔的关系。
传记开篇正是1948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这一年46岁的沈从文也带着张兆和与两个儿子前来。在风雅的霁清轩,沈从文写了篇现实的短文《“中国往何处去?”》,想要为一些问题找寻答案,中国有没有前途?它的出路在哪里?如何挽救它的危机?“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惟有寄希望于青年的觉醒,待有新生的机会。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中国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无可怀疑。于是,传统的写作方式和态度,恐怕都要决心放弃了。“重要处还是从远景来认识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国家明日必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更多方面机会的发展,事无可疑。”
新时代所要求的新文学,不再是沈从文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文学一个必需的前提。然而,文学作品一旦涉及政治,必然被時代左右。沈从文追求的则是文学作品的“年青”。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很年青”,将来还“很年青”。也就是作品不被时代所左右,不受时代的束缚,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脱离作品固有的“姿态”,其“意蕴”能与时代贴合,放在不同背景下,仍能为读者所接受,甚至于常读常新。
沈从文的旧日朋友虽然还在身边,但已经走在了不同的道路上,面对新时代皆有不同的期待。他每天活在精神世界中,如困兽之斗,并通过维持表面的祥和,压抑了情绪的发泄,反倒隔绝了与朋友关联的可能。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诉说没有人理解自己,朋友不再是朋友,家人不再像家人。所有人都跟着新时代的浪潮前进,只有自己游离在新时代之外,离群的苦闷使他踟蹰间不知道他自何处来,又要去向何处。沈从文希望留下余生为新的国家服务,然而社会在新生,自己却好像要在沉默中下沉。面对窄门,从一线渺渺微光中,看到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与他们遥遥相对。
时间不是突然开始的,在大历史的惊雷和新生背后,有个人的艰难选择、恢复和新生。
绝境和逢生:让一艘大而且旧的船作掉头的努力
一艘大而直航向前的船,太旧了,掉头是相当吃力的。
沈从文文学事业陷入绝境,明白当下个人文学写作没有了上升空间,接受“被孤立”的现实之后,他并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转换生命的核心,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基于爱好和兴趣,在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远景之下,投身文物研究工作。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创造另外一种身份。历史文物研究显然可以缓解他精神崩溃的痛苦,工艺美术使他在寂寞的生命中有事可做,同时,也使他愈加清醒。因为历史相当于现实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甚至有些现实是历史的重复。
在当时,历史文物是“过时的”,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也是“过时的”,相同境遇下,不免产生惺惺相惜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历史文物,不只是他的研究对象,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为历史文物工作,似乎也是在为自己奔走呐喊。他“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的‘人’的朴素的心。”拥有“真正的‘人’的朴素的心”的工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没有被时代所接受,无人明白他的珍贵性,这也正是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现状。受时代限制,沈从文选择封笔,但“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视”,他将创作的热情从文学作品转向文物研究,并结合自身的经历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在绝境中发现和创造自己的事业,转身投入文物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之后,他也拥有了恢复文学写作、迎合“主流”的一些机会。譬如,从革命大学毕业后,上级希望沈从文回到作家队伍之中,然而努力调头的“大而且旧的船”仍把握不好时代的“红绿灯”,沈从文放弃了这次机会,选择回博物馆做研究。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显然也是“主流”给沈从文“融入群体”的又一次机会,沈从文期待着把自己的创作和以前的接续起来,但是时间、体力和头脑已然快跟不上他的工作节奏,文物研究的紧迫性和因文学创作而年青的心快速燃烧着他的生命力,四个月的历程后,他依然选择之前的个人道路。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翻越了昏黄的过往和渐渐消弭的希望,又站在路口,屋后的枣树又发了新芽,生活似乎又有了很多的可能性。经过深思熟虑后,沈从文再次选择放弃。他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获得了独属于他个人的自由和荣誉。
个人与时代:著书老去为抒情
个人与他身处的时代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时代的力量摧枯拉朽,个人与时代好像难以构成平等的对话关系,于是只能从个体身上烛照、映射、观看时代的变迁。但沈从文的后半生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他身上有剧烈的自我冲突,由于对国家和时代的热爱,他很想参与其中,但又格格不入,深怀忧惧。他有着剧烈的自我冲突,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特例。正如张新颖所说:“写这本书,我想写的不是沈从文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写的不是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一个典型,我写的不是一个模式的故事,我写的就是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不一样,和他后代的很多人不一样,我就是要写出这个不一样。他是一个不能被放在一个共同的模式里叙述的人。”
对文学创作念念不忘的沈从文为什么一次次地选择放弃,始终执着于历史研究工作?个人与时代能够构成什么样的意义关系?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拯救一个时代的荒芜吗?
沈从文从事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感,他始终站在超越现实的角度,拥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譬如,基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的涉略和繁多的头绪,他在文物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延伸出从未研究过的新领域。
他逐渐明白,不能所有人都重复进行一些相同或类似的工作,必然要有人跳出局限,进行不同的任务,或许不被理解,但在一個新的时代,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跳出来,所有人都识时务的“随波逐流”,反而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作为一名文物研究者,沈从文特别留意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学术同行不理解沈从文,认为他的研究没有价值,甚至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他买来的“废品”。沈从文还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文献和文物互证,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探讨一些文物的“琐碎”,在那个“以为学术不需要考证,只需要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
1973年5月,沈从文完稿《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并正式上交。11月,他的人事关系才正式由五七干校转回中国历史博物馆,相应的户口和供应关系也转回到了北京。在沈从文写给博物馆馆长杨振亚的信中,焦虑且痛心地写到:“馆长,你明白这个十年,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但是,研究状况依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197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促使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研究。4月,沈从文正式报到,职称由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也就彻底结束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关联。
关于《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出版问题,出版单位几经变动,却迟迟不能付印。1980年,沈从文将稿件交至社科院科研局,最终确定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书名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负责人李祖泽到沈从文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拜访,但是家中只有一张藤椅可落座,主客皆推让,不愿独坐,于是两人站在院中畅谈,那天的北京下着大雪,就任由雪花飘落在身上。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从完稿时算起,这部书的出版前后已经经历了曲折的十七年。
《沈从文的后半生》图书封面用的是1957年5月1日在上海的沈从文画的即景图《六点钟所见》,内容是上海外白渡桥上的游行队伍和黄浦江里一只游离的小船。画旁写着“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隐喻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在众生沉迷于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海时,沈从文选择在自己的角落里,做自己的事情,他谓之“不醒”,这也是《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的隐喻和立场,这是一个个人和时代的故事、是绝境和创造力的故事、是生命经验和时间胜利的故事。不同于现代中国启蒙和觉醒的叙事模式,《沈从文的后半生》呈现了个人“新生”的累积和复杂,不是抛弃和转折,而是一点一点萌芽、抉择、生长并重建一个新的自我。
《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是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书写了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并尽可能的直接引述一手资料。于是,在写作中史料丰富,采用几近无一处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的写法,以图书的叙事逻辑为纲,编织、厘清各类文献资料,消弭作者的主观判断,让史料自己说话。《沈从文的后半生》以诗性叙述的语言,呈现了一个“有情”传统中的沈从文。
作者庄莹系青岛科技大学副教授、传播学系主任;张可系青岛科技大学出版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