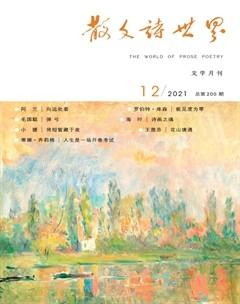秋风引
2021-12-17 18:57
散文诗世界 2021年12期
来不及收拢翅膀,标准的雁阵,坚韧的人字形队列出现不可补救的扭曲。
浓雾翻滚如魔方,有规则地变幻。
镜子里脱困的人,穿过一座又一座爱过的城市,陌生的街巷。
悬浮是一种瘾。
失重的异乡人,习惯了无根的形态。
一支烟的寿命比平时短了一半。父亲躺在刚撂倒的玉米秸上,吞吐星光。
风,一下子就过去了。
乱。
再乱,秋水还是水的形态,不缓不急。
还是望不到头的微澜,旋起的小漩涡儿,下沉内心的柔软。
不安分的鱼,集体跃出水面的刹那,瞬间静止了,将时间定格为悬念。
可以断想,它们只差那么一点儿,如果不赶上这阵风,就能跃入这阵风推开的,生满绿锈的传说中的龙门。
我踮起脚,秋收后的大地尽头,显现村庄的轮廓。
炊烟是老屋挥舞的水袖,极力搭上目光坠落的抛物线。
乱了最好!
鼓荡这阵风的,是正在赶路的雪?还是忘记归途的候鸟机械扇动的翅膀?
稻草人还需要一些雨水和温度。
我知道它在每一个秋天,第一陣仓促的北风里,都会许下一个无望的愿望。
像中年的我,摇摇晃晃。
风头里的刀刃,适时地割断故乡与异乡之间绷到极致的那根线。
莫名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伸手扼住风头,将这城里失色的秋天稍稍吹乱。
猜你喜欢
小小说月刊(2020年7期)2020-07-27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9期)2020-06-08
科教新报(2019年2期)2019-09-10
北方文学(2018年10期)2018-07-12
创新作文·初中版(2016年12期)2017-01-03
中国慈善家(2015年12期)2016-01-04
英语学习·新锐空间(2013年2期)2013-05-23
小小说月刊(2009年6期)2009-11-22
大学(2008年8期)2008-09-01
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08年9期)2008-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