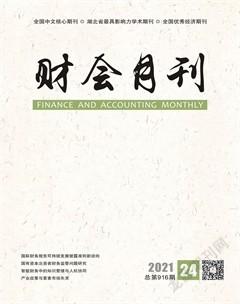公共风险转化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现实路径
徐玉德 李化龙
【摘要】财政承担公共风险诱发的潜在支出义务是形成隐性债务的根源所在。 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源自于私人部门风险公共化后政府作为最后担保人被动承担的支出义务, 以及政府部门主动将债务风险转嫁后私人化的风险再次回流所产生的支出义务。 政府行为特征在公共风险产生与风险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进而表现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典型的隐性债务转化路径。 从风险传播链条异质性角度进一步识别两类代表性路径下引致隐性债务的风险因素, 能够为隐性债务治理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公共风险;隐性债务;或有债务;债务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24-0130-4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 风险扩散呈现出难以预测和跨部门传染等特性, 对独立个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承担着防范化解包括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等在内的各类公共风险的职能。 财政因承担公共风险而诱发的潜在支出义务是形成隐性债务的根源所在。 从风险产生的源头来看, 公共风险既可能来自政府部门主动分散其责任范畴内的风险, 也可能来源于政府对外部风险的最终兜底。 前者源于政府部门内部的公共部门风险私人化后再次回流形成的隐性债务, 其风险传播的典型特征是政府对潜在支出义务的“主动”累积。 后者的风险传播方向则恰恰相反, 公共财政对“大而不倒”企业进行救助等形成的隐性债务本质上是公共财政对公共化的私人部门风险进行的“被动”对冲。 在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 公共风险在风险来源、风险传播与风险分担等环节的驱动因素迥然不同。 从风险传播链条异质性角度识别公共风险转化为隐性债务的现实路径, 能够为隐性债务治理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等发生债务违约诱发“主动型”隐性或有债务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等主体与地方政府“分而不离”成为隐性或有债务最主要的风险来源。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 地方政府由于受到财力制约, 通过组建各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筹集基建投资资金。 2009年中央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实施4万亿元投资刺激政策后, 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和城投债规模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的偿债责任一直未能得到明确划定。 2014年随着《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和新《预算法》的出台, 平台公司融资职能被正式剥离。 法律层面政府承担的或有债务被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范围之内。 随着2021年《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1]15号)的发布, 融资平台公司通过银行体系进行融资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 但在融资平台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债务风险分担制度安排中, 偿债责任与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政府信用与融资平台公司自身信用难以实现彻底分离。 新《预算法》颁布后, 融资平台公司不再享有政府法定的担保责任, 债务风险在法律层面与政府实现隔离。 但融资平台公司经营市场化水平仍然不高, 部分行政层级较低、经营效益较差的平台公司仍大量依赖或明或暗的政府补贴。 法律契约层面的风险隔离并未改变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公司业务层面的风险共担, 造成法律形式和业务实质的分离。
融资平台公司经营现金流与偿债能力不匹配的状况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扭转。 融资平台公司信用风险集中爆发时, 政府为避免形成区域性金融风险而对其进行违约救助可能形成隐性或有债务。 第一, 融资平台公司累积和新增的债务难以在短期内通过盈利改善来偿还, 不得不依靠政府持续的资产注入来将其债务水平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权利与风险承担责任存在不对称性, 地方政府通过资产划拨、资金注入等增强融资平台融资能力, 并通过绑定地方财政信誉、民生责任等达成风险联保, 最终获得超过一般市场化公司的不合理金融势能[1] 。 财政补贴、股权注入等持续投入进一步增强了金融机构对融资平台公司的隐性担保预期。 第二, 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滚动仍依赖于展期与借新还旧, 金融机构对融资平台公司稳定的再融资决策建立在政府潜在的隐性担保承诺基础之上。 在金融机构与融资平台公司双重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 商业银行间的过度竞争进一步加大贷款规模并放松对贷款主体的监督[2] 。 第三, 融资平台公司仅在信托等非标准化融资领域出现个别实质性违约, 但在债券直接融资市场尚未出现不兑付现象, 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仍预期融资平台公司享有政府隐性担保。 考虑到融资平台公司违约对政府和区域内国有企业信用的负面影响, 地方财政通常会实施必要救助。 隐性担保预期下政府代偿债务的潜在支出就可能会形成隐性或有债务。
二、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偿付风险回流引致“主动型”隐性直接与或有债务
地方政府在融资限额外以各类名目举借的违规债务可能由于发生债务风险而转化为政府方潜在的支出义务。 2015年《预算法》修订实施后,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管理为地方政府融资设置了发债“天花板”。 一些地方政府为突破债务融资限制, 采取多种形式违法违规举债。 政府对债务风险的救助等可能形成隐性或有债务。 例如, 部分PPP项目基金以“明股实债”形式融资, 或由与地方政府存在密切关联的国企、融资平台公司等采用ABO(授权—建设—运营)等制度规范不健全的项目融资模式, 如运营收入不足, 债务风险就可能由地方政府承担, 进而形成隐性债务。 又如, 在地方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政府因违规购买服务可能形成隐性直接债务。 再如, 个别专项债发行过程中存在人为高估项目预期收益现象, 债务偿付缺口在风险暴露后不得不由地方财政兜底, 最终可能转化为政府隐性或有债务。 地方政府在运用专项债的过程中, 存在包装适合市场化的融资項目发行专项债的情况, 但是如果以市场化方式筹集的资金到期无法获得充足收益, 在刚性兑付预期下就可能转化为公共财政负担, 使本应由市场承担的风险回流由政府方承担, 进而形成隐性或有债务。
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债务风险因政府预算外融资需求而产生, 地方政府采用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将原本应由政府主体承担的债务风险转化为私人部门风险。 当私人部门无力履行或拒绝履行偿付责任时, 债务风险可能发生外溢。 政府主体对债务契约的介入, 使其不得不参与到债务风险外溢后风险的再分配过程之中。 地方政府违约举债最终的风险承担方式主要可分为政府方主动将违规举债显性化和违规举债风险外部化两类。 对前者而言, 政府违规举债显性化是最为直接的纠偏措施。 政府方承担的全部偿债风险重新纳入未来期间预算从而转化为显性直接债务。 对后者而言, 政府方对是否承担违规举债责任存在较大的主动权, 由于预算并未纳入该部分政府债务, 若政府方不主动承担偿债责任, 则责任归属需要进入法律程序后才能得到最终确认, 政府违规担保偿债风险就可能转移给违规放贷的金融机构。 此时, 违规举债的风险外溢不一定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巨大的风险公共化后果, 但如果政府对同一类型的违规举债都选择不及时承接风险, 就会打破隐性契约基础上的信任平衡, 对金融市场中的政府信用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 因此, 为防止政府信用评级被银行和评级机构下调, 政府方不得不在发生债务风险时主动承接转移给私人部门的风险, 造成对公共财政的支出压力, 从而引致隐性债务。
三、政府救助“大而不倒”企业或对巨灾风险兜底保障责任等引致“被动型”隐性或有债务
1. 政府救助“大而不倒”企业产生“被动型”隐性或有债务。 政府为金融危机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纾困而产生潜在财政支出是最典型的“被动型”隐形或有债务。 政府为保障优秀企业能够渡过难关, 运用财政手段和各类创新工具帮助企业纾困。 例如,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财政部用7000亿美元资金购买花旗银行等美国知名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 此外, 个别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传染, 并衍生出区域性金融风险, 政府被动承担私人风险公共化压力, 就可能产生“被动型”隐性或有债务。 例如, 2017年山东恒丰银行巨额坏账曝光并爆发流动性風险, 地方政府为防止该事件引发的风险进一步扩散成区域性金融风险, 由山东省财政部门通过山东省资产管理公司与中央汇金公司等共同出资1000亿元对恒丰银行进行股权投资。 地方政府在金融风险发生时提供潜在的救助对地方财政形成了巨大的隐性债务压力。
突发性事件对非金融行业大型企业的冲击可能使其经营难以为继, 如放任其破产将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要防止风险产生过于广泛的社会负面影响, 就难以避免地会引致政府公共财政的潜在支出。 例如, 在新冠肺炎冲击下各国出台各类救助计划, 对饱受疫情影响的航空运输业企业给予财政救济等。 就我国而言, 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国有企业发生债务违约风险时, 尽管市场化处置水平也较高, 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往往对当地税收和就业贡献较大, 无论是从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角度出发, 还是从防范企业破产造成过大的衍生风险角度而言, 都可能产生潜在的隐性或有债务支出压力。
2. 财政对巨灾风险兜底保障责任衍生“被动型”隐性或有债务。 突发性巨灾风险是现代风险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典型的巨灾包括地震、海啸、台风、大规模传染病等自然灾害, 也包括恐怖袭击等人为灾难。 巨灾的直接社会危害表现为对农作物、工业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商业楼宇和居民住宅、交通工具以及相关人群造成的大规模集体损失; 间接危害包括由此引发的营业中断、合同违约与法律纠纷等深远的系统性灾害。 为应对巨灾风险, 政府依法履行应急响应、灾难救助以及灾后重建的责任, 财政收入因巨灾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而迅速减少, 财政支出却快速增加。 与此同时, 次生灾害还加剧了公共风险的扩散, 政府在法定救助责任外对个人和企业等的道义救助支出责任也同步骤增。
自愿性巨灾融资机制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政府承担隐性或有债务的责任刚性。 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失巨大且通常难以预测, 单个保险公司难以承担, 而且巨灾保险的保费往往非常高昂, 普通居民或单位可能难以支付。 因此,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 有利于让商业保险行业更好地进入巨灾保险体系,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巨灾保险作为自愿性的举债融资机制,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降低公共财政支出压力。 巨灾保险是制度化对冲或有财政责任的或有资本, 能够有效提升社会和财政治理科学化水平。 在我国, 自愿性巨灾融资机制尚不完善, 巨灾风险治理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 巨灾风险缺少充分的风险缓释措施, 在灾害救助过程中政府财政兜底预期强烈。 政府对私人部门企业和个人主体道义救助责任的增强, 可能诱发潜在的隐性或有债务。
四、社保基金潜在的缺口压力催生“被动型”隐性直接债务
公共财政面临养老和医疗等社会福利基金缺口补足压力而引致的潜在支出可能产生巨额的隐性直接债务。 养老金隐性债务(Implicit Pension Debt)是指养老金计划向在职员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的承诺, 其总值是对两类人群未来收益必须给付金额折现后的现值[3] 。 医保隐性债务主要源自中老年参保人未来缴费总额与医保补偿的差额, 该差额日益扩大, 对地方财政造成潜在支出压力。 我国社保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未能在改革进程中得到完全化解, 形成了潜在的隐性债务问题。 就养老保险基金而言, 为满足当期养老金支出, 不得不挪用新缴费群体个人账户资金, 导致个人账户成为空账, 统筹账户缺口持续扩大。 养老金缺口将不断增大并将最终不可持续[4] 。 社会保障金从“现收现付”转向“统账结合”的过程中, 历史欠账未来极可能转化为政府隐性直接债务。 而且,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社会保险基金转轨与并轨改革的迟滞使社会保障转型累积的历史欠账未能得到充分弥补。 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并轨需补缴的规模庞大的养老金也可能形成隐性直接债务。 李扬等[5] 在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SNA)编制框架为基础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 测算得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政府所应承担的隐性债务总规模高达25万亿元。 陆明涛[6] 测算并轨的改革成本高达9.1万亿元, 如不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转轨成本, 养老金体系将面临严峻挑战。 就医疗保险基金而言, 当前医保基金统筹存在较为突出的层次过低、个别地区收支不平衡的矛盾, 部分地区医保扣除中央财政补贴后的收支差额也逐步上升。 参保人缴费率偏低且生命周期内收支缺口较大, 长期折现后存在巨大的财政支出缺口[7] 。
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冲击与医疗养老体制遗留问题的共同作用下, 社会保险资金缺口带来的政府隐性直接债务问题愈加突出。 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 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矛盾加剧。 我国由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仅用时22年, 老年人口规模增长速度快于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 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 养老金支出迅速增加,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率居高不下。 多数省份养老金支出仍存在的缺口需由地方财政予以补充, 养老金转移支付压力与日俱增。 而“少子化”进程的加速将使人口规模面临断崖式下跌, 全社会抚养比迅速恶化。 1950 ~ 2019 年, 我国总和生育率从6.71下降至1.70, 减少5.01, 同期美、日、英则仅分别减少 1.28、2.08、0.33[8] 。 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 与2019年的1179万相比下降15%[9] 。 未来新出生人口若持续大幅减少, 将对社会保障基金代际平衡造成巨大压力, 新增缴费人口的减少让财政补贴几乎成为唯一的资金来源。 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保障支出的刚性。 与养老基金相类似, 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以后, 医保基金面临收入增长放缓与支出增长迅速的双重困境。 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影响, 医保缴费人数与参保人数的比重将逐步降低, 医保收入增长将持续放缓。 同时, 随着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 人均公共卫生支出快速增加, 医疗保障支出增速不断提高。 戈艳霞和王添翼[10] 对医保可持续性的测算发现, 2026年医保基金将开始出现缺口。 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向医保基金提供潜在补贴所导致的隐性债务问题日渐突显。
五、结论
后工业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种族歧视, 以及局部或突发性的传染性疾病、金融危机等都可能引致潜在的社会灾难[11] 。 经济和社会在风险分担上的制度短板都可能因突发性事件而产生“蝴蝶效应”, 诱发系统性风险。 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巨灾风险保险制度等尚不完善的背景下, 如何构建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长效机制, 有效应对累积性和突发性的经济社会风险, 缓释公共财政对冲公共风险的压力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政府是公共风险的最后担保人, 公共财政是政府对冲公共风险的重要手段。 政府运用公共财政资源应对可能发生的公共风险事件而产生的潜在支出形成了隐性债务[12] 。 在地方政府“主动”向私人部门分散内部风险, 并在风险回流后再次承担风险缓释责任的风险传播链条上,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政府变相违规举债债务风险转化為政府难以避免的支出义务是“主动型”隐性债务的典型现实路径。 在政府因履行公共受托责任而“被动”吸收私人部门风险的风险传播链条上, 政府对“大而不倒”企业的债务风险、巨灾风险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的“兜底”责任是催生“被动型”隐性债务的主要路径。 分类厘清诱发隐性债务的风险因素及其转化路径, 能够为制定隐性债务治理对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尤其对于缓解日益突出的“被动型”隐性债务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徐军伟,毛捷,管星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再认识——基于融资平台公司的精准界定和金融势能的视角[ J].管理世界,2020(9):37 ~ 59.
[2] 江曙霞,罗杰,黄君慈.信贷集中与扩张、软预算约束竞争和银行系统性风险[ J].金融研究,2006(4):40 ~ 48.
[3] 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J].经济研究,2001(5):3 ~ 12+94.
[4] 马骏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 李扬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6] 陆明涛.中国养老金双轨制并轨改革的成本测算[ J].老龄科学研究,2013(7):24 ~ 36.
[7] 宋世斌.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隐性债务和基金运行状况的精算评估[ J].管理世界,2010(8):169 ~ 170.
[8] 陈浩.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R].北京:中国人民银行,2021.
[9] 公安部.二○二○年全国姓名报告[EB/OL]. http://www.gov.cn/fuwu/2021-02/08/content_5585906.htm,2021-02-08.
[10] 戈艳霞,王添翼.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保基金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分析[ J].中国医疗保险,2021(2):20 ~ 25.
[11] 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2] 徐玉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内涵辨析与逻辑溯源[ J].财政研究,2021(9):30 ~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