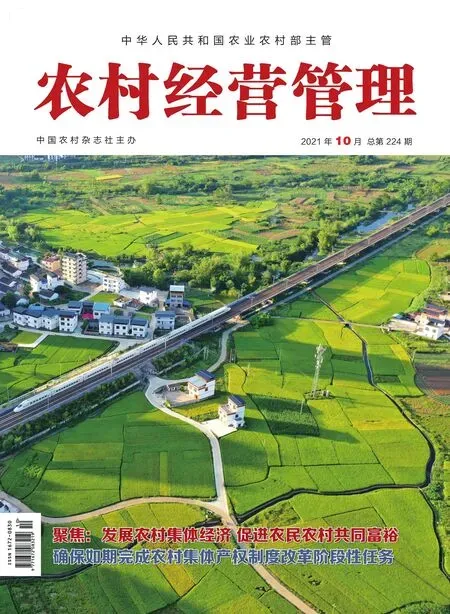现阶段家庭农场联合的主要特征与政策建议
赵翠萍 余 燕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自2014年《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家庭农场开展联合与合作以来,尤其是农业农村部印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明确提出“逐步构建家庭农场协会或联盟体系”,家庭农场及其各类联合组织发展迅速。但总体来看,家庭农场之间的联合还处于无序状态,无论是组织模式还是设立、服务、运行等都不够规范,亟待予以关注和引导。
家庭农场联合的主要特征
联合方式呈多元化态势。目前,家庭农场联合有协会、联盟、合作社、联合会、联合体等多种形式,协会方式出现较早。就联盟形式而言,主要是服务联盟和科技联盟,如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于2015年发起成立家庭农场服务联盟,通过创建区域品牌、联络金融机构等方式为成员提供服务;如山东省德州40名家庭农场主以农科院为依托成立德州家庭农场科技联盟,主要为成员搭建科技信息交流和技术培训平台。以合作社形式的联合在实践中也不少见,如浙江省衢州全旺道米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由全旺镇25家专业种粮家庭农场组建而成。形式多元化是各类组织在初创期的共同特征,类似情况在合作社以及合作社联合社的发展初期都曾经历过。但是,多元化特征一方面说明其发展的活跃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其过渡性。
既有同业联合也有混业联合。同业联合主要是家庭农场之间基于某一主导产品达成的合作,目的主要是统一技术标准、联合采购资料、统一注册商标、共同销售产品等。如河南省济源市的蔬菜制种家庭农场协会,专注于蔬菜制种方面的技术交流与协作;如安徽省定远县蒋集镇的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均为种植葡萄的家庭农场,同业联合往往具有实体性特征,多为区域内联合。混业联合型如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家庭农场服务联盟,将种植、农机、植保、购销甚至技术推广等环节的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吸纳进入联盟,通过拓展服务内容满足成员多样化需求。混业联合多为跨区域,呈现非实体特征。
区域性联合体系正逐步形成。一是县级家庭农场联合组织数量日益增多。比如,截至2020年12月底,河南省加入联盟或协会等各类联合组织的家庭农场数量已近万家,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县市级家庭农场联合组织数量27家。二是省级层面的联合组织纷纷成立,数量逐步增多。如河南、浙江、福建、山东、陕西、湖北、江西、河北等地纷纷成立省级家庭农场联合组织。省级层面的家庭农场联合组织多以协会命名,少数省份是以联合会命名。总体来看,家庭农场联合组织的区域性体系正在形成。
地方政府发挥助推作用。尽管实践中不乏家庭农场自发走向联合的案例,但总体来看,各类家庭农场联合组织组建过程中的政府推动痕迹显著。在设立过程中,政府部门多会扮演“建群者”的角色,为联合组织的设立提供合法性等必要支持和关键资源,甚至会在成员边界、运行规则等方面给予指导。调研发现,多数省份首家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家庭农场联合组织是由地方农业农村部门主导成立,甚至有些地方家庭农场协会的会长也是由公职人员担任。政府积极介入无疑有助于提高组织的发起效率。
现阶段家庭农场联合面临的问题
服务能力整体偏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数联合组织为成员提供的服务停留在简单的农资代买或技术信息交流,难以满足成员在资金融通、品牌共建、产品销售等方面急需的服务需求。二是运营能力较弱,多数联合组织没有网络运维,即便有也缺乏实质效果。三是覆盖范围小。比如,截至2020年12月底,河南全省参与各类区域性联合组织的家庭农场数量为9718个,这意味着全省还有近2/3的家庭农场是独立面对市场的状态。这种情况大体与联合组织缺乏持续运作的内在动力、缺乏有能力有格局的带头人、缺乏完善的运营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有关。
缺乏明确定位。政策鼓励家庭农场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赋予了其更大发展空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概念理解以及实践上的偏差。目前这种偏差导致的一个实际难题是,省级层面的家庭农场联盟难以统领省域内各种形式的基层联合组织。同时,政策允许以多种方式进行联合,令人产生“一合就灵”或者“泛合作”的感觉。因此,长期来看,家庭农场的联合应力避多元化。
缺乏统一的运营指导。首先是来自上级部门的指导缺位。实践中,尽管政府相关部门扮演了“建群者”角色,在联合组织的发起设立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省级联合组织普遍出现较晚,因此所谓上级的协调、监督等指导从一开始是缺位的。其次,从运行监管来看,缺乏统一的管理办法。此外,无论是家庭农场协会还是家庭农场联盟等,区域性联合组织普遍缺乏规范的示范章程。
引导家庭农场有效联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明确引导家庭农场以合作社方式进行联合。首先,从目标来看,家庭农场参与合作的目的是寻求报团取暖、联合应对市场,与合作社宗旨是高度一致的。其次,农民合作社历经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规范制度,相比合作松散的协会、联盟而言,合作社的运作机制更容易被家庭农场普遍接受。此外,从合作社自身发展看,很多发展良好的专业合作社都是始于同业者的联合,家庭农场尤其是同业家庭农场是天然的合作社社员,合作社的发展也有赖于家庭农场这类面向市场的农户。
政府应本着适度原则积极介入。家庭农场自发联合的组织成本极高,而政府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稀缺资源配置能力以及技术服务网络能力。因此,政府应本着适度原则在前期予以推动,突破家庭农场联合“起飞”阶段的难题。从经验来看,政府的作用空间主要体现在宣传、推动设立、立法规范、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部门引导联合组织发起成立后,应遵从市场要求,把后续的运营及时转移给联合组织,由组织内担任相应岗位职责的成员农场主牵头,自我解决面临的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合作。
通过立法等强化顶层设计。当前,家庭农场联合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生事物,顶层设计显得至关重要,应注重三个方面:首先,加快家庭农场立法进程,在明确家庭农场的主体地位、设立登记、补贴融资等扶持政策的同时,对家庭农场的联合进行界定。其次,制定家庭农场联合组织示范章程并给出格式化文本,便于家庭农场联合组织在设立登记、运行服务、清算解散等环节有明确遵循。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省级层面家庭农场联合会(联盟等)成立,应引导地方制定家庭农场联合组织管理办法。
着力培养职业化农民队伍。
农民的职业化,对家庭农场以及家庭农场的联合发展至关重要,应前瞻性地建立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稳定培养机制。首先,应出台相关政策,激励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取得专业技术职称、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其次,应通过政策激励,把传统农民、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等潜在群体纳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体系。此外,应强化“互联网+”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对现代农业组织运行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