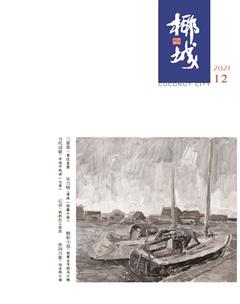太阳、蜜蜂与少年
作者简介:剑鸿,男,1977年生,江西新干人。作品散见于《岁月》 《奔流》 《牡丹》 《散文世界》 《鄱阳湖文学》 《内蒙古日报》等报刊杂志。
一
二十几年前的村子,大致由以下元素构成——
一条小渠,两口池塘,三排瓦屋,四棵樟树,茂密的桔林,土砖砌成的低矮茅厕,房前屋后零星的苦枣树、桃树和柿子树,村子外围是祖辈们长满青草的坟茔,还有站在小巷里和桔树下抬头可以望见的天空。
这些元素,掩映在那些往日时光所构成的黑白影像里,虽然单调、略显简陋,却无比和谐。以实用的眼光来看,它们都是农村生活的必需之物,迎合着人们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各项活动、各个阶段的基本需求,不可或缺,地位平等。你不能说哪种元素更为突出或者更为重要,樟树和桔林相互衬托,土地和天空同样辽阔,瓦屋和坟茔都是栖居所。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物,因为超出了村子的地理范围,也不属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或者只是作为短暂的存在,所以我没有将其视为村子的固有部分,比如在村子外无声无息流过的古老赣江,春季里开满田野的野花,飞来飞去的燕子、麻雀和蝴蝶,晚上才有的月亮和白天才有的太阳,还有养蜂人安放在村子里的蜂箱,到处忙着采蜜的蜜蜂。
村子里和我同一年出生的家伙,有二十多个。和我关系最密切的,要数大眼和矮子。我们当中,除了少数几个是在乡镇医院出生外,大多数是由大队唯一的接生婆接生的。在后来的游戏阵营中,由此而划分了医院生的和家里生的两派,医院生的这一方人数较少,所以每每身上所中的土块、“枪子”也就更多。这个接生婆我见过,穿着单开边的蓝色褂子,头发斑白,梳理得十分齐整,面目和善,为人热情,尤其是看到小孩子,不但能叫出名字,还会摸着头问这问那,好像哪个都是她的亲孙子。有几次,我和母亲去赶集,她微笑着和母亲聊天,用枯瘦的手抚摸着我的头,一个劲地和母亲说我出生时的情况,什么危险啊、紧张啊、太阳老高啊,就长这么大了,眼神泛着光彩。我听着心里怪怪的,似乎看到自己光着身子来到世界的样子。所以,我总躲在母亲身后,露出半个脸。
这个接生婆十几年前去世,母亲曾远远给我指过她的坟茔。
按照写在一张红纸上的出生纪录和接生婆的说法,我是中午前后生的,那时太阳温和地照着整个村子,枝头的桔子红得正浓。据母亲回忆,我在襁褓中的时候,每到天黑就开始哭,哭过晚饭,哭过深夜,哭过鸡叫一遍、二遍、三遍,一直到太阳升起。母亲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带着一些神秘的味道,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哭的孩子,好像我和太阳天然就有某种联系,以致于我自己也觉得和太阳关系不同一般。
第一次对太阳产生深刻印象,是在村子中央小池塘的岸边。当时,我和大眼、矮子一起用泥巴堆城堡。我最先发现了一把黄泥,可大眼说是他发现的,我说又没写你的名字,怎么是你的。大眼就来抢,我手一挥,一块黄泥就到了大眼嘴里,同时我的眼前一暗,眼睛也被一块泥蒙住了。我们一起哭。哭到眼泪把泥冲开一道口子的时候,我刚好看到沉在水底的太阳,一闪一闪的,照到我们脸上。我把手里握得发热的一团泥扔进水中,波纹荡漾,太阳顷刻就老了,满脸的皱纹,似乎在微笑,很像那个接生婆的脸。
二
太阳不会老,老的只有时光和面容。
这是我熟悉太阳多年之后才有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不但知道太阳是金黄的、伟大的,而且知道它是太阳系的国王,统治着地球和很多星體,它君临天下,光耀万物,目光一瞟,便将时光劈成白天和黑夜,将地上的事物照得辉煌,将无边的黑暗丢给角落。我还知道,在阳光的照耀下,花朵才会绽开美丽的笑颜,高远的山峰才会露出青翠的面庞。太阳底下,城市和乡村像巨大的蜂房,每天都有蜜蜂从里面飞进飞出,到处嗡嗡地采蜜。一些蜜蜂在飞行的路上,坠落花丛,跌落尘埃里,连同采集的蜜糖,一齐消失……
我也是一只蜜蜂,从长满庄稼的农村,飞到长满楼房的城市,在太阳下跑来跑去,和儿时所见的蜜蜂一样。
春天,温和的风吹过田野,唤醒一地的庄稼和野草,瓦楞上方的天空澄净,阳光灿烂。我和大眼、矮子经常向着村外跑去,远处是一道弧线,那些茂密的庄稼、河流的堤堰、起伏的山影、村子的脊梁,就像一道道篱笆,阻挡着我们的视野。我们鼓起勇气朝着篱笆奔去,每次翻过一道土坡,或者冲出一片桔林,都会沮丧地发现篱笆之外,还有很多道更大更远的篱笆。很多次,我们试图突破一道从来没有接近的篱笆,使劲地往前跑,但到了中途,我们就会犹豫,望望前面,又望望家的方向。我们的村子在身后也成了一道篱笆。再往前走,我们就会害怕,怕迷失了回家的方向,怕听不到姆妈叫我们吃饭的喊声。
于是,我们回头,朝着家的方向猛跑,地上的坎坷似乎也平坦了许多。田野平静,庄稼亲切,泥土松软,赤脚踩踏的脚印在土地上形成几条细细的长线,长线的两旁,鲜花正在盛开。
经过一块高产油菜地的时候,一只野兔从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跑出来,一头扎进油菜地。大眼手疾眼快,哧溜一下顺着兔子的背影钻进了油菜花丛,和兔子一样快。我站在原地,听见油菜地里发出一阵簌簌的声响,从地的这头到那头,以近似船舷分开水面的速度,菜花跟着一阵摇动。一条灰影飞快跑远,大眼披着一身的花粉从地里爬了出来,挥动的手势形成一道斑驳的光影。他遗憾地看着远处的灰影,气喘吁吁。那一刻,我知道大眼失去的不仅是一只兔子,还有美味的兔子肉和别人艳羡的眼光。
我不得不说,在这方面,我是相当佩服大眼的。这是我和大眼的区别,他善于从事物的内部和本身去寻找乐趣,喜欢钻菜地追兔子,喜欢挖地洞捉蛇,喜欢上树掏鸟窝,喜欢满身泥污地到沟渠里捉鳖。为此,他家的厨房经常飘出不同于别人家的香气。我则喜欢从事物的外围和上方去观察,像蜜蜂飞抵花朵一样,去欣赏事物的轮廓和色彩。比如,在大眼追兔子的时候,我正注目那些摇动的油菜花。它们有着太阳般金黄的颜色。当我拿着面庞靠近花瓣的时候,感觉自己正在靠近一个小小的太阳,温热,迷人而芬芳。
大眼后来在路上说,如果你在前面挡,我们就可以抓到那只兔子了。我说,也抓不到的。他说,你没抓,怎么知道抓不到。我说,你不会比兔子更快的,要是你家的狗还差不多。
三
在认识蜜蜂和兔子之前,和我们最亲密的是蚂蚁。
蚂蚁们似乎总在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出来活动,而且总像大人一样忙忙碌碌。尤其在我们哭得泪眼蒙眬的时候,它们在地上的身影比平时更加清晰。慢慢地,我们发现,透过眼泪,世界会有另外一种模样。于是,噙着眼泪观察太阳和蚂蚁,成为我们的一种游戏。大人们上工,我和大眼、矮子就围着一群蚂蚁打发时光。我们坐在门槛上啃红薯,蚂蚁跑过来围着红薯皮打转。它们从角落里的洞穴爬出,煞有介事地分头忙碌。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充当蚂蚁的麻烦制造者,用树枝挑动它们,用泥巴阻挡它们的道路,用尿液淹没它们的巢穴,然后看着它们抬着一只死去的苍蝇或虫子,像村里的八仙抬着一口棺材,热热闹闹地没入巢穴。
蜜蜂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对蚂蚁的兴趣。
蜜蜂是村里的养蜂人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至于是什么地方,大人们也说不清,有人说是内蒙古,有人说是北方,还有人说是四季开花的地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地方的地里可以长出我们从未吃过的玉米。矮子的伯伯是我们全村为数不多的几个养蜂人之一。他常年在外,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像一个客人一样回到村子,送一些金黄的玉米给左邻右舍。也不记得是哪一年的春天,矮子的伯伯将整箱整箱的蜜蜂运了回来,摆在桔林的外围。从此就再也没有出去过,矮子有一个拉屎经常拉到裤子里的小堂弟,就是那一年出生的。
在我们眼里,矮子的伯伯简直是一个英雄,令我们崇拜,主要的原因不是可以吃到他的玉米,而是他根本不怕蜜蜂。桔树花开的时候,他经常弯着腰在蜂箱边忙个不停,只需要戴一顶蒙着面纱的斗笠,光着胳膊,就可以直接打开蜂箱,提起一块块布满蜂巢的木架子,朝着密密麻麻的蜜蜂喷射白糖水。我们站在很远的地方,看他站在蜜蜂的包围圈里,像一个巨人。
后来发生的事情,损害了我们对养蜂人的崇拜之情。有一年春天,他竟把几只蜂箱放到上学必经的油菜地里。从此,每次上学和放学,我们都必须小心翼翼地穿越蜜蜂的封锁,胆小的同学干脆绕道走。但我和大眼、矮子还是坚持走这条路,这不但可以证明胆量,也是在女同学面前可以自豪的理由。尽管如此,每次走到蜂箱的地方,我们都好像怀揣着一只兔子,心里砰砰直跳,不再追打,放慢脚步,尽量小心安全地通过。有一次,一只蜜蜂飞到大眼的脸上,大眼连忙用手赶,结果他的眼皮被蛰了一下,眼睛肿得像包子,一个星期才消去。这个星期里,大眼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眼。
对大眼的取笑还没有结束。不久,矮子也被蜜蜂蛰到了,头上肿起两个老大的包。我们开始将话头从大眼身上转到矮子身上,说他是三头哪吒,只是没有六臂,也没有乾坤圈和风火轮。我被蛰的那次,正走在路上想如果有哪吒的风火轮就不必怕蜜蜂了,忽然听到耳边嗡嗡响。我吓得赶紧跑,但跑得越快,似乎蜜蜂追得也越快,一直跟在后脑勺。我回手一撩,就感到手指头一阵刺痛,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不得不改变握笔姿势,作业本上的字也歪歪扭扭,像一堆虫子。
于是,我们开始酝酿一次报复行动,想给这些蜜蜂一点颜色瞧瞧。矮子说,咱们撒尿淹死它们。大眼坚决反对,说撒尿会被蜜蜂蛰到小鸡鸡的。我想也是,就提出用泥巴封住蜜蜂的进口,让它们闷死在蜂箱里。我们从附近的沟渠中掏来一把泥,趁着夜色将蜂箱的小口封住,我放风,矮子协助,大眼执行,完成之后,飞快地溜走了。第二天,我们经过的时候,发现堵住的地方竟然被蜜蜂钻了一个洞,它们依旧悠然自得地进进出出。我们的报复行动,就此宣告破产。
那个春天,我们都感受到了来自蜜蜂的疼痛。
四
事实证明,这种疼痛只是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谁也不会去想,长大之后,还会有各式各样的疼痛,人生其实是一条挂满疼痛的荆棘条。
有一年夏天,中午的太阳照得整个村子都发蔫,我们却精神抖擞地游荡在桃树和苦枣树下,举着长长的扎着网兜的细竹竿到处捕知了,目的是为了晚上油炸知了。经过一棵高大的苦枣树时,我发现一个鸟窝。笔直的树杆下放着几只蜂箱,我努力避开蜜蜂的干扰,試着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大眼不屑地说,看我的,然后像猴子一样上了树,掏出鸟蛋放在口袋里,得意洋洋地做了个鬼脸,便顺着树干往下爬。快着地的时候,大眼抱着树杆,想将脚踩在蜂箱上下来,伸了几次腿,总是差一截。然后,我看到他的脸憋得通红,手一松,从树上掉下来,脚踩在蜂箱,人和蜂箱一起翻倒。受惊的蜜蜂像雾一样飘散开来,我们飞快地逃开,大眼还来不及爬起,就在蜜蜂的包围中像鬼一样嚎叫。
下午再看到大眼的时候,我们已经认不出他了,他满脸都是红肿的包,包上的泪痕还没有干。
这次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蜜蜂的态度。因为当大眼的妈妈带着他去向养蜂人讨公道时,不但得到了几勺蜜糖的弥补,似乎还得到了对付蜜蜂的秘籍。看到大眼一勺一勺地喝着蜜糖水,我们不断抿着嘴唇垂涎欲滴。接下来的日子里,大眼的表现也让我们感到惊奇。我们原本以为他再也不敢走先前那条路了,可他不但依旧走,而且每次都走在最前面。只是,神态有点不同,悠然自得,像没事一样。在我们的一再催问下,大眼才将养蜂人的秘籍公之于众,那是一个有关蜜蜂的世界,那里有蜂王、雄峰和工蜂,有和人一样的分工,有蜜蜂的原则和坚守,也有无奈和死亡。末了,他还睁着大眼说,蜜蜂是不会主动蛰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蛰了人之后的蜜蜂自己也会死掉。
在此之前,我们的确没有想到,一只小小的蜜蜂在给人以疼痛的同时,竟会付出死亡的代价。侵害与被侵害,居然完全颠倒过来。随着蜜蜂世界的打开,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和敌视蜜蜂,而是带着一种难以说清的同情和理解,当它们飞临额头,我们不再惶恐和紧张,而是心怀怜悯地去欣赏它们震动的羽翼、飞翔的姿势,甚至去体会它们在花间忙碌的心情。归根结底,在疼痛的教导下,我们和蜜蜂逐渐实现了和睦相处,彼此不再伤害。
当我们随手就可以抓一只蜜蜂在手掌把玩的时候,我们忽然感觉自己长大了,开始学会走近其他生命,看到更多未知的世界。我们看到,在太阳被乌云遮住的阴雨天里,蜜蜂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在采蜜的途中,蜜蜂会在疲惫中掉落泥水,尤其是在秋天,许多蜜蜂的尸体会跌落在它们曾经的家门口。那时,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过苍茫的田野。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追着蜜蜂飞行的轨迹,跑出村庄,跑向田野,直到有一天,我们大胆地冲破村外一道道的篱笆,跑向更远的世界,走向各自的太阳和花朵,然后在广袤的时空里彼此失去消息。
离开村子以后,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看到大眼了。据说,他先是到了一个很远的城市,后来又跟着一个女人入赘到了更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远方的大眼会不会偶尔记起我。如果会,在他的描述里,关于我的信息会有多少,会不会超过他少年时对一只蜜蜂的了解。不过,我相信而且希望,他会和我一样记得那个朴素的村庄、那时的太阳和蜜蜂,还有那些曾经的欢笑和疼痛。这样,我们浮萍一样的身影站在大地上才不至于来去两茫茫。
《椰城》杂志涨价通知
因纸张、印刷、人工等成本大幅增加,从2022年开始,《椰城》杂志定价将由每期10元改为15元,敬请理解和支持!
《椰城》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