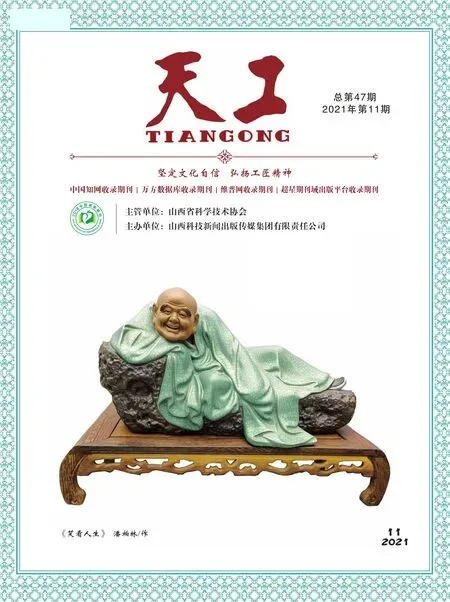浅析河南非遗洛宁竹编的活态传承
蔡玉硕 黄晴晴 朱蔚君
河南大学美术学院
豫西山区“绿竹之乡”——洛宁地处洛河中上游,当地的竹编历史悠久,起源于传统农耕社会,在社会生产及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而“竹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早已伴随着先民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文化活动,凝结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竹制生活器物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风俗和文化景观,凝聚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进入工业社会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技艺逐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传承的文化语境,在物质丰裕的当代社会,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物质产品有了更高的期待和更多元化的需求。洛宁竹编由百姓日常的手工技艺产品逐渐发展为传统手工艺品,再到今日的“非遗”身份,边缘化已成为其毋庸置疑的存在方式。“非遗”保护政策的实质就是文化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一种人为介入,虽然“非遗”保护是社会各界早已达成的共识,但在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的大时代背景下,非遗究竟要如何传承和发展始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一、洛宁竹编概述
洛宁县位于河南西部伏牛山系一带,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受洛河水的滋养,洛宁的竹子生长在北纬35°附近,栽植历史有4000余年,当地林业发展兴盛,是世界上纬度最高的竹林之一,也被称作“北国竹乡”。洛宁淡竹节长、壁薄、柔韧且富有弹性,但竹节较短,主要用于家具、农业工具的制作。其与南方竹编的不同之处在于南方竹编色彩清新雅致,精编细织,多以实用的工艺品为主,如四川瓷胎竹编、东阳竹编屏风以及梁平竹丝画帘等。而洛宁竹编则带有浓厚的中原地域特色,色彩古朴,多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产品造型大方典雅。竹编的编制方法有很多,基本可分为八大类:人字编、四眼编、六眼编、八眼编、绳结编、圆形编、菊花编、上条下丝,这些编法组合起来又会衍生出难以计数的编织方法。据民国四年(1915)《永宁县志》记载:“永宁制竹器者甚众,各以类分,艺不相兼,四方员贩咸来获取。”①洛宁县古称“永宁”,永宁这里制作竹器的人很多,以制作竹器的种类来划分,制作技艺各不相同,周边的商贩都来这里取货。传统的竹编生产以农户为生产单位,或自发地形成松散的联合体,不同的竹器由不同生产单位承担,各有分工,将完成的竹制品放到市面上统一进行售卖。
洛宁竹产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原竹贸易向简竹贸易、精细编织工艺向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竹编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发展,《诗经小雅》中的“上菀下簟,乃安斯寝”②夜里燥热,有一张菀簟(指草、竹混编的凉席),才可以安睡。是关于竹编产品最早的记载,其功能由最初单一存放食物扩大到符合用户的多种需求。唐代,洛阳作为当时的都城,皇宫纱灯的“筋骨”多用洛宁竹子制成。至明清时期,民间竹编技艺由简易编织转向技法成熟的工艺制作,编织方法更趋多样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当地成立了竹编生产合作社,扩大了生产并出口。而后洛宁竹编迎来了转折点,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当地政府为了促进竹编手艺的发展,曾邀请日本竹编专家八木泽到洛宁传授竹编技艺。八木泽曾为日本皇室编制竹工艺品,根据其教授的技艺所编制出来的产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感和艺术性,但由于不符合当地居民的需求,八木泽先生教授的竹编技艺后来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也未能给洛宁竹编带来转型发展。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洛宁竹编产业迎来严峻挑战:一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竹子质量、产量下降;二是新生代群体登上消费舞台,他们追求时尚潮流和个性化,可选择的功能替代品增多,加之竹编产品类别少、易腐蚀等弊端,因此,更具现代设计感的工业产品逐渐占据了市场。而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大部分从业者被迫转行另谋出路,竹编技艺逐渐濒临失传的境地。
二、洛宁竹编传承问题分析
(一)技艺传承遭遇发展瓶颈
据洛宁竹编传承人谱系记载,洛宁竹编的传承是从19世纪30年代第一代传承人张振东开始的,距今已有一百九十余年的历史。师徒相授、父子相授等是民间手工技艺最传统的传承方式。然而,如今竹编技艺已经很难吸引青年一代的兴趣,愿意主动学习传承竹编技艺的年轻学徒少之又少,加之现存的传承人年龄普遍偏高,故而无论是家传或是师传,竹编传承均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
(二)传播、销售体系亟待完善
长久以来,洛宁竹编的传播主要依靠竹编艺人在民间小范围地推广,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系统介绍竹编技艺和文化的文献和媒体寥寥,可供受众了解洛宁竹编的资料十分有限。“以人为核心”是非遗文化传承的宗旨,文化终究是要回归到群众生活。因此,如何利用自媒体平台提升洛宁竹编的知名度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次,洛宁竹编的销售渠道通常是客户定制、民间竹编老艺人零售或托人代卖,这种现象折射出当下竹编销售群体相对“被动”的市场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竹编产品的发展空间,亟须构建洛宁竹编新的传播与销售体系。
(三)消费市场萎缩严重
竹编产品种类少、技术含量低,在品类的丰富性,产品的耐用性、功能性、艺术性等方面的缺失使得竹编制品的市场萎缩严重,批量化生产的工业产品已然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优势。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竹艺传承人锐减。面临如此困境,借助科学的市场策略将竹编技艺转化为文化资本,提升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是洛宁竹编重新掌握市场主动权的关键。
(四)产品创新乏力
传统洛宁竹编产品类型以竹篮、簸箩等生活器具为主,多是一些小型的生活实用器物,其传承虽历经数百年,但依然保有竹文化的原始特征和物貌,这既是其传承之所长,也是其发展之所短。为了占据市场,产品制造者在造型、功能、美感等方面都力求不断创新,但洛宁竹编普遍存在造型保守、功能单一、时尚不足等问题。其实,活态传承的关键就是“活”字,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动态变化的传承模式、传播体系。基于此,结合当代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竹编产品在保持原有产品类型的基础上,必须在造型、功能、美感、内涵等层面进行升级,通过新型竹编产品的研发逐渐开拓市场。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洛宁竹编活态传承发展策略
(一)洛宁竹编“活态化”传承的必要性
一种传统手工艺技术能够在历史进程中保持、延续和认同,意味着其中存在着某种持续而稳定的要素,这取决于其自身的内部动力,而不是寄托于以往文化生态的理想化归复。乡民文化生态诞生出了非遗文化,这看似与现代工业大都市生活格格不入,然而现代都市生态正在转向“后大都市”①城市学家索亚认为,在“后大都市”中,不同文化有可能在分形( fractal) 并置的空间中形成各自的生态壁龛,通过交流和分享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这意味着文化的多元化,能够活态传承的非遗文化将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洛宁竹编活态传承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工业流水线所生产出来的批量产品相比,传统手工艺品是依托于“民”本身,立足于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及民族文化上的,因其与民众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因此也是非遗文化中最具活性、最具生命力的种类。在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当代社会,在原有材料和工艺独特性、民族性的基础上融合时尚文化理念创新洛宁竹编产品是传承发展的前提。
第二,“活态”一词蕴含着民俗生态的葆有和绵延,其概念的提出具有自发自觉意义上的保护。非遗的保护工作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操作形式,一是记录、封存、收藏,即档案式管理研究,常见的是建立博物馆和运用文字、影像等进行记录;二是衍生、开发、传承,即开放式活态保护发展,使其以新的形式重新生长。虽然对非遗文化进行立档和保存的博物馆式的遗产保护有其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经历过工业时代的人类在走进信息时代后愈发表现出对“慢生活”“传统手工”无比眷恋的精神需求,因此,如何让这些传统手工技艺仍能在信息时代为人们提供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服务是洛宁竹编产品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过去,洛宁竹编是为使用者提供方便的日常器具,或具有审美性、观赏性的工艺品,是手工艺人的谋生之计,但在当代社会,洛宁竹编在继承传统功能的基础上早已演化为河洛文化民间生活习俗中最具集体记忆特征的文化产品。借助理念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这种负载着中原百姓情感与文化认同的竹编产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定会寻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洛宁竹编“活态化”传承路径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洛宁竹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迎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机会。结合洛宁竹编传承现状,制定新的传承机制,实现其活态传承需要全新的传承理念和方式,更需要政府、传承人、民间组织、设计师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1.重塑非遗生存空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系列关于非遗保护的政策中,“社区”(community)一词被赋予重要的意义。虽然因语境不同“社区”的概念很难被界定,但一般指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非遗项目实施和传承的人,构建具有活力的非遗社区,建立手工艺人、艺术家、场地、群众之间相互交流的多维度空间,旨在打造地域、文化、艺术、大众生活及经济共荣共生的模式,以符合文化传承内在规律和现代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例如,景德镇老鸭滩艺术区一直是景德镇进行陶瓷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社区,除了专门进行陶瓷制作的窑场向外产出精美的陶瓷产品外,还有许多艺术家、设计师以及高校学生进行考察和创作,体现了社区网络与文化生活的融合,这种模式可以作为洛宁县发展与构建非遗社区的有效范本。洛宁县承载着深厚的竹编文化,是竹编工艺充满生命力的物质与文化载体,在遵循社区可持续发展和整体性、互动性、共融共生等理念下,积极构建洛宁县中原竹编文化非遗社区,使手工艺人和居民作为同一社区的成员,面向大众开放,建立传统技艺、艺术家、手工艺者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纽带,产生良性互动,使洛宁竹编获得更多人的认同。
2.构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体系
洛宁竹编传承人是竹编艺术实现活态传承的主体,也是保证竹编文化长久延续传承的基石。目前,洛宁竹编最具代表性的传承人主要有张永杰、张江文等,但鲜有年轻人愿意投身竹编事业。因此,如何吸引和积极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是解决“活态传承”问题的关键。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学习竹编文化,将竹编的内涵和价值辐射至更多的年轻人,提高他们传承竹编文化的积极性;借助更加丰富的培养方式,譬如借助洛宁旅游资源同步开发洛宁竹编文化体验项目;积极申报国家艺术基金培训项目,以寻求更大力度的支持;举办洛宁竹编非遗沙龙活动、洛宁创新竹编产品博览会、洛宁竹编创新设计大赛、非遗大师进校园活动等。例如2019年,浙江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举办了“竹编工艺文创设计人才培养”结项成果展,学员们在传统竹编工艺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富现代时尚感的竹编作品(如图1)。不仅开阔与丰富了非遗传承人的眼界与学识,更通过高校师生与非遗传承人的良性学习互动,促使非遗文化和高校学科建设协同发展。201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实施方案》正式印发。这些针对非遗传承人开展的培训计划的成功实施可以反映出当下中国非遗传承人积极传习的活跃局面。对于洛宁竹编的传承而言,则需要制定更细化的、可行的实施方案,逐步形成完备的竹编人才培养模式,以确保洛宁竹编技艺的传承发展。

图1 提灯 张立/作
3.创新竹编产品
(1)文旅融合焕发古竹新生
文化和旅游向来都是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旅游动态,旅游为文化提供重要的发展平台,二者之间天然的耦合性在新时代下催生出文旅融合的新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向。洛宁竹编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从旅游市场开发的角度切入对其进行文化衍生品的开发,刺激大众旅游衍生消费,不仅切合市场的发展需求,也可以借助市场的刺激持续不断地对传统竹编文化产品进行内部升级。例如,可以尝试实施竹编产业集群的战略,由竹编传承人在洛宁旅游景区打造集参观学习、创作体验、制作销售于一体的竹艺园区,推动竹编及其衍生品回归生活。当人们普遍认为竹编不是曲高和寡的手工艺产品时,走入寻常百姓生活的竹编制品自然也会重新获得消费市场的认可。同时,竹编文化产业与洛宁的旅游市场深度融合也可推动竹编非遗技艺转化成文化资本,旅游市场也将成为传承竹编文化的载体,如此,文化产业与旅游市场将实现双向带动,竹编的传承和旅游业的发展之间自会形成良性的“活态化”循环机制。
(2)创新技术赋能传统竹编
创新是信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国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传统竹编的复兴亦要借助创新技术的力量打造全新的文化特色。在此方面,互联网、数字媒体等新型技术在传播路径和技术力量方面可为传统竹编拓宽活态传承的途径和空间。例如,洛宁竹编既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传播其文化故事,也可以拓宽其销售渠道;借助数字技术的系统化、图文化处理和存储竹编艺术的信息资料,借助3D打印等前沿加工方式制作竹制工艺品,这些技术的变革可加强竹编的动态传播和智能化保护。2018年,由浙江理工大学一批学生设计的“线象——研究基于传统竹编的3D参数化打印产品”(如图2)曾荣获中国智造设计大奖之设计先临专项奖,他们将竹编图案进行参数化编程设计、进行3D技术打印,并通过网络共享平台为人们搭建起交流和学习竹编文化的平台,浙江理工大学团队成功借助科技的力量达成竹编的现代转型,实现了数字化竹编类产品的柔性化创作。可以说,借助技术进行产品升级是竹编产品重获市场竞争力的内在驱动力,当然,高新技术注入竹编工艺并非竹工艺与科技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深度融合。

图2 线象——研究基于传统竹编的3D参数化打印产品 浙江理工大学团队/作
(3)品牌构建助推竹编传承
著名营销实战专家刘永炬说:“现代的生存是品牌式生存,现代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是品牌行销的竞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牌战略是市场竞争的利器。例如,山东潍坊风筝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整体推出并完成了国际品牌的塑造,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并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洛宁竹编的活态传承更须借助品牌的力量呼应市场需求,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推广手段,展示洛宁竹编独特的品牌文化,以唤起消费群体中意见领袖的关注和青睐,激发其品牌传播的热情,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竹编产品的创新研发。长远来看,竹编文化结合品牌构建是对文化活态传承的一种延展,通过塑品牌—创产品—拓市场积极打造良好的洛宁竹编品牌形象,提升知名度,创研竹编文化创意衍生品,打开市场,提振从业者信心,推动洛宁竹编重新回归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活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