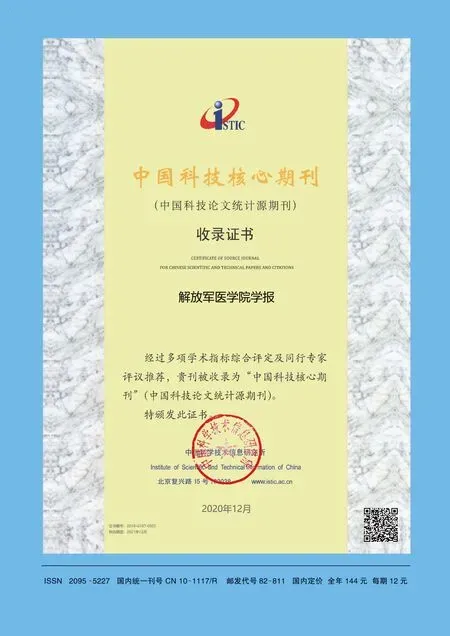肺类器官
——研究人类肺部发育和疾病的新途径
杨天立,王向东,白 楠,董柳含,车皓月,蔡 芸 解放军总医院 医疗保障中心,药剂科,药物临床研究室,北京 00853; 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院,北京 00853
肺是由一个高度分支的管道系统组成的复杂器官,能够参与各种重要的生理过程,包括气体交换和免疫防御。肺的发育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过程,任何阶段的失败/缺陷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先天性疾病甚至死亡。在成人肺内环境稳定的情况下,细胞更新率通常很低。现有的呼吸道祖细胞处于静止状态,而这些祖细胞在应对各种损伤时具有增殖和分化为一种或多种细胞的能力[1]。这种能力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虽然目前部分动物模型能够用来研究肺的发生和发病机制,但种属差异性却限制了许多试图阐明人类肺特性和发育的研究。目前,以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C)和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C)为主的人类多能干细胞(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hPSC)最常被用于体外研究人的肺部生理学和病理学[2]。3D体外模型被认为是最接近实际器官的模型,因此也被称为“类器官”,通常具有与原生器官相似的结构组织、来自多个胚层的细胞类型以及多个细胞谱系[3]。近年来,类器官也逐渐成为研究体外发育过程、组织内稳态和病理状况的复杂生理学模型[4]。人类类器官能够进行人类出生缺陷、人类特异性病原体以及临床试验前对试验药物进行疗效筛选等研究。同时在人类肺中干/祖细胞的特性研究,寻找哮喘和肺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CF)等疾病的新疗法,以及内源性修复在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肺气肿、家族性和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和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syndrome,BOS)等疾病中作用的研究方面,肺类器官也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5-6]。本文着重介绍肺类器官的主要类别及研究现状、肺类器官的培养过程、肺类器官技术的独特应用、肺类器 官培养的主要局限。
1 肺类器官的主要来源及研究现状
成人肺包括近端和远端两个区域,气管、支气管和细支气管构成传导区(气道),由Club细胞、杯状细胞、纤毛细胞、基底细胞和神经内分泌细胞组成,通过黏膜纤毛活动排出异物和病原体,有助于湿润空气和保护肺部。进行气体交换的呼吸区(肺泡)由Ⅰ型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1 and type 2,AT1 and AT2 cells)以及相关血管系统组成。肺类器官则主要由两种来源的细胞产生——从成熟肺组织分离的上皮干/祖细胞[7]和人类多能干细胞[8-10],前者包括基底祖细 胞、气道分泌细胞和AT2细胞。
1.1 基底祖细胞 基底细胞排列在人的大部分气道和小鼠的主支气管中,紧贴基底层,不延伸到管腔[1]。基底细胞特异表达的基因包括编码转录因子Trp63、细胞角蛋白Krt5、整合素α6(integrin alpha 6,Itga6)、平足蛋白(podoplanin,Pdpn;也称为T1α)和跨膜神经生长因子受体(nerve growth factor receptor,Ngfr;也称为p75)的基因[11]。
从人类肺组织中分离的基底细胞通过扩增能够获得类器官,而不同类器官则根据基底细胞是来源于气管还是大气道命名。在标准条件下,类器官应包含TRP63+KRT5+基底细胞、功能性纤毛细胞和分泌杯状细胞(MUC5AC+,MUC5B+)[12-15]。由于基底细胞也存在于鼻腔上皮细胞中,因此从这些细胞中获得的类器官能够方便临床医生对患者进行最终的药物筛选[16]。人类基底细胞来源的类器官目前能够被用来筛选影响纤毛细胞和分泌细胞比例的细胞因子和其他蛋白质,未来也可能作为某些稳态失衡性疾病的潜在治疗手段,如慢性哮喘。但目前由于缺乏检测基因表达的方法,使 用人类类器官作筛选仍受到较大的限制[6]。
1.2 气道分泌细胞 分泌细胞是指肺部气道上皮中的柱状、无纤毛、非神经内分泌细胞,主要有Club细胞和杯状细胞。成熟的Club细胞能够合成并储存Secretoglobins(Scgb1a1,Scgb3a2)和Splunc1等蛋白质,而杯状细胞能够合成并储存黏蛋白Muc5AC和Muc5B等。
Club细胞是一个异质性细胞群,在病毒和细菌感染、损害气道或肺泡上皮细胞的因子作用下,能够表现出相当强的表型可塑性[17]。使用化疗药物博来霉素损伤肺泡区域后,谱系追踪研究可以发现远端细支气管中表达Scgb1a1的细胞进行增殖并在肺泡中产生具有AT1和AT2细胞特征的后代细胞[18]。类器官培养提供了一个模型系统,理论上可以用于测试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对单个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以及识别具有较强再生潜力的Club细胞亚群。然而,目前缺乏同时纯化和定位这些Club细胞亚群的有效表面标志物。
气道分泌细胞类器官的研究目前只在小鼠中实现,主要使用流式细胞荧光分选技术(fluorescence activated cell sorting,FACS)。McQualter等[19]基于检测表面标记表达的方法分离出Scgb1a1+细胞用来构建类器官,而Chen等[20]使用Scgb1a1-CreER敲入等位基因和荧光表达等位基因进行谱系追踪,分离出Club细胞进行类器官研究。这些结果显示了Club细胞亚群与AT2细胞亚群转化为基底细胞的能力确实存在差异。而后,用类器官培养测试远端细支气管中同时表达Sftpc的部分Scgb1a1+Club细胞亚群对肺内皮细胞因子的反应[18,21],结果表明细支气管肺泡干细胞(bronchioalveolar stem cell,BASC)具有分化为AT2细胞和气道细胞的潜力。
目前,分离BASC的标准方法涉及FACS和其是否表达EpCAM和Sca1。未来的新技术将使这些细胞能够在编码Scgb1a1和Sftpc基因共表达的基础上得到更严格的纯化,从而找到其他标志物 来区分BASC与其他Club细胞。
1.3 AT2细胞 肺泡上皮细胞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及功能:AT2细胞,呈立方形,能够产生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如Sftpc、Sftpb)、板层小体以及与它们的生成和分泌有关的基因(如Lamp3和Lyz2),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可以降低肺泡表面张力,防止肺泡塌陷[22];AT1细胞,大鳞状细胞,覆盖肺泡的大部分表面积,与毛细血管紧密相连,通常表达糖基化终产物特异性受体(advanced glycosylation end product-specific receptor,Ager)、Pdpn和转录因子Hopx。
由于肺气肿和特发性肺纤维化等呼吸系统疾病影响气体交换区的结构和功能,需要更多地了解肺泡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人类的AT2细胞可以通过FACS或磁珠分选(magnetic bead sorting,MACS)经由单克隆抗体HTII280进行特异性分离。
肺泡的形成需要支持细胞的存在,为了更接近上皮细胞和间充质细胞之间的结构关系,需要一种能够使两种细胞群都能存活的培养基[19]。几种不同的支持细胞群已用于小鼠类器官的构建,与免疫/巨噬细胞亚群结合的效果正在研究中。同样,使用损伤前还是损伤后分离的细胞、老年小鼠还是年轻小鼠的细胞、携带与人类肺泡疾病相关特定突变细胞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中[23]。
用类器官研究肺泡上皮细胞基因功能的主要困难是小鼠或人的AT2细胞均不能在Matrigel基质 胶中进行有效的培养扩增。
1.4 hPSC 目前研究者们正在努力培育未成熟的肺上皮细胞和间充质祖细胞,这些细胞能够被大量扩增,然后定向分化为成熟的气道和(或)肺泡组织。如来源于慢性哮喘或CF患者的iPSC所生成的气道上皮细胞,可用来验证祖细胞表观遗传学的改变能够影响其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这一观点[24],以及CF患者iPSC来源的肺类器官也可以提供一个可靠和可重复的突变细胞来源,以筛选补偿或纠正患者特异性突变的药物[25]。
在肺泡组织中,hPSC分化为远端肺祖细胞将有助于研究AT2细胞的突变,这些突变可以导致呼吸衰竭和间质性肺病。对健康者和患者特异性hPSC来源的远端上皮进行组学对比,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突变细胞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调[26]。进行CRISPR/Cas9基因编辑后仍能够扩增并稳定分化的祖细胞,有助于该技术能够在发育过程中检测人类特异基因在气道和肺泡细胞分化中的功 能。
2 肺类器官的培养过程
与成熟肺上皮干/祖细胞来源的类器官相比,多能干细胞(pluripotent stem cell,PSC)来源的类器官需要额外的处理步骤,即将PSC诱导为肺上皮干/祖细胞,肺类器官培养的全程都涉及体内多种 信号通路严格的时间和空间控制。
2.1 hPSC向前部前肠球体分化 首先,使用重组人激活素A(Activin A)诱导PSC分化为终末内胚层(definitive endoderm,DE),在DE形成后,通过使用Noggin和小分子抑制剂(SB431542)分别抑制BMP和TGF-β信号通路,从而获得前肠特性,生成SOX2+AFE。许多信号通路对肺的诱导和发育非常重要,Activin A模拟的Nodal信号在脊椎动物的DE发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和Wnt信号的激活协同促进了hPSC源性内胚层中CDX2+肠道谱系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2D结构自我组织转化为由间充质层和极化上皮层组成的3D球体,抑制BMP和TGF-β信号能够促使组织进 入SOX2+前肠谱系[27]。
2.2 通过Fgf和Hedgehog信号转导诱导前肠内胚层(anterior foregut endoderm,AFE)进入肺谱系 为了进一步使前肠球体向肺谱系发育,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调控Fgf和Hedgehog(Hh)信号传导。Fgf信号在肺生长和分支形态发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Hh分子在体内对肺间质的增殖也有重要作用。高水平的Fgf分子可以诱导Sonic Hedgelog(SHh,即高等动物的Hh)在肺内胚层的表达,同时诱导甲状腺转录因子阳性(NKX2.1+)的肺祖细胞发育,而在前肠球体期添加Hh激活剂(smoothened agonist,SAG)则是提高NKX2.1表达最有效的方法。目前这两种信号通路的配体已经应用于2D培养的hPSC源性肺谱系[25,28]。
总的来说,在hPSC源性内胚层培养物中加入Fgf 2、Fgf 4、BMP、Wnt和Hh等生长因子混合物,可以使其成功分化为表达NKX2.1的肺祖细 胞。
2.3 前 肠 球 体 生 成 人 肺 类 器 官(human lung organoid,HLO) 将前肠球体植入Matrigel基质胶中,形成3D生长环境。在含有1%胎牛血清(Fetal bovine serum,FBS)的基础培养基中对前肠球体进行维持培养,3D培养20 d内就会逐渐失去钙黏蛋白(E-Cadherin,ECAD)阳性的上皮结构并由间质填充[29]。Fgf 10在成人肺的发育过程中,对于肺祖细胞的分支形成和维持以及组织内稳态是必不可少的。与基础条件和添加Fgf抑制剂相比,Fgf 10促进维持ECAD+上皮结构,减少间质的形成,并且在整个HLO中都表达近端肺标志物SOX2和远端肺标志物SOX9。随着时间的推移,Fgf 10处理的前肠球体能够保持NKX2.1的表达;然而,远端祖细胞标志物NMYC和ID2表达降低,而远端A T1和AT2细胞标志物Hopx和Sftpc表达增加[30]。
2.4 HLO产生近端气道样结构 培养2个月以上的HLO具有明显的类似近端气道的上皮结构,能够表达近端细胞特异性的标志物,如基底细胞表达P63、纤毛细胞表达FOXJ1、ACTTUB以及Club细胞表达SCGB1A1等,且近端类气道组织常被平滑肌肌动蛋白(smooth muscle actin,SMA)阳性的间充质隔层所包围[29]。在超过2个月的长时间培养时,能够看到P63+细胞沿着上皮管样结构的基底侧排列,并与SMA+间质相邻,类似于人类支气管和细支气管[15]。在HLO近端气道样结构管腔面的细胞可表达纤毛细胞转录因子FOXJ1,另一种纤毛细胞标志物ACTTUB则定位于这些细胞的顶端侧,但细胞表面并未发现纤毛,且鲜有细胞表达Club细胞标志物SCGB1A1[29]。
研究表明,hPSC源性纤毛细胞的成熟分化需要改变培养条件以促进细胞功能的分化,而Wnt通路能够调节NKX2.1肺上皮祖细胞向近端气道分化,使用Wnt激活剂(CHR99021)可促进向远端上皮分化,而停用CHR99021可快速促进向近端上皮分化[10]。因此,Matrigel基质胶和富含Fgf 10的培养基并不会促进所有类型细胞向终末分化。此时,如果将前肠内胚层接种于脱细胞肺基质上,可以观察到近端气道样结构,如细胞顶端表面 ACTTUB+的纤毛结构向腔内成簇生长[29]。
2.5 HLO产生未成熟的肺泡气道样结构 在HLO培养过程中肺远端上皮细胞可表达包括SOX9、ID2和NMYC在内的祖细胞标志物,其中SOX9为持续性表达,而ID2和NMYC表达量随着培养时间延长而减少[30]。在肺泡相关生长因子作用下,与人成纤维细胞共培养,可获得PSC源性肺泡。多数研究表明,联合使用地塞米松、CHIR99021、Fgf 7、cAMP和磷酸二酯酶抑制剂IBMX足以促进肺泡分化并产生Sftpc+上皮细胞[9,31-33]。在一项长时间培养HLO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表达Sftpc和Sftpb的极少量AT2细胞,以及表达Pdpn和Hopx的极少量AT1细胞[29],提示HLO主要为未分化的肺泡祖细胞,在远端类气道组织中分布着极少的分化成熟的AT1细胞和AT2细胞。
为了获得远端上皮细胞并部分克服PSC源性上皮细胞的成熟度限制,除了延长体外培养时间,与胎肺间质共培养[32]、植入脱细胞肺基质中[34]、在旋转生物反应器培养系统中进行分化[35]或小鼠肾包膜下的移植[28,31, 36]等方法也有探索。这些方法均表明,细胞外基质的机械外力作用,以及来自细胞外基质或来自间充质细胞的分子信号均在促进肺泡上皮细胞分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3 肺类器官技术的独特应用
建立肺类器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肺部的发育过程和病理生物学,这两点都是寻找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新方法的关键。人类肺部发育、修复和再生的几个重要研究结果都是从小鼠模型中推断出来的[37]。然而,人与鼠的肺组织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差异,如基底细胞遍布于人体气道,但在小鼠中仅限于气管,亦如杯状细胞在人呼吸道中常见,但在小鼠中少见等。虽然肺上皮细胞系能够表现出人类肺组织的一些表性特征,但这些细胞系只能单层培养,并且很难通过其进一步了解肺组织发育和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如上皮-间充质相互作用和分支形态发生等[22]。因此,建立人体模型是准确研究人肺发育的关键。近年来,已经成功实现了hPSC源性肺类器官的建立,虽然它们在体外培养时仍处于与胎肺相似的转录和功能状态,但可以通过移植到小鼠肾包膜或附睾脂肪垫下使其形态成熟且具备一定的生理功能[29,31,38]。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类器官模型不能在体外“成熟”,但这些hPSC源性肺类器官具有的未成熟性状成为探索未完全发育肺生理和病理过程的理想模型,最终能够为肺部发育不成熟的早产儿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对于某些呼吸道疾病研究来说,小鼠并非完美模型,如在建立小鼠CF模型时,通过致病基因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蛋白(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CFTR)突变的方法,小鼠模型并不能完全重现人类疾病的症状[39]。目前,通过CFTR突变的肺类器官可以成功建立CF类器官模型,并表现出关键的CF表型[40],这项研究表明肺类器官是一种易于操作的模型,可用于体外检测CFTR药物的疗效。杯状细胞化生是一种与CF、哮喘和COPD相关的表型,亟需体外人体模型来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最近一项对人肺类器官的研究发现,IL-13和IL-17A均可诱导黏膜高分泌表型,使纤毛细胞标志物减少且杯状细胞标志物增多,而Notch信号的调节是IL-13诱导的黏膜高分泌表型的一个控制因素,抑制Notch2可以防止杯状细胞化生[13]。因此,Notch通路是目前治疗杯状细胞化生的一个潜在的治疗干预靶点,该项研究也突出了类器官对呼吸系统研究的价值。
目前人们关于感染对呼吸道的影响及其发病机制的了解有限,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真实的模型来重现体外感染的表型。近年来,hPSC源性肺类器官已被用于研究麻疹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和人类副流感病毒3型(human parainfluenza virus type 3,HPIV3)感染[31,41]。婴幼儿呼吸道感染主要由RSV引起,目前尚无疫苗或有效药物,而RSV感染的hPSC源性肺类器官则再现了RSV感染人肺的重要特征,即感染细胞肿胀,与上皮细胞分离并脱落到受感染的支气管腔中。HPIV3是儿童下呼吸道疾病的常见病因,HPIV3感染的肺类器官在组织完整性方面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感染细胞脱落到管腔中,与临床表现一致,且肺类器官中的HPIV3全基因组测序与在临床环境中分离的病毒也完全相同。这些研究表明,肺类器官可以作为研究呼吸道病毒发病机制的可靠模型,能够重现宿主的感染情况,为研究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肺部感染和病毒在肺部传播机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引起COVID-19大流行的2019-nCoV主要导致包括AT2细胞在内的肺上皮细胞损伤[42],肺类器官能够重现肺的结构和细胞微环境,有望为揭示COVID-19发病机制和筛选有效治疗药物提供一个新方法。
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自1832年被Koch发现以来,对东南亚和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口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43-44]。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35年消除结核病这一策略,在此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耐药菌株的出现以及HIV合并感染[45]。用于研究结核病病理学和药物筛选的动物模型有几个明显的缺陷。首先,通常容纳MTB感染动物的设施都很昂贵,限制了动物在结核病研究中的应用;此外,这些动物不是MTB的天然宿主,因此它们只能部分模拟结核病的临床症状、特征性的病理病变(肉芽肿形成和肺空洞)和免疫指标变化[46]。而人肺类器官的显著优势在于其空间结构的存在和细胞成分的异质性[47],肺泡类器官的MTB感染可以纳入非常早期的MTB(动物模型很难做到),而且还能克服种属差异[48]。因此,将MTB注射到人肺泡类器官可用来研究MTB与肺泡上皮细胞之间的直接作用,或将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等)加入类器官结构中模拟体内免疫反应的复杂性[47]。
研究肿瘤发生和早期肺癌的特征可以大大提高早期诊断肺癌的能力,但目前肺癌的早期诊断能力仍较差,通常是其他医疗检查时意外发现[22,49]。肺癌的动物模型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但也存在着显著的种属差异,如人类细胞转化过程中与啮齿类动物所需的致癌和抑癌基因是不同的,这些差异可能会阻碍小鼠研究成果向人类的转化。而用人肺类器官体外模拟肺癌发生过程较肺癌细胞系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包含多种正常的肺细胞类型,还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检测特定突变驱动前体细胞的转化能力[22]。因此,探索肺类器官的致癌性转化将有助于开发可用于研究肿瘤发生的模型,并能够提供用于人体治疗评估的新临床模 型。
4 肺类器官培养的主要局限性
hPSC源性肺类器官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肺发育、再生以及肺部疾病发病机制的认识,迄今为止,它是唯一能够研究不同生殖层起源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完全人源性模型。而以肺类器官作为研究手段获得研究益处之前,其存在的局限性需要研究者们共同解决。
肺类器官模型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其无法在体外达到完全成熟。虽然可以通过在小鼠肾包膜下或附睾脂肪垫下进行移植来促进肺类器官成熟,但在异位移植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气体交换等原发性肺功能的研究。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了经气管内移植后的hPSC源性肺类器官在小鼠受损肺中存活的能力,提示了原位肺移植模型能够为肺类器官的植入、分化和功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50]。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移植细胞是否在功能上整合到宿主肺组织中并长期存活,且保留完整肺转录组的表达。这就需要更全面地探索介导人类肺部终末分化的分子机制,然而由于伦理问题,人们对妊娠晚期和产后肺发育的研究非常有限[2]。
肺类器官应用的另一个限制是其缺乏免疫系统、循环系统和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目前,体外培养或体内移植的肺类器官不具备自身的血管系统、免疫细胞(如肺泡巨噬细胞)等,而这些系统的成分和功能在调节干细胞行为和肺组织结构形成中也起着关键作用[47]。
肺类器官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也存在着挑战。大多数药物筛选平台要求使用相同的起始材料,如相应条件下相同的起始细胞数,从而获得比较可靠的结果[47]。而类器官是self-organize的组织,通常大小并不一致。如想要在类器官形成过程中控制其大小和直径,则可能会影响其分化的轨迹,又会使其失去招募和组织细胞的自由。但肺类器官仍是基于表型的药物发现平台(phenotypebased drug discovery,PDD)[51]的选择之一。
近年来,患者细胞来源的3D类器官培养物为肺部肿瘤类器官作为个性化用药工具提供了可能[52-54]。但单纯肺肿瘤类器官的建立仍是一个主要问题,可能会限制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来源于肺内非小细胞肺癌的类器官会被过度生长的正常气道类器官所替代 ,从而限制了单纯肺癌类器官的应用[55]。
5 结语
类器官技术是研究细胞间通讯和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的一种新病理模型,也是人类肺部疾病建模、药物筛选和毒性分析的有力工具。这种工具可以代替一些动物实验,从而减少动物在呼吸系统研究中的使用。未来待该技术成熟后,可以建立一个用于细胞治疗或基因治疗的人肺类器官库,为研究个体对治疗的反应和个性化药物的开发开辟了新途径。尽管目前用类器官技术模拟远端肺部疾病仍存在难以模拟气体交换过程中肺部膨胀和收缩的机械力、缺乏成熟的体外培养等局限性,但目前hPSC源性肺类器官的研究极大推进了呼吸道疾病的治疗和临床/基础研究,而肺类器官的应用与活体成像、基因工程和生物材料等新技术的结合将极大促进肺部相关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