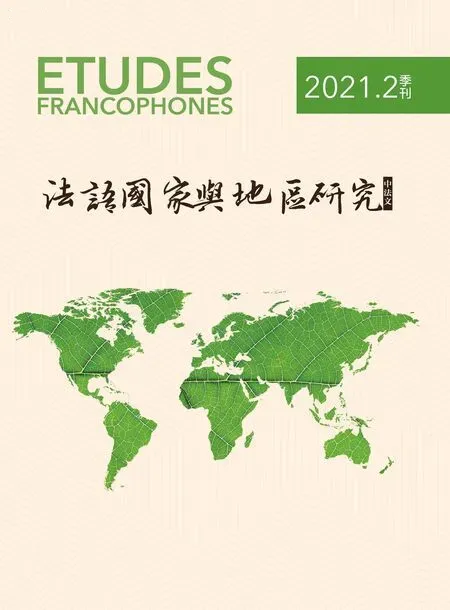渡尽劫波同窗在
——罗曼·罗兰与克洛岱尔的暮年砥砺①
刘吉平
内容提要 罗曼·罗兰和保罗·克洛岱尔同属法国20世纪的重要作家,二人是高中同窗。在经历五十一年的分离后,二人在暮年重逢,展开了深层的内心互动和砥砺:克洛岱尔试图在重拾旧谊的同时唤醒罗兰的天主教信仰;罗兰则以音乐为媒介,深入地展开与旧日同窗的精神交流。理想幻灭和晚年沉疴让罗兰晚年进一步偏离理性主义立场,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立场;克洛岱尔把帮助罗兰重拾信仰当作使命。这一互动从1940年开始持续到1944年罗兰过世,读者从中可以窥见晚期罗兰的价值调适和他思想二元性的特点。本文从罗曼·罗兰的视角出发,以罗兰晚年日记、与克洛岱尔的通信为研究文本,从他与克洛岱尔互动的角度再现出其晚年思想轨迹。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和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作为法国20世纪的文学巨擘,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二人曾经是高中同窗,在别离的半个世纪中未曾往来。他们的人生轨迹在垂暮之年又有了交汇,昔日同窗展开了一段动人的切磋砥砺。生命最后四年与克洛岱尔的交流构成了罗兰晚年内心历程的重要印痕,是研究罗兰晚年思想无法跨越的内容。本文试图根据法国近年出版的罗曼·罗兰日记和书信文献,介绍二人暮年的内心交流和互动,以求为读者展现罗兰晚年曲折思想轨迹的一个剖面。
一、罗曼·罗兰的晚境与二人的重逢
1938年,72岁的罗曼·罗兰叶落归根,从瑞士莱芒湖畔的新城(Villeneuve)迁返勃艮第地区的韦兹莱(Vézelay),一直到1944年末辞世,在此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六年。
1937年开始,随着二战前欧洲紧张气氛的升级,瑞士当局对外来侨民的政策愈加严苛,来自苏联的罗兰夫人对此感受尤深。当时法国法郎急剧贬值,罗曼·罗兰一家在瑞士的生活成本飙升,罗兰决定离开侨居了十六年的瑞士,举家迁至法国勃艮第地区的古镇韦兹莱。②Bernard Duchatelet.Romain Rolland tel qu’en lui-même.Paris : Albin Michel, 2002, p.337.罗兰的暮年除了完整地经历二战外,也经历了政治理想的幻灭。
1928年起,罗曼·罗兰的思想进一步左转,从三十年代开始,他自认为是苏联的同路人;三十年代初,来自苏联的玛丽(Marie Koudacheva, 1895—1985)走进他的生活,并于1934成为他的第二任夫人。这位俄法混血的伴侣被众多欧洲文化名流看作是一种政治存在,在罗兰的交际圈中招致很多非议,杜阿梅尔③杜阿梅尔,法国作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罗曼·罗兰交往较多。(Georges Duhamel, 1884—1966)公开表示,她受苏联政府指派来到罗兰身边,目的是拉近他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距离;④Bernard Duchatelet, op.cit., p.296.1936年11月,纪德(André Gide)访问苏联后出版了著名的《访苏归来》(Retour de l’U.R.S.S.),向欧洲知识界介绍自己访苏期间真实的见闻。罗兰为了捍卫苏联,在《人道报》(l’Humanité)刊文反驳纪德,出现了纪德与罗兰之间围绕苏联的著名论战。可以说,三十年代,罗兰因为自己政治理想的寄托,招致了众多欧洲知识分子的不解和疏远,在法国知识界再次受到孤立。⑤一战期间,罗曼·罗兰因坚决的反战立场在法国知识界受到孤立。从1937年开始,国际局势促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Le pacte germano-soviétique)的签订是罗兰晚年思想状态的分水岭。⑥Romain Rolland.Journal de Vézelay.Paris : Bartillat, 2012, p.248.作家此前的社会信仰寄托都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各种幻觉最终破灭,罗兰在垂暮之年迎来了一次社会信仰上的巨大幻灭。
罗兰绝望的心迹经常流露在其日记的字里行间:“在内心深处,我彻底从这些荣誉或不名誉中解脱出来了。从人生之始,我已然带上了生而为人的伤痕。在童年的门槛上,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被弃置的这个世界,我对它既怀有恐惧,又抱有悲悯(……)我永远无法对幕布后面的各种残酷厮杀熟视无睹,它们悄无声息、永不休止地上演着,自相残杀有时发生在动物之间,有时在人与人之间,我自感是他们的同谋,却没有任何办法从中抽离。我与生俱来地带有永恒的痛苦(……)我希望从人世离开后,永不再来人世。”⑦Bernard Duchatelet, op.cit., p.327.在写给妹妹玛德莱娜(Madeleine Rolland)的信中,罗兰向仅有的在世至亲陈述内心的痛苦:“这太让人阴郁了。我怀念莱芒湖,我更情愿在昏梦中麻醉,不是‘超越混战之上’⑧此处罗兰在映射他于1915年9月发表在《日内瓦论坛报》(la Tribune de Genève)上的反战文章《超越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êlée),此文在一战期间引发了欧洲思想界的激烈争论。,而是逃离这荒诞的生活,余生太长了。”⑨Ibid., p.353.信仰幻灭和对人性一针见血的洞见让晚年罗兰对人世的诸般境况几近绝望,从瑞士返回法国后,罗兰内心渴望与法国思想界交流,企图在交流中疏解自己内心的困惑。
罗兰的夫人玛丽在夫君与克洛岱尔之间穿针引线,让这两位失去联系长达半世纪的昔日同窗重新开始了书信往来,继而谋面,促膝长谈⑩Claudel-Rolland, une amitié perdue et retrouvée.Edition établie, annotée et présentée par Gérald Antoine et Bernard Duchatelet.Paris : Gallimard, 2005.p.74-75.,展开他们的暮年砥砺。
二、曾经的高中同窗
罗曼·罗兰比保尔·克洛岱尔年长两岁,二人均来自法国外省,中学时代负笈巴黎。1880年,罗曼·罗兰在圣路易中学(le Lycée Saint-Louis)求学,两年后(1882年)与克洛岱尔相遇,两人均进入法国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le Lycée Louis-le-Grand)学习。罗兰在此备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于1886年被高师录取,学习历史,三年后通过历史学科的教师资格会考。克洛岱尔1885年从路易大帝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政治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准备他的法学文凭。从1882年到1889年,罗兰和克洛岱尔在巴黎交游,前后有七年的交往史。
罗曼·罗兰与克洛岱尔因音乐而拉近了距离,音乐是二人早年交往的凝结剂,在暮年的书信往来中,二人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青年时代一起前往音乐厅聆听古典音乐的往事。罗兰在《高师日记》(Journal de Romain Rolland à l’École normale 1886-1889)中记录了1889年3月3日他们一起聆听贝多芬《D大调庄严弥撒》(la Messe en ré)的情景,读者从中能看到当时罗兰对克洛岱尔的观感:“克洛岱尔、苏亚雷斯⑪安德烈·苏雷拉斯,法国作家,诗人,罗曼·罗兰巴黎高师时期的挚友。(André Suarès, 1868—1948)和我步行,从巴黎音乐学院走回米什莱大街,一路上我们高谈阔论。克洛岱尔真是个怪异的小伙子,非常肤浅、缺乏逻辑,但是却拥有激烈人格、激情澎湃,敏锐善感,以至于呈现出像他的脸庞一样的膨胀感。……在他眼里,只有自然、直觉、感觉、爱、欲望、激情、烈焰和生命是存在的,但是它们都与思想无关,思想只是附着在它们之上的蘑菇。他自称是瓦格纳迷,却认为瓦格纳缺乏思想,瓦格纳只是森林中骑着马追求心爱女人的俊男;他也自称是贝多芬迷,但在他眼里,贝多芬也缺乏思想,贝多芬作品里只有光明与永夜的对决。他却是马拉美和维里耶文学圈中人,可是他坦率地承认,他只欣赏他们的形式,对他们的形而上学却弃如敝履。”⑫Cahiers Romain Rolland n° 4 - Le Cloître de la rue d’Ulm (Journal de Romain Rolland à l’école normale 1886-1889).Paris : Albin Michel, 1952, p.281.这是二人青年时代最后一次一起去音乐厅欣赏古典乐,之后二人便各奔东西,直到51年后的1940年重逢。
读者从中不难看出,尽管二人都喜好古典音乐,但是他们对瓦格纳和贝多芬的理解相去甚远,罗兰对克洛岱尔敏感饱满的诗人气质有敏锐的捕获和体会,但是对这位同窗理性精神的薄弱也直言不讳。罗兰对克洛岱尔的诗人气质印象至深,以至于三年后的1892年,罗兰参观完克洛岱尔的姐姐卡米耶·克洛岱尔(Camille Claudel)的雕塑展后,在写给高师挚友苏亚雷斯的信中说道:“你还记得克洛岱尔吗?那个说到自然和生命的时候鼓起腮颊的大婴儿,他姐姐展出了一尊深具罗丹气质的半身雕像,她是罗丹唯一的学生。这看上去不像女性的作品,她老师给她注入了粗犷之气,脸的下半部须髯凌乱,雕塑不像是从巨大粘土块中刻意雕琢出来的。我从中认出了我的克洛岱尔:物质、混沌与杂糅的生命。”⑬Claudel-Rolland, une amitié perdue et retrouvée, op.cit., p.46.
二人在青年时代有同窗之谊,同时被音乐所吸引,但是气质层面表现出迥异的风格。在天各一方的半个世纪中,罗兰书信中曾提到过克洛岱尔,流露出某种疏远。1920年前后,奥地利作家、罗兰的忠实的朋友茨威格(Stefan Zweig)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为罗兰撰写传记,并将已经完成的手稿寄给当时正在巴黎暂住的罗兰,向其请益。罗兰看完手稿后,提出了32条修改意见,其中第三条涉及他与克洛岱尔关系的定位:“关于和克洛岱尔的同学关系,用‘朋友’一词过大。我想把朋友这个词专门用在一小部分真正能称得上我的朋友、真正和我有至深感情的人身上,比如1900年之前的苏亚雷斯和马尔维达⑭马尔维达,侨居罗马的德裔文化女性,曾与尼采、瓦格纳等文化名人过从甚密。在罗曼·罗兰的罗马岁月(1889-1891)里,她曾予之以巨大的精神指引。在《回忆录》中,罗兰称其为“我的第二母亲”(Romain Rolland.Mémoires.Paris : Albin Michel, 1956, p.94.),据《罗兰·罗兰与茨威格通信集》记载,二人通信极为频繁,共留存1464封往来书信(Romain Rolland-Stefan Zweig, Correspondance 1920-1927.Paris : Albin Michel, 2015, p.539.)。(Malwida Von Meysemburg, 1818—1903)。”⑮Romain Rolland-Stefan Zweig, Correspondance 1920-1927.Paris : Albin Michel, 2015, p.101.可以看出,二人的疏远感并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消减。
三、暮年互动
克洛岱尔在收到罗兰夫人玛丽旨在促成两位老同学重拾旧谊的信后,对罗兰老年的信仰挫折抱有很深的同情:“我顾念您的夫君。看着他年事已高却陷入这般的黑暗,沉浸在这样的失望状态,真让人难过。”⑯Claudel-Rolland, une amitié perdue et retrouvée, op.cit., p.74.1940年初,罗兰主动给克洛岱尔写信,言称在老同学身上感觉到难得的真实,主动邀请克洛岱尔前来韦兹莱,希望继续51年前的同窗情谊。就这样,两位昔日同窗展开了暮年互动。
垂暮之年,两位作家通过阅读对方的文字真正走入了彼此的内心和灵魂,祛除了年少气盛时对彼此若隐若现的成见。二人交往过程中,克洛岱尔一心想让罗兰皈依天主教,而罗兰却试图通过二人的共同场域——音乐与旧时同窗展开思想交流。
1940年初,罗曼·罗兰把新写就的两册《贝多芬——伟大的创作年代》(Beethoven, Les grandes époques créatrices)寄给克洛岱尔,后者在3月21日的回信中情动于衷,感谢罗兰,从中读者能看到音乐在二人思想互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两本书能帮助我解决多少问题!贝多芬曾经出现在我年少时痴迷的梦幻里,我记得很清楚,整整五十一年前,我曾经请求您给我解释贝多芬末期这几首痛苦的夜曲,我已经开始专注地按照您的著作探索它们。(……)我对我们曾经的相聚留有美好的回忆,衷心期待能有机会重逢。”⑰Ibid., p.95.克洛岱尔时时处处试图在罗兰的音乐作品中提取出某些潜在的宗教符号,试图以音乐为外在依托,找到促使罗兰皈依天主教的载体。
克洛岱尔在阅读《约翰-克里斯朵夫》(Jean-Christophe)的过程中,特别在意罗兰字里行间的宗教态度,1942年他读完其中的《燃烧的荆棘》(Le Buisson ardent)后写道:“玛丽(罗兰夫人)指责我对罗曼·罗兰的认识有失偏颇……这颗伟大的心,庄穆的精神,一言以蔽之,这个伟大的灵魂,何以能对祖辈坚笃的信仰抱持如此贫乏、无味和庸俗的看法呢!他身为基督徒,竟然本着泛神主义,这让我很气恼。”⑱Ibid., p.209.
罗兰对克洛岱尔的重新涵纳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他眼中,克洛岱尔是半世纪前的同窗,二人心灵之间横亘着半个世纪的隔膜;罗兰做好准备,打算深入交流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心得,但是又在交流中暗设藩篱:罗兰特别在意自己的精神独立,在认真倾听的同时,警惕地防范着任何精神层面潜在的盲从,这种警惕在风烛残年里也未有丝毫的减弱。
罗兰的日记记录了他通过阅读克洛岱尔的诗歌来进一步了解这位昔日同窗,同时也展现出在信仰面前不先入为主的谦卑姿态:“近一两年来,在克洛岱尔出色的诗歌和玛丽的帮助下,我学着了解克洛岱尔(与此同时,克洛岱尔也在试图了解我)…… 我尽力接近天主教。我承认,我对天主教很不了解,能找到的(相关)书籍我都阅读。”⑲Journal de Vézelay, op.cit., p.704.
尽管二位同窗主观上互相接近,而且也重新发现了对方一度被漠视的才华,但是对彼此深层的思想并未全盘接纳。克洛岱尔在1942年6月的信中赞叹罗兰的卓异才华,忏悔自己对老同学才能视而不见的愚妄,但同时对罗兰的思想深处的不羁于范、奔肆激荡、拒绝定于一宗的深层自由有明显的察觉。很显然,克洛岱尔非常清楚,罗兰的泛神论思想根深蒂固。对此,克洛岱尔有清醒的认识。在忏悔完自己的“愚妄”后,他马上写道:“我对您充满敬仰、欣赏和深情,这些情愫让我在读到您的某些段落的时候倍感痛苦和受伤。您这样的精神生来就不会被拘囿于任何被造之物中——不管它是自然还是音乐。”⑳Claudel-Rolland, une amitié perdue et retrouvée, op.cit., p.209.
对克洛岱尔的钦佩、惊异、赞叹并不能促使罗兰全盘接受克洛岱尔的信仰。罗兰也没有生硬地拒斥老同学让其皈依的努力或善意,他以音乐家的口吻,这样定位二人的互动砥砺:“亲爱的朋友,请不要痛苦,我不认为我们彼此疏远,我不认为您所笃信的神的臂膀和心怀不够宽广,不能给予我一个小小的位置。我这样的念头不会降尊或抵触您所赖以存活的信仰吧?我们是两个互相和谐的音符,组成漂亮的和声。”[21]Ibid., p.208.
1943年初,罗兰身染沉疴,命垂一线,险些撒手人寰。病入膏肓的罗兰已经做好离开人世的心理准备。生死边缘的艰难处境让他在病发的间隙反复地纵观一生,重新直面自己在人世的得与失,检视过往的种种信仰和幻灭。在死神周边游移的经历突然让罗兰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冰冷的泛神思想”的偏执,罗兰特别对自己一贯以来对天主教抱持的警惕心理做了许多真诚的反思。两位故人终于承认,他们所侍奉的是同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在1943年8月15日的信中,克洛岱尔这样定位二人的关系:“我一直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越了同窗情谊,浅在的相惜(sympathie superficielle),甚至超越了感情,处于神圣的层级。”[22]Ibid., p.321.在9月2日的回信中,罗兰做出了类似的回应:“感谢您寄来的优美的长信,您劳神费力给我写信,让我感动。这是你我之间道德联系的宗教特征(这超越了同窗情谊和普通友情)。”[23]Ibid., p.337.反复阅读克洛岱尔的作品、《圣经》以及天主教的各种疏义文献后,特别是经历了1943年初的沉疴累身、生死徘徊后,罗兰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场大病让罗兰前所未有地贴近了死神,在康复后补写的日记中,读者能读到罗兰开始怀疑此前人生笃信的思想,他前所未有地感觉到游离在生死一线时信仰给他带来的巨大抚慰,他的思想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宗教信仰:
以下的文字,我可以命名为大去之旅的总排演或者预演(也是最后的排演)。因为我从邈远的地方返回来了。在十天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经即靠了彼岸。甚至可以说,某个夜里,我触摸到了死神的门槛。(……)
我终于从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中抽身出来了,它们悬浮在深渊之上。
我摔倒了,我感觉到自己摔倒了。我深爱的两个女人(我的妹妹和妻子)竭力要扶住我。但是还是没能扶住。倒下去的时候,徒劳地伸手去抓一个依靠。我尽力做内心反省。反省我一生的劳作和沉思。我无法找到支撑我的东西。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不能确定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行为、任何成就或者存活的理由之上,我对自己的任何作品没有任何记忆。约翰·克里斯朵夫们,贝多芬们,他们在哪里?竟然没有一个来支撑着我……他们都是虚无的。外部世界、战争、社会斗争、人类希望……都是虚无的,任何事物都不再重要了……尘埃,在我手中飞灭。[24]Journal de Vézelay, op.cit., p.878.
罗兰从死神手中挣脱后,克洛岱尔愈发觉得有责任将他重新拉入上帝怀抱。罗兰向克洛岱尔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又却坚持说自己无法完全分享老同学的信仰。与此同时,他不停地阅读克洛岱尔推荐给他的各种宗教和世俗的典籍,试图用更真诚的态度来体会克洛岱尔的良苦用心。在游走在生死之界的时候,罗兰鼓起勇气,诵读克洛岱尔给他寄来的《主啊,请教我们祈祷吧》(Seigneur, appreneznous à prier)。
但是宗教的慰藉在罗兰跨越了生死煎熬后变得淡薄起来,他本性中对理性的坚守又开始慢慢抬头。在1943年10月的日记中,罗兰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他(克洛岱尔)充满善意,我的理性却拒绝信仰(说理性拒绝信仰是不确切的,即使它有信仰的意愿,它也无法做到笃信)。我的心遵从来自生命他处(un autre monde de l’être)的冲动,它们来自深层的穿越代际的直觉,来自本能和灵光。当克洛岱尔告诉我:‘让你的精神谦卑起来,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顺从召唤你的声音!’,我既不愿意也无法做到。(……)如果上帝需要我,请他来说服我!”[25]Ibid., p.941.罗兰一生中在不同文字里反复强调自己思想中的二元特点:既相信直觉又尊崇理性。在大病初愈后不久的日记中,罗兰没有忘记重申他的这一立命之本:“我本性中奇怪的二元性:坚定、平静、不屈的理性,它拒绝信仰,任何信仰的规劝都对它无计可施;内心的直觉拥抱祈祷的热忱。就这样,我在两条平行线上跋涉着,二者互不相害,也不碰撞。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我本性中的任何一条主线。我将对二者都抱以忠诚。这是我的责任。”[26]Ibid., p.885.
四、弦断有谁听
对精神气质和思想迥异的罗兰和克洛岱尔而言,音乐是连接二人的纽带,也是二人求同存异的基点。早在青年时代,音乐就将他们聚拢在一起。富有戏剧性的是,1889年罗兰和克洛岱尔最后一次见面是一起在巴黎音乐学院的音乐会后,时隔半个世纪,罗兰和克洛岱尔的人生诀别也是围绕着音乐展开的。
1940年春分日的当天,克洛岱尔特意写信给罗兰,动情地回忆起年少时一起交流音乐心得的往事,邀请他一起走进音乐:“如果我没有记错,51年前,我曾经请求你给我解释贝多芬末期这些让人痛苦的奏鸣曲,今天终于要看到您的阐释了,衷心地感谢您!”[27]Claudel-Rolland, une amitié perdue et retrouvée, op.cit., p.95.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克洛岱尔告知罗兰他即将前往韦兹莱,并再次要求罗兰为他演奏贝多芬的第111号奏鸣曲(La sonate opus 111):“您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曾经要您为我演奏贝多芬的第111号奏鸣曲吗?我希望您会兑现这一诺言。”[28]Ibid., p.101.可惜克洛岱尔最终未能成行,计划中的会面被迫取消了。1941年10月罗兰写完了《贝多芬——伟大的创作年代》的第四卷,他将这部作品寄给了克洛岱尔,在随附的信中,罗兰深情地回忆:
您还记得1889年春天的那个星期日吗?我们刚刚在巴黎音乐学院聆听完(贝多芬的)《D大调庄严弥撒》,然而,这天晚上,我们并不知道,这将是半生契阔前的告别,此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为了纪念我们的重逢,请允许我向您赠送最新写就的关于贝多芬的书籍,在我们二十岁的时候,贝多芬是我们的光芒,它在今日西方的晦暗与风暴中依旧熠熠放光。[29]Ibid., p.178.此信为罗曼·罗兰于1941年10月20号写给克洛岱尔的私人通信,七卷本的《贝多芬——伟大的创作年代》付梓时,罗兰将这封信作为其中第四卷的题献文字放入书中出版。
两个月后,克洛岱尔途经巴黎,邀请罗兰和他在巴黎会面。罗兰因为身体羸弱而无法成行:“我不可能前往巴黎。上帝知道我特别想去和您会面!您是此刻我最想见到的人。您的身体比我健康得多,您不能来我家小住几日吗?终于有机会让我在键盘上通过我们的贝多芬之声和您交流了,您可以用您充盈着圣灵的伟大音乐来酬答。”[30]Ibid., p.184.克洛岱尔看完罗兰对贝多芬的阐释拍案叫绝。在1943年12月6日的信中,克洛岱尔激动地写道:“我满怀阅读欲望、谦卑和忧郁的心情,长久地把作品捏在手里掂量。某些被您称为是高妙的乐段,我反复听了许多次。我想谦卑地向您坦诚:我的内心倍感错乱。”[31]Ibid., p.341.很显然,罗兰对贝多芬的阐释深深地震撼着克洛岱尔,两个星期以后,克洛岱尔再次向罗兰坦言:“我读完了您的大作(……)感到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痛苦煎熬,这种痛苦比音乐伟人(贝多芬)的失聪更让人痛苦!我手头没有一架可供我蹩脚地弹奏的钢琴,哪怕用一个指头弹奏也好!”[32]Ibid., p.342.令人遗憾的是,此后的三年内,罗兰都没能有机会和他的高中同窗“在键盘上通过我们的贝多芬之声”交流。
1944年平安夜,罗兰夫人把虚弱的罗兰和前来探望罗兰的一对夫妇留在家中,自己去了圣玛德莱娜大教堂聆听午夜弥撒。罗兰预感到这是演奏贝多芬的最后机会,他请求二位客人扶着他,颤颤巍巍地从楼梯上下来,拖着虚弱的病体,来到钢琴旁,演奏起贝多芬的第111号奏鸣曲,大概心中在惦念着克洛岱尔。就在同一天,克洛岱尔从寓所给罗兰写信:“在这光耀的圣诞节,我惦记着您。我衷心为您祈祷和平、力量、光明和对上帝的信仰,这种欣悦超越了所有的感官!”[33]Ibid., p.361.
罗曼·罗兰演奏的奏鸣曲没能传到克洛岱尔的耳中。罗兰六天后过世,克洛岱尔的圣诞祝福寄到韦兹莱时,罗兰已经撒手人寰。
结语:“竭尽所能”
罗曼·罗兰将尼德兰画家扬·凡·爱克(Jan Van Eyck)的信条“竭尽所能”(Als Ik Kan)当作自己一生的信条。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少年》(L’Adolescent)篇中,他就借约翰-克里斯朵夫舅父高脱弗列特的之口,说出了这一信条:“对每一天抱着虔敬的心,一个人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34]Romain Rolland.Jean-Christophe.Paris : Albin Michel, 1950, p.370.罗兰从这一信条中汲取的不仅仅是字面所透露出来的谦卑气息,更包含了他对精神独立、和而不同的一贯诉求和尊崇。在1940年9月补充写就的《追寻内心的旅程》(Le Voyage intérieur)的第九章中,罗兰的文字再现了这一信条:“主啊,我已尽我所能。”[35]Romain Rolland.Le Voyage intérieur.Paris : Albin Michel, 1959, p.240.在1943年他写给克洛岱尔的一封信中,罗兰对这一信条做了更直白透彻的阐释:“不要害怕,也不要悲伤,请允许我以我自己的尺度——竭尽所能,去爱、服务、追寻、质疑、倾听上帝。为什么要将唯一的尺度强加于人呢?”[36]Claudel-Rolland, une amitié perdue et retrouvée, op.cit., p.302.罗兰尽管在垂暮时分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接近天主教信仰,但是,他心中的理性精神自始至终都没有沉睡,精神独立和拒绝盲从的内在气质让他在最后一道门槛处止住了脚步。
1944年圣诞节,也就是罗曼·罗兰去世前五天,他给克洛岱尔写了一张圣诞明信片,这是罗兰写给老同学最后的文字:“我多年的兄弟克洛岱尔,您比我离光更近,请宽容我的信条,这也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信条,它最初是扬·凡·爱克的信条——竭尽所能, 致以我全部的深情,罗曼·罗兰。”[37]Ibid., p.362.尽管一生历尽思想信仰的各种挫折和幻灭,罗曼·罗兰至死都在坚持自己内心的法则。
——读托马斯·克洛《18世纪巴黎的画家与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