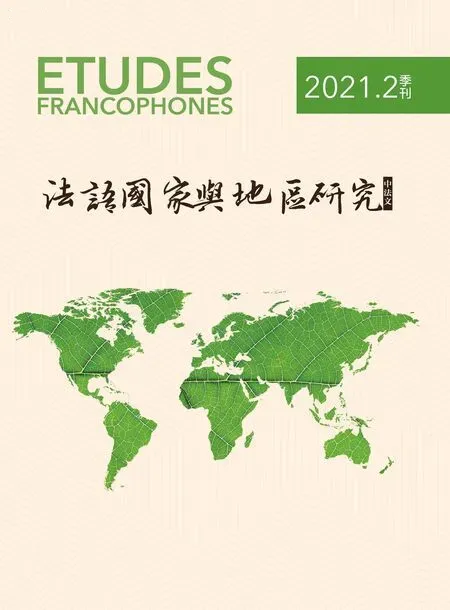《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
——论萨德的界限书写
季浩旸
内容提要 福柯在论述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古典时代和现代三种知识型时,将萨德的作品放在了古典话语与现代话语的断裂处。本文通过研究萨德的小说《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来阐释这种断裂处的界限书写。首先,萨德在对欲望的狂热追逐中保持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他尝试构筑一个欲望乌托邦的努力和现代文学“反话语”的尝试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这些相似处将萨德的书写推向现代的话语。其次,在萨德的小说中,书写同时展现出了古典和现代话语的特质。一方面,小说仍依赖古典表征来构建渐强结构;另一方面,描绘密闭空间的语言呈现出无限增殖的现代特质。最后,整部小说的叙述结构也有了现代文学空间的雏形,正是沉默的中断打开了女主人公原本无始无终的叙述。萨德的界限书写反映了现代书写永无止境的本质。
引 言
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Marquis de Sade)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无节制的性与暴力,对一切道德的嘲弄,对恶的宣扬,这些都让世人对萨德嗤之以鼻。但是,我们不应仅仅将萨德视为一个色情狂或恶人,因为对他来说,恶与性从来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萨德欲借助施虐实现的东西才是我们应该探究的问题。
萨德问题得到了诸如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福柯(Michel Foucault)、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等思想家的关注。在福柯看来,“萨德抵达了古典话语和思想的终点,他恰恰统治着它们的边界”。①Michel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Paris : Gallimard, 1990, p.224.也就是说,在福柯探寻到的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古典时代和现代三种知识型(épistémè)中,萨德的作品恰好位于古典话语与现代话语的断裂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萨德的书写理解为一种界限书写:他尝试突破以表征(représentation)为基础的古典话语格局却又最终失败,其作品也预见了现代文学面临的“作品难以完成”的困境。②本文提及的现代文学的概念主要指福柯所提出的一种“反话语”的文学,其定义将在后文给出。
本文将从《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 后文简称为《美德的不幸》)出发,对萨德的界限书写问题进行具体探讨。这就是说,本文并不会关注萨德的恶所引发的种种道德争议,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书写问题来分析。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出发研究萨德的界限书写:首先分析催生这一界限书写的土壤,即萨德以欲望为中心的哲学观点;然后结合文本具体分析《美德的不幸》的界限书写;最后研究这种界限书写和现代文学的联系,借小说叙事结构安排,反思使写作成为可能的条件。
一、欲望的乌托邦
欲望是萨德作品永恒的中心,肆无忌惮的恶行被视作进一步刺激欲望的手段,萨德借笔下的恶人不断论证自己以欲望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在他看来,道德善恶的标准都会随时间环境而变化,因而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只有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最符合自然的永恒的价值准则。于是,萨德总是在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对道德的僭越(transgression)中追寻着欲望。
不过,在他的欲望书写中,对欲望的狂热追逐同时采取了一种矛盾的克制形式:“必须去寻求的不再是激动,而是无动于衷。”③西蒙娜·德·波伏娃.《要焚毁萨德吗》.周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5.“无动于衷”意味着,萨德作品中的主人公与传统意义上的色情狂不同,萨德的主人公并不会狂热地投身于淫乐中。倘若全然地投入其中,忘我的主体就失去了把握欲望的能力。欲望实现的瞬间之所以醉人是因为它只能维持一瞬的时间,顶点的到达意味着衰退的开始,和欲望的对象切断联系的我们将很快坠回现实。因此,萨德使尽浑身解数,竭力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以通过“无动于衷”与欢愉的衰退相抗争。
具体而言,在书写的内容上,“无动于衷”表现为独特的享乐形式。萨德笔下的恶人永远在贪婪地注视着欲望的对象,无论以何种方式享乐,注视的目光都不会中断。因为“欲望在本质上是不可命名的,它只有在不断的客体化的过程中才能彰显自己的存在”。④赵文卿.《论福柯的文学观念》.硕士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17.比如在泰雷兹被关入修道院后,淫乐不是即刻发生的,先行的是两个小时的观察评测和长篇大论的理论。同时,为了对抗高潮后的衰退,享乐的方式开始逐渐脱离性的范畴,各式各样的暴力也成了欢愉的来源:几乎所有恶人都喜欢鞭打他们的受害者,热尔南德(Gernande)伯爵的癖好甚至只是观看他妻子被放血的过程。在书写形式上,“无动于衷”则表现为转述。萨德的作品永远沉浸于一种转述中。所有欲望的故事都不会直接在小说的叙事空间中发生,而是被叙述出来。例如《闺房的哲学》(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就是一部纯粹用对话完成的作品,《索多玛120天》(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中也安插了“故事员”用以叙述罪恶。在《美德的不幸》中,一切故事都是通过泰雷兹的转述展现出来的,而且与诸恶人的叙述相互叠加。转述带来的距离感不仅将读者也将书写者推开安置在了观察者的位置上。只有保持这一距离,才能不在欲望中迷失。
表面上,萨德笔下的“无动于衷”似乎与接近欲望的原则相冲突,但这并不只是简单的逻辑矛盾,而是反映了他对欲望的一种乌托邦式构想:消除了一切隔阂的一种不会衰退的完美欲望。小说的结构恰恰也在向我们暗示这一乌托邦:小说以泰雷兹对自己苦难的叙述作为主体框架,她作为绝对的欲望对象,同时也是欲望的叙述者本身,于是,欲望与其对象的边界被消融打破。由此呈现的是一个理想的欲望,一个能自我言说、自我呈现的欲望,它的一切真相都将会自发地向我们敞开。⑤Georges Bataille.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Paris : Gallimard, 1957, p.95.
当我们把这一乌托邦构想与现代文学的“反话语”(contre-discours)进行比较,我们将发现许多惊人的相通之处。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德的作品才区别于一般的情色文学,在触及古典话语边界的同时,预见了现代话语。福柯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词与物在相似性的原则下相互交缠,形成了一个原始绝对的语言的平面。一个原初的大文本(le Texte premier)就潜藏在这一平面下,并构成一切评论的基础。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末期,知识型经历了第一个重大的转变。词与物相互分离,能指与所指以表征的方式相互连接。到了19世纪,第二次知识型的重大转变发生了。标记与其所指只能以意指(signification)的方式来联系。在意指的游戏中,语言只在标记间运动,物并非必要且就此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19至20世纪诸如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和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文学作品中,一种深刻的断裂产生了。在他们的文学中产生了一种“反话语”,即反对语言的古典表征形式、尝试让文艺复兴时期语言的原始存在重新显现的话语。然而,这种尝试终将失败,因为自古典时期以来,语言与物的关联就已经中断。这种“反话语”最终只能不断地自我指涉,最终,只有无穷无尽的话语在不停地增殖。
我们可以尝试就萨德的乌托邦构想和现代文学“反话语”做一个类比。现代文学的“反话语”试图重新构筑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让词与物重新互相缠绕,且最终归于失败。萨德对乌托邦的构建也体现出了类似的企图,并遭遇了同样的窘境。作为欲望对象的泰雷兹自我言说、自我呈现,从而让欲望与其对象呈现出与词与物相似的缠结状态。不过,在现实中,这一乌托邦并无法实现,萨德追逐理想欲望的努力,即“无动于衷”,最终带来的只是一种欲望对象的自我指涉,因为当人保持着观察者的距离抵抗忘我时,他就只能不断地回返到欲望的对象。我们将看到,观察、转述、暴力,这些萨德式的享乐方法并不与生理的性快感直接相连,而只是确认欲望对象的方式。于是,追逐欲望的努力最终成了欲望对象的堆叠,一如“反话语”中话语的增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欲望及其对象的关系近似于现代文学中物与词的关系。
通过这些共通之处,我们将得以理解在萨德那里,欲望的游戏如何达到了古典话语的边界并预示了现代文学的话语。但是,抽象概念上的相似不一定指向一种革新式的界限书写,如果萨德仅仅满足于对欲望乌托邦的憧憬,那么他也只是一个“没有萨德的施虐狂”⑥Michel Foucault.« Sade, sergent du sexe ».Cinématographe, Décembre 1975-Janvier 1976, n° 16, p.3.。如果说萨德“统治着古典话语的边界”,那么到这里,他还仅仅是凭借乌托邦的幻想远望见了其边界。
二、渐进结构的幻灭
那么,萨德是如何接近乃至达到这一欲望的乌托邦的?下面,我们将从《美德的不幸》小说文本出发,进行分析。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萨德采取了简单的渐进结构:让恶行逐步变强,从而带来更大的欲望刺激。萨德在书中曾借恶人之口说道,恶行的程度由它所侵犯的美德来决定。恶所侵犯的准则越神圣,其罪行就越深重。从针对外在财物的偷窃转向强奸杀人,而后再进一步侵犯恩德与血缘关系……恶行确乎是在不断增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引入善恶的二元论只不过是将论证引入了诡辩的循环。在西方文化中,从原罪开始,恶曾经是违背上帝的禁令,是“不能做之事”。上帝的规定不需要逻辑或是道德来解释评判。而在此处,违背道德准则的恶,虽然仍要受到一般法律的惩罚,但本质上它已成为相对道德准则而言“不该做之事”,因而是一种抽象的“恶”。我们看到,在这一由善恶二元支撑起来的渐进结构中,恶成为道德的反向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通过让恶不断加强,萨德的书写仍处在古典话语之中。
接着,在小说第一部分结尾处对修道院的描述中,这一“恶”的渐进式增强结构抵达其顶点,欲望或更为确切地说萨德追逐欲望的努力也随之达到极致。在这个完全封闭的修道院中,四位淫僧囚禁了十几个美女以供他们享乐。满足欲望是唯一的准则,所有的受害者都被欲望的权力完全支配。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充满施虐性质的监禁密闭空间正是欲望的乌托邦的雏形,是“恶”的渐进式结构想要抵达的终点。诚然,在小说结尾处,泰雷兹最终的脱逃宣告了这一乌托邦的幻灭。然而,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将发现,萨德用以描写修道院的那些语词却成功打破了古典话语的格局,并让自己的书写来到古典话语的边界处。
那么,萨德是如何描写这个修道院的呢?借修道院中的另一个受害者翁伐蕾之口,萨德连用了好几页篇幅不厌其烦地描写修道院的结构。“六面厚厚的围墙用来向外界掩盖这座建筑的存在,”“一条曲折阴暗、布满陷阱的小道。”(Sade 1969—1977:143)在这座密闭的堡垒里,一切都是为了监禁而设计,为了灭绝一切逃跑的可能,为了填补每一道缝隙。“五十英尺高”“三十英尺深”(Sade 1969—1977:143-144),萨德甚至详尽地给出了建筑各部分的尺寸。因为在这个监禁的宏大计划中,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也不能放过。模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空隙,这些疏忽将会从内部侵蚀破坏监禁的堡垒。此时语言已不再仅通过表征的方式与事物关联。否则,简单的一句“这个建筑戒备森严,毫无脱逃的可能”,就足以指明它密闭的属性,泰雷兹所有逃跑的可能都会被断绝。事实上,当萨德喋喋不休地去叙述时,他是想要用修道院囚禁住欲望以便实现其乌托邦,这时,语言亦渴求着重新成为和物对等的存在并重新相互缠结——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那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萨德喋喋不休式的讲诉却是通过断开语言与物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实现的:修道院的描写从加强监禁出发,却不再与加强监禁的功能直接相关。“这一层有两个单人囚室,厨房,办公室……”(Sade 1969—1977:144),我们看到,叙述中相当一部分信息并不直接展示恶的权力。不过,它们仍是叙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模糊性的所有潜在风险,重要的是话语占据和照亮的空间本身。然而同时,补充细节的过程意味着更多空隙的暴露:正是翁伐蕾的描述让泰雷兹了解了修道院的结构并给了她实现逃跑计划的可能。即便如此,填补空隙的唯一方法只能是补充更多的细节。在这种诡异的循环中,泰雷兹注定将逃出修道院,修道院囚禁住欲望的方法注定将要失败。而当她成功出逃后,却发现那所谓的六面厚厚的、五十英尺高的围墙并不存在。话语曾指向的物已然消失,从始至终只有话语自身在无限地增殖,而这也就是萨德书写的现代性。
即使如此,修道院的故事也只代表第一部分的结束。小说仍将继续,伴随着渐强结构的崩塌,萨德似乎并未找到新的力量来凝聚文本。他执拗地重复着先前的故事模式,只是在具体内容上继续寻找着新的享乐方式。但这些想象力的游戏都未能跳出既有的框架,失去了监禁的密闭空间的约束,文本的力量逐渐耗散减弱,退回到古典话语的边界处。我们还可以偶尔看到一些对监禁的回溯,比如罗兰那阴森的地下洞窟,或是卡多韦勒的公馆,但是监禁的“强度”完全无法与修道院相比。语言即使保持着反复的特征,也不再是走向“反话语”的无限增殖。总而言之,萨德并未完全脱离以表征为基础的古典话语格局。在“顶点”之后,萨德的语言更多表现为一种在边界处的撕裂的张力。
在盲目地追寻顶点的途中,萨德一层层地筑起他的高塔,竭力向上接近欲望的苍穹。渐进结构的谎言,也在脱离古典表征大地的过程中被逐渐揭露。世界本没有既定的方向,而是向所有维度开放。脱离了大地也就意味着用以定位的标志不再与物相连,要追求的欲望失去了依托,变为一个无法被对象化的虚空。萨德的目标是抓住欲望,抓住不可命名的事物、写出不能写之物。所以在这片欲望的虚空中,原本从能指走向所指的单向拔升就变成了不可控的运动。渐进结构将被推翻,而萨德的书写最终变成了一种徘徊,徘徊于古典与现代话语的边界。
三、朱斯蒂娜——现代文学的阴影
在前面,我们曾将萨德构建的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反话语”的尝试进行类比,如果说萨德的乌托邦已然破灭,那么后者的境遇又如何,卡夫卡(Franz Kafka)、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马拉美等等现代作家追寻的作品的完成是否可能?萨德的界限书写究竟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泰雷兹或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福柯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将朱斯蒂娜称作“欲望的不确定对象和纯粹源泉”⑦Michel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Paris : Gallimard, 1990, p.223.,这一判断其实有失偏颇。必须要区分泰雷兹和朱斯蒂娜,作为小说故事的叙述者,她的这一身份转变也预示着古典话语的巨大变革。
泰雷兹是小说叙事的主人公,整篇叙事以泰雷兹向朱斯蒂娜讲述自身不幸遭遇的过程为基本内容:她遇见了形形色色的恶人,他们藐视一切道德准则,犯下各种可怖的罪行并从中取乐,非但没有受到惩戒,反而取得了世俗的成功。相反,美德的化身泰雷兹受到的却是数不尽的苦难:被强暴,被鞭打,被诬陷,被监禁,被判处死刑……只有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她才获得了救赎:泰雷兹的化名被识破,朱利埃特发现她就是自己的妹妹朱斯蒂娜。在姐姐的帮助下朱斯蒂娜洗清了自己的罪名,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然而幸福转瞬即逝,等待她的仍是终极的不幸。朱斯蒂娜被一道闪电劈中,当场死去。
事实上,既作为故事叙述者又作为故事主角的泰雷兹就是欲望的完美对象。她高尚、虔诚,永远维持着贞操,永远不会被恶劝诱玷污,也永远不会因屈辱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出逃只是为了逃向下次的受难,维持着追求欲望的无限反复。我们看到,叙事并不是在故事发生的空间中进行,而是从泰雷兹的叙述中流淌而出。最终,正是在泰雷兹对自身不幸的转述中,我们得以始终注视着泰雷兹,并牢牢抓住欲望的对象。
相反,姐姐朱莉埃特则与读者处于相同的位置。同读者一样,作为泰雷兹故事的倾听者,她也是随着泰雷兹的叙述一点点地发掘与肯定朱斯蒂娜的真实身份。事实上,作为读者,我们从一开始便知道泰雷兹极有可能就是朱斯蒂娜,因为小说在最开端就先叙述了这对姐妹互相分别的情境。随着故事的逐步推进,朱斯蒂娜的不在场只是让泰雷兹的身份愈发清晰,否则先前的铺垫将毫无意义。那么,叙事为何要安排一个具有“读者”功能的朱莉埃特角色?事实上,这与泰雷兹言说的性质密切相关。
泰雷兹在言说。每次遇到一位表面善良的恶人,她都会对他们倾诉自己过去的苦难。而恶人终将撕下他们的假面,继续折磨她。新的苦难经历又会进入泰雷兹下一次面向新的恶人的倾诉,如此膨胀增殖。所有这些倾诉并不会占据过长篇幅,除了这最后一次对朱利埃特的诉说。这也就是小说的全部内容。为什么是这一次?是什么力量将我们指引到这独有的一次叙事,这构成小说全部内容的一次诉说,道出一切真相的诉说?要开始写作,“即传播那种无法停止说话的东西……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强制其沉默”⑧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在小说的叙述开始之前,即和朱利埃特相遇之前,泰雷兹倾诉的话语就一直在无止境地自我增殖。朱利埃特打断了泰雷兹原本无始无终的言语——揭开朱斯蒂娜的身份,结束她的受难。无休止的诉说于是被中断,并成为了似乎是最后一次的决定性的话语。在这一中断引起的沉默中,那话语才能向我们敞开。泰雷兹的倾诉才能走出它的沉默,使写作亦或小说成为可能。揭示身份的叙述成了开启小说叙述的先决条件。正如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说:“只有达到了这个时刻,才能写作,而人们只能在这个由写作的行动打开的空间中趋向于这一刻。”⑨同上,第178页。叙述的语言在无尽的自我折返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反话语”空间。显然,泰雷兹的叙述已经有了现代文学空间的雏形。
与此同时,当泰雷兹的身份逐渐被自己的叙事所消解,成为朱斯蒂娜之时,欲望的对象也消失了。朱斯蒂娜得到了姐姐的庇护,远离了一切恶的侵袭。她不再被叙述,不再被注视,不再能承载一丝欲望,不再能引动僭越的力量,于是她将被闪电毁灭,因为朱斯蒂娜对欲望的游戏来说已经丧失了价值。泰雷兹的消失比修道院的幻灭更为决绝,它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预演了表征在古典时代末期的消亡。
朱斯蒂娜的死亡不仅意味着小说的结局,同时也意味着欲望乌托邦的完全幻灭。对于现代文学的困境,泰雷兹给出的答案相当简单。要避免这一失败,就只能一直逃避朱斯蒂娜身份揭晓的时刻,让泰雷兹的叙述无限地继续,让欲望的旅程永不终结,永不停歇地写下去,最终只存话语在修道院中,在这无法完结之处无休止地增长。正如布朗肖所言:“写作就是永无止境,永不停歇。”⑩同上,第8页。
结 语
《美德的不幸》一书以一种保守的姿态作为起点,一步步向我们展示了萨德如何从古典话语出发逐渐到达其与现代话语的边界处。萨德从欲望的对象出发,通过反复的僭越,尝试突破隔阂以达到欲望本身,最终只是将自己撕裂。要避免这一失败,就只能永不停歇地写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萨德的书写超越了一般的道德伦理问题而成为一种界限书写,他在古典时代的末尾就已窥见了现代文学的困境。我们曾经以一种传统的批评姿态,指责其理念的道德败坏,但是不必质疑其作品中所谓“文学价值”的缺乏,因为萨德的作品本身就是对我们的道德体系以及传统文学价值体系的挑战。萨德所欲注视的,只是那完美的欲望,其界限书写正是不断迫近那乌托邦的中心点的努力,而如今,当写作已是“永无止境,永不停歇”之时,或许作家的职责正是让泰雷兹开口倾诉,让话语流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