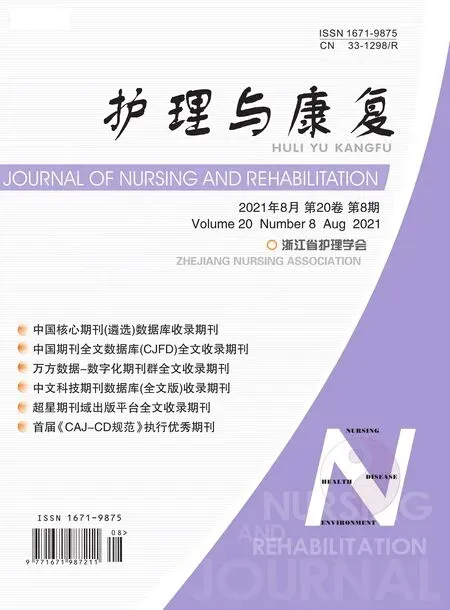医疗不良事件中第二受害者干预现状的研究进展
冯 楚,黄丽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杭州 310003
医疗不良事件也称患者安全事件,是指可能或已导致患者不必要的人身损害的事件[1]。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导致不良事件难以避免。WHO指出,每10例住院患者中就有1例患者可能受到伤害[2]。同时,由于人们对医学的完美性抱有很高的期望,不良事件往往被视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个人失败[3],这导致发生不良事件后医护人员产生较大的内疚、挫败感和自我怀疑,进而影响工作效率、增加医疗差错[4]。2000年,学者Wu[5]首次提出第二受害者(second victim)这一概念,以解释与工作相关的不良事件对医护人员的影响,概念中提到:医疗保健中不良事件的第一受害者是患者和家属,他们受到直接的创伤,而医疗服务提供者是第二受害者,他们心身同样在不良事件中受到伤害。本文对第二受害者的定义、第二受害者受到的影响、我国干预现状、国外医疗不良事件中第二受害者的干预支持模式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医院管理者制定第二受害者干预计划提供参考。
1 第二受害者概念界定
第二受害者最初由Wu提出,但未给出正式的定义。Scott等[6]在2009年给出了一个正式的定义,即第二受害者是在非预期的不良事件、医疗错误或与患者相关的事件中受到心身创伤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随着国际上对第二受害者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及第二受害者概念的持续发展,Wu等[4]在近年再次探讨了涉及不良事件的临床医生的相关术语,并发现使用最广泛的一词是“第二受害者”,并且已得到广泛认可,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医院管理者而言,“第二受害者”意味着倡导和立法所需的紧迫性。
2 医疗不良事件对第二受害者的影响
不良事件的发生对医护人员造成了严重的心身伤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护人员的生活质量,对医疗机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良事件发生后支持第二受害者已经成为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重要议题[7]。经历不良事件后第二受害者身体可能会出现疲惫、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失眠等症状,心理上可能会出现内疚、紧张、焦虑、自我怀疑、恐惧、抑郁等负面情绪,甚至产生职业倦怠、缺勤、离职等,有些人还会滥用药物、酗酒,甚至自杀[3,8]。Kobe等[9]对加拿大放射治疗师的研究显示,在经历了不良事件后,放射治疗师往往感到内疚、焦虑,以及对职场的自我怀疑、职业信心不足和羞耻感,部分人会在短期内难以胜任原来的岗位。Kaur等[10]报告了不良事件对第二受害者身体方面的影响,包括失眠、重复生活事件、难以集中注意力、日常活动失去兴趣等。此外,Burlison等[11]研究了第二受害者现象与工作的相关性,指出第二受害者会担心受到诉讼和惩罚,导致丧失职业信心、工作满意度下降、缺勤,甚至离职,这些症状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在组织方面,主要表现为对工作的满意度下降,影响团队合作,增加医疗差错,导致医疗护理质量下降[11-12]。这样可能会导致工作产出减少、在职人员流失增加,影响整个组织的发展。Vanhaecht[13]等发现,不良事件对有效的团队合作也有影响,最常见的是医护人员对知识和技能的怀疑,无法提供优质护理,导致团队凝聚力下降。Quillivan等[14]指出,第二受害者经历可能会引发恶性循环,导致进一步的医疗错误,影响患者安全。此外,由此带来的工作满意度下降迫使很多医生提早退休或放弃医学。据估计,更换医生的直接招聘成本和费用可能高达85 000美元,收入损失超过100万美元[15]。每位注册护士流失成本从44 380~63 400美元不等,美国医院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421万~602万美元[16]。医疗机构可能通过医疗错误的财务成本、第二受害者的人员流失以及未来医疗错误的增加而成为第三受害者[17]。
3 我国对第二受害者的干预现状
我国对第二受害者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处理不良事件时,医院管理者关注更多的是不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分析和防范措施[18],对第二受害者心身健康的关注尚不普遍。在经历了不良事件后,医护人员的情感是脆弱的,他们渴望得到外界的支持与帮助[19],包括个人支持和机构支持,即时支持和长期支持,文化、制度方面的支持和情感支持等。充分有效的支持能够帮助第二受害者恢复心身健康,更好地投入工作,保障患者安全[20]。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步开展了对经历不良事件后医务人员的研究,但只处于调查我国的医务人员作为第二受害者体验的现状[21],国内医疗机构尚未建立正式的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
4 国外第二受害者的干预模式
4.1 医学创伤支持服务(medically induced trauma support services,MITSS)
MITSS于2002年成立,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不良事件后患者、家庭和临床医生负性情绪的认识,并通过网络向美国各地的第二受害者分享支持资源的非营利性组织[22]。2010年MITSS开发了一个工具包,包括成功情感支持模型的10个模块:内部安全文化,组织意识,多学科咨询委员会,领导层的认可,风险管理的考虑,政策、程序和实践,操作可行性,员工培训,沟通计划,学习改进机会。每个模块描述了具体的行动策略,并提供一些参考资源,共包括55个行动策略和95篇参考文献,可供免费下载或在线使用。通过参考这些模块的内容,医疗机构能够在支持第二受害者过程的多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并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制定干预流程。MITSS在发布后的一年,38个国家访问了MITSS的网站,并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多数人觉得工具包是有用且受益的。MITSS的成效也受到认可,曾获NPSF Socius奖等多项医疗安全领域奖项[23]。MITSS网站资源丰富,获取资源方便快捷,可为我国医疗机构制定第二受害者支持计划提供借鉴,但需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各模块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4.2 布莱根妇女医院同伴支持计划(peer support program)
由布莱根妇女医院启动的小组同伴支持计划,以支持发生手术不良事件后的医护人员,由外科医生、麻醉师和护士组成的多学科团队经培训后为第二受害者提供团体支持,根据不良事件类型的不同,向第二受害者提供一对一支持或团体支持[24]。同伴支持者主要通过自我推荐并经科室提名的医生和护士组成。该计划培训了60多名医生和护士,详细介绍了同伴支持的原则以及同伴支持中常见的陷阱。当发生不良事件后,医院风险管理部门、第二受害者的同事或科室负责人等会通知同伴支持者的负责人;负责人根据第二受害者的年龄、性格、资历等匹配合适的同伴支持者;同伴支持者主动积极倾听第二受害者的经历,分享自己的经验,并一起讨论第二受害者的个人应对策略;无论第二受害者情况如何,同伴支持者都向其提供其他资源如心理医生或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的联系方式,让第二受害者了解其并没有被孤立。整个支持过程是保密的,无任何记录,且同伴支持者不会是负责调查该不良事件的人或是第二受害者所在科室的负责人。若第二受害者拒绝接受同伴支持者的主动帮助,同伴支持者尊重其选择,并向其发送有关应对策略和其他资源信息的电子邮件,让其知道如果将来有任何需要,可以向其提供支持。在计划实施的4年期间,该计划的同伴支持者共提供了220起一对一的支持服务,平均每月4~5起,其中有135名(61%)第二受害者来自急诊科、产科、外科或麻醉科,同时为240名临床医生提供了团体支持。但是,该同伴支持计划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其覆盖面不够广,例如门诊医生或一些小科室的临床医生很可能得不到帮助,且该计划不能像处理急性不良事件那样有效地处理慢性压力。我国医疗机构若需借鉴该计划,可能需要从每个科室中选拔1~2名医护人员组成同伴支持者团队,并需要改变医护人员传统的惩罚性文化,消除机密性和耻辱感方面的顾虑,卸下担心受到批评指责的思想包袱,自愿接受同伴支持者的帮助。
4.3 密苏里大学医疗保健系统(University of Missouri Health Care,MUHC)的forYOU计划
2009年,MUHC部署了第二受害者快速响应小组,称为forYOU计划。ForYOU团队主要由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等组成,以Scott等[25]的3级支持模型为理论依据提供情感支持。第1级为科室支持,所有工作人员都接受第二受害者现象、识别第二受害者和为潜在第二受害者提供初步支持的相关培训,以在第二受害者出现痛苦时提供即时情感支持。约60%的第二受害者能在第1级获得足够的支持。如果第1级支持不足,则启动第2级同伴支持,由经过专业训练的forYOU团队成员为第二受害者提供支持。这些同伴支持者接受18 h以上的课堂教学、小组讨论和模拟训练,主题包括第二受害者文献概述、团队的研究结果、与第二受害者反应相关的高风险事件、第二受害者6个阶段的恢复轨迹、理想支持的8个主题、团队的3级支持模型、关键时刻的处理技巧、主动聆听技能、使用关键事件压力管理技术进行一对一保密危机干预、团体支持中的支持角色以及第3级支持中的转诊程序。这些同伴支持者被战略性地安排在临床高风险科室和各种班次中,以持续观察同事是否出现第二受害者反应,通过提出适当的问题和倾听,迅速为第二受害者提供一对一支持。必要时,同伴支持者可以为第二受害者推荐医院内部的其他资源,如在事件发生后或机构调查时向患者安全专家寻求支持,或在法律诉讼阶段,向风险管理部门寻求指导和长期援助。约30%的第二受害者能在第2级获得足够的支持。如果第2级的支持团队认为第二受害者的需求超过了他们的帮助能力,则启动第3级支持,将第二受害者转交给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员工援助计划人员等,该级别必须确保第二受害者快速、有效地获得专业支持和指导。3级支持人员是2级同伴支持团队的成员和导师。据估计,10%的第二受害者在精神受创伤后的某一时刻需要接受第3级支持和指导。ForYOU团队每周7 d、每天24 h为第二受害者提供支持,成员每个月开会1次,进行案例分享和持续学习,以不断提高对第二受害者的支持能力。截至2016年,超过1 075名医护人员接受了团队的支持[26]。MUHC花了近3年时间部署同伴支持计划,规模庞大,成效显著,但实施forYOU计划任务艰巨,我国医疗机构若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资源,医院管理部门没有巨大的决心,将存在较大的实施难度。
4.4 约翰霍普金斯的压力事件复原同伴响应计划(resilience in stressful events,RISE)
2010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第二受害者制定了RISE,首先在儿科部门试点,然后扩展到整个医院[27-28]。RISE的领导团队由患者安全主任、患者安全研究员、风险管理师、医生、护理管理者等组成。来自不同学科的医生、护士和其他技术人员组成响应者团队,为所有第二受害者提供一对一或小组形式的心理急救。根据组织领导者的建议及为同事提供支持的能力,同伴响应者自我推荐并提交申请,由RISE执行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后,所有同伴响应者需参加6 h的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PFA)培训、每个月的RISE团队会议和对第二受害者实施支持后的总结会。PFA培训包括反思性倾听、评估、优先排序、干预和处理;团队会议每次持续1 h,以讲座、讲故事、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的形式呈现,内容包括对第二受害者相关文献讨论、PFA实践练习以及案例汇报。总结会上,同伴支持参与者会汇报对第二受害者实施支持的过程,供其他响应者学习,并开展集体讨论以优化后期的支持方案。RISE计划设置了双层呼叫系统,每周7 d、每天24 h都有2名同伴响应者值班。当发生不良事件后,受影响的同事主动传呼RISE团队,接到传呼的同伴响应者在30 min内回电,并在12 h内计划与呼叫者会面。会面明确关注对方情绪而不是事件的细节。会面结束时,同伴响应者提供可能有助于持续恢复的组织资源,例如员工援助计划、社区咨询等。RISE计划实施后的52个月内共接到119个电话,涉及约500人。87.8%的同伴响应者认为他们满足了第二受害者的期望,为其提供了有效的心理急救服务。RISE计划规模适中,实施难度适宜,但第二受害者主动寻求帮助需要克服耻辱感、对服务机密性及可能受责备、处分等的担忧[29],由于我国目前对第二受害者认识不够深刻,医护人员工作繁忙,无法抽出足够时间来处理自身情绪等问题[30],实施RISE计划可能存在阻力。
4.5 西班牙的减轻第二受害者影响(mitigating impact in second victims,MISE)在线项目
2017年,西班牙研究人员开发了MISE在线项目[31],是西班牙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关注第二受害者的首批举措之一。MISE针对医院和初级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提供关于第二受害者信息的在线培训。培训形式丰富,包括文本、图像、便携式文档格式、带有语音旁白的PPT演示文稿、视频等。培训内容含信息和示范两大模块。信息模块内容包括患者安全事件(近似错误、不良事件)的定义,第二受害者的相关研究、机构援助计划、西班牙卫生部患者安全战略,以及第三受害者的相关研究等。示范模块内容包括不良事件影响的演示文稿,不良事件后采取的行动建议指南,与患者和家属沟通的演示视频,照顾第一受害者的示范,管理者沟通、同伴和管理者支持第二受害者的演示视频,以及因系统故障导致错误后的预防措施、根本原因分析的演示文稿等。MISE在线项目通过了专门评估健康网站的质量评价机构的认证,其内容的可理解性和实用性也得到了医务人员的积极评价。MISE在线项目设计简单、操作方便、内容体系完整,可在单位或家中进行上网访问,并根据不同的需求灵活选择相应内容进行学习。我国可借鉴MISE计划开展第二受害者知识的在线培训,但需把培训内容本土化,符合我国的患者安全战略政策、医疗机构的工作模式及医患沟通习惯。
4.6 皇家布里斯班妇女医院同伴支持计划
2018年,澳大利亚皇家布里斯班妇女医院开发了针对麻醉师的同伴支持计划,为经历不良事件的麻醉师提供第二受害者支持[32]。该同伴支持小组由协调员和响应者组成,协调员负责方案的日常运行,包括选择和培训响应者、提供所需资源,组织人员跟进,安排每月同伴支持小组会议,会议成员是与该计划有关的主要负责人。响应者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受人尊敬、富有同情心、不带偏见的麻醉师,需参加由心理学家量身定制的4 h心理急救培训课程,内容包括识别行为预警信号,扩展积极倾听技能,处理复杂情绪对话,告知现有的医院和社区支持资源以及心理学家转诊的指征和途径。协调员在麻醉部门会议上介绍该方案,并在茶水间和手术室张贴事件处理流程及写有协调员和所有响应者联系方式的海报。由于轮班工作,以及在工作时间以外似乎更高发严重不良事件,第二受害者并不能总是在事件发生后24 h内联系到同伴支持小组工作人员,后来将最初的24 h干预时间延长至48 h。当发生不良事件时,最资深的麻醉师将在场麻醉师姓名和事件概述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协调员,协调员收到信息后与响应者团队联系,分配任务。响应者在48 h对当事麻醉师予面对面或电话、短信干预,之后分别在事件发生后1周和1个月跟进,以了解麻醉师的心理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每位响应者最多同时跟进3名第二受害者。跟进期间如果第二受害者需要持续支持,可协助其转诊至心理学家处。该计划具有保密性和自愿性,可在任何时候为员工提供安全、非评判性的支持,且无需向主管或行政部门提供讨论或反馈。我国医院管理者若采用该计划,并逐步推广至麻醉师以外的医疗群体,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资源,以不断跟进和随访,且需完善除面对面干预以外的电话、短信干预,以提高效率。
4.7 薰衣草代码(code lavender)
研究表明,薰衣草具有镇定作用,可缓解压力和焦虑[33]。薰衣草代码最初主要是为经历危机情况的患者和家庭提供帮助,此后该概念被多家医院采用,以为遭受创伤或危机情况的患者和员工提供支持。根据不同的需求,薰衣草代码干预包括按摩疗法、音乐疗法、放松或呼吸练习等。圣地亚哥的一家医院对薰衣草代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试点研究[34-35]。研究团队包括志愿者、医院员工和管理人员等,在确定干预方案后,研究人员在院内张贴告示,告知医院员工该研究正在进行中。由心理学教授对感兴趣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提供2 h的培训课程,旨在描述如何通过自我护理和同情行为来应对继发性创伤压力,并对薰衣草代码研究项目进行解释。该项目主要是一个标识为“Code Lavender”的护理包,为一个4英寸(10.16 cm)×3英寸(7.62 cm)的薰衣草色网状抽绳袋,袋子里装有一个薰衣草香薰小瓶,可以通过闻香薰气味以镇静心神;一块巧克力,可以增加积极的感官体验;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鼓舞人心的名言;一张淡紫色的小贴纸,如果员工选择粘贴贴纸,表明其正在经历特别艰难的一天。研究团队共同组装护理包,并将其放置在医院中央容易到达的地方,如果员工遇到了工作压力或在不良事件中受到了伤害,可以自取使用。在干预3个月内,医院员工共使用了500个护理包(每包成本为1.20美元),接受基线调查的83名员工均表示对自己有所帮助,其中的84%向他人推荐了该护理包。薰衣草代码干预不需要安排太多人力进行面对面干预,使用者也不会产生机密性、耻辱感方面的顾虑,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为遭遇压力或情绪创伤的第二受害者提供支持,但是长期使用薰衣草代码需要资金支持。我国医院管理者若借鉴薰衣草代码,需得到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同时需追踪护理包的使用者,评价干预效果难度较大。
5 结语
第二受害者体验对受害者本人、患者安全和医疗机构都有着负面的影响。有效的支持能帮助第二受害者更好地从不良事件中恢复。国外较多医疗机构建立了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操作难易程度不一,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成本不同。我国可选择性地借鉴国外经验,加强非惩罚性文化建设,构建支持性医院组织文化,建立本土化的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为第二受害者的心身健康及职业发展提供及时、专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