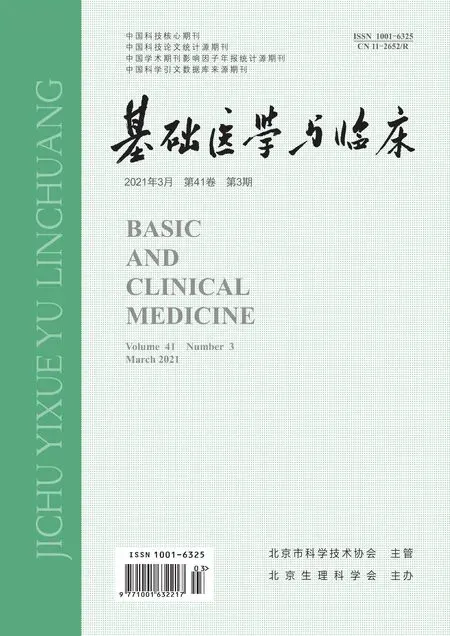代谢相关生物学标志物在老年人衰弱中的研究进展
潘一鸣,李 耘,马丽娜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老年医学科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北京 100053)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老年人健康保障方面需求突出。在老年人群中,衰弱(frailty)是公认的健康问题,表现为人体内多个系统生理功能和储备的进行性下降,会增加残疾、死亡等不良事件发生的风险,从而导致老年人对长期照护需求和医疗费用的增加。衰弱具有潜在的可逆性,若能早期诊断衰弱并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将有益于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减轻医疗保健系统负担。发现特异敏感的衰弱生物学标志物是实现其早期诊断的关键,而衰弱个体中存在的代谢紊乱是标志物研究的理想切入点。本文将从能量代谢、肌肉代谢、骨骼代谢和激素代谢层面对衰弱的生物学标志物分别进行阐述。
1 衰弱的定义与评估
衰弱是一种与增龄相关的综合征,伴随着多种生理功能和应激能力的减退。实践中对于衰弱的界定主要依赖于各种评估工具,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但不同的衰弱识别工具差别很大,且认可度不一。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有两种。一是衰弱表型(frailty phenotype,FP)[1],将衰弱视为一种生物综合征,包含以下5个要素:不明原因体质量下降、疲劳、握力下降、慢步速和运动量降低。若符合3项或以上,可判定为衰弱;只符合一项或两项,为衰弱前期;不符合任何一项,则为健壮。另一是衰弱指数(frailty index,FI)[2],认为衰弱存在多维性,可基于多项与年龄相关的健康缺陷的累积程度来识别衰弱,例如合并症、心理因素、症状和残疾等。
2 衰弱早期诊断的意义
衰弱在老年人群中有着较高的发病率。在≥60岁的社区居民中,衰弱发生率为60.6/1 000人/年[3]。衰弱会导致老年人应激脆性增加,出现失能、认知障碍、住院和死亡等不良结局。
个体可以在衰弱、衰弱前期和健壮之间相互转化,说明衰弱是可以进行有效干预的。在衰弱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能对衰弱潜在生物途径的识别起到帮助,并能为衰弱的干预和管理提供机会,对衰弱的早期诊断、治疗决策和疗效评价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迫切需要开发出有效识别衰弱的诊断策略,不断进行创新、实用、可靠的衰弱生物学标志物研究和评价工作。
3 衰弱的代谢相关标志物
衰弱综合征会伴有多个器官及系统生理功能的下降,表现出生理代谢的紊乱,如胰岛素抵抗、肌少症和骨质疏松等。因此很多研究试图以代谢作为切入点,验证相关标志物在衰弱诊断中的价值。衰弱的代谢相关生物学标志物可大致分为以下4类:
3.1 能量代谢
在能量代谢紊乱的机制中,胰岛素抵抗的作用不可忽略。糖尿病与衰弱风险增加有关,这种关联一方面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肥胖所引起,另一方面更可能是由血糖控制不佳及血脂分布异常所致,而胰岛素抵抗是其潜在机制。胰岛素抵抗的发展几乎完全是由年龄相关的身体成分变化所引起的,即使在没有糖尿病的个体中,胰岛素抵抗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从而促使机体出现衰弱。因此,胰岛素抵抗相关的标志物是衰弱理想的研究靶点。
3.1.1 瘦素:瘦素(leptin)作为一种通过抑制饥饿以维持能量平衡的激素,可以促进骨骼肌的脂肪酸氧化,其水平与衰弱相关。瘦素浓度越高,老年人衰弱的风险越大,其机制可能涉及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性反应[4]。
女性循环瘦素水平升高还与步速下降有关[5],而慢步速正是衰弱表型的要素之一。由此可见,瘦素可能是衰弱的候选标志物。
3.1.2 脂联素:脂联素(adiponectin)是一种多功能脂肪因子,具有胰岛素增敏、抗感染、代谢调节等作用。在日本老年人中,脂联素升高与衰弱相关[6]。同时,在中国老年人群中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并且发现脂联素水平与握力呈负相关,从而表明脂肪因子可能是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脂联素抵抗则可能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关键机制[7]。
另外,脂联素与衰弱的关联似乎在男性中比女性中更强,但血清脂联素在女性和男性中的关联指标不同:在女性中,脂联素浓度的独立阴性预测指标是肌肉量和焦虑水平;而在男性中该指标则是认知功能[8]。这也体现了衰弱生物标志物中性别差异的存在。
然而,在老年癌患者中却并未观察到脂联素与衰弱的相关性[9]。这可能与该研究特殊的受试人群(癌患者)和衰弱评估工具(G8)有关。
此外,在动物试验中,衰弱的白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基因敲除小鼠的血浆脂联素水平较低[10],与人类研究结论相反。因此,脂联素水平在老年人衰弱中的作用仍需深入探究。
3.2 肌肉代谢
鉴于老年人衰弱的特征,肌少症可以作为衰弱的生物基质。肌肉蛋白质更新的标志物可能与衰弱的诊断有关,如3-甲基组氨酸(3-methylhistidine,3-MH)、Ⅲ型胶原蛋白的N末端肽(procollagen type Ⅲ N-terminal peptide,P3NP)和骨骼肌特异性肌钙蛋白T(skeletal muscle-specific troponin T,sTnT)等。
3.2.1 3-MH:3-MH(3-methylhistidine,3-甲基组氨酸)作为肌动蛋白的一种成分,是肌原纤维蛋白水解的标记,是肌少症发展的分子机制之一,其水平在整个生命中都保持恒定,因而可能是研究骨骼肌蛋白与年龄相关变化的良好生物标志物。在衰弱的老年人中可以观察到3-MH水平升高、肌肉量降低,表明衰弱时会出现肌肉蛋白分解代谢加剧,3-MH以及3-MH/肌酐(3-MH/Cr)和3-MH/估计肾小球滤过率(3-MH/eGFR)或许是识别衰弱及衰弱高危个体的潜在标志物,可以协助早期诊断[11]。而3-MH的来源肌动蛋白(myokines)也有作为衰弱标志物的潜力[12]。
3.2.2 P3NP:P3NP(3型前胶原肽,procollegen type Ⅲ N-terminal peptide)是在肌肉胶原蛋白合成过程中释放的一种肽,其含量增加不仅是肌肉生长的标志,也是肌肉修复和纤维化的标志。绝经后女性的血浆P3NP水平与肌肉质量相关,故可作为衡量肌肉状态的生物标志物[13],但在男性中并未观察到这一关联,该标志物具有性别差异。
3.2.3 sTnT:sTnT(慢型肌钙蛋白T,slow froponin T)是肌肉消瘦的潜在标志。衰弱患者的sTnT水平升高,但抗阻运动训练可以显著降低衰弱患者的sTnT水平,并能预防肌肉萎缩、提高身体机能[14]。血清sTnT水平有望成为评价衰弱患者肌肉健康的新标志物。
3.2.4 其他:在衰弱中许多肌肉代谢相关因子也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经典补体途径的信号分子补体蛋白C1q可通过年龄依赖性方式激活Wnt信号通路,从而诱导肌肉纤维化。血清C1q水平可能反映了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肌肉质量和力量的丧失,因而具有作为肌少症的新型标志物的潜力[15]。在衰弱标志物的研究中,C1q可能也存在潜在价值。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是对肌肉具有合成代谢作用的循环激素。衰弱老年人的循环IGF-1水平较低[7]。IGF-1可作为社区居住的老年女性中患衰弱和肌少症者性别特异的生物标志物[16]。
肌生长抑制素(myostatin)是转化生长因子β超家族的成员,是肌肉生长的内源性抑制剂。其循环水平与老年男性的衰弱程度呈负相关[16]。但对长期居住在疗养院的人群进行的另一项单盲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却发现,男性受试者身体素质的改善与肌生长抑制素浓度的增加呈正相关[17],这与对肌肉生长抑制素功能的预期恰好相反,因此其与衰弱的关联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3.3 骨骼代谢
3.3.1 维生素D:人们逐渐认识到了骨代谢对衰弱老年人的影响,而衰弱中骨代谢的研究最先开始于维生素D。维生素D是一种脂溶性类固醇,是由7-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照射下于皮肤中形成的,有增加肠道对钙、镁和磷酸盐的吸收的功能。3年内低维生素D摄入与衰弱之间存在纵向相关性[18]。也有横断面研究认为I型胶原蛋白的N末端肽(procollagen type Ⅰ N-terminal peptide,PINP)和维生素D可作为衰弱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和干预目标[19]。随后,一项对9 030名受试者进行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维生素D水平可以强烈预测衰弱个体的死亡风险[20]。因此,通过口服维生素D进行营养补充,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并治疗衰弱,已在《亚太衰弱管理临床操作指南》中得到了推荐。
3.3.2 骨保护素:骨保护素(osteoprotegerin,OPG)是骨组织中核因子Kappa B配体的受体激活剂的抑制剂,对调节破骨细胞分化和功能发挥重要作用。OPG与步速较慢有关,与衰弱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21],因而OPG也可被用作老年衰弱的标志物。
3.3.3 循环骨祖细胞:人们还在循环中发现了一个干细胞种群,称为循环骨祖细胞(circulating osteog-enic progenitor cells,COP cells),是骨髓干细胞的替代物。COP细胞不仅具有形成骨骼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形成其他间充质组织的能力。循环中的COP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较低的COP细胞百分比(%COP)与衰弱、残疾和健康状况较差有关,且%COP越低的受试者越容易变得衰弱[22]。但%COP与衰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还有待进行纵向研究。
3.4 激素代谢
在衰弱相关的诊断和监测中,激素与其他类型的生物标志物相比,具有多个优势:激素功能测试成熟且简单,临床应用广泛,并且具有正常参考范围;此外,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反映疾病的潜在机制。
3.4.1 皮质醇:皮质醇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的主要激素,可用于调节环境、生理、心理和社会压力对机体的影响。妇女健康与老龄化研究(Women’s Health and Aging Study)检测了受试者唾液皮质醇水平,发现衰弱老年女性体内皮质醇平均水平较高,且昼夜变化较小[23]。随后,德国一项衰老研究项目对老年男性和女性均进行了唾液皮质醇测定,发现皮质醇昼夜变化减少与衰弱表型相关,并提出昼夜皮质醇比率可作为标志物衡量衰弱程度[24],表明HPA轴功能与衰弱之间存在关联。血清皮质醇浓度升高也与衰弱负担增加相关,结果支持年龄相关的HPA轴失调与衰弱状态相关的假说[25]。但皮质醇在衰弱中发挥的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3.4.2 性激素:性激素在衰弱中的作用也开始被重视起来。衰弱的老年男性睾丸激素水平会降低,而衰弱的绝经后女性体内的雌二醇水平会升高。而脱氢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DHEA)作为一种类固醇激素,既是睾丸激素的前体又是雌激素的前体。DHEA的水平在衰弱老年人中有所下降[26],说明性激素及其前体也可能在衰弱中发挥了作用。
4 问题与展望
衰弱是老年人群中常见的一种综合征,表现为机体储备和应激水平下降,随后出现跌倒、失能、认知障碍等不良结局。生物标志物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更快、更准确地识别衰弱患者,并给予针对性地干预,以减轻甚至避免不良结局的发生。
但目前衰弱标志物的研究领域仍存在许多问题。首先,衰弱的发生机制不明,也尚未发现特异、敏感、可靠、可应用于临床的生物标志物。鉴于衰弱中存在多个层面的代谢异常,故从代谢相关标志物着手或许更易有所发现,也可进一步为衰弱机制的探索提供思路和理论基础。其次,衰弱综合征涉及多个系统的功能恶化和储备能力下降,其固有的复杂性意味着不能应用单一的标志物来识别和评估衰弱。未来研究应着眼于寻找衰弱特异性的标志物组合,以提升诊断效力。另外,纵观前述研究结果,可见某些代谢相关标志物存在性别差异,在后续的研究设计中也应将该因素考虑在内,做好性别匹配或分别进行分析,减少相关偏倚,并可深入探究衰弱中的性别差异机制。随着检验手段的进步,未来还可对血液、尿液、肌肉、唾液、汗液等多种生物基质进行检测,从而更全面地描述老年衰弱人群的代谢特征,以进一步指导衰弱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最终实现延长老年人健康寿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