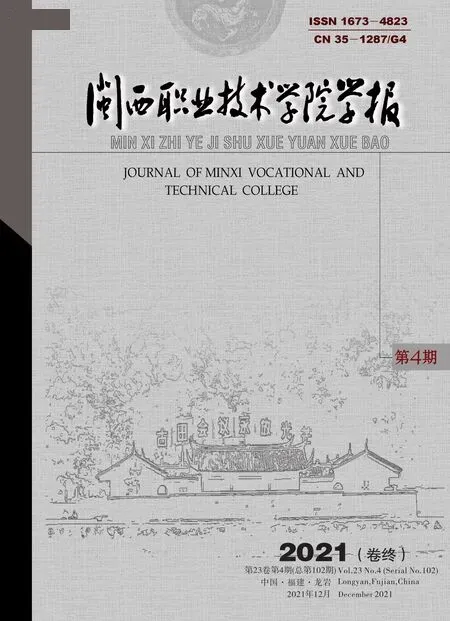奥尼尔早期戏剧创作的空间表征与伦理诉求
——以《安娜·克里斯蒂》为例
詹舒丹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00)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美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一生创作了五十余部戏剧作品,曾四次赢得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一位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这样评论他,“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奥尼尔之后,美国才有戏剧”[1]。 《安娜·克里斯蒂》作为奥尼尔的早期代表作, 融入作家个人丰富的海上生活体验, 体现奥尼尔戏剧创作的突出特征——对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安娜·克里斯蒂》主要讲述老水手克里斯为了避免女儿安娜重蹈家族命运的覆辙,将安娜从小寄养在内地农庄里,远离大海,希望她与陆地上具有稳定工作的人结婚, 然而长大的安娜还是来到海上,还与爱尔兰裔水手马特相爱结合。
国内学界研究奥尼尔戏剧创作的视角比较多样,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对于早期创作的《安娜·克里斯蒂》关注度较低,研究多集中在女性主义解读、主题意象分析、作家悲剧意识,以及中国甬剧《安娣》对《安娜·克里斯蒂》的跨文化戏剧改编,尝试运用文学伦理学解读该剧的只有一篇。 本文运用空间理论和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解读《安娜·克里斯蒂》的三种空间意象,分析戏剧文本中不同的空间与人物伦理诉求的建构关系, 从而探讨奥尼尔早期戏剧创作特征。
一、克里斯:空间表征与伦理困境
“什么样的居住空间,就能锻造出什么样的身体与习性,习性是空间的产品。 ”[2]《安娜·克里斯蒂》中的大海和陆地是相互对立的空间意象, 象征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大海属于自然空间,陆地属于社会空间;大海是宏阔的、动荡的,充满各种变数,陆地是稳定可靠的,充满诱惑;海上生活孤独寂寞,陆上生活温暖幸福。 对大海和陆地的不同看法是克里斯与安娜产生矛盾的焦点。“空间对个人具备一种单向的生产作用,它能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个体”[2],大海和陆地所代表的不同伦理环境塑造出迥异的性格。同时,同为大海塑造的产物,马特和克里斯在性格上也有许多不同:马特是纯正的海洋之子,乐观、坚韧、不惧挑战,身上的血性赢得安娜的倾心;克里斯徘徊在大海和陆地之间,过着漂泊无定的异乡生活,身处社会底层,无所依靠,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无所归属。奥尼尔将自身的海洋生活体验融入戏剧创作,通过描绘克里斯在大海和陆地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展现底层水手的孤独和艰苦。
伦理困境指文学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 伦理困境往往是伦理悖论导致的,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3]。 在《安娜·克里斯蒂》中,克里斯始终处在亲情伦理困境之中。 克里斯出生在瑞典一个世代以航海为业的水手之家,他的祖辈至亲除一人之外全部丧生于海中, 家族中的女人饱受孤寂,母亲和妻子临死之际他远航在外,没有尽到应尽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在克里斯看来,大海是人生悲剧的根源,是“老魔鬼”的存在。为了避免安娜重蹈家族不幸命运,他违背亲情伦理,将安娜寄养在内地农庄家庭,15 年来从未去看望过女儿, 在安娜成长过程中,缺席父亲的角色。克里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安娜远离大海,与陆地上具有稳定工作的人结婚,便是最好的安排,毫不顾及安娜内心真实的意愿。缺失的父爱在父女之间形成无法弥补的裂痕,“只是——见到了你,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真有趣。你简直就像——一个陌生的人”[4]。 无依无靠的安娜只好来到海上,与父亲一起生活,并在海上与水手马特相识相爱。是眼睁睁看着安娜嫁给一名水手为妻,重复她母亲孤独不幸的命运, 还是坚决否认他们的爱情,破坏安娜的幸福,使父女关系进一步恶化? 克里斯不可避免地陷入伦理两难的处境之中: 难以作出选择,一旦作出选择,就往往导致悲剧[3]。剧本在安娜袒露自己在内地倍受欺辱沦落风尘的遭遇中迎来高潮,也将克里斯遭遇的亲情伦理困境推向顶峰,现实理想的破灭、对女儿的负罪感击垮了他,使他选择自我放逐, 通过与远洋航行公司签订新的合同来逃避现实。克里斯不缺乏伦理意识,但更多时候他不是忘记作为父亲的伦理身份, 就是逃避这一身份赋予的伦理责任和义务,而将一切过错归结到大海的头上,始终没有认识到父爱的缺失是造成安娜痛苦和不幸的根源,“难道你就不明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跟你过去常做的还是一样的吗?你不明白吗?”[4]克里斯遭遇的亲情伦理困境归根结底在于他的逃避, 而非所处的大海空间。
同时,克里斯还遭遇职业伦理困境。《安娜·克里斯蒂》 展现以克里斯为代表的底层水手孤独艰苦的怪圈式生活:他们辗转于世界各个码头和水滨区,在海上干最糟糕的活, 上岸随意挥霍掉用生命代价挣来的微薄工资后,不得不踏上新的海上之旅,过着长期远离家人漂泊无定的异乡生活。 大海使青年克里斯迷失了生活方向, 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过着纵情声色的堕落生活,忘记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酒醒之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却为时已晚, 克里斯只能通过诅咒大海来宣泄自我的愤怒,他憎恨大海,却无法摆脱大海,迫于生计只能从事海上工作。他知道自己的诅咒软弱无力,只是他无法更改已有的生活轨迹,更无法在他的余生中去创造和适应一个新的伦理环境。臣服于大海力量之下的克里斯精神上被阉割,他畏惧大海, 相信只要逃离大海就可以逃避命运的安排。 正如马特指出,“海曾给你猛地一击,把你打倒,你却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站了起来, 再和它拼搏, 而是躺了下来, 后半生只是嚎叫海是杀人的家伙”[4]。 向大海屈服的克里斯后半生选择窝在一条破烂的货船上当船长,过着单调、没有挑战的日子。 克里斯为了赎罪将自我放逐, 与远洋航行公司签订合同,回到他憎恨的大海上,重新成为一名水手。 剧本最后“港口那边传来一声声沉闷、悲恸的轮船汽笛声”,暗示着克里斯充满悲剧色彩和不确定性的命运[4]。大海给克里斯职业选择,也束缚着他的职业选择。
二、安娜:空间转换与伦理身份探寻
在剧本中,安娜在不同的空间之间流转,经历了从陆地(社会空间)到海上(自然空间)再复归陆地(建构家庭空间)的过程。伴随着空间的转换,安娜的自我意识、伦理关系、伦理身份出现变化。 安娜一出场,便揭示出她身上的悲剧性,“她年轻的面容,在一层化妆品的下面已变得冷酷无情和玩世不恭。她的穿戴是农村姑娘当妓女的那种打扮,既华丽又俗气”[4]。与《复活》中的玛丝洛娃一样,安娜从事着特殊的职业, 生活给予她的欺辱和痛苦早已使她年轻的心灵变得麻木和冷酷。 无依无靠的安娜踏上投靠父亲之路,也踏上了寻找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旅程。与父亲克里斯将生活悲剧的根源推到大海头上一样, 安娜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陆地。安娜从小丧母,被寄养在内地表兄的农庄, 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指导。 寄人篱下的她在农庄每日被当作下贱的奴隶般使唤,16 岁那年安娜被表兄奸污, 愤怒之下她选择逃走。但在社会上她只能找到像保姆一类的工作,最终沦为妓女,依靠出卖身体养活自己。尽管安娜多次写信向父亲诉说自己在农庄的悲惨遭遇, 但憎恨大海的克里斯坚信陆地是正确的选择, 对女儿的痛苦不管不顾。在海上漂泊的水手向往陆地,而在农庄生活的安娜却渴望逃离陆地向往大海。
来到海上的安娜,从身体到精神都发生改变。初到牧师约翰尼酒店的安娜,喝劣质啤酒,抽香烟,对男人抱有戒备之心。但在与年龄不符的装扮之下,掩盖着一颗渴望亲情、渴望被爱的心。当安娜与父亲见面时, 她 “非常羞怯”“声音中带有真正的感情”“他(克里斯)说话的时候,她热切地注视着他”[4],剧本中对人物行为举止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安娜冷峻的外表下包裹着单纯善良的本性, 父亲的关怀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 和父亲在海上生活一段时间后,“她显得健康,模样改变了,脸上恢复了自然本色”[4],安娜情不自禁地爱上了海上生活。大海的宏伟广阔、浓雾的宁静纯粹赋予她摆脱过去、净化自身的力量, 在货船上安娜第二次找到了归属感,“好像我发现了我曾经失去了某种东西, 而且一直在寻找着——好像这儿正是适合我的地方……我这一次真的感受到了快乐, 比以前我所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快乐! ”[4]亲情伦理的回归是安娜找到归属感的重要原因,“由血缘构筑成的亲情关系是人类最强烈,也最为珍视的情感体验, 它是构成家庭关系最基本的伦理要素”[5]。克里斯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实现身份的回归,亲近和关怀安娜,主动承担起规范和引导女儿的义务, 努力维系父女关系。 来到父亲身边的安娜,体会到被需要、被关爱、被保护的温暖,在陆地上漂泊不定的心也安定下来。 父女伦理关系的重建开启了安娜的新生之路。
人的身份是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3]。当遭遇船只失事的司炉工马特·伯克走上克里斯的货船时,马特旺盛的生命力和血性吸引了安娜的注意。 出于负罪感,她选择隐瞒自己不堪的过去,谎称自己是名家庭教师。真挚的爱情赋予安娜新生的勇气,同时也使她陷入伦理两难之中:是隐瞒过去,接受马特的求婚,还是大胆地向他袒露实情, 展示千疮百孔的过去从而断送爱情? 在大海的净化下, 安娜的灵魂迎来新生,她意识到尽管渴望爱情、向往家庭,但不能以牺牲真诚和自我作为代价。 她拒绝成为父亲或爱人的私有财产,让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你们这样争吵,好像我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人。可是除了我自己,我不属于任何人,懂吗?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任何人能够对我发号施令……我是我自己的主人”[4]。她正视过去的遭遇,像苔丝一样,在马特求婚时勇敢地坦承一切,“我想瞒住真情嫁给你,可我不能那么做”[4]。坠入痛苦深渊的马特无法接受现实, 通过酗酒放逐自我,但在爱情的驱使下又回到安娜的身边,痛苦的马特恳求安娜承认之前的自白是谎言, 选择真诚的安娜拒绝再次欺骗他人。可以看到,与初到大海“冷酷无情、玩世不恭”的安娜相比,此时的安娜从身体到灵魂都迎来新生,她大胆地接受和拥抱过去的自己。
不少学者认为,剧本结尾安娜与“不计前嫌”的马特结婚并返回陆地是她向命运妥协的结果, 婚后马特与克里斯即将远航暗示着未知的命运。 这些学者大多停留在安娜重返陆地、 回归原有的生活这一层面, 而没有关注剧中人物在这一过程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尤其是家庭空间的组建带来的积极变化。安娜并非回到原点,而是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上。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 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3]与马特结婚后,安娜的伦理身份发生变化——从女儿到妻子、未来的母亲。正是与马特的结合才使安娜渴望的家庭空间得以构建,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摆脱独自在陆地漂泊的命运。尽管面临着父亲和丈夫即将远航的未知命运,回归陆地的安娜在等待中怀揣着重新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对美好家庭伦理生活的渴求。
三、马特:想象空间与两性伦理的构建
《安娜·克里斯蒂》中除大海、陆地这两个实体空间之外,文本中还存在着想象性空间——小房子,即克里斯三人渴望拥有的家庭空间, 表现他们的家庭伦理生活诉求。 “家宅是形象的载体,它给人以安稳的理由或者说幻觉。 ”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指出家宅不仅是庇护所,还是堡垒,让孤独的人在其中学会战胜恐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 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 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是人类最早的世界”[6]。家宅是伦理关系尤其是婚姻关系续存的重要外在形式[7]。 马特对家庭空间的憧憬和向往,不仅仅是想要一处可供他停靠的港湾, 还出于他对正常的两性关系的渴求。如前所述,真挚的爱情赋予安娜新生的勇气,同时也促进马特的新生。
马特的新生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体现在对安娜态度的转变上。当他一开始在货船上遇见安娜,以为安娜是船上的妓女,便举止轻浮,企图对安娜动手动脚,在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之后真诚道歉,此时的马特无疑是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接近安娜, 被她的外貌、气质和教养所吸引。 他追求安娜,不过是在追求幻想中“漂亮端庄的姑娘”,他爱的不是安娜本身,而是和安娜结合后可以实现的婚姻生活。 所以当安娜拒绝他的求婚时, 愤怒的马特露出专横的嘴脸,“我想你就跟没有主意的女人一样, 一定要人指点。那么,好吧,我很快就可以替你拿出主意来”[4]。 在他看来安娜是一件可以被占用的物品, 而不是有着自我意识和伦理诉求的独立个体。 剧本在安娜的自我袒露中迎来高潮,也将马特的幻想击个粉碎,他所追求的家庭天使原来有着如此不堪的过去, 与他鄙弃的水滨区女人毫无两样, 他拒绝相信安娜身上发生的改变。马特之所以受到严重的伤害,是因为他对安娜的爱情是建立在他理想化的、 完美无缺的形象之上, 安娜真实微妙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独特的生命体验是他不曾在意的。 绝望中的马特在爱情的驱使下不顾一切重新回到安娜的身边, 他终于明白自己爱的是安娜本身,而不是虚构的理想形象。二是马特的新生体现在对待两性关系的认识上。 从戏剧文本的细节可以看出,遇见安娜之前,马特过着与其他水手无异的怪圈式生活, 在船只靠岸后流连于水滨区找乐子,但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真诚的两性关系。当马特与安娜确立婚姻关系后, 他自我审视以往放纵的经历, 对未来充满希冀, 幻想即将拥有的家庭空间。可以看出他对待婚姻是认真的,“我发誓,她绝不会为此后悔的! 那么,我不再喝酒了,不再四处浪荡了;发工钱的那天,把钱全交给她;我到港口的那个星期,每晚和她呆在家里,就像羔羊一样地驯服”[4]。为了给安娜一个陆地上的家, 马特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和义务,选择再次踏上远洋航行的旅程,去遥远的非洲。
张生珍在 《<安娜·克里斯蒂>剧中的悲剧女主角》中认为马特与安娜的结合纯粹出于动物本能,表面上安娜获得幸福的归宿, 实则隐含着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笔者基于文本细节,认为安娜与马特的最终结合是和谐的两性伦理的建立, 在马特追求安娜时, 他渴望的不是与她发生肉体关系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是想与她组成家庭建立合法的婚姻伦理关系,从而获得作为丈夫的伦理身份。 马特拿出破旧的十字架要求安娜对此发誓,可以看出他始终以认真、尊重的态度对待安娜。马特作为天主教徒,母亲遗留给他的十字架对他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意义,象征亲情伦理,要求安娜对着十字架起誓,可见婚姻在马特内心是神圣的。 虽然得知安娜是路德教教徒, 但对安娜的爱冲破了宗教信仰给他带来的冲突和限制,“我有权利离开你——可是我做不到! 尽管有这一切,我还是爱你的,老天爷宽恕我,无论你是什么人,我都要和你在一起”[4]。
四、结语
《安娜·克里斯蒂》中大海和陆地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空间意象,小房子是剧中人物的想象性空间,寄托人物对组建家庭空间的渴望和亲情伦理回归的诉求。 老水手克里斯因为性格和职业面临多重伦理困境,最终在命运的安排下重返海上,将自我放逐。 而安娜经历了完整的空间循环, 她从陆地上的农庄来到海上的货船而后回归到陆地, 在大海这个空间安娜迎来了从身体到灵魂上的新生, 伦理身份的回归和转变、家庭空间的组建使安娜寻找到归属感,站在新的生活起点上。在剧本结尾老水手克里斯和年轻水手马特碰巧与同一个航海公司签约,即将远航出行,体现命运的不可预测性。 奥尼尔无意于编织一个完满的团圆结局,在《安娜·克里斯蒂》笼罩着浓雾的结尾里寄托着剧作家对人性和伦理的更深入思考。
尤金·奥尼尔的一生充满戏剧式的冲突与悲伤,他咀嚼、体验自己的痛苦,并由此咀嚼、体验人类的痛苦。 《安娜·克里斯蒂》的三种空间意象,体现剧本不同空间与人物伦理诉求之间的建构关系, 体现奥尼尔戏剧创作的突出特征——对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 奥尼尔关心社会问题,为现代社会的冷酷、残暴和现代人没有归宿的境地所困扰, 在剧作中探讨人们遭遇困境的出路,最终创作出不朽的戏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