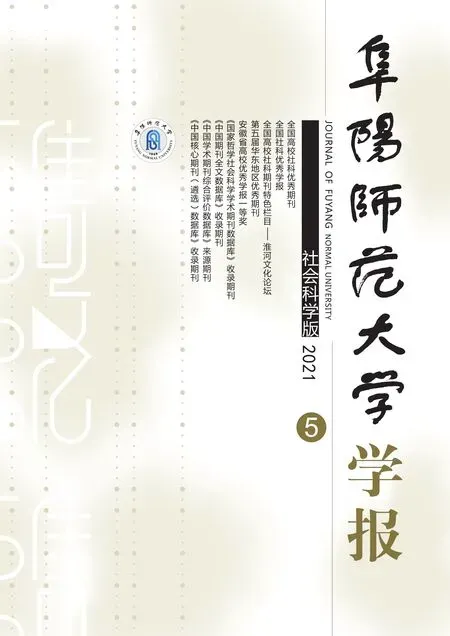论日记书信材料的阅读史价值——以孙宝瑄、溥仪、柳亚子等为例
尹奇岭
□文学研究
论日记书信材料的阅读史价值——以孙宝瑄、溥仪、柳亚子等为例
尹奇岭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近年来阅读史研究的兴起与其他学术潮流一样,是对西方学术热点的跟进。作为私人叙事,日记书信是阅读史材料集中的地方,通过作家的阅读史研究作家的价值判断、政治倾向、趣味偏好、审美取向等,更具学理性,可以借以破除一些习焉不察的偏见和谬误,综合众多民国时期文人的阅读史,则为人们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社会转型与知识接受和传播之间关系打开一扇窗口。
日记书信;阅读史;知识传播;社会转型
利用日记、书信材料追踪作家阅读史,是深入了解作家思想形成和变迁的有效手段。民国时期的学者文人,在日记、书信中有大量记学、论学文字。通过作家的阅读史研究作家的价值判断、政治倾向、趣味偏好、审美取向,更具学理性,可以借以破除一些习焉不察的偏见和谬误。以鲁迅日记书信为例,除了为一般学界所熟知的对苏联和东欧文学的提倡、介绍、翻译外,我们还发现他也大量阅读和收集墓志、碑刻、佛书等“国故”,以及日文、英文、德文的外语书籍,从阅读材料可以领悟鲁迅思想的复杂以及多源头性,从而破除对鲁迅思想僵硬的、模式化的理解方式。
在晚清,延续了几千年的旧制度濒临尾声时,社会大众的阅读物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1905年科举的废除,四书五经的约束力从根本上失去权力保障。近代出版业的飞速发展,阅读材料陡增,可供阅读的书刊不仅数量剧增而且范围广泛。维系思想统一性的基础无形中崩解,正如周作人概括的“王纲解纽”,为“维新”“革命”解开了思想的缰绳。
一、关于阅读史
近年来阅读史研究的兴起与其他学术潮流一样,是对西方学术热点的跟进。阅读史研究的渊源考辨,已有不少成果,大致脉络清晰。就西方来看,阅读史成为一种学术领域,与19世纪后期西方史学的转向密切相关,这一史学潮流将视点从上层精英转向下层民众,研究视野急遽扩大,以往不被关注的大量材料被容纳进来,如社会机构的记录材料、私人的日记书信等等。具体地说,阅读史是从书籍史中“分娩”出来的,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夏蒂埃和美国达恩顿横空出世,成功完成了书籍史向阅读史的转向,分别出版了阅读史领域的经典论著。此外还有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和新西兰史蒂文·费希尔的《阅读的历史》堪称经典。当然,作为一个学术新领域,阅读史研究不是单一学术领域影响的产物,而是跨学科综合影响的产物。除书籍史外,阅读史研究还深受法国年鉴学派以及传播学的影响。年鉴学派的马尔坦、费夫贺等人关注书籍的阅读与流通背后的社会等方面因素,将阅读看作是文化实践,凸显了阅读史的地位。在传播学方面,20世纪60年代,德国姚斯创立了接受美学,提升了读者的地位,将对作者和作品的关注引向了对读者阅读的过程和阅读效果的关注。以上是西方阅读史的大略情形。
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对阅读史关注较早的有大陆的罗志田、台湾的潘光哲等人。王鹏飞认为,中国阅读史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史学领域,潘光哲的《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张仲民的《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是代表性成果;二是图书情报学领域,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洋洋十卷本,是代表性成果;三是传播学领域,蒋建国在“中国报刊阅读史”,卞冬磊在“晚清报刊阅读史”,都有扎实的学术成果。西方汉学界对中国阅读史方面的介入,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如虞莉《中华帝国晚期的阅读史,1000-1800》、何谷理的《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的阅读》、戴思哲《帝制中国的地方志编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马兰安《构建中国晚明时期新的阅读公众》等[1]。
晚清民国以来,列强的入侵及知识精英群体内生的拯世济民的激情,共同催动中国社会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从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社会更新为一个近现代的工业社会,吁求一场知识更新运动,抛弃掉束缚社会发展的传统沉疴,补充新鲜的知识血液,成为近代中国的必然选择。谈到知识更新,阅读史的变迁便成为一个核心内容。在这一时段,阅读者、阅读对象、阅读动力、阅读效果、阅读习惯、阅读的地域性差异等等与传统相较发生了重大变迁。从阅读者来看,随着学堂大量建立,读书识字的人大幅增加,读者群体广泛化。从阅读对象来看,伴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扩展,以及“西学东渐”,大量廉价的书刊出现,社会上的阅读物丰富起来。“从传统的四书五经和诸子著述,扩展到承载西方新知识、新观念的内容。从形式上说,从原来的主要阅读书籍,扩展到图书、报纸、期刊、宣传册等多样化的知识载体。”[1]从阅读的动力上说,随着科举制在1905年被清政府废除,“举业”已从历史中薅除,实用之学大兴,除了传统固有的升官发财梦,“启蒙”“救亡”成为很多读书人的动力。从阅读习惯说,近代以来有个阅读方式和习惯的变革,从读经要求的精读,到读报刊需要的泛读,从背诵需要的朗读,到博览需要的默读,从单一知识追求的公众阅读,到私人趣味下的私下阅读。从阅读的地域性差异看,朱至刚指出,地理空间和社会层级影响着阅读主体的分布。“身在核心或是边缘区域,对他们能日常阅读的书籍数量多少、品类丰寡,势必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人数上看,后者在任何时段都是大多数。”[1]
阅读有影响社会人心之力,发生大影响的思想观念总是通过阅读来传播的。1919年4月20-21日,顾颉刚在给叶圣陶的信里说:“试看严又陵的《天演论》给中国社会以极大的影响,大概中国所以能改革的这样快速,他这一本书大有功效。然《天演论》是从生物学出来的,生物学又在数理化博物诸科出来的,他没有将生物学同数理化博物诸科相关的常识介绍给大家,凭空译一本《天演论》,所以生出来的影响,便是躐等的改革。‘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成了口头的习语,强权的护符论;到现在情形的扰乱拂逆,他可要担当些罪孽了。”[2]这段文字不仅说出了《天演论》对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也指出了它的副作用。然而匡正的手段无论是“科学常识”还是“确当的人生观”,其实还是要通过书刊文字的阅读传播来实现。下面结合具体的日记书信材料,来谈谈晚清民国以来的阅读变化。
二、《忘山庐日记》中的阅读扫描
勒庞说:“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3]然而,过渡时期,正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桎梏被打破的特殊时期,共享的基本环境处于危机状态,从而为新因素的介入预留了缺口。晚清民国正是一个过渡时期,西方的强势入侵,惊破了清朝江山永固的迷梦,变革图存成为知识精英的共识。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制度等等方面,都面临调整和更迭。所有的变迁总是与思想认识有关,而思想认识的更新又是与阅读材料的新因素加入有关。除旧学之外,“西学东渐”风力正劲,这些“西学”翻译为中文后,通过近现代报刊、书籍广泛传播,以阅读为中介,引发了知识精英阶层的“思想风暴”,其后的“改良”“革命”潮流,皆是思想文化变迁的结果。在日记书信中,有大量材料记载着当事人的阅读经历,可以从中发现思想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
若以阅读物为考察对象来选取个案的话,孙宝瑄的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孙生于1874年,死于1924年,正好经历晚清民初这一时段。孙宝瑄生活于标准的仕宦家庭,父亲孙诒经,哥哥孙宝琦,岳父李瀚章,皆为贤达之士。他爱好读书,家藏万卷,涉猎广泛,爱交友,好友如严复、章炳麟、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等人。在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里,记录了大量日常的阅读生活。考察他在晚清时段的阅读内容,可以窥见当时上层知识精英阅读内容之一斑。下面把孙宝瑄1893-1908年间具体阅读内容分列如下:
一是旧学方面:
1893-1894年:《左传》《南史》《北史》《汉书》《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文史通义》《通鉴》《皇朝经籍志》《皇朝经世文编》《明纪》《先正事略》《列朝兵制大略》《致直隶讷制军书》《群书治要》《游仙诗》《招隐诗》《应诏观北湖田收》《赠从弟》《杂诗》《登江中孤屿》《七发》《秋声赋》《月赋》《闲情赋》《圆圆曲》《北山移文》《禅林宝训》《离骚经》《册九锡文》《张良庙教》《奏记诣蒋公》《挽王可庄》《湖山草堂图》《丰乐亭记》《禅林宝训》《虎丘夜集图》《国朝别裁集》《梅村集》《熙朝新语》《王彦章画像记》《樊侯庙灾记》《六臣记》《晁错论》《南海庙碑》《臣事论》《蒯通论》《续辞类纂》《名实说》《唐两京城坊考》《圣哲画像记》《策秀才文》《陈情表》《封建论》《明儒学案》《危言》《阅江楼记》《三国演义》
1897-1898年:《周礼》《周礼注疏》《庄子》《管子》商君书》《列子》《朱子语类日钞》《无邪堂答问》《圣武记》《白虎通》《中国度支考》《大清会典》《石渠余记》《周书》《吕氏春秋》《汉书》《后汉书》《史记》《隋书》《唐书》《魏书》《晋书》《辽史》《元史》《金史》《宋史》《明史》《史通》《皇清经解》《明儒学案》《文献通考》《华严经》《大乘起信论》《六祖坛经》《文心雕龙》《戴东原集》《东原年谱》《中论》《潜夫论》《盐铁论》《困学纪闻》《说苑》《四益馆丛书》《莽苍苍斋诗》《三代沿革论》《辨微论》《潜书》《大云山房集》《樊南文集》《随园诗话》《颜氏学记》《齐名四术》《儒门医学》《黄书》《明堂针灸图》《延年益寿论》《说文解字》
1901-1903年:《中庸》《易》《尚书》《道德经》《戴记》《论语疏》《春秋繁露》《左传》《公羊解诂》《诗谱序》《哀江南赋》《王船山遗书》《式训堂丛书》《东华录》《北史》《政务处条议明辨》《通典》《西厢记》《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论衡》《老子》《品花宝鉴》《石头记》《今古奇观》《无行经》《晋书》《通鉴论》《神仙通鉴》《止观辅行》《吕祖全书》《龙舒净土文》《天台小止观》《冠导本俱含论》《唯识论述记》《八大人觉经》《林间录》《楞严经》《妙玄节要》《净土十凝》《大弥陀经》《俱舍论》《瑜伽师地论》《归田琐记》《抱朴子》《道藏全集》《仙史》《皇朝掌故汇编》《续经世文编》《申鉴》《考古类编》《耿庵诗稿》《癸已类稿》《论语稽求篇》《郁光集》《西斋偶得》《说文》《说文通训定声》《无能子》《顾黄公集》《感旧集》《空山堂今始考》《墨池编》《玉磐兰》《骈体文钞》《西域考古志》《曾涤笙家书》《何大复集》《李沧溟集》《憨山年谱》
1906-1908年:《玉露》《九经古义述》《山海经》《楚辞》《笔塵》《古欢录》《管制议》《西斋偶得》《风雅广逸》《集韵》《经世文编》《官场现形记》《劫后英雄略》《燕丹子》《胡子知言》《薛子道论》《阅史郄视》《平书》《通鉴评语》《萝摩亭札记》《丹铅续笔》《消暑随笔》《八家四六文选》《郁离子》《鹤山笔录》《落帆楼文稿》《茗柯文编》《灌畦暇语》《快书》《池北偶谈》《绿雪亭》《考古质疑》《丹铅总录》《国史大臣别传》《蒿庵闲话》《松窗杂录》《舆地广记》《伤寒总论》《古今说海》《今石文字记》《积古斋钟鼎款识》《古韵标准》《四声切音韵表》《薛浪语集》《存学篇》《世说新语补》《学界罪言》《青箱杂记》《三箱从事录》《癸巳类稿》《法苑珠林》《德安城守记》《居业堂文集》《樵香小礼》《潞城考古录》《乾坤大略》《兰台奏疏》《博物志》《西域传补注》
二是新学方面:
1893-1894年:《海国图志》《万国史记》《中西纪事》《西事类编》
1897-1898年:《新学伪经考》《西学述略》《电学须知》《光学》《心灵学》《植物图说》《地学稽古论》《兽百种论》《几何原本》《交涉公法论》《万国公法》《日本政记》《日本外史》《日本新史》《明治新史》《孔子改制考》《天演论》《全体学》《天文图说》《太平洋岛受道记》
1901-1903年:《西学探源》《饮冰室自由书》《哲学论纲》《国法泛论》《译书汇编》《国家学》《宪法精理》《宪法比较论》《万法精理》《万国宪法志》《公法论纲》《民约论》《政法哲学》《政治学提纲》《原富》《教源论》《开皇三宝录》《政治学》《佐治刍言》《物竞论》《理财学》《普通妊娠法》《胎内教育》《男女交合无上之快乐》《男女造化新论》《卫生学答问》《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日本新地图》《万国新地图》《日本游学指南》《宇宙形质论》《各国国民公私全考》《李鸿章传》《李鸿章》《日本维新儿女英雄奇遇记》《仁学》《古教汇参》《现今世界大势论》《黑奴吁天录》《中国魂》《埃及近世史》《生利分利之别论》《欧洲财政史》《名学》《中国最新度支》《财政四纲》《吾妻镜》《农学初级》《传种改良答问》《修学篇》《读书法》《经国美谈》《社会学》《日本制度提要》《日本国史略》《日本政党小史》《埃及史》《支那文明史》《土耳其史》《俄罗斯大风潮》《英国工商业发达史》《族制进化论》《道德进化论》《二百年后之吾人》《地球之过去未来》《帝国主义》《外交通义》《精神之教育》《理财学纲要》《鬻子》《政教进化论》《续包探案》《哲学要领》《哲学原理》《群学肆言》《爱国精神谈》《中英商约驳议》《西湖图志》《心理教育学》《泰西学案》《自助论》《支那地图》《万国商业志》《白山黑水录》《露濑格兰小传》
1906-1908年:《日本宪法》《泰西礼俗新编》《电术奇谈》《法国司法组织》《政教考》《空同子》《朝鲜近世史》《意大利游记》《越南游历记》《出使九国日记》《日本交通史》《日本维新三十年史》《铁路臆说》《中国铁路指南》《轨政要览》《邮政讲义》《满汉通行刑法律》《战血余腥记》《血史》《日本剑》《马氏文通》
三是报刊方面:
1893-1894年:《邸报》
1897-1898年:《知新报》《万国公报》《清议报》《时务报》《苏报》
1901-1903年:《清议报》《汇报》《新民丛报》《大公报》《格致汇报》《政法学报》《新闻报》《新世界学报》《中外报》《格致报》《日日新闻》《大陆报》《浙江潮》《顺天时报》《新小说报》《湘报》
1906-1908年:《东方杂志》《时报》《北京日报》《外交报》《国粹丛编》《京报》《沪报》《浙江日报》《神州报》《顺天时报》《惠兴女报》《政艺通报》《大同报》[4]
从以上列举中,可以看出孙宝瑄日常阅读生活的概貌,随着年份不同,阅读的内容在发生着变化。中上层知识分子因为得风气之先,率先阅读了很多传统“知识库”中没有的内容,于是“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便在他们心中被打破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稳定性也失去了基础。就孙宝瑄的阅读史来看,戊戌变法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其后新学方面的书刊阅读量明显增加,1903- 1904年达到更高水平。从阅读的大致走向看,从读四书五经的“举业”之文为主,到读经世致用的实用文为主,从关注本国历史,到关注别国历史,从传统医学的读物,到西方生理卫生的读物,从本国异端书册,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书籍,甚至书单中有理工科的一些书籍,如电学、地学等等,眼界一步步开阔,阅读量也非常惊人。有论者指出:“从整体上来看,孙宝瑄阅读的书籍1893、1894年以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学书籍为主,介绍西方学说的新学书籍虽有阅读,但比较少,只有4本。1897年之后西学书籍开始多了起来,在1901年至1903年之间,他的阅读主要以国人翻译的西学书籍为主,再辅之以部分传统的旧学书籍和报纸。在1906年至1908年,这三年间主要以读报纸为主,再辅之以以前读过的旧学书籍,而新学书籍比较少。在不同时段,他所阅读内容侧重点的不同,这本身可以反映一种社会的变化。”[4]
三、《溥仪日记》中的书单
溥仪的日记,李淑贤说是“爱新觉罗·溥仪的最后遗产”,是她从火舌下机智抢救下来的仅有成果。李淑贤回忆说,文革发生不久,为了紧跟“革命”,溥仪决定烧掉他的“笔记本、日记本、诗文册一类东西”。于是,溥仪一页一页撕,让妻子李淑贤一页一页地烧。李淑贤觉得很可惜,就想出一个办法——谎称有人敲门,乘着溥仪去开门的时间,从“火堆前抢救出十几本日记和笔记”[5]。
溥仪是末代皇帝,一生命运多舛。他生于1906年2月7日,死于1967年10月17日。1908年11月13日,两岁多的溥仪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第二天光绪帝驾崩,幼童溥仪入承大统,同年12月2日,正式继位,史称宣统皇帝。从1911年起,6岁的溥仪开始在毓庆宫读书,先后担任帝师的有陆润庠、陈宝琛、易克坦、徐坊、朱益藩、梁鼎芬和庄士敦,都是享有盛名的人物。从1914年起9岁的溥仪开始写日记,宫内的生活千篇一律,日记所录也如流水账,却为我们保留了一份末代皇帝的读书单。这份书单对于我们了解皇家的教育内容、教育理念等方面非常重要。下面将日记中部分读书内容选录如下:
1914年11月13日:读《左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至“是无善人之谓也”,《礼记》“八十者”至“[百工]各以其器食之”。[5]3
1914年11月14日:读《左传》“夏,成周宣榭火”至“执南郭偃于温”,《礼记》“道路”至“为田九万亿亩”。[5]3
1914年11月15日:读《左传》“苗贲皇使”至“郤献子为政”,《礼记》“自恒山[至于南河]”至“其余六十亿亩”。[5]3
1914年12月8日:在养心殿温习《左传》《礼记》《书经》,写大“福”“寿”,写仿。[5]8
1914年12月28日:在养心殿温习《左传》《礼记》《唐诗》《四书》,写仿、写“福”“寿”字、写匾。[5]11
1915年1月1日:读《左传》“秋会于沙随”至“宋齐卫皆失军”,《礼记》“是月也”至“草木蚤死”。[5]12
1915年1月7日:在养心殿写仿、写大匾、写大“福”“寿”字,温习《左传》《礼记》《唐诗》《四书》《孝经》。[5]12
1915年1月15日:在养心殿写仿“开笔[大吉]”,温习《左传》《礼记》《唐诗》《四书》《孝经》《书经》。[5]13
1915年6月17日:在养心殿温习《左传》《礼记》《唐诗》《四书》《书经》《孝经》,写仿,写大匾。[5]30
1916年1月1日:读《左传》“冬[十月丙申]”至“[能用力]于王室也”,《礼记》“子曰”至“而不可使为乱”。[5]49
1916年1月30日:在养心殿写仿,温习《左传》《礼记》《唐诗》、[十二]字头《单清语》、《圣谕广训》。[5]52
1916年2月26日:读《左传》“秦伯使辞焉”至“败吴师于军祥”,《公羊传》何休序。[5]54
1916年2月27日:读《左传》“秋七月”至“吾以志前恶”,《公羊传》“元年”至“母以子贵”。[5]54
1916年4月14日:在养心殿写对联,在长春[宫]写仿,温习《左传》、《公羊传》、《单清语》、《满洲孝经》。[5]58-59
1916年5月25日:读《易》“乾”至“吉”,《诗》“关雎”一什,《公羊传》“冬”至“记异也”。[5]64
1916年7月30日:在长春宫写仿,在建福宫写“福”“寿”大字,在养心殿温《易经》,在延辉阁温《诗经》,在绛雪轩温《孝经》,在毓庆宫温《书经》,在钟粹宫温《庭训格言》,温《左传》。[5]70
1917年1月1日:读《诗》“潜”、“雍”二篇,《公羊传》“至仲孙何忌及邾娄子盟于枝”。[5]83
1917年1月28日:读《谷梁传》“元年春”至“蹈道则未也”。[5]85
1917年11月16日:读《周礼》“七事者”至“则国有大刑”。[5]92
1914年溥仪八周岁,每天学习内容都是传统士大夫阶层必须接受的教育内容,如《左传》《礼记》《书经》《唐诗》《四书》《孝经》等,再就是临帖练字。1916年十周岁的溥仪日常功课中增加了《圣谕广训》《公羊传》《满洲孝经》《易经》《诗经》,其中《圣谕广训》是清朝历代皇帝的语录,《满洲孝经》也是传承祖训家风的。1917年,溥仪十一岁,日常功课增加了《谷梁传》和《周礼》。从以上书单可以看出,幼童溥仪在一群妇人和遗老的包围下,沿袭旧习,在教育内容上几乎没有更新。
在清代,皇族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一年四季几乎没有空闲。在《溥仪日记》里,我们发现即便是除夕和大年初一也是很忙,虽不读书了,但却有“礼仪训练课”。1917年1月22日,是甲子年的最后一天,这天的日记中,溥仪写道:“封笔大吉,拜五宫全佛,拜四贵妃。”[5]84第二天,是旧历乙丑年,也就是大年初一,仪式更加繁琐,溥仪在日记中写道:“开笔大吉,拜五宫全佛,遂如坤宁宫,诣西案北案君前拈香行礼,遣永祥如东陵阁佛前,拈香礼毕。朕遂如承乾宫,又遣永祥如孝全皇后御容前,拈香行礼,毕。又至西暖阁朕诣孝定景皇后,拈香毕。毓庆宫、建福宫、斗坛、养心殿、千秋亭、万春亭、妙莲花池、凝晖堂、广生楼,皆遣人恭代行礼,乾清宫立写宝殿钦,翊坤宫朕行礼,遂如太极殿,诣敬懿贵皇妃、庄和皇贵妃、荣惠皇贵妃、端康皇贵妃行礼毕,御乾清宫受诸王大臣贺毕,乃如养心殿。”[5]85此时的溥仪虽已退位,但宫里的规矩一点未乱,行礼如仪,照旧如常。1918年,溥仪12岁。这年的1月13日,是庚申年的第一天,所谓“开笔大吉”。溥仪按照规矩梳洗打扮之后,举行“开笔大吉”仪式,书写春联和“福”字赐给亲宠大臣。这一天比较特殊,溥仪不仅写了日记,还画了一幅图,赐给老师梁鼎芬。梁家把这幅图装裱,成为长卷,并请了著名的遗老题跋。这幅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为纸本,日记部分纵18.2厘米,横27.2厘米。在这幅少年的涂鸦上,居然还有几十名旧臣遗老的题跋[5]95。溥杰在《“关门皇帝”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尽管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皇权制度在辛亥革命时被推翻了,但清代的一些遗老遗少,还眷恋着过去。在一个还是孩子的溥仪一文一画后面,竟有几十位‘名人’题跋、吟诗、作赋。甚至已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年代了,还称‘宣统××年’,还自称‘臣’者,其中有朱汝珍、胡嗣瑗、郑孝胥、朱益藩、黎湛枝、赵尔巽、王季烈、陈夔龙、叶尔恺等等。”[5]97-98
随着年龄的增大,溥仪的阅读面也在拓展。1921年1月5日,在日记中,溥仪写道:“8时上课,同溥杰、毓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宝琛]师讲《通鉴辑览》。9时半餐毕,复读《左传》《谷梁传》,听朱[益藩]师讲《大学衍义》及写仿、对对联。11时功课毕,请安四宫。是日,庄士敦未至,因微受感冒。遂还养心殿,书‘福’‘寿’字三十张,复阅各报,至4时餐。6时寝,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5]99-1001月6日:“早4时即起,静坐少时,至8时上课,仍如昨日所记。至12钟三刻余,庄士敦至,即与溥佳读英文。3时功课毕,还养心殿。”[5]1001921年,溥仪十五岁了,日常的学习内容里增加了英文,他的阅读自主性也大了,包括阅览各报,及《古文观止》。1922年,溥仪十六岁时独立自主做了一件具有传奇色彩的事,就是在电话簿上看到胡适的名字,直接打电话给胡适,要求见他。这件事在胡适日记里有三处记载。
第一次是在1922年5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6]第二次在5月30日,为了见溥仪,胡适没有去上课,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见面的情景:“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6]680溥仪抱怨说有些新书找不到,胡适答应可以帮忙找,谈话大概进行了20分钟。第三次在6月6日,胡适日记中抄录了一首名为《有感》的诗:“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6]689这首诗显然是写宣统帝溥仪的。从胡适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溥仪的阅读受到时代风尚影响,已经将注意力放在新学上,思想和追求与列祖列宗们也大有不同。
然而,溥仪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复辟皇权、充当傀儡的不归路。或许“阅读是很容易从记忆中剥落、风化掉的东西”[7],真正决定一个人行事的还是现实的利益计较。也就是说,阅读带来的思想认识的改变能否转化为现实政治的选择,是需要实践检验的。
四、柳亚子《乘桴日记》中的阅读
柳亚子是民国时期著名旧体诗人,反满诗社南社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南社事务的主持者。“四·一二”发生后,柳亚子避难日本。1927年5月至1928年4月,柳亚子在日本避难时写了《乘桴日记》,日记分为两部分:前半部以江南唐瑛署名,后半部以隐芝居士署名。下面以1927年7月份为例,抄录几条日记中有关阅读的信息:
7月3日:甘君假我周作人先生所著《雨天之书》,即翻阅一过,藉消永昼。[8]
7月4日:从李君处假阅《天籁》两卷,钱塘悟痴生辑,光绪三十四年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出板,上海科学仪器馆发行。内容多顾颉刚《吴歌甲集》所未采,颇可宝贵也。[8]8
7月13日:阅蒯斯曛君著《凄咽》,暨蒋山青君著《秋蝉》,两君均青年作家也。[8]9
7月14日:阅郁达夫君著《曼殊作品杂评》,及罗建业君著《曼殊研究草稿各一首。》[8]9
7月23日:阅曼殊翻译小说《惨世界》。[8]10
7月24日:阅商务书馆翻译小说《孤星泪》,书为法人嚣俄原著,实即《惨世界》之下半部也。[8]10-11
以上列举只是日记中七月份的书单,并非全貌。检视《乘桴日记》(江南唐瑛)中阅读刊物和书籍,大致如下。一是期刊类:《语丝》《莽原》《北新》《白露》《狂飙》《文字同盟》《王国维专号》《小说画报》《幻洲半月刊》《创造月刊》《国闻周报》《现代评论》《时事新报》,共13种期刊。二是书籍类:《曼殊诗集》《苏曼殊书札集》《曼殊文集》《苏曼殊及其友人》《译诗集》《苏曼殊年谱》《话雨楼遗集》《左传菁华录》《定庵词》《烟霞万古楼诗集》《定庵全集》;周作人《雨天之书》、蒯斯曛《凄咽》、蒋山青《秋蝉》、郁达夫《曼殊作品杂评》、钱塘悟痴生辑《天籁》、徐祖正《兰生弟的日记》、陶晶孙《盲肠炎》、刘半侬译《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册)、鲁迅《华盖集续编》、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鲁迅译《一个青年的梦》、鲁迅《野草》、陈衡哲《西洋史》、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郁达夫《寒灰集》、郁达夫《日记九种》、金声《北伐从军日记》、周全平《苦笑》、王任叔《监狱》、法国古尔蒙著篷子译《处女的心》,共31种之多,其中关于苏曼殊的7种,关于鲁迅的4种,关于郁达夫的3种,关于翻译的4种。
检视《乘桴日记》(隐芝居士),日常阅读的书刊如下。先说期刊,与上面列举的比较,有延有增。主要有:《语丝》《现代评论》《洪水》《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新女性》《真善美》《小说月报》《沈钟特刊》《少年杂志》《儿童世界》《国学门月刊》《太阳月刊》,共13种。再说书籍类,主要有:《红楼梦本事辨证》《石达开日记》《磨剑室诗词》《唐五代词选》《孽海花》(初二编)《银匣》《法网》《冲积期化石》《最后的幸福》《翠英及其夫的故事》《花圈周年》《少女日记(上卷)》《少女日记(下卷)》《苔莉》《使命》《流浪》《旅心》《断片的回忆》《性而已》《圣母像前》《鲁拜集》《革命的故事》《俄罗斯文学》《堪克宾》《短裤党》《战线上》《野祭》《血痕》《谈虎集》《杨贵妃之死》《鸡肋集》《过去集》《怂恿》《鸽与轻梦》《文艺与性爱》《志摩的诗》、鲁迅《热风》、刘大杰《渺茫的西南风》、王独清《死前》、蹇先艾《朝雾》、陶晶孙《音乐会小曲》、鲁迅《呐喊》、周全平《梦里的微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白采《绝俗楼我辈语》、周作人《泽泻集》、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胡云翼《西泠桥畔》、焦菊隐《女店主》,共49种。
从以上列举可以看出,柳亚子的日常阅读主要集中在文艺和文史方面,不同于传统文人阅读集中在旧体诗词、诗话、史籍等方面,而是与时俱进,阅读的注意力主要在当下的创作及翻译,一改阅读尊崇前贤的“向后看”传统,更多致力于眼前的“新文学”方面。另外,也可看出柳亚子的阅读趣味,阅读眼界,也都与传统文人有很大区别。
五、日记书信中的“中学”“西学”
中国传统儒家书籍传递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服务于既定的权力机制、社会构架,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近现代以来的书刊,渐渐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分离出来。儒家典籍在此过程中,渐渐历史化,因西方典籍及其携带的思想观念勾兑进来,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降低。
在有识之士看来,中国欲图强,必须引入西学。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抑吾闻英伦大书楼所藏书凡八万种有奇,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今之译出者何寥寥也?彼中艺术,日出日新,愈变愈上,新者一出,旧者尽废。今之各书译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视之,已为陈言矣。而以语吾之所谓学士大夫者,方且诧为未见,或乃瞠目变色如不欲信。”[9]经过晚清变法,到民国初年,西学的重要性已不待言。1913年9月,林纾在给儿子林璐的信中说:“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10]陈平原指出:“现代大学所需要的,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而非趣味高雅的文人——借用传统术语,那就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开始从‘文苑传’向‘儒林传’转。如此大趋势,对于林纾等传统文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11]虽然林纾对西学十分反感,他说:“学生出洋,只有学坏,不能有益其性情,醇养其道德。然方今觅食,不由出洋进身,几于无可谋生。”[11]129可见潮流所向,顺昌逆亡,西学已大行其道了。
民国时期,胸怀壮志的才俊之士只要有条件,多数会选择去发达国家经受西学的洗礼。近现代以来重要知识分子没有出过洋的是很少的,西学影响中国的规模和范围虽不可能做精确的量化研究,但其极端重要性无人可以否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无不如此。举凡孙中山、蒋介石、瞿秋白、王明、王国维、陈独秀、鲁迅、胡适、陈寅恪、胡先骕、李四光、陈省身、饶毓泰、叶企孙、侯德榜、卢嘉锡、林巧稚、徐悲鸿等等各界精英,都有海外经历。当年,俞平伯到英国刚刚两周多就因想家而归国,傅斯年大为惋惜,1920年8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一句话说,平伯是他的家庭把他害了。他有生以来这次上船是第一次离开家。他又中国文先生的毒不浅,无病呻吟的思想极多。”“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12]
关于东西文化的优劣,一直伴随着激烈的论争,论者众多。1923年12月16日,王国维与胡适有一段漫谈,也涉及东西文化的对比问题,颇有意思,抄录如下: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种。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也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惠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13]
王国维在学术上多有发明,但在政治上拥护皇权。1924年8月11日,在日记中,钱玄同写道:“叔平谓王国维因研究所对于大宫的事件之宣言中有‘亡清遗孽盗卖古物’之语,且直称溥仪之名,大怒,于是致书沈、马,大办其国际交涉,信中有‘大清世祖章皇帝’、‘我皇上’等语。”[14]在文化上,王国维持文化保守立场,1922年5月29日,他在回复顾颉刚的信中说:“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考,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15]王国维与胡适的闲谈,可以看作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过招,显然胡适占有上风。西学东渐以来,如何调适中西,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晚清时期,张之洞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新文学革命一段时期,胡适等人提出“全盘西化”。实际上,自从西学进来后,“中学”再也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学”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吸收借鉴了西方的方法论,几乎无人可以例外。学问精湛如王国维,不是也要借用叔本华来阐释《红楼梦》嘛。然而,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何种观念,必须要“服水土”,才能发挥正面作用,否则就会在现实中发生种种龃龉。
结语
在日记书信中,有大量材料可以作为研讨阅读史变迁的资源。阅读对社会的改变根本上说是通过改变阅读者来完成的。晚清民国,传统知识库引进了新内容,即所谓的“西学”。对西学的引进和接纳有一个“中国化”的历程,就是说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满足中国人的情感的、审美的需求。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阅读是知识获取的主要渠道。莎士比亚、歌德、列夫·托尔斯泰都谈论过阅读好书籍的重要性,将其比喻为是全人类的营养品、与高尚人的谈话、开启智慧的钥匙等。近年来,很多国家已经将“全民阅读”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国家工程的层面,并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确认。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倡导阅读方面力度不断增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走向阅读社会”(1972年),1995年宣布了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美国进行立法引导阅读:《阅读卓越法》(1998年)、《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案(2001年)。日本也一样,出台了《儿童读书推进相关法律》(2001年)等等。我国在宣传、立法等层面也在不断推进“阅读强国”的建设。[16]
当然,关于阅读的研究还有更为复杂的问题。诸如阅读与意识形态、阅读与审美趣味养成、阅读与知识再生产,等等。在个体的意义上说,阅读与知识传统,阅读与政治见解,阅读与思想革命,阅读与个体期待,以及如何通过阅读进行自我培养、自我教育,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教育系统,出版系统,整个社会机器所出品的阅读材料,涉及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应该自在自为,顺其自然,还是介入规范,控制传播,则涉及到更高层面的制度选择,而社会控制模式选择,背后是复杂的权力关系运作。
[1]本刊记者.阅读与近代社会转型[J].编辑之友,2019(4).
[2]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 2011:57-58.
[3]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1.
[4]秦利国,李振武.孙宝瑄的阅读实践与社会变迁——以《孙宝瑄日记》为中心[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5]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日记(上)[M].王庆祥,注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
[6]胡适.胡适日记全编·3[M].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673-674.
[7]卞冬磊.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5(1)
[8]柳亚子.柳亚子日记[M].柳无忌,柳无非,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
[9]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C].张静庐,辑注.上海:上海书店,2003:58.
[10]林纾.林纾家书[M].夏晓红,包立民,编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6.
[11]陈平原.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J].文学评论,2016(1):
[12]王汎森,潘光哲,吴证上.傅斯年遗札[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0-11.
[13]胡适.胡适日记全编·4[M].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31-132.
[14]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97.
[15]房鑫亮.王国维书信日记[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5:678.
[16]王迎春.从私人走向公共:阅读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的变 迁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9.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Reading the Scholars’ Letters and Diari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king Sun Baoxuan, Henry, Liu Yazi as Examples
YIN Qi-l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29, Anhui)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study of reading history, like other academic trends, is a follow-up of western academic hotspots. As a means of private narrative, letters and diaries are places where much concentrated reading history material lies. Through the writer’s reading history, it is more academically rational to do research on their judgements, political inclination, tastes and preferences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it can also eliminate some prejudices and fallacies that are often ignored.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many scholars’ reading history opens a window to deepl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diffus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etters and diaries; reading history; knowledge diffus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2021-09-0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记书信中现代文人私人叙事研究(1917-1949)”(15BZW163)。
尹奇岭(1970- ),安徽淮南人,博士,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5.11
I210.7
A
2096-9333(2021)05-0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