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险志士在干训班讲述红岩往事
甘小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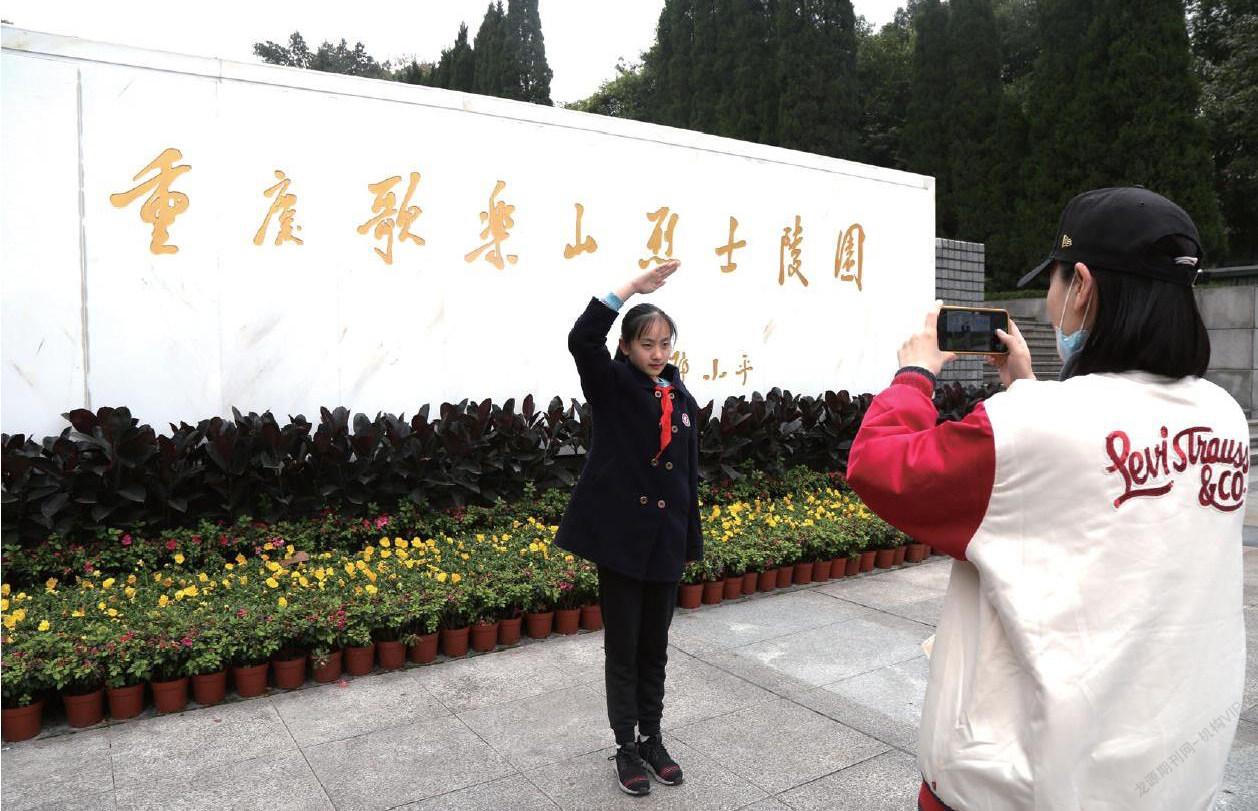


几年前,我被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抽调参与编纂《重庆市志·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志·党校工作卷》。工作期间,我曾向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黨史专家胡大牛请教。胡教授特别提到一个细节:“重庆刚解放,党组织就把地下党员集中到党校培训,事实上是写材料,一写就写出问题,不少叛徒就这样现出了原形……”
这番话让我深受启发。随着搜集和发掘的史料越来越多,最终有了这篇文章。
寻找档案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1年3月2日,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成立。在市委党校正式成立前,市委举办过三期干部训练班。档案显示,这三期干训班从1949年12月持续到1950年7月,每期大约两个月,共培训学员193人。干训班主要加强学员的政策教育与组织教育,各期内容根据学员来源不同略有增减。
第三期干训班结束当天,组织者就起草了一份《市委会第三期干训班总结及给市委的建议》,其中提到:“市委干训班应该是逐步的向中级党校方向进展,调训的对象应该是至少有两三年工作历史(或相当于连级以上的干部)和缺点严重的县级干部。目前市委欠缺县团骨干……只有及时培养营连级干部,才能逐渐到自力更生,为县团来源打下基础。”可以说,干训班是市委党校的前身。
在三期干训班中,第一期比较特殊,学员共102人,大部分是从狱中脱险出来未解决组织关系的党员,少数是进步群众、地下党员和烈士家属。根据这份档案,我寻思,那些从渣滓洞、白公馆“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志士,会不会就在这个班上呢?
我在档案中寻寻觅觅,找到了第一期干训班的材料。
翻开这本混杂着各种不同纸张、笔迹,且散发出浓烈岁月气息的案卷,我看到的第一份文件就是学员名单。我小心翼翼地翻动边缘早已残破发黄的毛边纸,一个个钢笔抄写的名字跃入眼帘。
经核对确认,至少有8位从“11·27”大屠杀中幸存的革命志士参加了中共重庆市委第一期干部训练班。他们是从白公馆脱险的郭德贤、谭谟、郑业瑞、杜文博,从渣滓洞脱险的孙重、萧钟鼎、傅伯雍、钟林。还有一位叫蓝国农,曾被关押在渣滓洞,在“11·27”大屠杀前获释。
根据档案材料,我大致梳理出市委第一期干训班的开展情况:重庆解放后,组织部门将从四面八方前来登记报到的党员集中起来,要求身份和历史存疑的脱险难友、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写自传、写材料。经过谈话、多方了解后,初步确认其身份的,视本人要求编入干训班或作其他安排。
档案显示,学员撰写的内容包括革命经历、历史问题说明、在训练班的学习情况等。市委组织部还与脱险同志、失联党员谈话,询问每位同志的要求和希望。从渣滓洞、白公馆脱险的革命志士被找去谈话的,除前文所述的9名同志外,还有盛国玉、杨培基、杨纯亮、周仁极、杨同生,这5名同志的要求是“返家”,被编入干训班的9名同志提出的要求是“学习”“先学习后工作”。
这些经初步确认身份,又要求学习的脱险志士、失联党员,同进步群众、烈士家属一起共109人,被分为三个分队。每个分队建有党小组,设组长1名、组员5名。学习开始后,组织仍以各种方式确认学员的身份和历史问题,并作出不同处理。出于种种原因,训练人员又减少了几位,最后统计为102人。
狱中往事
翻阅档案中各种简历、自传、谈话材料等,犹如展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史篇。它们中有的简明扼要,有的长篇叙说,还有人写成了革命回忆录。例如从白公馆脱险的郑业瑞,他饱含深情地用毛笔正楷写下了厚厚一沓《二十六年话沧桑——郑业瑞自传》。
材料显示,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都是因为上级领导叛变而被捕,如傅伯雍在谈话中提到“因上级已供出,始承认身份”,从新世界饭店临时拘留所脱险的张科淑在自传中称是上级出卖了自己的哥哥张中(烈士,1949年11月29日遇害于松林坡)。唯有杨同生的情况比较特殊。杨同生原是八路军第3旅某连战斗员,在湖北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左臂被子弹打断,退下火线躲在老百姓家,不料被地方保甲发现送至乡公所被捕。因伤势过重,他先后开刀五次,治疗近两年,最后被送到重庆陆军总医院。尽管敌人给予了一定治疗,但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被投入监狱。
被捕同志有的遭受了酷刑。傅伯雍提到自己“受电刑二次”,盛国玉也“曾受过电刑”,郑业瑞更是详细描述了受刑经过:“被捕当天夜里就受了一次‘刑讯,十个指头夹上筷子再用板凳碾,周身被打得发紫。第三天,被送到二处,又是‘刑讯,坐老虎凳,用火柴烧皮肤,用枪柄敲螺丝骨。”除红岩志士外,被关押于石灰市看守所的王常风(索夫)也“受过两次毒刑”。不仅自己受刑,还牵连了家人。王常风说,家中曾被反动派搜过两次,父亲也被抓走关押,直到家中送上金银才被放出。
尽管深陷魔窟,遭受酷刑,他们仍然坚持狱中斗争,努力学习,期待重见天日,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郑业瑞在自传中记述:“我们自己学习,我们帮助人家学习(有书看),我们教育别人(包括特务在内)也接受教育。在我来说,王朴、刘国鋕、陈然等同志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与教育(我们都同被当作要犯关在第二室内)。我虽然只坐了半年牢,但我自信这年的进步,胜过在外面的五年。没有坐牢前,我有很多旧社会的恶习,很深的智识分子色彩。坐牢以后,这一切虽不敢说已经全部澄清,但至少也澄清了一大半。”
脱险志士在自传和谈话中还提到了难友。杨同生说,他在狱中认识了三位八路军,是三年前在巴东被俘的,参谋长吴某某已被枪决,排长李宁已殉难,团书记吴某某已病死。郑业瑞说:“监牢是一面灵魂的镜子,在那里面我认识了许多有善良的‘人的灵魂的人,如像已死的王朴、陈然、刘国鋕,脱险的罗广斌、毛晓初等。”
虎口脱险
从1949年9月起,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狱中志士进行分批屠杀。9月6 日,杨虎城、宋绮云等6人被害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枪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被害于电台岚垭;11月24日,杨虎城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被害于中美合作所梅园公路边。
11月27日下午,集中屠杀开始了。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狱中同志仍未放弃生的希望。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试图脱险,只有极少数人脱险成功。
档案中零星记载了部分情形。一位党员这样描述萧钟鼎的脱险情形:“萧钟鼎,在渣滓洞监内,因睡在死者底下,未被中弹。”又如名单上一位学员的基本信息:“谭谟,男……11月27日脱险受伤于白公馆。”事实上,谭谟已被敌人执行枪决,但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堆里爬出来,侥幸逃生。
再如郭德贤。她在谈话中提出,希望组织上考虑安置自己的两个孩子——郭小波和郭小可,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在11月27日大屠杀那天,郭小波、郭小可分别被郭德贤和难友周居正带在身边,成功脱险,保留了火种。而在另一边的渣滓洞监狱,不满周岁的卓娅,在母亲左绍英的怀抱里被敌人枪杀,母女殉难。
与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志士相比,其他监狱的难友境况略有不同。11月29日,当反动派将新世界饭店临时拘留所的32名革命者集体枪杀于松林坡后,由于人民解放軍步步逼近,他们已无力组织进一步屠杀,放松了看守,给了狱中志士可乘之机。从新世界饭店临时拘留所脱险的庞克在谈话时说:“11月29日,因为炮击极为激烈,哨兵只有1个,30余人一起突出。”
从石灰市看守所脱险的杜邦怀说:“于29日正当反动派稽查队全体撤退之际,在那生死关头的一刹那间,我们被囚的60余人(内有30余人是政治犯)冲出了牢狱,重见了天日。”
公开身份是公务员的朱明初,从重庆监狱脱险的情况是:“11月29日,经给看守长7个金戒指而被放出。”
被关押于太平门“反省院”的刘斯成则是“11月30日解放出狱”。
还有两位被关押于渣滓洞,但在大屠杀前被释放。
一位是蓝国农。他因参加进步组织而被捕,于1949年4月国共北平和平谈判前夕被国民党释放。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被作为伪和谈的装饰品,于3月31日离开了渣滓洞!”出狱后,他改名为蓝又耕继续活动。重庆解放后,曾担任第一届民进重庆市委会副秘书长、顾问等职。
另一位是杨同生,于1949年11月23日获释。据他描述,当晚国民党反动派将包括他在内的6人送到位于山洞的罗广文司令部,第二天司令部写下条子,叫他们自行去找部队,几个人就各自走散了。当时杨同生手臂残疾,眼睛也坏了,无法当兵,就在乡间乞讨为生。重庆解放后,他步行了两天才到达重庆城内找到组织。
市委干训班的红岩志士们,迎来了黎明曙光,投身于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渴望学习和工作,“要把剩下的生命献给更彻底的革命事业”。他们英勇不屈的事迹,也留给后人许多的思考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