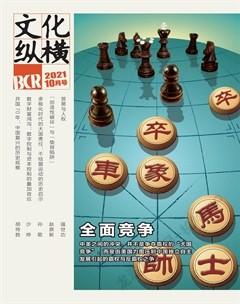迷雾:阿富汗之变

美国撤军阿富汗引发全球热议,国际社会围绕撤军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带来的影响、美退中进及其地缘政治后果、塔利班重掌政权后的意识形态及带来的全球安全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美国撤军及其霸权的未来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在全球范围引发了一系列对美国自身地位的讨论,主要涉及美国的阿富汗战略是否失败、撤军对其霸权和信用的影响以及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弥补过失等议题。
在美国的阿富汗战略是否失败这一议题上,持失败论者占多数。在6月22日《外交事务》组织的一次全美阿富汗问题专家的调查问卷中,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教授、阿富汗问题专家巴尼特·鲁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阿富汗问题,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已经宣告失败。鉴于目前的阿富汗局势,美国撤军是一项及时止损的明智选择。
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前,美国地缘战略学家乔治·弗里德曼撰文指出,美国已经输掉了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试图转换阿富汗人的价值观是徒劳的,美国既不熟悉阿富汗,也没有以恰当的方式来应对阿富汗,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当天,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迈克尔·麦金利撰文声称,“我们都失去了阿富汗”。他指出战争的失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过早满足反恐战争的胜利而忽视了国家建构;阿富汗国民军建设的失败对阿富汗政府的军事失败负有主要责任;过度相信并依赖地方势力和军阀来提供安全保障,没有协调好普什图族同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没有注意到塔利班的变化及其策略;在阿富汗问题上同巴基斯坦沟通的失效等。在美国撤军过程中,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在《经济学人》上撰文,指出美国设定的错误的军事、政治目标以及国内政治进程的分裂导致了在阿富汗的失败。
但在上述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查尔斯·柯赫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参与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的威尔·鲁格认为美国定点清除了本·拉登,并有效地保卫了本土安全,已完成了“反恐”这一战略目标。他认为不应该在阿富汗花费更多的财力人力,撤军并不意味着战略失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虽然也严厉批评了拜登的撤军政策,但是否认了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的失利。在他看来,美国撤军并不是軍事失利导致的,而是一种主动放弃的行为。
美国各界普遍认为,撤军阿富汗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势衰。持此观点者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他在26日做客盖洛普的广播节目时,同主持人穆哈迈德·尤尼斯讨论了“美国撤军及其未来霸权”这一主题,称虽然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失败了,但美国撤军并非军事失利,也不应过分夸大其影响。他认为当前美国依然在军事、高科技等领域保持了全球领先态势,这是未来美国霸权得以立足的根本。
拜登政府撤军阿富汗的决定及其表现遭到盟友的质疑和批评,盟友们除了表达对美国信用和能力的质疑外,也表达了对北约存在必要性的担忧。面对盟友的质疑,拜登在8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失去信誉。美国白宫安全事务顾问杰克·苏利文也表示美国对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承诺是一如既往且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如何弥补过失这一议题上,美国形成了战略转移论和维护核心利益论等观点。战略转移论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和前国家情报总管约翰·拉特克利夫为代表,认为美国此刻应当将战略目标转向亚太地区,并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操作来对抗中国,从而重新赢得全球信誉。维护核心利益论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中心应当是反恐,维护美本土免遭恐怖主义的袭击。这一论点意味着美国在保持现有能力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以反恐为借口干预阿富汗及地区事务的可能性。
后撤军时代的中国对阿战略
在中美全球竞争态势越发激烈的大背景下,美国撤军阿富汗也引发了评论界对中国在阿富汗战略定位的讨论。总体上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普遍持中国进击论。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塔利班代表来天津谈判之后,上述观点已经在西方世界发酵。兰德公司分析人士德里克·格罗斯曼撰写分析文章称“中国和塔利班将开始一段蜜月期”。他指出,通过同塔利班交涉沟通,以及同巴基斯坦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将更深入地介入该地区事务。除了分析中国介入阿富汗事务的有力抓手之外,他也分析了中国介入阿富汗事务可能面临的挑战:一是引起俄罗斯的怀疑和排斥,二是中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诉求同巴基斯坦的战略利益相抵触,巴方更愿意恐怖组织在其领土外活动。
除了认定中国会进击阿富汗之外,西方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在阿富汗的战略利益。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东亚政策高级研究员瑞恩·哈斯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哈斯认为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中国会从中获益。中国获取的利益不仅仅局限于西方分析人士认为的维护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获取重要的战略资源,以及为推进“一带一路”获得更广泛的地缘空间,还包括可以利用美国撤军阿富汗来渲染美国势衰论,以及开展更加强硬的对台宣传攻势。
一些分析人士重点突出了中国对阿富汗矿产资源的重视。在他们看来,阿富汗拥有丰富的金、银、锡、青金石以及稀土矿藏,这些矿藏的总价值在3万亿美元左右。而中国为了获得这些矿藏很有可能会姑息塔利班的极端政策,尤其是在侵犯人权和妇女权利等方面。有人认为在所有矿产资源中,中国最看重的是阿富汗的稀土资源,如果中国获取了阿富汗的稀土资源,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对这一资源的垄断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可以让中国应对美国的贸易制裁,甚至可以让中国反制美国,而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危险的。
阿富汗局势引发的安全问题
阿富汗一系列的局势变化会引发怎样的安全问题,被国际社会密切关切,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威胁的加剧、地缘安全、难民问题以及随之引发的新冠疫情的扩散等。
深受“9·11”恐怖襲击的影响,美国最关切的安全问题是重掌政权的塔利班会不会再次为恐怖组织提供庇护,并让阿富汗成为发动恐怖袭击的策源地。虽然塔利班在占领喀布尔前后已数次发布声明,表示会同恐怖组织划清界限并将注意力局限于阿富汗事务,但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卡尼网络”仍在塔利班的组织结构内,其领导人塞拉柱丁·哈卡尼目前担任塔利班副领导人一职,该组织仍然同“基地”过从甚密,因此美国并不信任塔利班,并对塔利班再次上台带来的本土安全问题表示重大关切。
美国前驻阿富汗联军司令、前中情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以及研究阿富汗安全问题的赛斯·琼斯、科林·克拉克等人都从反恐预防战略视角出发,反对美国撤军阿富汗。他们认为将阿富汗留给塔利班是危险的,会极大增加恐怖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危险。
科罗拉多基督教大学百年学院研究主任汤姆·卡普兰德表示,从时间节点上来看,阿富汗政权更迭与“9·11”事件20周年接近,美国本土再次遭到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极大。他进一步指出,目前连同“基地”组织在内,依然有将近20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这些恐怖组织虽然目标不同,但对待美国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在近期对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极大。对于卡普兰德的判断,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哈森颇为认同,他表示未来的三年半时间,对美国来说都是冷战以来的最危险时刻。
与美国相比,周边大国和邻国更多关注的是地缘安全问题。俄罗斯一方面对极端组织向中亚地区的扩散发出警告,称恐怖分子可能会混入难民对邻国进行渗透,另一方面强调应发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作用来应对这一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对美国重返中亚建立军事基地发出了警告。这些举动表明,俄罗斯正在重新规划其中亚战略,并试图在后撤军时代赢得先机。
对印度来说,地缘安全问题最值得关切。作为加尼政府的长期支持者和塔利班的敌视者,阿富汗政权更迭让印度陷入一个险恶的地缘政治空间中。以亚欧集团为代表的分析人士表示,受塔利班重掌政权的鼓舞,巴基斯坦极有可能会在印巴边境重新挑起事端。在巴三军情报局局长法伊兹·哈米德9月5日出现在喀布尔之后,印战略界表达了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担忧,并称中巴两国同时支持塔利班政权会进一步压缩印度的战略空间。
作为中亚地区第一大经济体,哈萨克斯坦更为关心的是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中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会被打破。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恐怖主义渗透问题,哈萨克斯坦并没有过于担心。该国政治学家多西姆·萨特帕耶夫表示,除非邻国遭遇政治版图变动,否则恐怖主义对哈国的影响将不会特别严重。但是,对后撤军时代中亚被某一大国支配的可能前景,哈国则颇为担心。对此,萨特帕耶夫指出,俄罗斯试图利用当前地缘态势,通过军事渠道重返中亚的图谋是后帝国综合征。
与阿富汗并不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表达了对恐怖主义扩散的关切。吉国防部总参谋长捷尔济克巴耶夫和边防局局长图尔甘巴耶夫都认为,随着塔利班上台,极端恐怖势力会向吉国渗透。鉴于“巴特肯事件”的前车之鉴和近年来“伊斯兰国”对该国的持续渗透,吉尔吉斯斯坦不得不对阿富汗局势保持警惕。
作为域外参与者,欧洲更多关注的是新一轮难民潮带来的冲击。这其中不仅包括对难民的接纳问题,还包括因接纳难民而带来的欧洲价值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右势力的崛起。上述问题在2015年之后已经对欧洲产生了全方位影响。对此,包括欧盟外交政策主席何塞·博雷利在内的重要人士已多次发出警告。
塔利班及其意识形态
在对塔利班意识形态来源的追问和探讨中,其意识形态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如此保守和极端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美国学者托马斯·巴菲尔德认为,塔利班意识形态是普什图部落法和伊斯兰教法的混合,而研究阿富汗地方势力和军阀问题的学者安东尼奥·季乌斯托兹认为,其意识形态内涵是乡村毛拉高举伊斯兰主义的旗帜来反对普什图部落法。巴基斯坦籍阿富汗和地区事务专家艾哈迈德·拉希德指出,在历史上,阿富汗伊斯兰深受迪欧班迪教团(Deobandi)影响,具有浓厚的苏菲主义传统。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极端性和保守性并非来自阿富汗伊斯兰传统,而是其成员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习得的结果。封闭的环境使得塔利班成员既不了解阿富汗伊斯兰传统,也不了解外部伊斯兰世界的理论争鸣,由此造成了他们的保守性和极端性。
在2021年塔利班发动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总攻势之际,供职于独立研究机构“阿富汗分析网络”的合作研究主任、高级分析师托马斯·鲁蒂格撰文分析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问题。鲁蒂格曾作为驻站记者先后采访过毛拉奥马尔和阿赫塔尔·曼苏尔两任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在提交给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的报告中,鲁蒂格追溯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演变轨迹,指出塔利班失去政权后,在对待妇女权利和教育问题、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以及对待媒体、与外界沟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软化迹象,而这种改变是由塔利班政治地位的变化、新一代领导人和成员的成长环境及塔利班的学习能力带来的。但与此同时,鲁蒂格也强调,这一变化的出现是塔利班学会政治妥协的结果,而其最终意识形态目标并不会改变。
在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之后,上述问题受到更多关注。通过对塔利班的长期观察,季乌斯托兹近日撰文指出,塔利班在圣战叙事上进行了去全球化宏愿的处理,但在管理外籍圣战分子问题上仍会遇到困难。而出身苏格兰的南亚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则认为,部落因素会在塔利班的意识形态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塔利班内部的实权派哈卡尼网络和雅库布派分属艾哈迈德扎伊部落的扎德兰分支和霍塔克分支,而代表逵达舒拉的巴拉达尔则出身于杜兰尼部落。这些部落和部落分支之间长期存在矛盾,更在如何对待美国和圣战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未来塔利班在意识形态表达上还要受到其内部派系分权的影响。
俄罗斯与阿富汗有着更紧密的地缘关系,该国学者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其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东方研究所所长、伊斯兰问题专家维塔利·瑙姆金对塔利班的态度同鲁蒂格相似。他认为目前的塔利班是实用主义者,在经历了长期的内战之后,新一代塔利班已经发生了改变,至少他们当中的某一派是期待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并获得国际援助和贷款的。与瑙姆金相比,伊梅莫·拉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阿列克谢·马拉申则更为乐观,他认为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已更趋于温和,并强调他们效仿先知穆罕默德和平进入麦加的方式进入喀布尔,展示了一种受过教育的软伊斯兰吸引力。圣彼得堡高等经济研究院东方语非洲研究所所长叶甫根尼·泽列涅夫则表示,2.0版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并不会出现根本性改变,伊斯兰价值作为其价值追求是根深蒂固的,在掌权后,塔利班会以他们认为正确的伊斯兰价值作为施政准则。但与此同时,泽列涅夫也注意到,2.0版塔利班追求建立的是一个伊斯兰的,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政权。(文/宛程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非洲大湖地区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主要参考文献:
Antonio Giustozzi, Koran, Kalashnikov, and Laptop: The Neo-Taliban 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2007.
Thomas Ruttig, “Have the Taliban Changed?”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CTCSENTINEL), March, 2021.
George Friedman, “Why America Loses Wars?”Geopolitical Futures, August, 2021.
P. Michael Mckinley, “We All Lost Afghanistan-Two Decades of Mistakes, Misjudgments, and Collective Failure,”Foreign Affairs, August, 2021.
Ryan Hass, “How China Seek to Profit the Talibans Takeover in Afghanistan?” Brookings, August 18, 2021.
Ирина Тумакова,“Террористы или строители? Как《Талибан》* поменяет захваченную страну — рассказывают востоковеды, ”novayagazeta,19 августа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