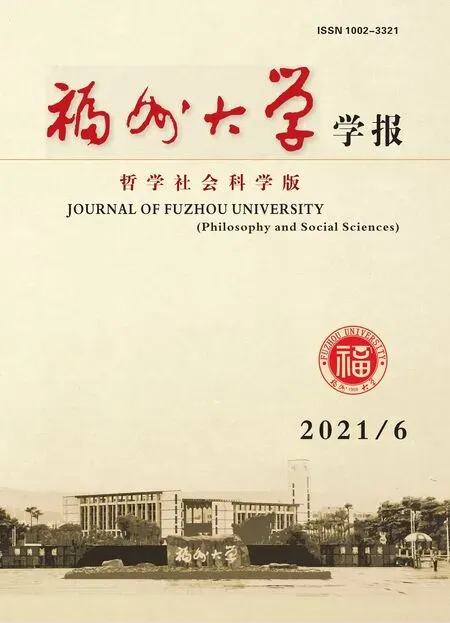“下南洋”与中国传统音乐在东南亚的传播
王昕野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中国传统文化对南洋地区发生最深刻持久的影响就是在著名的“下南洋”时期。[1]大批“下南洋”的华侨在东南亚的政治文明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他们在不畏艰险“下南洋”过程中不仅只身前往,还带上了中华故土的音乐文化。以“南音”为例,在南音起源的阶段,正是一群“下南洋”的中国人将南音带到了泉州以外的地区,让南音文化能得以传承和发扬,促进了人与人、族群和社会之间的和谐。[3]也许就像当初随着中原移民东移南迁至古代泉州一样,随着闽南人“下南洋”,南音也被带到了东南亚。中国的传统音乐被华侨带到东南亚后,经过磨合、适应和改变,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相融而形成了独特的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体系。
一、回眸近代“下南洋”
“南洋”包括今天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11国。17世纪以后,西方殖民势力开发东南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已经衰落,西方殖民国家把目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在国内,乾嘉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签订条约,允许华工出洋。“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下南洋”移民潮受东南沿海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影响,移居海外地理指向相当集中,一般是来自同一省域、县域或同一姓氏、家族的人聚居在一起,进而形成了地域和血缘居住社区。
近代“下南洋”以福建人和广东人为两大主力。福建人主要分布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广东人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下南洋”的华人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南亚所在国种植业、矿业、贸易、工商业、制造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近代中国“下南洋”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这次是以华人劳工输出为主体的“中国苦力贸易”移民潮。这阶段约有200万华工被送到东南亚,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种植园和锡矿场。这些华工契满后,有的回国,有的则成为自由劳动力留在当地谋生。这个时期,还有许多中国移民进入东南亚各国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行业。至1902年,东南亚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达400万人。第二次移民高潮从20世纪初到1950年代初,是“下南洋”的高峰期,其直接动力是东南亚经济的繁荣。20世纪初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带动的新型产业波及东南亚,大量的工商资本也涌入东南亚,投资铁路、港口、电力、航运、制造业、金融业等,传统的采矿、种植、原料加工、商贸业也有较大发展,对廉价劳动力需求旺盛,大量的闽粤民众流入东南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商企业崛起,更加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民众向东南亚移民。据资料显示,1851至1925年,仅契约华工去东南亚的就有177万人。到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口已达270万人,其中,爪哇岛170万,苏门答腊岛60万,加里曼丹岛26万,苏拉威西岛14万。持续多年的大量移民使得东南亚诸国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4]
二、“下南洋”与中国传统音乐在东南亚的传播
闽粤两地的“下南洋”移民将中国传统音乐带至落地国,并扎根发芽,形成了今天东南亚的华人传统音乐。华人的传统祭祖酬神活动成为传播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场域,华人社团组织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提供组织保障,商业性演出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与当地音乐的融合并职业化。
(一)中国传统音乐在东南亚的主要传播形式
1. 酬神祭祖活动与各类戏曲的传播
华人移民定居“南洋”时,也将家乡的神明带到了居住地。为了祈求平安、答谢神恩、祭祀先祖,他们会在每年的农历重要节日或神灵的诞辰进行酬神活动。不同地缘的华人会用家乡的地方传统戏曲演出酬神戏,在“南洋”的酬神戏台上,闽剧、高甲戏、歌仔戏、潮剧、琼剧、粤剧等各派系的地方剧种争奇斗艳、经久不衰。
早期,“南洋”的华人生活拮据,免费观看的酬神戏不仅仅是他们思乡之情的寄托,更是重要的精神娱乐活动。因此,在20世纪中叶以前,酬神戏起着娱神和娱人的双重作用。一年中的几个重大节日,华人神庙都有酬神活动,场面壮观。大的神庙设戏台,专门上演酬神戏,演出少则三四天,多则一个多月。华人居住的街区公所设置神棚(行宫),其正对面扎戏棚,彻夜演戏。酬神戏的消费需求吸引了大量中国戏班到“南洋”各国演出。据《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福建省志·戏曲志》《泉州戏班》等文献记载:20世纪20、30年代,粤剧、福建高甲戏、潮剧、琼剧、福建南管戏、莆仙戏、台湾歌仔戏、京剧、广东和闽西的汉剧、闽剧、梨园戏、福建十番、锦歌、飏歌、粤曲总计15个剧种、曲种的演出团体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20世纪30年代后,歌仔戏开始兴盛,歌仔戏班大量赴新马献艺,逐渐取代了高甲戏的地位,到后来“甚至连山芭里的酬神戏也都由歌仔班取代了”[5]。以新加坡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演出时间越来越长,从最初的二三十天增加到一百多天,新加坡也渐渐成为“南洋”最重视地方戏曲的国家。此外,为了满足酬神演戏的需求,当地华人移民也开始学习传统戏剧,他们自办戏班,许多社团设置有自己的戏剧小组,为自己本社团或本派系酬神演出酬神戏,较有影响力的有马六甲同安今夏会馆的戏剧组、马六甲明星慈善社的粤剧组、槟城广东顺德会馆的粤曲组等。
进入21世纪,“南洋”的华人移民后裔早已落地生根,虽然看戏听曲者越来越少,社团的传统戏剧组纷纷解散,但是酬神戏依然为歌仔戏、布袋戏、粤剧、琼剧等传统戏曲提供生存的空间,如活跃在马来西亚的筱麒麟戏班与九皇爷庙的酬神戏、月宝凤班与观音诞和拿督公的酬神戏、琼剧戏班与巴生港海南村水上人家华光神庙酬神活动等。正如马来西亚筱麒麟戏班老板刘臣虎先生所言:“只要有神在,戏班就不会消亡。”[6]华人重族性归属感,传统酬神祭祖活动如同一把保护伞,让中国传统戏曲音乐文化在“南洋”的土壤上得以生根、发芽、传播、成长,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2. 社团音乐活动与华乐发展
华人社团是彰显华人团结互助的典型代表,承担着联络乡情、酬神祭祖、互相扶持、解决纷争、发扬传统文化等责任,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华人社团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华乐的兴起和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堡垒作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方面面都为传统音乐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早期的“南洋”华人社团的音乐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属于某一非专业音乐社团的业余音乐活动,很多地缘社团都设有音乐组和戏剧小组,例如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的南音组和戏剧组、巴生永春会馆南音组、马六甲明星慈善社的粤剧组、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吉兰丹、甘马挽、关丹、马六甲等地的琼州会馆下属的琼剧组等。[7]这些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业余爱好者,教授、学习与表演活动都是义务性的,目的多为宣传华人传统文化,增进社员间感情,或为需要帮助的华人团体和学校义演筹款,这类社团音乐活动推动了中国传统音乐在当地的发展,使其日渐本土化,为文化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类是专业音乐社团的音乐活动,如菲律宾的南乐崇德社、新加坡湘灵音乐社、马来西亚的梨园公会、八和会馆等,这类社团拥有优秀的音乐人才,他们以传播发展家乡的音乐文化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向“南洋”乃至世界人民展示中国传统音乐。如1941年成立的湘灵音乐社是南洋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南曲社团之一。湘灵音乐社不附属于会馆,而是正式的南曲社团,社团以研习南音和发展南音艺术为宗旨,编辑出版了许多曲谱集。它拥有优异的演出人才,演唱技艺精湛,经常于广播电台播放南曲,在星马南音界声誉很高。[8]
由于时代发展以及华人地位和认同的变化,社团中的音乐活动随着社团社会功能的转变逐渐发生着变化。20世纪中叶以后,新兴的具有共同欣赏性的华乐取代了纯地方性的传统音乐活动,地方性的音乐组纷纷改为华乐队,专门性的文艺社团活动代替了其他各类社团组织中的附属音乐组和戏剧小组的音乐活动,移民华人传统音乐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存在发展的文化艺术。
3. 商业性演出活动与中华传统音乐的融合
随着南洋移民华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华人社会的精神娱乐生活需求日渐庞大。1840年到1949年,福建地方戏在这一时期“下南洋”商演形成高潮,先后有32个有明确名称、主要演职员名单的戏班出国演出。中华传统音乐与商业性演出的融合,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进一步传承、创新奠定了市场基础。
19世纪下半叶,地方戏已开始有固定的职业演艺场所,出现戏院、戏园等可供戏班租赁演出的地方。1878年中国驻英公使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使英法,期间曾途经新加坡作短暂停留,他在日记中写道:“华人约十万人,闽人居其七,粤人居其三……廊宇、会馆、酒楼、戏台、无不具备。”[9]到了20世纪60年代,固守传统的社团音乐活动逐渐人迹寥落,而依赖商业演出活动生存的戏院、游艺场、华人戏班等纷纷建立,并且生意兴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国内华人社团进一步统一,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不断壮大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往来,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政策,促进了华乐的创作和活动。游艺场成为闽剧、粤剧、潮剧等传统戏曲的重要演出场所。[10]在当时的南洋,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新加坡的娱乐总汇游艺场、马来西亚的安乐世界游艺场、马六甲的极乐园游艺场、槟城的新世界游艺场等。这些游艺场大多收费较低,经济实惠。例如新加坡的娱乐总汇游艺场,每人只收一角叻币即可进场观看,所以游艺场内,每晚游客络绎不绝。[11]
南洋的华人戏班是市场需求的产物,职业戏班常年在各地巡演,不同的剧种有专门的戏班。如歌仔戏较有影响力的戏班有1937年由新加坡人林金美组建的新麒麟闽剧班、槟城商人吴金狮组建的牡丹歌舞团,以及林莺莺、林燕燕姐妹在吉隆坡建立的莺燕闽剧团等;粤剧方面有新加坡的普长春、新佳祥、庆维新三班,吉隆坡的安邦、芙蓉、金宝等戏班,这些戏班和戏院是一体的。此外,还有庆丰年剧团、万年青班、新同庆班和红棉粤剧班,它们经常聘请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名角来演出。在南洋的土地上,这些华人戏班为了更好地适应海外社会市场需求,长久生存下去,它们的表现灵活多变,努力与当地文化互动融合。[12]各剧种的戏班之间也会相互交流学习,博采众长,灵活吸收当地方言,例如马来西亚的歌仔戏对白中就大量采用马来借词。这些举措不仅使戏班获得更大的受众群体,而且也更有利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下南洋”的过程中传承下去。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南洋的传播途径和扩散人群
在“下南洋”的迁徙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如何扩散落地?究其途径而言,一是移民本身传播,二是专业艺人传播,三是华文教育传播。
1. 移民本身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时局动荡,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迫使大量华人移民南洋。这些以劳工、小商贩等下层劳动者为主的移民将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地区的各种民间音乐艺术,如南音、潮州音乐、广东民间音乐、潮州歌谣、客家山歌等带入了南洋各地,各类民间音乐艺人在南洋各国活跃起来,华文音乐社团也随之设立,从而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东南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早期的南洋华人移民大多是穷苦劳工、农民和小商贩,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饱受生活的苦难,漂泊在异国他乡,习惯哼唱家乡歌谣来直接表达内心感受和抒发思乡之情,无意识地传播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此外,一些福建民间音乐也依赖这种口头传播在南洋不胫而走,如南音、锦歌等音乐形式。移民劳工无意识的口头传播是早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南洋扩散的主要途径,由此,华人文化开始在南洋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随着华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从单一向多层次转变,移民华人中开始出现富裕的工商阶层,从事科教文、医疗等行业的“士”阶层。这些人均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虽不从事专业音乐职业,但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他们常以高雅音乐自娱活动。“士”阶层也成为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特殊传播群体,是移民传播扩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基础途径之一。
2. 专业艺人传播
在南洋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专业艺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乡情邀演、政府组织或艺术交流,从国内到南洋进行短期演出的艺人;另一类是南洋土生或长期定居在此的华人艺术家,他们中有创作家、演奏家、理论家,还有乐团的组织领导者。
乡情邀演大致有酬神演出、剧场演出、庆典演出以及慈善义演四种形式,前三种属于商业性质。在早期,海外华人移民会因节日娱乐、宗教酬神活动的需要,请国内的专业艺人去南洋演出家乡戏等。以马来西亚为例,19世纪中叶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传统音乐艺人和团体到马来西亚演出,1840-1843年高甲戏三合兴班南来演出。这些戏班和艺人南来演出,传播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充实了当地人的精神生活,为后来中国音乐团体前来演出打下基础,开辟了道路。到了20世纪30年代戏院、游艺场等纷纷建立以后,大量的国内戏班、艺人受邀到南洋演出谋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注重文化外交活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以自上而下的形式选派艺术团体、专业艺人到东南亚进行各种形式的出访交流活动,文化演出时间较短、节目精干,参与演出的艺人大都经过筛选,为中国传统音乐在东南亚的传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长期活跃在东南亚的舞台上的专业艺人,或以演艺为职业或传艺或组建剧团,常年在南洋各国巡回传艺,技艺精湛,受到当地华人的尊重和喜爱。如福建泉州著名南音老艺人陈天波,青年时期曾在印尼等地传授弦曲,他的学生刘鸿藩几十年来在菲律宾等地传授南乐。古筝大师陈蕾士先生20世纪60、70年代担任麻坡中华学校教师,周末在吉隆坡教授古筝,经常参加雅集式的演出。[13]音乐理论家陈松宪是马来为数不多的华乐理论研究者,他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从事华乐研究工作,2003年12月,他出版了华乐论文集《寻音觅韵》,填补了当地华乐理论研究的空白。还有东方民族音乐中心及东方民乐团的组织者——丘治安,一家三代都是华乐爱好者,为马来西亚华乐团探索专业化道路做出了不懈努力。正是这些专业艺人的辛勤耕耘,为南洋培养新生代音乐接班人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音乐在海外的传播。[14]
3. 华文教育传播
在华人移民集中的南洋社会,华文教育一直是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手段,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20年代基于国家认同设立的中华会馆、教育社团的近代华文学校,海外华文教育历经百年沧桑,逐渐步入规范正轨。华文音乐教育是华人寻求文化认同、提升族群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各所华文学校也成为传统音乐文化在东南亚扩散落地的重要基地。
南洋的华文学校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最为显著的是表现在华乐方面。其中,海外华校创办最多最成功者,当首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这与该国宽松的华文教育政策和当地客属公会及各界客属社团的贡献密不可分。1965年,马来西亚第一支中学华乐队——马六甲培风中学华乐队成立。自此开始,学习华乐、成立华乐队在南洋的华文学校中蔚然成风,几乎每所华校都拥有自己的华乐队。它们依靠社会各界捐款筹募资金,华乐工作者的义务教授、辅导,乐队队员们互相传帮带、自学自练的传承方式,以及华人社会各界的重视,在南洋遍地开花。据统计,马来西亚各州华校华乐队约55个,著名的如大山脚日新校友会A队(槟城)、怡保陪南独立中学(吡叻)、北海钟灵中学(槟城)等。
现如今,大批海外新一代华人开始学习独奏型华乐器,不同于在学校和社团学习的个体学习行为,其目的更多的在于培养一种业余爱好或一技之长,并通过中国的考级来检验学习成果。1990年和1991年,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和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联合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华族乐器分级考试,当地华人纷纷报名参加。此后,部分东南亚主要城市开始每年正式举办华族乐器分级考试,考生逐年增加,考试项目有二胡、古筝、琵琶、笛子、扬琴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近几年,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引进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教师举办短期培训,当地学生学习到一定程度还有机会到中国深造,学有所成后归国为华乐发展做贡献。
传统音乐文化扩散的过程中,也深受南洋诸国的民族、宗教、风俗、审美观念的影响,进而不断融合、演进,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扎根,成为东南亚民族音乐文化的一道风景线。
三、“下南洋”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启示
回溯中国传统音乐在东南亚的传播、开枝散叶这个过程,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化认同”的思考,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既是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成果,同时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彰显,其价值与意义已经超过了艺术本身。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成功“下南洋”,对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有很多有益启示:
1.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海外传播要坚持先器后道、多途并进、交流互鉴的传播原则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传播内容上应该先器后道。音乐虽然被称为是“无国界的语言”,但海外异域,不同国家的国情民情迥异,宗教民俗审美也不一样,加上语言上的障碍。我们在国内认为是最好的“国粹”,在国外就不一定能够让人们认知和欣赏。为此,在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时,不宜“纠缠文化观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要尊重差异,要想在短时间得到大范围推广,内容才是最关键的要素,内容要创新、表演要精彩、表现方式要有所改进,增强所在国民众的感性认知,逐渐上升到音乐之“道”的理性认同。
在传播形式上应该多途并进。近代“下南洋”时期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播主要还是靠人这个载体,传播的形式也较为单一。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科学技术特别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各国民众之间的交往交流日渐密切。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播要改变靠人单独单向传播的方式,应契入商贸、教育、文化项目、体育活动、品牌活动、各种驻外机构中,综合力量,多渠道多途径潜移默化地传播。如举办中华音乐文化“艺术节”“文化周”“文化年”等活动促进传播。[15]
在传播目标上应该交流互鉴。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要实现本土化、世俗化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过程。我们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旨在塑造“文明大国”形象,我们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其实质就是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对话。[16]因而在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活动、文化理念时,要注意挖掘和汲取所在国音乐文化的精髓,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播,应建立在奠定文化认同的基础上。
2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海外传播要坚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跨国民心相通,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的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中,应当充分借鉴“下南洋”的历史经验,锤炼符合自身实际的文化传播特色。同时,要紧随国家发展战略,不断厘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中的定位。就目前而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中要秉承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跨国民心沟通,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的。这样才能让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中更容易获得各国百姓的共鸣,进而推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特色的国际倡议的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加强国际间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标志之一。音乐无国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宣介,可以让各国百姓更全面细致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消除文化鸿沟,进而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下南洋”等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音乐是搭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民心交流的最佳“桥梁”与“纽带”。民心相通,才能真正带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这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开具的又一良方。正如总书记习近平所言:“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合作共赢,必须要坚持公平、开放、包容的发展观,践行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是推动各国文化之间“和而不同”、互动交流的重要突破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不是进行西方所谓的“文明入侵”,而是要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赢效果。
3.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海外传播要坚持政府支持、民间参与的传播路径,重视现代新媒体线上传播平台的利用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已经有了多年的历史,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但要进一步提升传播效果,需要加大力度,使更多人参与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中来。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播不同于其他普通物质产品,应从社会效益出发,把海外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当作政府行为予以支持,纳入国家社会发展规划。同时,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走出去,奖励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国际友人。国家可建立海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地,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走出去”提供稳定的空间。同时要鼓励民间社团积极参与,利用地缘、侨缘优势积极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积极构建海外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鼓励外国青年来华学习、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日后回国成为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大使。
随着现代新媒体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强大技术平台。目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下南洋”中对新媒体技术的倚重也日益增强。以抖音海外版 Tik Tok为例,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海外日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3.2亿人,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国内。尤其是年轻用户下载人数激增,连续多月助力Tik Tok成为下载量最高的新媒体APP。未来, Tik Tok海外用户超过国内用户是一种必然。除此之外,全球知名新媒体平台还有快手、脸书等。新媒体的快速崛起,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插上技术腾飞的翅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要积极行动起来,紧紧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节奏,创建属于自己的网站、平台,将更多的信息推送到观众面前,通过多种方式与市场和观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洞察受众的真实需求,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
注释:
[1] 李 朦、孙良好:《许地山笔下的南洋形象——以〈命命鸟〉〈缀网劳蛛〉为中心》,《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 刘小敏、薛永贤:《粤人“下南洋”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启迪》,《岭南学刊》2009年第5期。
[3] 王 青:《泉州南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探析——兼议海峡两岸对南音的传承保护策略》,《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4] 郑长铃:《中华文化海外“泛家族”式传承传播初探——以马来西亚适耕庄福建会馆南音复兴为例》,《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5] 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王静怡:《中国大陆传统音乐在马来西亚的传播》,《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7] 王忠林:《四大传奇及东南亚华人地方戏》,南洋大学研究院出版,1972年。
[8] 王静怡:《东南亚华族传统戏剧与酬神活动生存关系之调查研究》,《音乐研究》2009年第3期。
[9] 王静怡:《中国传统音乐在海外的传播与变迁——以马来西亚为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 吴少静:《近代福建音乐向南洋传播的主要方式》,《八桂侨刊》2002年第4期。
[11] 曾纪泽:《使西日记》,《晚清海外笔记选》,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年。
[12] 王静怡:《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主题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3] 王静怡:《东南亚华人传统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6期。
[14] 王静怡:《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迁》,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
[15] 吴少静:《近代东南亚华人对闽南音乐的继承与传播》,《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16] 苏颖雯:《潮剧在泰国的传播与发展研究》,《当代音乐》2018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