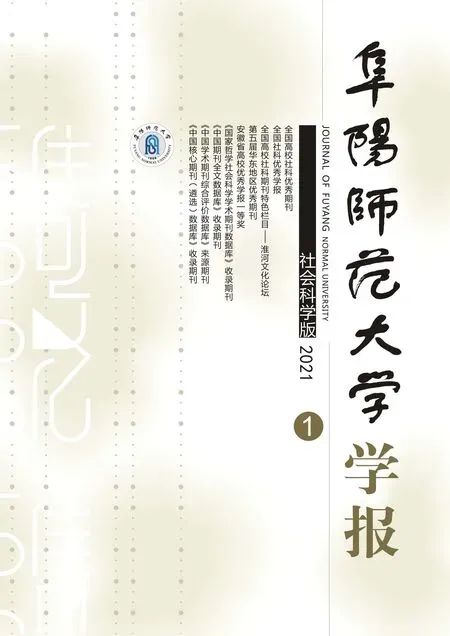莫言小说对苦难叙事的超越与突破
徐 涛
莫言小说对苦难叙事的超越与突破
徐 涛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莫言小说苦难叙事独具特色,通过声音与色彩的运用展现出苦难的无奈与沉重;通过多元叙事与时空重构阐释出苦难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幽默与讽刺显反射出苦难的荒诞与隐痛;通过日常生活伦理的解读实现苦难的顺应与救赎。莫言小说实现了对于传统小说苦难叙事的超越与突破,让所有卑微的生命面对苦难的压迫时能够平静面对、无所畏惧,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重要意义。
英言小说;苦难;叙事;突破;超越
莫言作品对于我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他通过乡土小说的苦难叙事,提炼出了一种悲苦、苍凉的现实;通过对家乡土地上的悲苦、苍凉的描述、剖析,挖掘出其中深藏的悲剧性人生体验;通过声音与色彩的运用展现出苦难的无奈与沉重;通过多元叙事与时空重构阐释出苦难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幽默与讽刺显反射出苦难的荒诞与隐痛;通过日常生活伦理的解读实现苦难的顺应与救赎。与传统的乡土小说相比较,莫言对于苦难的书写有继承,但是更多的是超越与突破,这使其小说苦难叙事展现出不一样的写作特色与审美效果。
一、通过声音与色彩的运用展现出苦难的无奈与沉重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通过色彩和声音渲染苦难叙事的作品是非常多的,张爱玲、苏童、刘震云、铁凝等现当代作家也都对此进行过尝试,如张爱玲曾经对苍凉的白色、忧郁的蓝色进行过深刻的探讨。但当前大部分文学作品利用色彩和声音进行苦难叙事时,写实较多,关注的是色彩、声音对于苦难叙事的帮衬。在莫言的作品中,对于色彩与声音的运用是非常多的,既有实写,也有虚写,充分利用色彩的变化和声音的传递实现对于人性的挖掘。在莫言的作品中,色彩和声音不仅仅是一种帮衬,而是苦难叙事中比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打开莫言的作品,就如打开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多彩多姿的颜色。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杏树的浅红、地瓜的皮白、萝卜的暗绿无不荡漾着生命的光彩。《红高粱》中对于红盖头、红高粱描写的给人心灵一颤的感觉,这里红盖头、红高粱中的红,是一种能够穿透人心的色彩。《金发婴儿》中对于婴儿皮肤、毛发的描述,与外面的世界浑然一体,让人在色彩中领略了生的本源。另外在《怀抱鲜花的女人》《生蹼的祖先们》《红蝗》中也都出现了令人心动的色彩描写,这使莫言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五颜六色的高密风格。在色彩的描写上,莫言的手法是多元的,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虚实相间。例如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对于树叶的绿、牙齿的白、眉毛的淡黑等描写是实写,就是对外界的客观描述,但对于水的颜色、翠鸟及麻雀的颜色等描写则是虚写,作者并没有真正看到这些景物,而是通过黑孩的想象去完成的。在莫言看来,单纯的实写虽然能够实现对于景物的细致刻画,但不利于情节的拓展,会在创作过程中影响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而单纯的虚写虽然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驰聘,但不利于与人物情感、情节发展紧密融合,而虚实相间的运用,能够在客体和本体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作品对于色彩的客观描绘通过叙述者的想象实现,从而创造出一种迷离可感的梦幻,意旨深远。例如在《红高粱》中莫言对于血的描写就与常态不符,奶奶的血本来是红的,但是却把父亲的手和自己的胸脯染绿了,增加了作品的魔幻色彩。在《枯河》中面对冉冉升起的太阳,莫言看到的不是绚烂的色彩,而是借助阳光的温暖感受到音乐的华彩,在音乐的华彩中,主人公脑袋里面的火苗不停地变幻,一会黄,一会红,最终在变绿变小的过程中熄灭了。其中对于父亲手上血的颜色的描写、对于屁股伤痕斑斑的描写就是实写,带给人强烈的现实感受;而对于奶奶胸脯的描写、对于脑袋里面火苗的描写就是虚写,给人带来奇特的幻觉。通过虚实相间的描写,使读者在一种奇特的虚幻中感受到生命的真实,以及生命将逝的悲哀。
“色彩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代表某种象征,承担特定的含义。”[1]对于莫言的作品而言,同样如此,在莫言的作品里面所有的色彩都具有独特的生命内涵意义,莫言把这些生命的意义赋予色彩的定义,实现了独特的审美功效。在莫言的色彩审美中,大部分色彩的“美”不是光辉灿烂的美,莫言通过对色彩内涵的反转来实现对人性的剖析,解读困难的现实与感受。在《狗皮》中莫言面对充满绿色的高粱地,感受到的是蛇一般的缠绕,闻到的是暗绿色毒素的气息,丝毫没有感受到生命的希望,在莫言看来,这里的绿色根本就不是生命的本色,是丑恶的食草族的代表色,莫言把食草族用绿色去描述,其实质就是想表达出丑恶力量的“生生不息”,在这些“生生不息”的丑恶力量中杂种高粱、退化人种是一种广泛的存在,显示出生命的悲哀,在作者的笔下,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苦难的卑微,还有对于苦难的无奈。同样的描写还出现在《欢乐》中,作者通过对于绿色的诅咒,表达出全方面的痛苦感受,耳朵里面、眼睛里面、鼻子里面、甚至灵魂里面都充满了肮脏的绿色,让人无法呼吸、无法直视、无法思考,这种令人窒息的痛苦让人感受不到生的欢乐,世界上充满的都是暗淡荒凉。在莫言的笔下,色彩中的温暖明亮都是表象,其深层语意下隐藏的都是对于苦难的独特感知。
莫言在困难叙事中除了对于色彩的把握非常成功之外,对于声音的运用也炉火纯青。儿时的经历让莫言对于声音的感觉非常敏锐,那些农村集市的说书艺人生动形象的声音描写对莫言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莫言曾经说过,儿时的他对于说书艺人模拟风的声音、马蹄的声音、水的声音、鸡鸣狗叫的声音都印象深刻,甚至时时会在脑海中回忆,也会努力在现实世界中去感知。成为作家以后,莫言在写作的过程中也逐渐感受到声音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有着厚重的生命内涵的,通过声音可以让人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欢乐,也可以让人感受到无法言传的困苦,尤其是对于苦难书写,声音具有难以替代的本体论意义。在关于苦难的描写中,声音既有显著的映衬作用,同样可以单独成为一个自我展现的叙事空间,从声音的描述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听”出苦难的类型、苦难的程度,这种通过“听”感受到的痛苦与通过文字描写感受的痛苦是完全不同的,能够直达人的内心深处,让读者感受到撕裂般的疼痛。根据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声音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在”,声音不仅可以实现对于困难的“镜像”,而且可以实现对于苦难的升华。莫言在困难叙事中对于声音的运用手法是多样的,有单一的声音,例如在《檀香刑》中孙丙的嗥叫就是单一的,无论是最初凄厉的尖叫、行刑过程中一声接着一声的嚎叫,以及最后淹没一切的惨叫,都是单一的声音叙述,通过孙丙凄厉的叫声展示他的刑罚痛苦。另外莫言在很多作品中对于苦难的声音运用是综合的、交叉的、混合的,比较典型的是对日本鬼子强奸二奶奶过程的叙事,莫言通过多种声音的交互混杂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无耻、二奶奶的愤怒无奈、孩子的恐惧惊慌,这其中有女人面对侮辱时反抗的嘶叫,孩子们面对恐吓时的嚎哭,被人类行为惊吓后的小鸡咯咯叫和毛驴的鸣叫,这些声音共同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受到整个世界都是无情的、凌乱的。在这里你无法得到生命的尊严、生活的安全,一切的一切都充斥着让人无法闪躲的苦难,在这里苦难没有边界、苦难没有终点,这种苦难是是令人绝望的。如果说二奶奶被强奸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苦难,那么刘罗汉被剥皮就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痛苦,在对于刘罗汉被剥皮的描述中,莫言通过日本鬼子的咆哮、孙五的撕心裂肺、罗汉大爷滴血的痛骂展现出一个令人恐怖的人间惨剧,在这里人和动物没有任何分别,人在面对非人的折磨时无能为力,这种痛苦对于刘罗汉来说是肉体的痛苦,而对于其他人是心灵的撕裂,而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则是沉重的民族灾难。
莫言的作品中,人们之所以能够感受到苦难叙事的深沉,与其对声音和色彩的运用是分不开的,从莫言的声音和色彩描写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肉体的痛苦、生活的艰辛,更能够感受到主人公精神的压抑与苦闷,而莫言正是通过对于肉体的痛苦、生活的艰辛以及人精神的压抑与苦闷的描述,实现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探索。另外,莫言在色彩和声音的运用时,经常是互相映衬的,通过色彩和声音的相互映衬实现苦难的深层书写,这是莫言小说苦难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色。
二、通过元叙事与后现代主义手法阐释出苦难的深度与广度
声音与色彩的运用,可以使小说叙事过程中对于苦难的描述更加准确生动,打动人心,但是仅仅利用声音和色彩对苦难进行书写显然是不够的,在莫言的作品中,苦难是沉重的,是有强大的辐射力的,为了阐释出苦难的深度与广度,莫言充分利用了元叙事和时空转换的技巧,通过叙事者的选择和叙事视角的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时空结构,为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创造出坚实的结构支撑,既能深刻反映出苦难的深度,又能全面反映出苦难的广度。
首先莫言创造性地使用了“元叙事”手法。在莫言的很多作品中,叙事者本身,不是高高置身与事件之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视野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进行讲述,而是深度参与到事情的发生、发展之中,也就是说,在莫言的作品中,很多叙事者本身也是参与者,作为叙事者不能仅仅冷静地就事件的过程进行讲述评说,还要与故事的发展密切相关。实际上当前很多西方现代作家都采用过类似的“元叙事”方式,但是莫言与他们不同的是,叙事者介入故事的讨论非常深入,有时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理解与判断。莫言这么做的主要意图是通过叙事者介入故事的讨论“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引导读者认同叙述的可靠性和权威性”[2]。莫言的很多作品中,叙事者都具有较高的思维导向意识,通过叙事者的思维导向,引导读者走向作者的创作思维方向,这是在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大胆尝试,对以“元叙事”为主要手段创作方式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例如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那天只有一个日本兵来侮辱二奶奶,我们是否敢于上前解救呢?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于二奶奶苦难的讨论,6个日本兵是一个恶势力集团,人们无力反抗,对于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日本兵呢?有没有人敢于大胆反抗?二奶奶的苦难是不是会消失?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莫言的苦难书写往往与苦难的思考互融互通,莫言的写作目的不是仅仅展示中华民族的苦难表象,而是希望挖掘出苦难的内里实质。这种挖掘如果仅仅通过作家的哲理反思,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通过叙事者身临其境般的讨论则更能够直达人心。另外在中国大部分作家的叙事主体中,通常以一个叙事者为主,但是莫言对多主体叙事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且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逐步形成了莫言特色的“元小说”叙述方式。在《檀香刑》莫言选择由5个叙事者对事件的发展、变化进行叙述,在《生死疲劳》中选择2个叙事者进行叙述,这些叙事者一方面对于自身的事件进行叙述,另一方面对其它叙事者的叙述进行评说。实际上,这些评说仍然和前面我们所说的叙述者参与事件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多元叙事者的互相评说实质上就是通过他们的争论带读者进入一个讨论的空间,只不过这个讨论的空间是隐性的,不是显性的,这种讨论方式会让读者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忘我的境界,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产生深深的认同,对苦难叙事的内容和形式产生共鸣。
莫言的作品,除了对于“元叙事”的创新应用外,也大胆借鉴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通过叙事者的有意引导,使读者和叙事者产生时空中的距离。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创作理论看来,一味地将叙事者与读者的时空重叠,虽然有利于读者进入到作者的创作空间,对作品产生共鸣,但由于读者独立的时空有限,很难进行独立意义的深度思考,容易在短暂的共鸣后产生困惑与疑问,反而不利于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地位的提升。西方后现代主义创作理论建议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需要适当拉开读者与叙事者再现的历史场景,使读者在听故事的同时,能够冷静客观地对于叙述者的观念进行判断思考。从整体上看《蛙》的叙事方式采用了书信体叙事方式,但是与我国传统书信体小说的叙事不同,莫言不是完全通过书信对于整个事件进行叙述,而是在书信叙事的过程中插入了话剧成分,又在话剧叙事中加入了电视戏曲片的拍摄,使整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异常复杂。莫言使用这么复杂的叙事结构去实现《蛙》的叙事,一方面是因为民国阶段的社会发展非常复杂,单一的书信结构无法准确、细致地分析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苦难现实;二是希望通过陈眉的败诉来挖掘在那个历史时期人民苦难的根源。如果仅仅依靠书信,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很多语言和观点是不可能清晰地展现的,而硬展现则有可能引起读者的质疑,而通过电视戏曲片的拍摄则很好地回避了当时的历史现状,对造成中国民众苦难的成因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作者理想的叙事效果。
莫言在苦难叙事中除了采用叙事技巧外,在时空重构方面也非常注意,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时空体。时空体是什么,不同的研究者给出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巴赫金对“时空体”内涵的理解,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一文中,巴赫金提出“时空体”就是“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在莫言的小说中,对于时空体的把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开放的,二是所有的叙事都是在一个整体化的空间进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莫言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善于在世界的空间整体中看到时间、读出时间,另一方面又能不把充实的空间视作静止的背景和一劳永逸的定型的实体,而是看作成长着的整体,看作事件”[3]。在莫言的作品中,所有的困难都是一个具体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的艺术时空中,空间与时间高度融合,并进行着动态的发展,在这里时间不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而是凝聚浓缩为一个艺术的“实体”,虽然不可触摸,但可以通过艺术显现。而空间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要在时间的范畴内去感受、去把握。莫言通过对于时空的重构使苦难叙事存在于一个完整的空间当中,使所有的苦难叙事不会脱离客观主体而独立片面的存在,不同的苦难事件形成一个苦难的整体,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增强了苦难叙事对于读者感官、视觉等方面的冲击力。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丰乳肥臀》中关于上官鲁氏生育痛苦的叙述,单独看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虽然1939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但在这一时间段生产的妇女多了;单纯从空间看,游击队员的尸体被日本人践踏在桥头的空地也不是那个年代的偶然现象,但把二者放在一起,通过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体,我们则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上官鲁氏遭受的痛苦之久、程度之深、强度之烈。在上官鲁氏遭受的痛苦中,有肉体的苦、心理的苦,有自身的苦、为孩子担忧的苦,有生活的苦、外界环境的苦。对于这些苦,莫言都有单独的叙述,但是所有的叙述都没有脱离这个活动着的时空体,不同的苦难在这个统一的时空体中共同发展,“他把空间并列的东西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的成长时代”,然后把它们凝集在一起,形成一种苦难张力,剧烈地向外迸发,强烈冲击读者心灵。
总之,莫言的苦难叙事才能是无与伦比的,能够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外界与内部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并最终把它们形成一个完整的时空体,通过这种完整的时空体,不仅能够增加苦难叙事的深刻性,也能为读者对于苦难的反思提供重要帮助。
三、通过幽默与讽刺反射出苦难的荒诞与隐痛
中国文学作品自古就有通过讽刺和幽默进行苦难书写的习惯,现当代作家中能够熟练运用幽默与讽刺进行小说叙事的也并非莫言一人,鲁迅、张爱玲、王朔等作家等都曾经在幽默与讽刺中,对人性的丑恶、苦难的沉重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其幽默与讽刺和我国现当代其他作家有相似的一面,基本都是通过夸张、揶揄和荒诞的语言进行讽刺,从而实现对于人物苦难的描述。但是与张爱玲的女性略带柔情的表象描述相比,莫言的幽默与讽刺是深刻的;与鲁迅的尖刻锋利相比,莫言的幽默与讽刺是温和有力的;与王朔的荒诞不经相比,莫言的幽默与讽刺是稳重深厚的。
在对于人物的刻画描写中,莫言经常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通过对人的外貌、心理等方面的揶揄,反映出他们生活的艰辛、心灵的负担、面临的悲剧,再通过个人折射出整个社会的病态,深刻挖掘出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安全等诸多问题。在鲁迅的笔下,人们往往能够感受到他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鲁迅很少站在普通国民的视角去探究这些劣根性的成因。而莫言则通过相对温和的语调去对人的苦难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是站在普通公众的立场上进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道德职责,多了一份理解与宽容。当然莫言的温和只是对于普通苦难的百姓,而对于那些给百姓带来苦难的社会和时代,莫言的讽刺与批判也是非常强烈的。在《白沟秋千架》中莫言通过轻松的语调对“伊”的行为进行了善意的调侃,在这里既有对她行为的揶揄,但更多地是理解与宽容。通过这大段的描写,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伊”生活的艰辛与面对苦难生活的无奈,然后才是对其行为的关注。但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的理解与宽容则完全被讽刺和批评代替,在那个年代里,右派对于任何人、任何家庭都是一个灾难的象征,按照常理,对于右派的审查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但在这里,大王仅仅凭谁走路先迈右脚就判定谁是右派,无疑是极其滑稽和不可思议的,莫言通过这些滑稽的叙述和描写,实现了对现实批判的目的,其力度丝毫不亚于犀利的语言。
莫言非常善于从一些小人物的日常行为中发现他们的悲苦,这些悲苦平常人是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但在莫言看来,这些看不见的悲苦有时比一些生活上的悲苦更加沉重。《我们的七叔》中,七叔就是农村里面一个普通的老年人,生活在新时代的他在生活上看起来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解放军当年的俘虏,在那样的年代里,这种身份带给人的压力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因为这种苦是不愿意向别人讲述的,也是无法与别人解释的,时刻堵在七叔的心中,虽然不似千斤巨石,但却像身体内部的一个肿瘤,使他无法轻松地去生活,对于七叔来说,这是一种无形的苦难,在这里,莫言通过幽默的叙述将七叔的隐痛表达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莫言对于苦难的描述过于委婉了,但恰恰相反,有时温婉的幽默更具有强大的苦难叙事作用,就像太极拳一样,看似温柔,但凝聚的杀伤力是不容小觑的。
真正好的幽默与讽刺作品绝对不是简单地为了博读者一笑,而是为了实现作者对于社会、人生、人性等方面的剖析与反思。对于莫言来说,“幽默与滑稽可以是含笑的,也可以是含泪的微笑,尤其是幽默的深层,每每与悲剧精神相通”[4]。在《生死疲劳》中,作者对于被革命燃烧的社会激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整个社会充斥着荒诞的色彩,其中有卖鸡蛋老太太的“光辉的革命形象”、有集市管理员的“理论家”形象等,在莫言的笔下,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希望积极地融入革命的大熔炉,每个人不是首先反思自己的条件怎么样,能不能为革命奉献什么,首先想到的是挤进革命的队伍。从个体行为看,这些人无疑是可悲的,在政治的潮流中失去了自我,给人以跳梁小丑的感觉。但莫言并没有将讽刺的重点放在这些小人物身上,而是引导读者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荒诞行为来反思这场运动带来的人性扭曲。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莫言的笔下,无论对于个人的苦难描述或深或浅,最终大都会归纳到社会、历史、人性的整体批判当中,从而引起人们对于苦难本质与源头的反思。例如在《筑路》中作者写道:“我是马桑小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马桑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高向阳。高个子男人愣了一会儿,才如梦初醒般弯下腰,伸出两只手,捧住男孩的小手,使劲摇着,满脸堆笑地说高主任、高队长,失迎失迎。”莫言没有对个人行为进行任何讽刺,而是重点突出了“我是马桑小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马桑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高向阳”,通过小男孩对当时整个社会环境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整体看来,莫言小说叙事中的幽默与讽刺,既看不出锋利的刀刃,也没有爆炸的震撼,莫言的幽默是温和的幽默,莫言的讽刺是含笑的讽刺,莫言善于通过人物外貌行为的描写、人物与环境的错位来展示苦难的深沉与绝望。从文艺美学的视角看,幽默与讽刺是一种审美态度,但这种审美态度建立的基础是作者的人生态度,作者对于人生的理解既对他幽默与讽刺的风格形成影响,也对他幽默与讽刺的目标形成影响。在莫言看来,世界上的荒诞与严肃、善良与邪恶、真实与虚假、理想与现实既是对立的,又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苦难、社会的苦难等都是由这些对立而又客观存在的元素在碰撞交流中形成的,普通民众无法回避,人们对于苦难可以抗争、可以忍受、可以漠视,莫言通过艺术辩证手法的灵活运用,较为轻松地用幽默来表达憎恶,用讽刺来化解苦难,在作品中通过荒诞与严肃、善良与邪恶、真实与虚假、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面,莫言利用幽默与讽刺取代了写实主义乡土叙事中怨天尤人的情感基调,通过普通民众的言谈举止,为苦难书写披上一层幽默的外衣。这也造成了苦难叙事中幽默的轻松与悲剧的沉重之间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平静的叙事中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艺术感染力一方面使读者被莫言的睿智所打动,另一方面也在叙事张力的作用下完成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审判,使我们在幽默诙谐的情绪当中,被苦难的深沉和隐痛所震撼。
四、通过日常生活伦理的解读实现苦难的顺应与救赎
在小说的苦难叙事中,主人公面临的苦难是多方面的,既有肉体的疼痛、心理的压抑,也有生活的艰辛、社会的偏见。不同的作家对于苦难的阐释是不同的,在西方命运悲剧小说中,主人公通常要面对超自然力量的迫害,由于这种力量过于强大,导致主人公无可回避、无可躲闪,从而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悲苦的命运。例如在《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面对的压迫是来自于神谕,神谕在小说中就是超力量的化身,人在神谕的面前是渺小的、无力的,面对神谕所有的反抗几乎都是徒劳的。但是即便面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有的反抗都没有任何胜算,但主人公依然显示出坚定的决心,进行大无畏的抗争,展现出主人公顽强不屈的精神品质和敢于冲破一切的英雄气概。与不可抗争的力量进行抗争,结果虽然是失败的,但是却在抗争中实现了对于苦难的完美救赎。与西方悲剧小说相反,我国很多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苦难的叙述有较大的不同,从余华、张爱玲、苏童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导致主人公苦难的不是超自然力量,而是一系列自然的、社会的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随时可能对主人公的生活、心理等方面形成强大的冲击,使主人公不断遭受命运的折磨。面对命运的折磨,余华等作家带给主人公的通常都是被动挣扎、无奈的呐喊、滴血的控诉,但却没有带给他们一条救赎之路,他们努力地活着,也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所以从西方悲剧小说和我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当中,对于苦难的关注主要停留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这种宏大叙事中的苦难书写,带给读者的要么是虚幻的救赎想象,要么是无奈的救赎放弃[4]。莫言的作品受到西方悲剧小说和我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对于苦难叙事的理解与二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于苦难的理解、顺应和承担,在对苦难的理解中发掘生命的意义,在对苦难的顺应中展示生命的态度,在对苦难的承担中实现生命的价值。
莫言的作品中,对于苦难的顺应和救赎基本都是在日常叙事中自然实现的。在莫言的笔下,既没有西方悲剧小说中的英雄,也没有新历史小说中的宏大历史场景,作者关注的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在这个社会阶层中,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自然流动,需要不自觉的去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多方势力粉墨登场,无情地对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个体进行碾压。这些势力是达官显贵吗?是日本鬼子吗?是封建文化礼制吗?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在莫言的笔下,这些压迫看似有形,但又似无形,让人能够感受得到,但又无法抓住。在莫言的叙事空间里,苦难个体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没有能力去探究给他们造成伤害、压迫的力量来源,无法找到反抗的对象与目标,其中对于母亲和姑姑的描写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从表面看,就是具体的执行者给她们带来了精神压迫与肉体折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执行者的反抗实现苦难的救赎。但是在这里执行者并不是一个有形的力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存在,在这些执行者的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制约着母亲和姑姑的行为。这种力量是什么?是革命的正义?是社会的变革?是母亲和姑姑这个阶层的人物无法弄清的,在她们看来,这就是社会现实,造成自身苦难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命运,所有的苦难都是生命之中注定的一种结果,而她们则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自觉承担起苦难的压迫。作为苦难人物的母亲和姑姑既没有反抗的动力,也找不到反抗的对象,对于苦难唯有理解、顺应与承担。所以母亲在为司马库送行前说:“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在这里母亲对于苦难的理解就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常态,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和担心的,在这里虽然没有英雄式的反抗,但依然展现出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越难越要活则很好地诠释出主人公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
对于姑姑来说,除了出来生活给她带来的苦难外,她还自觉地承担起在她自己看来充满救赎的精神苦难。在姑姑生命的后期,她时常为自己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进行反思。虽然从政治层面看,姑姑不仅没有错,而且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即便从道德层面看,她的行为虽使一些幼小的生命失去了生存的机会,作为一个政策的执行者她是没有太大的责任的,但她依然在人性伦理的空间中为自己的行为忏悔。在她看来,政策本身是死的,政策的结果是通过人的执行而产生的,而她就是其中的执行者之一,就必须为那些没有能够存活的生命负责。在莫言的笔下,姑姑不仅没有从历史伦理的视角给自己开脱,反而主动把自己置于苦难的空间中,对于自己的“罪行”进行救赎。她说:“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我们从宗教文化学的理论可以得知,人的苦难可以分为肉体苦难、生活苦难和精神苦难,而在三者当中,精神苦难对于人的压力是最大的,而姑姑在这最为沉重的苦难面前不逃避、不开脱,主动承担,也是对人生苦难的一种高层次的救赎。
在莫言的笔下,主人公对于苦难的理解、顺应和承担,是他们实现苦难救赎的道路选择。在他们的自我救赎之路中,莫言通过温情的叙事给生命带来暖暖的温度,他从不强调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关注个体性的道德境况,使主人公在自然的生活叙事中实现道德自觉。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伦理学中的各种教化描写,而是通过日常叙事让主人公找到自己,使个人行为尽量不要被社会的表象所欺骗,不能为了化解困难,以失去良知为代价[5]。莫言的苦难叙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种不同于宏大历史叙事和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如何面对生命苦难的生活伦理。
结语
莫言作品对于苦难的关注是一贯的,他把目光聚焦到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从民间立场和底层视角探究苦难存在、发生、发展的历史现实,真实呈现出普通民众对于苦难的理解、顺应与承担。在莫言的作品中,看不到锋利的态度和语言,却能感悟到作者的悲悯情怀和浓厚的社会批判意识。莫言的苦难叙事,没有一呼百应的气势,却给苦难带来了温暖与慰藉,能够让人去触摸、去感受。他接通了民间传统文化与现代写作理论之间的源头活水,让所有卑微的生命面对苦难的压迫时能够平静面对、无所畏惧,这是莫言苦难叙事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从莫言的创作历程看,苦难一直是其作品关注的焦点,但是其苦难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淡化。在前期的文学作品中,莫言以少年或者女性等弱势群体为描述对象,以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为叙事背景,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为他们创设极端的生存环境及生存处境,带来动人心魄的悲欢离合及生活磨难,并对他们的苦难通过夸张或者隐喻进行展现[6]。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莫言对于新社会图景关注不断增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莫言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关注,例如对马小奥的描写与黑孩、阿义等孩子的描写不同。在短篇小说《拇指铐》中,莫言开头就指出阿义与母亲相依为命,穷困潦倒,不仅孤儿寡母无法进行必要的财富创造,还要面对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然环境。所有的人对他们的生活境遇漠然视之,没有人关注他们的死活,在作者的隐喻中,他们母子的命运是无法预测的,他们自身更是无法实现对于命运的把握,这导致后来阿义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铐住,无法挣脱,正如作品题目“拇指铐”一样,给人带来一种无奈的悲苦[7]。与阿义相比,《天下太平》中的马小奥因为是留守儿童,会产生心灵的孤寂与生活的不适,但在莫言的笔下,他不再是孤苦伶仃,虽然存在一定的生活苦难,但是能得到社会的关爱,而他面对的苦难不再是无法解决的,而是可以化解的。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在他平和而又有节制的叙事中,人们渐渐看不到悲风凄雨、愁云荒野,一个平和、轻逸的莫言正在向我们缓缓走来。
[1]王爱侠.从沉重到轻逸——论莫言作品中苦难叙事的变化[J].齐鲁学刊,2019(5):145-152.
[2]郭群姚,新勇. 苦难和悲剧的另类书写——论莫言乡土小说的幽默风格[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77-81.
[3]颜水生.莫言的苦难叙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49-53.
[4]田苗论《红高粱》家族意象的生命意识和酒神精神[J].名作欣赏,2015(1):33-36.
[5]刘为钦,刘斯羽. 论莫言叙事的独特性、前卫性和本土性[J].江汉论坛,2014(10):111-115.
[6]付欣晴. 莫言高密世界的色彩与声音[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38-143.
[7]李茂民. 论莫言小说的苦难叙事——以《丰乳肥臀》和《蛙》为中心[J].东岳论层,2015(12):93-99.
Transcendence and Breakthrough of Suffering Narrative in Mo Yan’s Novels
XU T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 236037, Anhui)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in Mo Yan’s novels has unique features. Through the use of sound and colors it shows the helplessness and heaviness of suffering; Through multi-narrativ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suffering are explained, the absurdity and hidden pain of suffering are reflected through humor and satire, and the Adaptation and redemption of suffering are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daily life ethics. Mo Yan’s novels have realized the transcendence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nar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ovels about the suffering, which makes all humble lives face the oppression of the suffering calmly and fearlessly, and has unique literary value an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Mo Yan’s novels; suffering; narrative; breakthrough; transcendence
2020-11-26
202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项目(2020CX127);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20A0345)。
徐涛(1971- ),女,安徽合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写作学。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1.13
I247
A
2096-9333(2021)01-008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