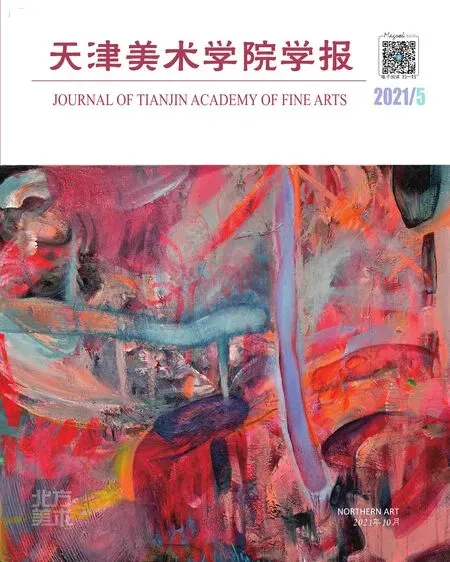感觉、形象与无器官的身体
——试论德勒兹的培根阐释
韩子元/Han Ziyuan
一、引言:在艺术与哲学之间
2019年6月29日,苏富比纽约晚拍创造了奇迹,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作品《启发自艾斯奇勒斯〈奥瑞斯提亚〉之三联作》以直播的形式成交,价格超过8400万美元,这位曾经被撒切尔夫人称为“画恐怖画的男人”又一次得到了世界的瞩目,在诸多论述其画作的批评作品中,《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无疑是最具有哲学思辨意味的,因为这本批评著作的作者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是一个野心勃勃而与众不同的哲学家,他与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法国后现代哲学家齐名,在结构主义、现象学风靡法兰西的年代独辟蹊径,沉浸于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人的哲学世界并最终建构起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同时撰写了大量文艺批评作品。德勒兹自始至终都期望外界对自身的评价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家,那么他为何又屡屡涉足文学和艺术领域?又是如何对培根的画作产生兴趣的?他又要通过这种文艺批评讲出什么样的哲学来?
在《感觉的逻辑》一书的前言中,德勒兹强调了这本书章节编排的无规律性,这本书的每一章节都谈论了培根画作的某一个方面,这些方面同时存在着。[1]3但就其哲学思想而言,一定有几个章节和概念的引出是相对来讲更为关键的,本文试图通过抓住“感觉”“形象”“无器官身体”这几个关键概念,从柏格森等对德勒兹影响甚大的哲学家出发,读懂德勒兹的培根阐释,并试图进一步揭示这种德勒兹式文艺批评背后更深层次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伦理学指向。本文试图勾勒出这样一条线索:向前追溯柏格森哲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其他对德勒兹影响深远的流派,从而层层推进,理清感觉、形象、身体之间的关系,再具体关注德勒兹是如何借助这些核心概念评论培根的画作,最终向后关注“无器官身体”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反俄狄浦斯》及《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中的伦理学转向及其在《感觉的逻辑》中早已显示的必然性。
二、为什么是培根?——画家与画作
弄清楚为什么对德勒兹来讲,诸多20世纪的艺术家中,必须是培根和他的画作?这个问题的关键性就像对福柯来讲,为什么是《宫娥》和委拉斯凯兹(Velazquez)?哲学家在评论文艺作品时,必然是借用这一作品来为其哲学工作服务的,或者是将自己的哲学理论具体下放来一次“个案研究”。福柯在《词与物》中开篇即提到《宫娥》,为其知识型的区分过渡服务,《宫娥》代表着前古典时期对客观自然的描摹仿照到了古典时期“语词”(画中的视线)进入了人们观看事物的逻辑之中,最终推出现代时期人终将死去的惊人论断。[2]
培根是一个生于爱尔兰的英格兰人。与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一样,他们都生于爱尔兰,带着“同样的来自爱尔兰的怪诞”(德勒兹语),但他们却没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狭隘,他们的思维是欧洲的,是世界的,关怀的是普遍的问题。培根自小体弱多病,与梵·高一样有着强烈的痛苦意识,严重持续的哮喘使他无法继续正常的学业,他只能开始自学着作画。另外,在个人生活方面,其与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儿子关系甚密,还拥有一名叫作乔治·戴尔(George Dyer)的同性情人,所以同性恋的主题也似乎隐藏在他的画作中。如果真正地对吉尔·德勒兹的著述和思想有所了解就会发现,其喜爱分析的艺术家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黑暗、怪诞、不羁、深邃及形而上。
在画的主题和内容方面,德勒兹认为培根的画作主要充斥着三大元素,分别是材质结构(作为背景的大面积的平涂)、圆形(场地)与形象,三者互相交织,诉说着不同的意涵。[1]19具体而言,培根用大面积的单调平涂作为背景而非建构复杂的环境背景,这么做的目的在德勒兹看来是为了拒绝一种形象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交代,如果采用复杂的手法画出环境,那么解读时一定会带有对该环境的先验认知,观者会开始从此出发来理解形象所处的自然、历史背景。昆德拉(Milan Kundera)也认为,培根的背景极为简单,基本是以平涂的形式完成的。[3]131970年创作的《三联画:人体习作》中,我们甚至看不出形象是否处在一个房间内,背景中只有大量简单的色彩平涂,毫无结构与环境的交代。甚至,培根会用一些夸张的划痕来代替一些视觉上的透视,一道划痕直接分裂两个平面,极尽简单之艺术。圆形作为绝对封闭的场所也时常在培根的画作中出现,或是椭圆,或是圆形,形象和人物总是在一个圆形场域中被封锁住,场地和人物的关系是复杂的,但主要的作用就是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再者,为形象和背景的邻近性提供一个支座或轮廓。第三个元素——形象当然更加重要,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德勒兹认为,平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背景,它没有描绘透视意义上的远近大小,没有刻画阴影,这是一种极度的清晰,但同时又滑向一种模糊,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背景存在,它与形象之间的关系是共在的,极其邻近的而非相互区分的。“这是同一层面上相邻近的两个元素的关联关系。”而圆形作为结构、作为场地,又使两者的相遇成为可能,圆形“是这两者的共同界线、是它们的轮廓”[1]10。1970年《三联画,人体习作》的中间幅是以上论述良好的例证,圆形的场地将形象与和其保持共在邻近关系的大面积单调平涂统合了起来。另外,与简单的平涂代替背景相反,培根十分强调对色彩的表现,他在《培根访谈录》中多次表达自己的画是要达到一种“明亮”的色彩。1965年《三联画,十字架刑》与1968年《三联画,两个躺着的人体与见证人》中鲜艳的橙红色都诉说着“明亮”的主题,这种张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绘画的主题方面,除了一些纯粹的人像习作,培根还善于模仿和进行为我所用式的挪用,比如挪用了委拉斯凯兹画的教皇,将教皇变成了一个叫喊的异形,培根对艺术史与经典名作并非不够了解,只不过他的挪用方式非常具有自身的特色,才使他的作品十分怪诞与反叛传统。
总之,德勒兹认为培根的任务和功劳就在于采用各种新奇的手法来攻击“具象”(正如普鲁斯[Marcel Proust]特采用了各种文学上的创举来反抗客观主义)的绘画传统和观看绘画的视觉传统,培根走的这条道路不是极端的具象,也并非直接走向抽象主义,而是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对“形象”和纯粹事实的刻画,用一种触觉式的视觉摆脱了具象。[1]xii
三、感觉的逻辑
如果非要对德勒兹如此散乱的文本做一个归纳,那么我们可以说培根画作的一个核心特点在于:作为一种非形象化形象的无器官身体使感觉穿越了各种层而直接到达了神经系统,以一种绝对的内在性封闭实现了自身的敞开,使身体“在场”。感觉(sensation)成了问题的核心,从书名The Logic of Sensation可以看出,这是德勒兹培根批评的核心概念,德勒兹批判了两种理解感觉统一性的方式(幻觉主义的极端具象与完全的抽象派),认为这两种尝试都无法彻底破解形象化带来的后果,并指出了另一条比较有可能成功的道路,即通过绘画营造出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的“感觉”,这是德勒兹时常拿塞尚和培根作比的原因,也是培根走的“第三条道路”。感觉的逻辑不是我们平素理解的逻辑,而是一种打破逻辑的逻辑,德勒兹又引出了形象、无器官身体、在场、图表等概念来阐述感觉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首先,在画作表达的形象中,感觉是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的,不需要大脑进行阐释、解码的,这可以和德勒兹对形象化的嗤之以鼻相联系,感觉究竟是画中形象的感觉,还是观画者的感觉,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感觉一定是有一种代替“思考”和“理智”的意涵在内的,这种反对客观主义的决心从《普鲁斯特与符号》延续至今。[4]德勒兹借“歇斯底里症”患者对自己身体的感觉道出了和《普鲁斯特论符号》一样的道理:对世界的认知应该有一种“滞后性”,就像对符号的感知和解读也不是先在的理念一样,求真的意志可能只是西方哲学的徒劳和虚妄,重视“感觉”才能重构认识论,接近世界真正的本质。
在感觉和感官的逻辑中,德勒兹强调一种流变的状态,即一种节奏,节奏在听觉领域就是音乐,上升到视觉层面就是绘画,德勒兹在此对绘画带来的纯粹审美体验推崇备至。这种流变和节奏是带有时间性和运动性的,它来回穿越不同层面,这就是感觉的力量。
感觉是超越具象的一个途径,这是塞尚开辟的一条道路:用形象传达感觉,感觉就是纯粹事实直接对神经系统的刺激,这很像现象学对存在的把握,“此在”就是一个通过感觉统合主客的现象学核心概念,我在感觉中存在,事物也通过感觉来把握。观画者的身体与画中被观看的形象之身体合一,这样才能达到感觉的层次。[1]47但是,现象学只能解决主客之间的问题,却无法实现感觉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穿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帮手。
四、无器官的身体:一种非形象化的形象
感觉与某种范畴不是一一对应的,就像意义不确定一样,它是来回穿梭的,现象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无器官身体可以做到,由此提出了无器官身体。“于是我们看到,如何一切感觉都意味着一种层面(范畴、领域)的差异,而且是从一个层面过渡到另一个层面。”“形象就是无器官的身体。”[1]60德勒兹明确地将两者画上等号(所以本章将二者合并讨论)。于是,感觉、形象、无器官的身体三个核心概念关联了起来,要想营造出一种直接刺激观众神经系统的感觉,就必须绘画出一种纯粹的“形象”,接下来,本文将在德勒兹对柏格森主义的继承与超越中阐释这一脉络。形象最早来自柏格森的一种一元论尝试,是柏格森最先将形象与身体关联起来来超越二元论,形象超越表象和物自体隔阂的努力必须借助身体,而身体又不再是物质,而是一种不断超越的心理流和生命力。
形象(figure)是区别于形象化的,形象化代表着一种故事、一种阐释,而培根画的则是纯粹的事实与形象自身,形象的恐惧不需要外物加以刺激,他自身展现的恐惧可以说明全部问题,所以他们是封闭的,不需要观众的,不需要叙事的。但形象一词除了与形象化的对立之外,还蕴藏着更深的哲学渊源与伦理学动向。
(一)形象与一元论:忘却分歧
在笔者关于形象一词来源的考察中,柏格森最为瞩目。早在《物质与记忆》(或译作材料与记忆)的开篇,柏格森就用形象一词来反驳二元论,[5]1柏格森提出“形象”一词是顺延着其物质理论的,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在对战康德的过程中,将柏格森视作了自己的盟友。“我们所说的形象是一种存在物,它大于唯心论者所称的表现,又小于实在论者所称的物体。”在柏格森看来,形象是统合主观与客观唯心主义的之间区别的一个关键概念,它确实可以被我们感知,但某种程度上又可以作为一种“独自的持存”。在阐释培根画作的过程中,德勒兹所用的这个形象的概念明显来自于柏格森,感觉其实也不例外:感觉可以说就是柏格森讲的“纯粹知觉”,它通过对象自身展开,是纯粹的当下,没有记忆(没有故事和叙述),[5]31而形象则对应着柏格森的形象,邓刚认为,纯粹知觉和形象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主与客的关系,纯粹知觉与意识也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由此解构了康德相对主义认识论。在纯粹知觉中,形象的某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我的身体”,在德勒兹这里变成了“形象直接进入了感觉”。[6]
用柏格森来诠释培根画作中的形象,可以使我们忘却一种二元,抛下一种分歧,即画中形象本身的存在和我们对其外观呈现的感知的二元分歧。
“身体是形象的,而非结构”[1]28,德勒兹认为,脸部是结构,是叙事,代表着一种解读,而脑袋则是形象的代表,所以,培根乐意画脑袋,却很少表示脸部。这一段论述通常可以看作德勒兹认为培根在表达对结构的不满,但更重要的是,培根笔下的脑袋经常变成了动物,人与动物经常混在一团肉中难以区分,培根的作品可以说是对“肉”的礼赞,而在德勒兹看来,对肉的赞美是因为单看一团肉是无法区分人与大部分哺乳动物的,在这个层面上,培根与卡夫卡(Franz Kafka)有相似之处,德勒兹对卡夫卡推崇备至,并在对他的评论中提出了“生成-动物”的概念,以期建构一种少数文学,用一元论的自然观统合人与动物,解构多数(占统治地位)物种的中心地位,在培根这里,德勒兹似乎嗅到了同样的一元论气味。在对肉的礼赞中,培根忘却了人与动物的分歧。
(二)形象:从封闭到敞开
培根画中的一切椭圆形、圆形都被德勒兹视为一种封闭,自我的封闭,但这种封闭却在“无器官的身体”之处走向了无限的敞开。这并不是前后矛盾,当德勒兹谈到封闭时,他在强调形象本身的力量,之所以将形象视为自我封闭,是为了确保其不受其本身之外的叙事、意义打扰和解释,故事性和叙事性将被在培根的绘画中革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纯粹的内在的形象自身,没有外物,没有和环境的联系和解释关系,环境也被纯粹的背景取代。
而封闭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敞开。这种敞开不同于外物、环境强加于形象本身的叙事关系和意义阐释体系,而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由自身诉说的、纯粹内在性的敞开,由形象自身开始生成,与外物无限联系、结合、成长、共生……
这里还能看到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反对“理智”,反对机械论,①反对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以来将存在“生成”的对立面。机械论总是用理智将人的生命和存在也还原为一种“事实”、静态的符号,一种必然的因果。[7]这就是封闭的必要性,只有形象将自身完全封闭,才可以躲开因果论的袭击,才可以躲开机械论的决定、还原。柏格森解构笛卡尔式身心观的关键就是将身体当作一个与外物紧密联系甚至没有区分的存在,外物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对象,我们与外物不可分割,这是生命的“绵延”——一种纯粹的时间,而不是被空间化的时间,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物质”而更接近一种心理维度的本体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必须做到封闭,拒绝阐释,拒绝物质化的被陈述,但这种封闭又是为了从内在、心理、神经系统中敞开,与世界共思。德勒兹这种封闭-敞开的悖论就是在表露着这样的声音:培根笔下的形象为了对抗理智、因果、机械论而自我封闭,但这种封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敞开,呐喊、表达(培根经常突出表达人物的嘴巴)直至与宇宙融合,这也是他超越柏格森的地方,他看到了“生成”的力量,这难道不是一种伦理学吗?
(三)形象:何以成为一种伦理学
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两卷本中,受1968年法国的革命氛围影响,“无器官的身体”的意涵发生了一次“伦理学转向”。福柯在《反俄狄浦斯》的序言中认为这本著作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虽然德勒兹本人可能不愿意被阐释为一位伦理学家)。[8]在《千高原》中,涉及无器官身体的章节题目以“how”打头,这就更加明显地赋予这一概念伦理学的意义,尤金·霍兰德(Eugene W. Holland)也认为《千高原》中涉及无器官身体的讨论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论述。[9]德勒兹在《千高原》中告诉人们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无器官的身体,在日常生活实践和政治、革命的意义上作了新的延伸。虽然在《感觉的逻辑》中,这一概念还停留在对“感觉”“形象”的阐释层面上,但这种“转向”即将发生的趋势我们必须把握,否则无法厘清德勒兹整个学术思想的一种历时顺承性。
其关键就是德勒兹在培根笔下的形象中看到了这种能量与一种伦理学。形象是具有力量的,其力量来自自身,其就是事实本身,不需要意义,不需要故事,不需要阐释,不需要观众。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伦理学,甚至为无器官身体这一概念日后转向伦理学打下了基础,
而在培根的画作中,德勒兹明显还没有将它放在伦理学的层面来探讨,但似乎走向伦理学已经是无器官身体这一概念的宿命,他蕴藏着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可以生成,可以呐喊,可以抵抗结构化的自我和被理解为匮乏的欲望。“精神是身体本身,是无器官的身体。”[1]62从这个概念初次被德勒兹引用就可以预见到其后期的伦理学转变,德勒兹在不同文本中对其赋予的意义是一脉相承的,前后联系的,从未断裂。
(四)身体:摆脱桎梏
探究形象的秘密还是为了引出“身体”,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无器官的身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因为如果德勒兹强调的仅仅是结构的不复存在,那么他完全可以使用“无身体的器官”这个词。[10]corps sans organes②还是一种cops,德勒兹对身体的强调是始终如一的,无论是柏格森还是尼采,无论是精神病学还是哲学,德勒兹论述的目标就是重构身体,尤其是伦理学转向发生以后。身体可以说是一众后现代学者眼中唯一的真实,培根画作中的形象就是这样的身体,它是纯粹的事实,是一团肉,反对一切福柯口中的“人类学”,人已死的情况下,只有身体尚为真实,那么意义已死的情况下,只有感觉(作用于非大脑的神经系统)尚可捕捉。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甚至可以从德勒兹的培根阐释中解出一条鲜明的后现代哲学谱系,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德勒兹解构意义的野心。
另外,这种身体的狂躁状态其实也隐喻着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状态,德勒兹在“歇斯底里症”为标题的小节中引出了无器官身体的概念,这里其实已经为德勒兹最为世人所知的两卷本著作《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写作埋下伏笔,他之所以找上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就是因为他痛恨精神分析的论断可又不够熟悉精神分析,在《感觉的逻辑》中就可以发现他已经开始着手用歇斯底里的状态来反击精神分析了。德勒兹对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史颇为关注,歇斯底里症患者的那种“醒游”状态和“内视”(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或自己看到自己的身体处于某个器官中),这种特殊的对身体的感受正对抗着有机体(有组织的身体)的身体观。这样的论述对德勒兹研究者来讲一定十分熟悉,它正像《反俄狄浦斯》中用精神分裂症对抗精神分析的家庭结构观,也像《普鲁斯特与符号》中对世界后知后觉(可以理解为一种自闭症)的主人公对符号世界的体验。总之,这种对精神病学意义上病态身体的推崇是为了一种反抗的目的,解构的需要,自闭症用拒绝友谊生成纯粹的内在性差异,从而破坏约定俗成的符号释义;精神分裂症用身份的不确定性反抗家庭结构的微观法西斯;而培根创造出的歇斯底里症则蕴藏着对有机身体和有组织的器官的分解力量,也用一种“滞后”(董强在《导读:德勒兹的第三条道路》中指出了歇斯底里症在拉丁词源上与“滞后”的含义相关)性。[1]xii
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如上所述的那样,形象不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摆脱了形象化的事实,它还作为“无器官的身体”跨越感觉的诸层面,构成了纯粹内在性差异的本体,这种层面上“事件”代替了固定的意义本身,无器官身体不断地在作为事件的感觉中穿梭,在某个瞬间固定下来,但转眼又开始流变,所以德勒兹才会强调培根“画出了时间”。
五、结语:新形而上学家培根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发现德勒兹对艺术作品的鉴赏的态度和路径绝对是“为我所用”“从我出发”的,这是德勒兹文艺批评与哲学史工作的最大特点。为什么如此强调感觉?因为德勒兹一直在对意义进行颠覆,从《普鲁斯特与符号》时期就已经开始尝试,他不喜欢客观主义,不认为有一个真理在那等待发觉,也不认为柏拉图(Plato)以降的西方哲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本质”。[4]他在倒转柏拉图,他在强调一种主体与客观的融合,但他强调这又是现象学也无法达到的,所以不如索性直接说是忘却其间的区别。
在弗朗西斯·培根摆脱具象的第三条道路上,首先,感觉,就是代替主动思考、理智与理性的词汇,这种近乎于触觉的视觉反对了传统的视觉解读机制,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的感觉代替了大脑对某个带有确定意义的符号的阐释,这是德勒兹眼中培根的重要之处,也是培根的画作为他的哲学服务的地方。感觉的“逻辑”并不是西方哲学界或者科学界理解的逻辑,感觉的逻辑正是反逻辑,正是反形而上学的新形而上学。其次,培根笔下的形象,像极了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他们被动地接受符号的洗礼,不奢望可以理解什么,主动地达到什么,这将反客观与反先在的“善良意志”贯彻到底。更进一步讲,形象还意味着一种纯粹的事实,这与“形象化”、叙事、故事性相区别。最后,这对形象的刻画又引出了一种崭新的身体观,“无器官的身体”被用来讲述这样一种纯粹的形象、歇斯底里的身体、来回穿梭的感觉。其实德勒兹的全部学术生涯都在做这样的尝试,在与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康德(Immanuel Kant)、柏拉图、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等论敌的对抗中,弗朗西斯·培根与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人一样,只是德勒兹为我所用、信手拈来的“武器”与旗帜,德勒兹的确是一个文艺批评的天才,但是如果不了解其哲学上的工作和野心,以及文艺批评在其哲学蓝图中所处的地位与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对其批评要旨的理解就会落入庸俗化。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培根似乎并不喜欢表达一些当下的主题,战争与反战、杀戮与和平、宗教与信仰、伦理与真善美的想象……这些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似乎都在他的画作里匿去了踪影。“这不是悲观,也不是绝望,这是显而易见的简单事实,只不过这事实通常会被集体属性这片纱给蒙蔽,因为集体的梦想、兴奋、计划、幻象、斗争、利益、宗教、意识形态、激情,让我们什么也看不到。”[3]18昆德拉如是说。昆德拉认为培根是一个借助“身体”绘画纯粹“事实”的人,这与德勒兹对他的评价如出一辙,也与德勒兹的哲学野心如出一辙。这其实回应了本文“为什么是培根”的部分,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培根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他与贝克特一样,不关注一些浅表的当下,因为真正关乎本质的艺术不应该去过多地表达生活中的种种,他们也不相信艺术与现实生活如此紧密的反映和影响关系。他们追求一种本质,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事实,只不过这种形而上的追寻并不是通过现代西方自诩的科学、结构、论证的方式完成而是通过一种“古埃及”式的混沌、原初方式来完成的,这大概就是“对德勒兹来说,为什么是培根?”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
注释:
①但德勒兹与机械唯物论的关系相当复杂,德勒兹唯物思想的形成也少不了伽森狄、斯宾诺莎的影响。
②法文:无器官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