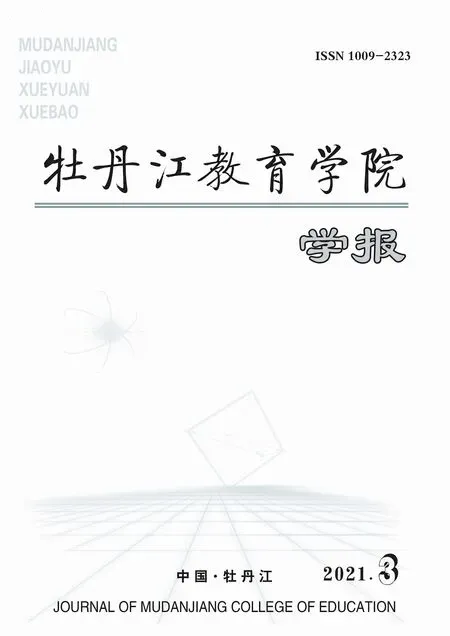《粤西诗载》中的贬谪文人创作
张 啸
(广西民族大学,南宁 530006 )
一、《粤西诗载》与寓桂贬谪文人
《粤西诗载》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汪森于康熙年间编成的历代有关广西的诗歌总集。全书共分为二十四卷,收录了由汉代至明末各体诗歌二千九百六十五首,附词一卷四十五首,可谓洋洋大观,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广西地方史文献典籍。《粤西诗载》一书从较早的地方志书、历代史籍、诸家文集、类书、小说等典籍中选取资料,所选取的书,不下二千多种;又从碑石中广为搜罗,补充了典籍所未录者。正如清代大儒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说:《粤西诗载》“搜采殊见广备”,“以视曹学佳《全蜀艺文志》赡富不及,而谨严殆为胜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粤西诗载》既是一部作品丰富的诗歌总集,更是一部记录了详细历史史实的文献资料,与《粤西文载》和《粤西丛载》合称为“粤西三载”。
汪森自己陈述编纂“粤西三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公诸同好”,“俾粤西之山川风土,不必身历而恍然有会;其仕于兹邦者,因其书可以求山川风土之异同,古今政治之得失;且以为他日修志乘者所采择焉。”[1]8在成书的70多年之后,“粤西三载”受到了清乾隆一朝的极高评价,并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纪晓岚认为其“所录碑版题咏之作,多志乘所未备”[2]1,称赞“粤西三载”搜罗的文献资源相当广泛完备。沧海桑田,如今汪森在编纂“粤西三载”时所引用的典籍大多已经亡佚,然广西的历史文献有幸依托“粤西三载”而得以保存下来。“粤西三载”流传至今,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典籍,而是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森罗万象、浩如烟海的诗歌所表现出的既有广西的山水奇丽秀美,也有地方民俗的多姿多彩,既有对广西当地人民勤劳务农的由衷赞美,也有对苛政时弊的无情揭露。诚如“粤西三载”的点校者所言:“时至今日,就研究广西地方各项历史问题而言,在保存原始资料上,在资料的完备充实上,还没有超过它的著作。”[3]1
近十年来,关于《粤西诗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方面:其一,整体性研究方面。首先是将《粤西诗载》放置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考量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如马树良的硕士论文《历代广西风土诗研究》[4]将广西风土诗进行整体性宏观研究,既考察横向的共性和差异,又研究纵向的发展和新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广西风土诗在发展和演变中的脉络;钟乃元的博士论文《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5]以《粤西诗载》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互相关联的视角来对广西古代诗歌进行宏观、整体的研究。其次是基于个人视角的系统观照,如刘海波的《从〈粤西诗载〉看唐人对广西情感印象的演进》[6]以《粤西诗载》中的唐代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中勾勒出唐人对广西情感印象的演进轨迹,表明从初唐到晚唐,唐人对广西的好感是与时俱进的。其二,局部研究方面。首先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如张维的《略论柳宗元之于柳州的文化意义——“粤西三载”中明代人咏柳诗文的解读》[7]通过对《粤西诗载》中明代文人吟咏柳宗元和柳州的诗文作品的解读,探讨柳宗元与柳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次是地域研究,主要论及广西独特的地域资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如唐基苏、秦幸福的《〈粤西诗载〉中关于“兴安道中”的诗人及其诗作》[8]选取《粤西诗载》收录的以“兴安道中”为题的诗作,由此观照这些诗作反映出的兴安一带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物,印证出兴安一地曾是“一带一路”上连接中原的纽带。
中国的贬官制度可追溯到上古的尧舜时期,到了唐宋年间,贬谪已发展成为针对犯罪行为尚未达到五刑量刑标准的有罪官员的重要处罚方式,并形成了越来越完备的制度。《通典·南蛮下》有言:“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之前是为荒服”[9],唐宋时期,岭南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一部分地区。岭南距离中原地区路途异常遥远、交通不便,自然气候和环境与中原地区迥异,气候恶劣、瘴疠肆虐,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在历史上一度被视为蛮荒之地,因此成为古代贬谪和流放文人和官员的主要地区。杜佑在《通典》中明确指出岭南是“荒服”之地,即政府安置贬臣之地。
贬谪文学是伴随着文人或官员遭遇贬谪而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屈原的《离骚》和《九章》,及至唐代则达到兴盛。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0]198,文人在贬谪过程中时常百感交集、心绪复杂,宦海的沉浮也造就了创作主体文思的涌动,从而产生出大量情真意切的优秀诗歌。
贬谪作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获罪被贬至广西为官的作家,一类是贬谪途中路过广西的作家。如唐代的张说、沈佺期、宋之问、王维、刘言史、窦群、柳宗元、李德裕等人,北宋的丁谓、王巩、赵抃、苏轼、秦观、邹浩、黄庭坚、曾宏正等人,南宋的王安中、孙觌、胡寅、李纲、胡铨、汪应辰、胡舜陟、吴元美、徐梦莘、张孝祥等人,明代的严震直、解缙、顾璘、董传策、苏浚等人。
二、内心情感的真实抒发
贬,损也;谪,罚也。被贬之人有些为“大凡政有乖张,怀奸挟情,贪渎乱法,心怀不轨而又不够五刑之量刑标准者”,也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挟裹受牵连的无辜之人。贬谪之人的心态总体来说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贬谪初期或途中时的挫败感和屈辱之感;到达贬谪之地后对异乡异俗的不适甚至恐惧之情;以及贬谪后期越来越浓烈的思归怀乡之情。
贬谪初期或途中时的挫败感和屈辱之感,来自于贬谪前后身份的巨大差别或者蒙受冤屈的屈辱经历。
首先是身份的转变,在遭遇不幸前,这些诗人大多位列庙堂,身居朝廷要职,有的甚至位至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荣宠加身,风光无限,一朝失势,云泥之别,谪前与谪后,“昔如鹄矫云,今如兔罹罝”[1]60,境遇之异判若云泥。人人皆可随意轻贱,昔日身边攀附之人或树倒猢狲散或落井下石,连朋友都相继远离。昔日受人尊崇依附、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朝廷重臣一夜之间变成狼狈不堪的罪臣,此情此景触目惊心,其中辛酸屈辱令人不禁掩面而泣。贬谪或流放途中更是艰苦难捱,日行百里的疲累和煎熬,小吏动辄的打骂,使人身体和心灵受到双重的折磨,如邹浩在其《闻彦和过桂州二首》其二中所描写的流人境况:“削迹投炎荒,有吏督其後。一州一易之,稍缓辄訾诟。所历多官僚,岂无亲且旧。前车覆未遥,不敢略回脰”[1]60。诗人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柳宗元两次被贬,有“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茅是海边”[11]4的孤独,也有“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11]8的深深隔膜感。
其次是蒙受冤屈的苦难经历。这一类多为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挟裹受牵连的文人,以初唐被贬诗人群为代表。唐神龙年间,张柬之发动政变诛杀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二人,逼迫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清理二张集团的文人,一大批文人因此遭受贬谪,沈佺期、宋之问等被贬谪至广西,他们都认为自己属于无辜遭贬,在接到贬谪诏令奔赴贬地的过程中内心感到十分屈辱与愤懑。沈佺期曾经是“黄阁游鸾署,青缣御史香。扈巡行太液,陪宴坐明光”[12]97的皇帝宠臣,“三春给事省,五载尚书郎”。而今一夜之间“忆昨京华子,伤今边地囚”[12]117,流放到岭南道的最南端驩州,“京华子”与“边地囚”的身份悬殊差异,让他倍感委屈和屈辱。“死生离骨肉,荣辱间朋游”[12]117,与骨肉至亲的生离死别,往日身边攀附之人一哄而散,连朋友都避之不及。贬谪途中“夜则忍饥卧,朝则抱病走”[12]97,委屈之情难以言表。宋之问被贬钦州,获罪被贬后也认为自己含冤受屈。宋之问在诗歌中以虞翻之典自比贤臣,“虞翻思报国,许靖愿归朝”[12]551,虞翻之典指的是虞翻被毁谤,遭孙权放逐交州之事。宋之问以忠而被谤的虞翻自比,抒发其内心冤屈的愤懑之情。贬谪途中境遇也十分凄凄,在《发藤州》中自述“朝夕苦遄征,孤魂常自惊”[13]150,内心十分凄苦。
唐代“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的张说,并未曾依附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仅仅因为秉持正言不愿颠倒黑白诬陷魏元忠谋反,得罪二张和武后而被流放钦州。《旧唐书》记载:“时临台监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令证其事。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元忠由是免诛,说坐忤旨配流钦州”[14]3050-3051。坚守正义、敢于直言反而落得贬谪的结局,张说心中的委屈和失望可以想见,流放途中一首《石门别杨六钦望》道尽心中之失落与委屈:“燕人同窜越,万里自相哀。影响无期会,江山此地来。暮年伤泛梗,累日慰寒灰。潮水东南落,浮云西北回。俱看石门远,倚棹两悲哉。”[15]77
绍兴初孙觌编管象州,一路上失魂落魄,看到行行大雁北归,联想到自己却要去往陌生而又瘴疠横行的广西,心中顿生无限感伤之情,作《回雁峰》以抒发:“吾生将安归,墮此瘴江浦。逐臣正南遊,倦鸟已北翥”[5],感叹此行去国离乡,深感被贬的失落和对将至的新环境的恐惧;至桂州时作《七星岩》,“十载污修门,簪槖侍帝垣。五云深莫窥,众星拱以繁。一坐犊背书,身落海上村”[1]92,作《来风亭》“投老落蛮峤,暍死愁吴侬”[5]。诗作中透露出的深切的孤独与落寞,飘零与伤感,令人不忍听闻。
三、对他乡异地的陌生化描写
经历了贬谪初期的挫败与屈辱,等到抵达贬谪地后,诗人们的情感逐渐发生着转变,开始流露出对异乡异俗的不适甚至恐惧之情,变为声泪俱下的泣诉。沈佺期在过岭南地界时作《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
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16]99首联所提到的“岭头”是指岭南岭北的分界线,“茲山界夷夏”,过了此岭即是“去国离家”唯有白云相伴,意味着远离了熟悉而又繁华的“洛浦风光”,千山万水奔赴十万大山瘴疠可怖之地驩州。连大雁飞至衡阳也便不再往南,而自己却要继续往南前进。此去经年,或许再也不能在回来,相隔万里,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得到赦免重归朝堂。此中绝望与痛苦与对异乡的恐惧令人不忍闻之。
过此岭后继续往西南前行,便进入了传说中的鬼门关,沈佺期又写下了一首《入鬼门关》:“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露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1]31鬼门关地处偏远,环境恶劣,作者惊异的发现当地的人们皆短寿或早夭,可想而知异乡人来到这里更加难以适应,很少有能活着回去的。作者自从离开京城以后,终日愁思和惊惧导致头发斑白、容颜衰老,正可谓是“艰难苦恨繁霜鬓”。天刚亮就要开始艰难地在毒草间前行,到了晚上也只能投宿在满是毒蛇虫蚁的地方。一路上骑马要经过千仞之深的危险山谷,坐船则要经过千回百转的险湾。历尽重重艰险却来到一个蛮荒之地,这一路上的艰难苦恨难以想象,沈佺期已经足够幸运,想来又有多少人未到贬谪之地就已饮恨殒命途中。
诗人对于贬谪之地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俱增,身边的一切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如此的陌生,没有亲人和朋友,异乡,异俗,异语,恶劣的环境,使诗人们的身心都受到了双重的折磨,他们渴求摆脱现有的贬谪生活,对美好生活进行追忆,感叹岁月的流逝,感叹自己的容颜因忧愁而衰老,渴望回归帝都和家乡,思乡之情和渴求被赦的心情开始成为诗歌的主要表现内容。
宋之问被贬至广西桂林以后,看到当地民族节日三月三的载歌载舞,心中百感交集,一首《桂州三月三日》道不尽这百转的愁肠:“代业京华里, 远投魑魅乡。登高望不极,云海四茫茫。伊昔承休盼,曾为人所羡。两朝赐颜色,二纪陪欢宴。昆明御宿侍龙媒,伊阙天泉复几回。西夏黄河水心剑,东周清洛羽觞杯。
苑中落花扫还合,河畔垂杨拨不开。千春献寿多行乐,柏梁和歌攀睿作。赐金分帛奉恩辉,风举云摇入紫微。晨趋北阙鸣珂至,夜出南宫把烛归。载笔儒林多岁月,襆被文昌佐吴越。越中山海高且深,兴来无处不登临。永和九年刺海郡,暮春三月醉山阴。愚谓嬉游长似昔,不言流寓欻成今。始安繁华旧风俗,帐饮倾城沸江曲。主人丝管清且悲,客子肝肠断还续。荔浦蘅皋万里馀,洛阳音信绝能疏。
故园今日应愁思,曲水何能更祓除。作伴谁怜合浦叶,思归岂食桂江鱼。不求汉使金囊赠,愿得佳人锦字书。”[16]99遥想到自己以前曾经在京城为官,身边聚集了多少攀附之人,享受皇恩,平步青云。何等的风光无限。而如今却被赶出京城,投身在这魑魅魍魉之乡。回想起以前的种种,就好像是一场梦,然而顷刻之间再回首已是沦为罪臣,被贬谪在这遥远的边地。清幽的管弦之声听起来也是如此的悲切,令人肝肠寸断。这管弦之音勾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而家乡的音讯却是如此的稀疏。自己不求来使能够给我带来金银财宝,只求能得到家人的一封家书就心满意足。这浓浓的思乡念归之情令人闻之动容。
沈佺期被贬驩州的诗作中,经常以“洛中”、“帝乡”、“京华”等代指帝都的意象,寄托抒发自己的思乡思归之情,情到深处甚至经常泪流满面。“搔首向南荒,拭泪看北斗”[12]97,“帝乡遥可念,肠断报亲情”[12]98,这些忧愁哀怨的字句无不透露着诗人对“何年赦书来,重饮洛阳酒”[12]97的渴望。沈佺期思归之心切切,还曾梦到自己被赦,回到家乡洛阳与妻儿团圆吃饭的美好情境,梦境的美好更加反衬出现实的不堪,以至于刚从美梦中醒来时神情恍惚,分辨不出现实与梦境究竟哪个才是真实,待到终于痛苦的认清冰冷的现实,只能“肝肠余几寸,拭泪坐春风”[12]97。宋之问经历两次贬谪,最终被赐死桂州,相比起很多贬谪诗人或长留当地、或卒于途中的遭遇,沈佺期无疑是足够幸运的,他最终得以遇赦北归,终于和家人团聚了。
四、结语
贬谪文学以其特定的情感表达和创作题材成为古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此类作品往往感情真挚,带有明显的纪实性色彩。由于广西在历史上的独特位置,《粤西诗载》中有大量的诗歌作品属于贬谪文学范畴。这些诗歌的创作主体大都经历了由北向南的地域变迁以及内心深处的痛苦蜕变。与此同时,贬谪文人以他者的视角对广西的环境进行了新的描摹与阐述,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可贵的地域文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