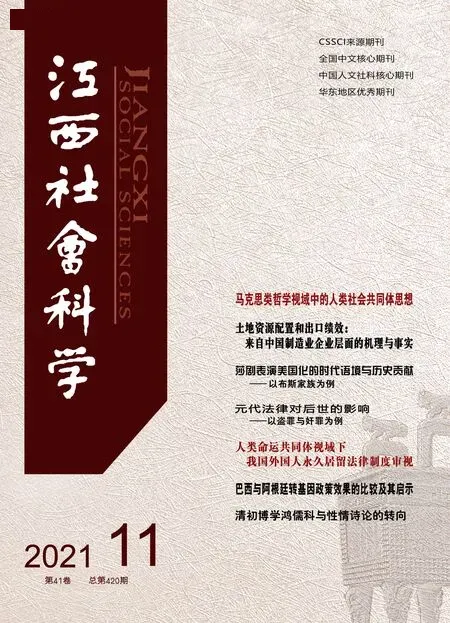元代法律对后世的影响
——以盗罪与奸罪为例
■刘 晓
元代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不少影响后世的新罪名。像传统盗罪衍生出的掏摸与白昼抢夺,传统奸罪衍生出的刁奸与欺奸,均从元代才开始出现,由此产生了不少相关判例与法律解释。这些罪名在当时的法律文献中常有单独篇目,如掏摸与白昼抢夺在《元典章》“刑部·诸盗”篇中列有专目,欺奸在“刑部·诸奸”篇中亦有专目,刁奸虽无专目,但在元后期颁行的《至正条格》中至少有六个条目。元代有关盗罪与奸罪的司法实践,直接影响到以后明清的相关立法。
元代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立法形式、内容及司法实践均对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不过,因元朝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且统治时间不长,其法律影响并未引起后世足够重视。①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元代法律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即多次提及中国古代罪名与处罚变化过程中元代的影响,其中有关盗罪,他根据《元史·刑法志》的相关记载,认为:“明律除规定了上述各种盗罪外,还有掏摸和白昼抢夺二种盗罪,都是承自元代。”[1](P135)至于刁奸,蔡枢衡虽也有所讨论,但因其所根据的《元史·刑法志》未出现刁奸一词,导致他在探讨刁奸的起源时出现误判。本文受蔡枢衡观点启发,拟将视野从《元史·刑法志》扩及《元典章》《至正条格》等元代其他重要法律文献,试图就掏摸、白昼抢夺、刁奸及欺奸诸罪在元代立法中的面貌加以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以后明清的影响,以期引起学界对元代法律地位的重新认识。
一、掏 摸
掏摸类似今天的扒窃,元徐元瑞《吏学指南》将其列入“贼盗”项下,定义为:“择便取物曰掏,以手揣物曰摸。”[2](P114)
元初有关强窃盗贼案的处理,主要是比附亡金《泰和律》,在此基础上断罪。至元八年(1271)禁行《泰和律》后,则采取“因事制宜,因时立制”[3](P2)“随事立法”[4](P726)的原则,由此出现了大量前后不一、量刑各异的断例。直到大德五年(1301)十二月二十六日,中书省才在“与御史台、也可札鲁忽赤一同分拣前后行过体例,斟酌轻重,定到各各等第”的基础上,奏准圣旨,颁布了一部《强窃盗贼通例》通行全国。[5](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强窃盗·强切盗贼通例》,P1624-1627)这部通例广泛涉及各类强盗、窃盗的量刑等级,徒、流、刺字等刑罚的具体内容,以及捕盗的奖惩措施等。因内容较系统全面,被现代学者认为标志着元代刑法体系的初步形成。②不过,在这部通例中并没有出现对“掏摸”的规定。目前所见“掏摸”一词,多见具体案件的判决。
《元典章》最早出现的掏摸案判决,是在至元十一年(1274)。
中书兵刑部:
为至元十一年五月捉获到掏摸钞贼人王合住、齐丑脸,责得各年一十四岁,同情于木塔寺前掏摸讫卖面事主钞五钱,又于杨和门里偷讫事主钞四两,被捉罪犯。呈奉都堂钧旨,依理刺断施行。[5](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掏摸·年幼掏摸刺断》,P1679)
这是在禁用《泰和律》后、颁布《强窃盗贼通例》前发生的一个案件。掏摸贼人王合住、齐丑脸年仅十四岁,两次掏摸钱钞累计四两五钱,数额也不大,即便如此,二人依然被按普通盗窃罪刺字断罪。这当与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严厉打击贼盗的历史背景有关。至元二十三年(1286)四月,中书省臣上言:“比奉旨,凡为盗者毋释。今窃钞数贯及佩刀微物,与童幼窃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议,一犯者杖释,再犯依法配役为宜。”世祖回答说:“朕以汉人徇私,用《泰和律》处事,致盗贼滋众,故有是言。”[6](卷一四《世祖纪十一》,P289)其中“窃钞数贯”与“童幼窃物”竟要处以“配役”(即徒刑),惩罚力度远超以前朝代。这种局面直到《强窃盗贼通例》颁行后,才有较大改观。
至大元年(1308)又发生一起类似案件,程福孙受人唆使掏摸事主熊十二案,因案犯程福孙年仅十五岁,又兼赃不满贯(至元钞伍佰文),在地方层层上报中书省后,由刑部做出裁决:“程福孙年方十五,未行出幼,拟合免刺。”紧接其后,刑部又对此案做了扩大性解释:“今后强切盗贼,已得财者,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废疾不任重刑,合行免刺收赎。”因刑部的判决与扩大性解释“事干通例”,裁决做出后由中书省遍行各地作为类似案件的判决依据。[5](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免刺·老幼笃废疾免刺》,P1661)由此我们亦不难看出,掏摸案犯年幼免刺,也是与强窃盗贼一体做出规定的。
以上掏摸案,案犯均为未成年人,那么,对成年人的处理又是如何呢?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发生李万一伙同他人掏摸事主袁庆钱钞案。该案发生于江西行省抚州路某处勾栏门前。经抚州路录事司初步审得,李万一等人从事主袁庆处共窃得赃物计至元钞二贯文十张,合计至元钞二十两(一贯文为一两),折合中统钞二锭(一锭五十两,中统钞与至元钞折算比例为5:1)。在分配赃物时,李万一两个同伙分得至元钞二贯,另有“赶趁需求”军丁索要至元钞四贯,剩下至元钞十四贯,也即中统钞一锭二十两,均归李万一所有。抚州路按规定将两个同伙刺字,决杖五十七下,但李万一因系中统钞一锭以上罪名,上报江西行省裁决。江西行省援引先例,认为李万一所犯,“即与断过偷盗官布贼人赵春二定之上罪名无异”,将李万一项上刺“切盗一度”字样,决杖六十七下。[5](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掏摸·掏摸钞袋贼人刺断》,P1679-1680)本案发生在《强窃盗贼通例》颁布前,处罚与《通例》也不尽相同(按《通例》,窃盗赃满至元钞十贯以上至二十贯,杖七十七下),但也是严格按照当时盗窃罪的相关判例——赵春偷盗官布案的判决量刑处罚的。
大德五年《强窃盗贼通例》颁行后,屡有更动,至仁宗延祐二年(1315),又颁行全面修订的新例[5](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强窃盗·处断盗贼断例》,P1634-1636),因执行力度不够,延祐六年(1319)又重申新例[5](新集《刑部·诸盗·总例·盗贼通例》,P2166-2168)。同大德旧例相较,延祐新例的处罚力度明显加大。也正是在此期间,又发生了陆九住掏摸钱钞案。
江浙省咨:宁国路申:归问得贼人陆九住状招:不合于延祐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掏摸讫事主万众奴中统钞二十五两五钱,被捉到官。取讫备细招词,蒙襄阳路将九住刺讫左臂,杖断六十七下,转发镇江翼江百户下应当军役。不合违例,于当(司)〔年〕自用针墨,将元刺切盗一度四字,填作花绣,迷没不见所刺字迹。又不合于延祐六年三月十八日,纠合唐定孙同情,于构栏门首,九住掏摸讫事主潘文兴中统钞一定三两六钱,被捉到官是实。[5](新集《刑部·诸盗·骗夺·掏摸贼依切盗断》,P2182)
江浙行省在发给中书省的咨文中提到处理本案的倾向性意见:
看详:陆九住先于延祐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掏摸讫事主万众奴中统钞二十五两五钱,刺断讫六十七下,转发本翼当军。不悛前过,又行纠合唐定孙,掏摸客人潘文兴中统钞一定三两六钱,准至元钞一十两七钱二分。若比依切盗曾经断放、偷盗十贯以下再做贼为首出军例断遣,缘本贼二次所犯,倶系掏(抹)〔摸〕钞两,恐涉太重。如照偷盗财物十贯以下(上?)例,杖断六十七下,及于本贼右臂上刺“切盗一度”四字,左臂上补刺,徒役一年。[5](新集《刑部·诸盗·骗夺·掏摸贼依切盗断》,P2182-2183)
咨文两处援引的法律规定,实际上都是延祐新例。其中前者,据延祐新例:“经断放偷盗十贯已下的,再做贼呵,为首出军,为从徒三年。”后者,“切盗财物:……十贯以上者断六十七,徒一年”。陆九住第二次掏摸折合至元钞十一两七钱二分,实际上已超过十贯。江浙行省之所以援引“经断放偷盗十贯已下的”云云,是因延祐新例只有此项规定,且举轻以明重,十贯以上的处罚只能更重。因掏摸钞两比一般窃盗社会危害性小,江浙行省建议比照初犯窃盗十贯以上而非再犯窃盗十贯以下的处罚规定结案(前者徒一年,后者则要出军)。该案经中书省判送刑部后,刑部认为:
贼人陆九住所招,先犯掏(抹)〔摸〕钞两,刺左臂,杖断六十七下,在后将元刺字样填刺作花绣。今犯不悛前过,又复掏(抹)〔摸〕事主潘文兴至元钞一十贯七钱二分,合同切盗再犯,回咨行省,补刺,杖断六十七下,依例发付肇州屯种相应。[5](新集《刑部·诸盗·骗夺·掏摸贼依切盗断》,P2183)
据此,刑部坚持本案应比照窃盗再犯处理,建议“回咨行省,补刺,杖断六十七下,依例发付肇州屯种相应”。所谓“肇州屯种”,在元代适用出军罪行较轻者,较重者则要发付“奴儿干地面”。此后,延祐七年(1320),中书省又“定拟到轻重合发奴儿干、肇州流囚”,适用“肇州屯种”者共有六类,其中就有“经断放、偷盗十贯以下的,再做贼呵,为首出军”者。[5](新集《刑部·刑制·刑法·发付流囚轻重地面》,P2156-2157)刑部的这一建议得到中书省批准。
应当说,通过本案审理,元朝又重申了掏摸完全比照窃盗处理的原则。据《元史·刑法志》:“诸掏摸人身上钱物者,初犯、再犯、三犯,刺断徒流,并同窃盗法,仍以赦后为坐。”[6](卷一〇四《刑法志三·盗贼》,P2662)上述内容应为包括本案在内的一些相关判例的摘要性文字表达。
掏摸作为元代才开始出现的一种特殊罪名,应在元代颁行的法典性文献汇编——《大元通制》尤其是《至正条格》中有记载。只是前者断例今已全部失传,后者目前仅断例卷二八《捕亡》有《掏摸依窃盗捕限》条[7](断例目录,P165),内容也已失传,但据标题及所属篇目,显然不是掏摸罪的处罚规定,但也可视为掏摸比同窃盗处理的又一旁证。至于掏摸的具体规定(有可能是判例),很有可能载于《至正条格》断例卷一六《贼盗·盗贼通例(三条)》中的某一条。[7](断例目录,P160)
明朝建立后颁布的《大明律》,吸收了元代有关掏摸的罪名设定。其中《大明律》有关窃盗的规定中,即有“掏摸者,罪同”[8](卷一八《刑律一·贼盗·窃盗》,P141)的表述。
掏摸比同窃盗,明代各家律学注释大同小异。如明初何广《律解辩疑》:“谓如窃盗一体科罪。本条云‘掏摸’者,择便取物曰‘掏’;以手揣物曰‘摸’。”[9](卷一八《贼盗》,P183)这显然是元代《吏学指南》定义的翻版。应槚《大明律释义》:“掏,择便也;摸,取也。谓择便而摸取其物也,即窃盗也。故罪同窃盗,三犯亦绞。”[10](卷一八《贼盗》,P138)王肯堂《王仪部先生笺释》也有类似解释:
择便取物曰掏,以手探物曰摸。如白昼闯入人家,因便取其财物,及剪绺割包之类。此与窃盗无异,故其科罪,或笞或仗或流或徒或刺字,及为从减等,俱与窃盗同,仍并入窃盗次数通论,三犯坐绞,拒捕者亦同窃盗拒捕律论。[11](卷一八《贼盗》,P527)雷梦麟《读律琐言》则强调掏摸与窃盗的手段不同和时间差异:
夫曰窃盗,谓其潜隐踪迹,行之于昏夜者。若夫白日之间,乘事主之不觉而掏摸人财者,其踪迹诡秘,与窃盗无异,故罪与窃盗同;亦以一主为重,并赃,分首从论,并刺“掏摸”二字。初犯右臂,再犯左臂,三犯处绞,一如窃盗之法,仍并入窃盗次数通论。[12](卷一八《刑律·贼盗·窃盗》,P323-324)
对将掏摸从窃盗罪单独列出的原因及其弊端,蔡枢衡有很好的总结与评价:
从传统观点看:掏摸人身上财物亦属《唐律疏议》中所谓“方便私窃其财”,显属一种窃盗,无庸另定罪名及处罚。惟因《明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条夹注解窃盗为“潜行隐面,私窃取其财。”掏摸既非潜行,又不隐面,因而不属窃盗范围。若不另定罪名,便成于法无据。这就是《明律》在窃盗条中所以明定“掏摸者罪同”的缘故。实则潜行既与私窃含义重复,不可并举;强盗化装,亦属隐面。隐面、显面实非强、窃分界的合理标准。《明律》夹注变更《唐律疏议》解释,显属画蛇添足,以致割裂窃盗概念。拙劣解释之为害,于此足见一斑。《清律》尤而效之,不觉其非,自属汉、唐以来重儒轻法积弊之一种表现。[1](P135-136)
盗窃罪传统理论对“秘密窃取”的界定曾经历从“绝对秘密”到“相对秘密”的发展,掏摸不属“潜行隐面”,因此在元代被从盗窃罪名中剥离出来,成为比同窃盗处理的一项新罪名,这一罪名历明、清两朝而不改,直到民国始废除,重又并入盗窃罪。
除普通意义上的掏摸外,《元典章》在“掏摸”项下还列出两个特殊案例,一为李广志使用懵药摸钞案,一为席驴儿等白昼殴打抢摸钞两案。但两案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掏摸。其中后者笔者将放入白昼抢夺进行讨论,这里只介绍前一案。
案犯李广志,专门摘取曼陀罗、萆麻子制作懵药药丸,后在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二十七日,买到荤面一份,将事先准备好的药丸碾碎放在面中,诱骗吴仲一食用。等到吴仲一昏迷不醒,李广志即将其拽至东湖畔空野处,用刀子将其绢袋割断,窃去中统钞五锭二十五两。此案刑部照依窃盗例拟判,结果被监察御史刷卷时查出,由御史台呈报中书省:“刑部拟依切盗,似有未尽。原其罪犯,合从强盗论罪。然系通例,宜令合干部分再行定拟相应。”刑部在接到省判后,虽然认为:“李广志所犯,用懵药令吴仲一食用,割取钞定情罪,既已照依切盗呈准刺放,又系大德十年十二月十八日钦遇圣旨分拣踈放罪囚已前事理,别难定夺。”但也不得不做出规定:“今后似此贼徒,若于饮食内加药,令人迷谬而取其财者,合从强盗法论罪相应。”[5](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掏摸·懵药摸钞断例》,P1680)也即变相承认了以前的判决违错。
实际上,对此类犯罪行为,《唐律疏议》已有比同强盗的解释:“若饮人药酒,或食中加药,令其迷谬而取其财者,亦从‘强盗’之法。”[13](卷一九《贼盗·强盗》,P357)《元史·刑法志》:“诸以药迷瞀人,取其财者,以强盗论。”[6](卷一〇四《刑法志三·盗贼》,P2658)及《至正条格》断例卷一七《贼盗·药人取财(二条)》(已佚)[7](断例目录,P160),均应与本案相关。《大明律》亦将其列入“强盗”项下:“若以药迷人图财者,罪同。”[8](卷一八《刑律·贼盗·强盗》,P140)此后清代颁布的《大清律》直至清末《大清现行刑律》,均相沿而未改。
二、白昼抢夺
抢夺在元代多指白昼强抢财物。早在元朝建立前的大蒙古国时期,当权者就曾打击过这种犯罪行为。像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去世后,“燕多剧贼,未夕,辄曳牛车指富家,取其财物,不与则杀之”。所谓“未夕”,应指傍晚之前的黄昏。这些剧贼实际上“皆留后(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亲属及势家子”,他们的行为表现为恃强凌弱,公然强抢百姓财物。当时因成吉思汗业已去世,新任大汗尚未选出,由主持蒙古政务的拖雷派出耶律楚材等到燕京,将这些人按图索骥,“尽捕下狱”,“狱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6](卷一四六 《耶律楚材传》,P3456-3457)入元后,元朝相继在大德五年(1301)与延祐二年(1315)颁行《强窃盗贼通例》与《新例》,但其中并无有关白昼抢夺的特别规定。[5](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强窃盗·强切盗贼通例》《处断盗贼断例》,P1624-1627,P1634-1636)对白昼抢夺的记载,目前主要见一些具体案件的处理。
《元典章》有关白昼不持仗抢夺的案例主要有三件。
一为巡军张焦住抢夺顾同祖钱钞案。本案案犯张焦住,系南康路建昌县巡军。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二十九日,张焦住碰到事主顾同祖携带赎田价钞回家,即暗中尾随。在跟踪至大街无人处后,张焦住将顾同祖拖入巷内偏僻处,打了两拳,夺走钞一百二十五两。此案先经审断罪囚官审理,拟“比附强盗不伤事主刺断”,但“缘所犯在分拣罪囚已前,却该释免”。江西行省以张焦住“情犯颇重”为由,建议杖断一百七下。最后中书省的意见为:“贼人张焦住罪犯,依准本省所拟,市曹对众杖断一百七下,刺面配役。”[5](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抢夺·巡军夺钞刺断》,P1682;新集《刑部·诸盗·骗夺·革闲弓手祗候夺骗钱物》,P2185)
二为席驴儿等白昼殴打抢摸缪喜等钞两案。本案案犯席驴儿,以前曾因偷盗铜钱,经断刺臂。后来再次纠合孙儿、张驴儿,“于街衢白昼将缪喜等用拳打伤,抢摸钞两”。此案经杭州路及江浙行省审理后认为:“若以比附强盗持杖劫物伤人刺字,恐涉太重。”在经江浙行省移咨中书省判送刑部后,刑部认为:“席驴儿等所犯,既非持杖施威,强劫民财,难同强盗定论。合咨行省照勘,如已招明白,比依切盗刺字相应。”并得到中书省批准。[5](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掏摸·白昼殴打抢摸钞两》,P1681)在这里,刑部开始将持仗与否作为区分比同强盗抑或窃盗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为唐周卿等抢夺蔡国祥棕帽案。本案案犯唐周卿,纠合贾国贤,将蔡国祥棕帽抢去,上有红玛瑙珠子一串、白毡帽一个。此案在经潭州路录事司审理后,由湖广行省移咨中书省,建议:“如蒙比同切盗一体刺字相应。”中书省接获咨文后,判送刑部。刑部认为:“唐周卿所招,纠合贾国贤同谋强行夺抢蔡国祥棕帽罪犯,即与席驴儿一体。既已断讫,拟合比依切盗刺字相应。”[5](新集《刑部·诸盗·骗夺·革闲弓手祗候夺骗钱物》,P2186)
上述三案,除时间较早的第一个案件比附强盗不伤事主例,处罚较重外,其他两案的处理均发生在仁宗皇庆元年(1312),且均比依窃盗罪处理,理由正如席驴儿案中刑部所云,系“非持杖施威,强劫民财”。
《元典章》有关白昼持仗抢夺的案例亦有三件。
一为出征军人罗八等持仗抢夺案。罗八本名罗俊,为起补云南出征军人。起先,罗俊等人只是恐吓勒取百姓钱物,后来发展到公然手执刀刃棍棒,“白昼强劫打伤”。江西行省经审理认为:“若同杀伤事主定拟,却缘诏书已前(或指大德六年三月诏赦),止招持杖强劫民财。详情,拟合将各人杖断一百七下,刺讫,发付云南应充军役。”移咨中书省后,中书省裁决:“罗俊等所犯,若依行省所拟刺断,缘系云南出征军人,拟将各人比同强盗,免刺,杖断讫,发付云南出军。”[5](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
抢夺·出征军人抢夺比同强盗杖断》,P1682)
二为杨贵七等持仗白昼抢夺施进孙、柯唐保案。杨贵七此前曾因偷盗牛只被断罪刺臂,后又骗要潘益隆等钱物,被再次断罪。此次,杨贵七又“为首起意,纠合何胜一持仗,就路上打夺过往客人钱物”。[5](新集《刑部·诸盗·骗夺·持仗白昼抢夺同强盗》,P2184)二人诱骗事主施进孙、柯唐保至僻静处,夺得中统钞七锭三十两五钱(合至元钞七十六两一钱)及绢缠袋一条。当时,施进孙曾挣扎反抗,被杨贵七用木棒在左边腰下打讫二下。柯唐保要向前揪住杨贵七,又被杨贵七持刀威逼,何胜一用言语恐吓,不敢向前。事后,杨贵七与何胜一坐地分赃,将钱物全部挥霍完毕。本案先由太平路总管府审理,将杨贵七杖断九十七下,何胜一八十七下。太平路对本案的处理,显然依照的是《强窃盗贼通例》中的窃盗条款:“十贯以下六十七,至二十贯七十七,每二十贯加一等。”[5](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强窃盗·强切盗贼通例》,P1625)至元钞七十六两一钱,量刑适合赃物六十贯至八十贯的幅度,首犯杨贵七合杖九十七下,从犯何胜一减一等,合杖八十七下。不过,依《通例》的规定,窃盗已得财是要刺字的,对此,太平路总管府却犹豫不定,以“若便刺字,终无通例”的理由,将此案上报江浙行省,移咨中书省请示处理意见。
刑部接到省判后,全盘推翻太平路的处理:“杨贵七等所犯,将施进孙打讫二下,及用刀子唬吓,虽无检验到伤痕,即系强盗有仗不曾伤人,正赃已及二十贯以上,拟合依例,将首贼杨贵七结案,从贼何胜一流远。外据太平路官吏不应将杨贵七等减轻断讫一节,系在延祐元年正月二十三(二?)日以前,别无定夺。”[5](《刑部·诸盗·骗夺·持仗白昼抢夺同强盗》,P2184)在这里,刑部认为,杨贵七等使用暴力(棒打)与威吓(持刀恐吓)手段抢夺钱物,虽然事主没有检验到伤痕,但应比照《通例》中的强盗条款:“持仗……不曾伤人者……但得财……至二十贯,为首者死,余人流远。”[5](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强窃盗·强切盗贼通例》,P1625)因此,“拟合依例,将首贼杨贵七结案,从贼何胜一流远”,并得到中书省批准。[5](《新集《刑部·诸盗·骗夺·持仗白昼抢夺同强盗》,P2183-2184)对照《通例》,我们不难看出,刑部所称对杨贵七的所谓“结案”,实际应指处死。至于太平路官员的故出人罪的错判责任,因碰到延祐元年改元大赦③,没有受到追究。
三为余云六等白昼持仗抢夺案。江浙行省信州路贼人余云六,以前曾犯撇捲骗钞,虽经多次断罪处罚,仍怙恶不悛。后来纠合陈嫰、徐仁三,同谋白昼持仗劫财,将客人王寿甫以呵问私盐为由,用棒殴打,推下水坑,夺走其袋包钱物。本案先经信州路总管府与江浙行省审理,将余云六、徐仁三、陈嫰三犯“比依切盗一体刺配”。因“事干通例”,由江浙行省移咨中书省请示。中书省判送刑部后,刑部援引以前杨贵七等持仗白昼抢夺施进孙、柯唐保例,认为:“贼人余云六、徐仁三、陈嫰,供系先犯撇捲骗钞经断贼徒,不悛前过,今又同谋白昼持仗截路,虚指巡问私盐为由,将事主王寿甫用棒打伤,推入水坑,夺讫钱物,比依合同强盗定论。缘本省已将各贼刺断,以此参详:贼人余云六等所犯,既已刺断,似难追改。拟合将各贼发付奴儿干出军相应。”刑部意见得到中书省批准。延祐七年(1320)六月,中书省有关本案最终裁决的咨文送达江浙行省。[5](新集《刑部·诸盗·骗夺·持仗白昼抢夺同强盗(又)》,P2184-2185)
本案的处理是在延祐七年(1320),也许正因此前元代历次所颁案例不一,较为含混,信州路总管府与江浙行省在处理此案时,仍将首犯余云六、从犯陈嫰与徐仁三,比依窃盗例一体刺字断罪。其实,本案与前面提到的杨贵七等持仗白昼抢夺案极为相似,且案发地均发生在江浙行省。江浙行省也许为慎重起见,又以“事干通例”为由,将案件移咨中书省请求批示。中书省将本案移交刑部后,刑部首先援引杨贵七等持仗白昼抢夺案,并以此为据,认为余云六等所犯情节与杨贵七等持仗白昼抢夺案同,应“比依合同强盗定论”。虽然江浙行省已将余云六等人刺字杖断,无法追改,但刑部仍要求将三人按强盗例发付奴儿干出军。
上述三案,因涉及案犯携带武器(持仗,即执把器仗),均比照强盗处理,处罚力度明显比不持仗要大许多。
此外,尚有周大添累犯窃盗、白昼抢夺案。周大添曾有多次窃盗、白昼抢夺等犯罪行为。“初犯切盗刺断,今次白昼抢夺张四嫂麻皮,强行剥脱王千二〔衣服〕钞物,又复为首纠合陆贵六等,偷盗金正二桑叶,用禾叉戳伤事主,前后十次,如此凶恶,累犯不悛。”在首次窃盗被断刺字后,周大添还曾将刺字改作雕青,以图遮盖。此案先后经嘉兴路与江浙行省审理,“拟将本贼杖断一百七下,补刺元字,迁徙他方”。移咨中书省后,刑部建议:“合准行省所拟,将本贼杖断一百七下,补刺,迁徙辽阳地面屯种相应。”后得到中书省批准。[5](新集《刑部·诸盗·再犯贼人·再犯贼徒断罪迁徙》,P2181-2182)本案案犯周大添“白昼抢夺”“强行剥脱”,不曾明言是否持仗,但因属累犯,处罚也很严厉。
综合上述案例,不难发现,元代对白昼抢夺的概念定义比较含混,不论持仗与否,有时作“抢夺”,有时又作“殴打抢摸”“强劫”“强行劫讫”“强行夺抢”“打夺”乃至“强行剥脱”等等,不一而足,并不统一。但有一点似可基本肯定,即依持仗与不持仗的区别,当时此类犯罪行为可分别比同强盗与窃盗处理。
除上述案例外,元朝颁布的法令或批复中有关此类规定还有不少,多集中在仁宗在位期间。
如皇庆元年(1312)刑部根据中书省判送江浙行省咨文所拟批复提到:
江浙行省咨:“据安抚使王宣武所言:澉浦海口等处新附军人弟男子侄,结连灶户、卤丁、恶少、泼皮人等,纠合成群,执把器仗,白昼聚众抢劫商船财物,及拆毁船只”等事。以此参详:今后若有经过官民船只遭风着浅,拘该地面诸色人等昼即并力救护,敢有似前乘时聚众抢劫财物、拆毁船只之人,即将犯人捉拿赴官,追问是实,同强盗法科断。……[5](卷五九《工部二·造作二·船只·禁治抢劫船只》,P1988)
上述意见得到中书省批准。
再如延祐二年(1315)江浙行省咨文提到:
理问所知事刘将仕呈:“杭州路军人赵黑儿,延祐元年闰三月初五日,达达镇抚将引前来佑圣观桥救火,中路背弃,强盗民财,不能钤束,不为无罪。各处官司别无奉到遵守定例,轻易发落。”以此参详:遇有居民不测遗漏,军民官司严加关防,军民人等毋得乘时为奸。凶徒恶党乘风火惊扰之际强夺财物,比同白昼抢劫,枷令示众,照依强盗通例科断。……即系为例事理,咨请照详。
刑部所拟批复除援引上述皇庆元年禁治抢劫船只例外,又提到:“居民不幸遭值风火,烧胤房屋,惊扰之际,抢夺财物,亦合比依强盗例计赃科断,仍刺字。”刑部上述意见也得到中书省批准。[5](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遗漏·遗火抢夺》,P1908)
通过这些批复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元朝的公文用语中,抢劫与抢夺确实混用不分。上述无论是抢劫船只财物、拆毁船只,抑或失火乘机抢夺财物,以后都被《大明律》据以吸收进“白昼抢夺”罪的相关规定中(见后)。
延祐七年(1320),针对淮西廉访司申文所云:“今因照刷文卷,多有革闲弓手、祗候、无役军人纠合游食之徒,聚成朋党,多者十数人,少者不下五六人,悬带弓箭,执把枪、刀、铁尺,将路行客旅拦截,诈称捕限拿贼、根捉逃军,辨验引据,将平民拷打,搜番行李,劫夺钱物。若不禁治,虑恐滋蔓。”刑部接连援引前面提到的巡军张焦住抢夺顾同祖钱钞案,唐周卿等抢夺蔡国祥棕帽案,杨贵七等持仗白昼抢夺施进孙、柯唐保案,余云六等白昼持仗抢夺案,共计四案判决,认为:
公取、切取,皆为盗论。今淮西廉访司所言,革闲弓手、祗候人等执把器仗,拦截路行客旅,诈称捕捉逃军、辨验引据等项为名,强行夺骗钱物等事,若便议拟,中间各各情犯不同,难便定立通例。以〔此〕参详:今后此等贼徒发露到官,招赃明白,比依前例,临时量情刺断。其有司禁治不严及不依例决遣者,验事轻重断罪相应。[5](新集《刑部·诸盗·骗夺·革闲弓手祗候夺骗钱物》,P2186)
“公取、窃取皆为盗”,源自《唐律》的表述。“‘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13](卷二十《贼盗·公取窃取皆为盗》,P379)直到此时,虽然地方多以此类案件“事干通例”,上报中书省移送刑部拟定意见,但在处理多起案件后,刑部依然没有定立相关通例,而是要求地方比依四案处理,临时量情刺断。检讨上述四案,其实只有唐周卿等抢夺蔡国祥棕帽案未见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比依窃盗处理,其他三案案犯,不论持仗与否,均使用了暴力与威胁手段,比依强盗处理。这大概就是当时刑部对如何处理白昼抢夺罪的倾向性意见。需要提到的是,此处刑部没有援引席驴儿等白昼殴打抢摸缪喜等钞两案,大概是因案犯虽使用暴力手段(用拳打伤),但被当时的刑部比同窃盗定罪,已不太符合此时刑部对白昼抢夺的认识。正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
元朝前后颁布的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前者因系收录延祐三年(1316)以前的法律文书,上述刑部意见肯定不在其中。《至正条格》断例卷一七《贼盗》单独列有《强夺财物(三条)》[7](断例目录,P160),应该与白昼抢夺有关,但可惜具体内容已失传。
《元史·刑法志》与白昼抢夺有关的记载如下:
诸强夺人财,以强盗论。……诸白昼持仗,剽掠得财,殴伤事主;若得财,不曾伤事主,并以强盗论。诸官民行船,遭风着浅,辄有抢虏财物者,比同强盗科断。若会赦,仍不与真盗同论,征赃免罪。[6](卷一〇四《刑法志三·盗贼》,P2658)因《元史·刑法志》对据以成书的《经世大典·宪典》删节很多④,这是否就是全部内容,目前还不好判断。但从《至正条格》与《元史·刑法志》的表述,似可认为此罪到元代后期或已统一定名为“强夺”。
明朝建立后颁布的《大明律》,开始列有“白昼抢夺”的专条:
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计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伤人者,斩。为从,各减一等。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若因失火及行船遭风着浅,而乘时抢夺人财物及拆毁船只者,罪亦如之。其本与人斗殴,或勾捕罪人,因而窃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夺去者,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并免刺。若有杀伤者,各从故斗论。[8](卷一八《刑律一·贼盗·白昼抢夺》,P141)
“白昼抢夺”条在《大明律》的位置,介于强盗、劫囚与窃盗之间。按,有关普通强盗罪,《大明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窃盗罪,“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者,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8](卷一八《刑律一·贼盗·强盗》《窃盗》,P140,141)由此可见,《大明律》对白昼抢夺的量刑幅度,应是介于强盗与窃盗之间,这与元朝依案情分别比同强盗与窃盗论处的做法明显不同。至于“若因失火及行船遭风着浅,而乘时抢夺人财物及拆毁船只者,罪亦如之”,显然参考了元朝的立法经验。除《大明律》外,《皇明条法事类纂》专列“白昼抢夺”一项,收录从《白昼抢夺三五成群及打搅仓场充军为民例》(天顺八年,1464)至《各处聚众争斗及拒捕挟仇强奸夺财殴打职官号称搥聊娄头等项不分首从俱充军》(弘治四年,1491)相关事例15件。[14](卷三四《刑部类·白昼抢夺》,P340-364)以后编纂成书的《(万历)问刑条例》对白昼抢夺亦有专门规定:
凡号称喇唬等项名色,白昼在街撒泼,口称圣号,及总甲、快手、应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摄为由,各殴打平人,抢夺财物者,除真犯死罪外,犯该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虽系初犯,若节次抢夺及再犯、累犯笞、杖以上者,俱发原抢夺地方,枷号一个月,照前发遣。若里老、邻佑知而不举,所在官司纵容不问,各治以罪。[8](附录《问刑条例·刑律一·贼盗·白昼抢夺条例》,P410)
所谓“喇唬”,元代多作“泼皮”“无藉之徒”,相当于今天的地痞无赖。《皇明条法事类纂》所收事例,多系此类人当街撒泼,殴打平民,强抢财物,这应是明代白昼抢夺罪最常见的一种情形。
除官方规定外,明代律学家对白昼抢夺也多有解释,像王肯堂《王仪部先生笺释》认为:
白昼抢夺与邀劫道路,形迹相似,须当有辨。出其不意攫而有之曰抢,用力而得之曰夺。人少而无凶器者,抢夺也,人多而有凶器者,强劫也。凡徒手而夺于中途,虽暮夜亦是抢夺,但无白昼二字耳。若昏夜抢夺,执有凶器,即是强盗,欺其不知不见而取之,即是窃盗,故不言。[11](卷一八《贼盗》,P524)
雷梦麟《读律琐言》的解释大致相同。[12](卷一八《刑律·贼盗·窃盗》,P320-321)按,王肯堂将“人少而无凶器”与“人多而有凶器”作为区分白昼抢夺与强劫(即强盗)的区分标准,直接影响到以后《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定。[15](卷二四《贼盗·白昼抢夺》,P386)不过,他的观点在当时还仅限于学理解释。像人数,《皇明条法事类纂》所收相关事例即有一人、“二三成群”“三五成群”甚至“数十成群”不等,并未有人数多少的限定。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也提到:“注虽以人少人多,有无凶器,分别抢夺、强劫,然亦不可拘泥。有人少而有凶器为强劫者,有人多而无凶器为抢夺者,总以情形为凭,不在人多人少。”[16](卷一八《贼盗·白昼抢夺》,P590)至于凶器,前述元代白昼抢夺已多含持仗威胁施暴的情况,《皇明条法事类纂》也有类似案例。如金吾右卫前所军匠籍余丁张昭,多次抢夺他人钱物,罪行累累。其中,“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内,因昭手执铁斧,将军匠张源要砍,强夺绸巾一顶”,后被捉获到官,“就于名下追出行凶斧棍等器”。[14](卷三四《刑部类·白昼抢夺·一人凶恶节次抢夺财物满贯徒罪充军》,P350-351)不过,王肯堂对抢夺概念的定义,虽不尽符合明代实情,却对后世抢夺罪有一定影响。蔡枢衡认为:
抢夺实是强夺、剽掠和抢虏的概括,而含义不尽相同。抢者,突也。突者,猝也。夺是争取。抢夺是猝然争得。特点在于抢者出其不意或乘其不备;被抢者措手不及。取得虽非平稳,究未行使威力,显不同于强盗,亦有异于窃盗,情节在强窃之间,颇与恐吓相当,但有用智、用力之别。故其处罚亦重于窃盗而轻于强盗。惟白昼限制,有不如无,白璧之玷,显在多此一举。[1](P136)
蔡枢衡的观点,无疑是从现代刑法学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的,这也与目前中国刑法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分大体一致。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别,目前一般认为抢夺行为是直接对物而非对人使用暴力,且其暴力尚未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但通过对白昼抢夺的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抢夺,从最初的比同窃盗、强盗,到罪名的单独划出,及其概念定义的确定,应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三、刁奸与欺奸
元代诸奸罪出现的新罪名主要有刁奸与欺奸。其中刁奸即通常意义上的诱奸,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因对元代法律的研究取材仅限于《元史·刑法志》,认为刁奸仅见于明清法律。[1](P130-131)迄今为止,法学界一般也认为刁奸源自明代,其主要依据当为《大明律》:
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刁奸,杖一百。……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8](卷二五《刑律八·犯奸·犯奸》,P197)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元史·刑法志·奸非》的相关记载:
诸和奸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诱奸妇逃者,加一等。男女罪同,妇人去衣受刑。[6](卷一〇四《刑法志三·奸非》,P2653)
前者的刁奸实际上对应的就是后者的“诱奸妇逃者”,二者各罪刑罚的等差也大致相同,只不过《大明律》将元代减三下以七为尾数的杖刑又恢复为整数,即杖七十七、杖八十七、杖九十七分别调整为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其实,刁奸一词在元初就已出现了。据《元典章》:
至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尚书刑部符文该:来申:“任用刁奸路贵妻于都声,招伏。倶两目盲,即系笃疾。”省部相度:各人虽有所犯,既是笃疾,难议科决。仰将各人疏放,内于都声分付伊夫路贵收管施行。[5](卷四五《刑部七·诸奸·凡奸·笃疾犯奸免罪》,P1534)
上述案件奸夫任用与奸妇于都声的非法性行为被定义为刁奸,只因二人均为双目失明的盲人,属于笃废残疾,才免于刑事处罚。这是笔者发现刁奸一词在元代司法审判中最早出现的例子。《元史·刑法志》如前所述,取材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成书的《经世大典·宪典》,使用的是“诱奸妇逃者”,没有出现刁奸一词,这似乎表明,直到文宗时代,刁奸尚未成为一种成熟罪名。但到顺帝至正五年(1345)成书的《至正条格》,则出现了较大变化。《至正条格》断例卷25《杂律》主要收录诸奸罪名,其中集中出现了《刁奸品官妻妾》《刁奸侄妇》《首子刁奸》《刁奸图财》《刁奸遇革》《刁奸庶母》六个条目。[7](断例目录,P163)虽然上述条目的具体内容已佚,不过,我们根据《元史·刑法志》的相关表述,仍可推测其中一些条目的大致内容。如《刁奸品官妻妾》,据《元史·刑法志》:“诸以傔从与命妇奸,以命妇从奸夫逃者,皆处死。”[6](卷一〇四《刑法志三·奸非》,P2655)傔从指侍从、仆役,命妇即品官妻妾。“以命妇从奸夫逃者”与前面提到的“诱奸妇逃者”,也即奸夫诱拐奸妇出逃,大概就是元代刁奸的最原始定义,后来又引申为至别处行奸(见后)。此外,《刁奸侄妇》,类同于《元史·刑法志》:“诸与同居侄妇奸,各杖一百七,有官者除名。”[6](卷一〇四《刑法志三·奸非》,P2654)《首子刁奸》,类同于《元史·刑法志》:“诸子犯奸,父出首,仍坐之。”[6](卷一〇四《刑法志三·奸非》,P2654)
从《至正条格》所载刁奸诸条目来看,至少从元末起,刁奸已成为一种新罪名,而这直接影响到后来明清的相关立法。
明代刁奸罪名,除前引《大明律》外,《皇明条法事类纂》收录《校尉犯刁奸改调别卫充军例》(成化十一年,1475)、《军职奸同僚妻女革职》(弘治三年,1490)两则案例,[14](卷四三《刑部类·犯奸》,P725-726)均为奸夫勾引奸妇至他处通奸,以后编纂成书的《(万历)问刑条例》亦有相关规定:
凡军职及应袭舍人犯奸,除奸所捕获及刁奸坐拟奸罪者,官革职,与舍人俱发本卫,随舍余食粮差操。[8](附录《问刑条例·刑律八·犯奸·奸部民妻女条例》,P433)从和奸分离出来的刁奸罪名,与和奸又有何区别呢?明何广《律解辩疑》云:
谓其人用刁诈巧言,百般调戏而求奸,〔况有〕□行他处,其妇女本以奸论,因而不合听从刁引相类,与背夫〔在逃〕之罪同,故杖一百。又云‘刁’者,谓用言刁,而挟制求奸。盖〔妇女先〕与人奸,而后(故)人觉者,刁而从之,妇女本以奸论,因而〔不合先与〕□不节,故坐同罪,杖一百。[9](卷二五《犯奸》,P258)
何广虽提到“□行他处”“背夫〔在逃〕”,但对刁奸罪名的阐释较为复杂,不易具体操作。应槚《大明律释义》:“诱引妇人出其家之外和奸者。”[10](卷二五《刑律·犯奸》,P196)可谓抓住了罪名要害,较符合刁奸本意。以后明清律学著作大体沿袭了这一定义,雷梦麟《读律琐言》:“听从奸夫刁引,出外通奸。”[12](卷二五《犯奸》,P447)王肯堂《王仪部先生笺释》:“和,谓男女相愿;刁,谓用威力挟制,及巧言诱出,引至别所。然刁必从和来。”[11](卷二五《刑律·犯奸》,P648)沈之奇《大清律辑注》:“刁奸,谓奸夫刁诱奸妇,引至别所通奸,亦和奸也。”[16](卷二五《刑律·犯奸》,P912)等等。
接下来再看欺奸。欺奸在元代又被称作吓奸,系由强奸罪名衍生而成,大概指威逼妇女与之发生性行为的犯罪。《元典章》专列吓奸篇目,但仅有《欺奸囚妇》一条,由此可见吓奸与欺奸含义完全相同。⑤以下为该条全文:
至元二十一年八月,福建行中书省:据汀州路来申:“谢阿丘告:‘姊夫张叔坚兄张十习学染匠师弟陈生来家,将阿丘近腹肚下摸讫一下。告到人匠提领所,将阿丘、陈生监收,有谢押狱吓奸讫。’除干犯人陈生量情断罪外,据谢旺所招欺囚罪犯,府司不曾断过如此体例,诚恐违错。乞照详”事。得此。省府议得:谢旺所招欺奸囚妇谢阿丘罪犯,量情拟杖一百七下。合下,仰照验,当官再审已招,别无寃(仰)〔抑〕,依上决断,省会罢役施行。[5](卷四五《刑部七·诸奸·吓奸·欺奸囚妇》,P1524)
谢旺有押狱职衔,为监狱管理人员,因而有利用权势威逼囚妇谢阿丘就范的条件,这种目的不需凭借暴力手段即可达到。公文提到谢旺的这种行为属“吓奸”与“欺奸”。谢阿丘从其称谓来看(夫家姓谢,娘家姓丘),应为有夫妇人,福建行省对谢旺的处理,大概比照强奸有夫妇人减一等,拟杖一百七下。《元史·刑法志》“奸非”篇至少有5条内容涉及欺奸:
诸翁欺奸男妇,已成者处死,未成者杖一百七,男妇归宗。和奸者皆处死。
诸欺奸义男妇,杖一百七,欺奸不成,杖八十七,妇并不坐。
诸男妇与奸夫谋诬翁欺奸,买休出离者,杖一百七,从夫嫁卖,奸夫减一等,买休钱没官。
诸居父母丧欺奸父妾者,各杖九十七,妇人归宗。
诸奴有女,已许嫁为良人妻,即为良人,其主辄欺奸者,杖一百七,其妻纵之者,笞五十七,其女夫家仍愿为婚者,减元议财钱之半,不愿者,追还元下聘财,令父收管,为良改嫁。[6](卷一〇四《刑法志三·奸非》,P2653-2655)
有鉴于此,有的论著在总结元代欺奸时,认为:“欺奸,也称吓奸,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利用权势威逼妇女就范实施性交行为,因而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其实质也属强奸。”[17](P305)不过,《至正条格》断例卷二五《杂律》有《欺奸使妻》条[7](断例目录,P163),虽内容已佚,但从条目名称看,“使妻”应指使长(类似奴隶主)之妻,此条规定的犯罪主体应为驱口(类似奴隶),而驱口欺奸使妻,自然与所谓“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利用权势威逼妇女”无法榫合。揆之元朝立法本意,很有可能利用威胁手段强迫妇女就范,即可构成欺奸或吓奸。至于一般意义上的强奸,以后的限定范围更窄,须视“强暴之状”也即强暴的具体情节而定。如雷梦麟《读律琐言》:“凡问强奸,须观强暴之状,或用刀斧恐吓,或用绳索捆缚,果有不可争脱之情,方坐绞罪。若彼以强来,此以和应,始以强合,终以和成,犹非强也。”[12](卷二五《犯奸》,P447)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以后《大清律例》的规定:“凡问强奸,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肤体,毁裂衣服之属,方坐绞罪。若以强合以和成,犹非强也。”[15](卷三三《刑律·犯奸》,P552)
明代欺奸,首见《大明律》:
凡男妇诬执亲翁,及弟媳诬执夫兄欺奸者,斩。[8](卷二五《刑律八·犯奸·诬执翁奸》,P199)
明何广《律解辩疑》云:“诬罔曰‘欺’,谓〔诬〕尊欺卑行奸,尊非欺非行,卑反诬反执,故得斩罪。”[9](卷二五《犯奸》,P261)王肯堂《王仪部先生笺释》:“欺奸者,欺其卑幼孱弱而凌制之成奸也。”[11](卷二五《刑律·犯奸》,P654)上述诸家解释欺奸,均强调尊长依仗地位欺凌奸淫卑幼,这显然是对欺奸更为狭义的理解,与元朝对欺奸的宽泛定义明显有别。清朝继承了明朝对欺奸的狭义解释。如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即称:“欺奸,谓欺其卑幼,凌制以成奸,犹强奸也。”[16](卷二五《刑律·犯奸》,P924)
在讨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阶段时,学界常常宋元并举,过分强调宋代法律对元代的影响,甚或以为元代法律是宋代法律影响下的产物。其实,辽宋金元大致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期,最后由元完成统一。撇去蒙古族自身的法律传统不论,即使作为北朝系统的元朝,其法律传统是否受到宋朝的直接影响,也是颇值得怀疑的。宋元类似第一次南北朝时代的陈隋,并非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王朝更替,而是又一次从南北对立走向统一。我们评估元代法律的渊源及其发展,应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出发,才更符合实际。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元年(1368)颁行吴元年(1367)编定的《大明令》与《大明律》,其实应该就是《至正条格》“条格”与“断例”影响下的产物。其中“条格”与《大明令》的承继关系,日本学者内藤乾吉曾有过较详尽的研究,因当时《至正条格》尚未被发现,他使用的是其前身——《大元通制》的“条格”残卷。⑥至于“断例”与《大明律》的承继关系,因《大明律》早期版本业已失传,研究起来要困难许多。不过,我们仍可通过今本《大明律》的具体内容窥见一二。从上述盗罪与奸罪之类新罪名在明代乃至清代的发展嬗变,我们应当不难看出元朝立法活动与司法实践的深刻影响。以此而论,笔者认为,将元明清三代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阶段似更为合理,至少元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阶段。此外,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本文所揭示的新罪名仅为例举,就盗罪而言,除掏摸与白昼抢夺外,明清法律亲属相盗规定中“无服”亲的出现,恐怕也有元代的影响渗透其中。至于其他罪名及其处罚变化,元代法律在其中还起过怎样的作用,尚需进一步探究。
注释:
①对元代法律的重视程度不够,可以说自明以后即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对元代法律评价不高,制定《大明律》时,多次强调要效法唐律。清人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应该说也是这一思想意识下的产物。
②参见姚大力《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后收入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延祐元年正月“丁未,诏改元延祐。释天下流以下罪囚”。(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63页)《元典章》卷三《圣政二·霈恩宥(二十)》:“延祐元年正月□日,钦奉改元诏书节文:自延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除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故杀致命、但犯强盗、伪造宝钞及官吏取受侵盗系官钱粮不在原免,其余一切罪犯,已未发觉,并行释免。”(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④具体详情,可参见拙文《再论〈元史·刑法志〉的史源——从〈经世大典·宪典〉一篇佚文谈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吓奸一词,还可见《元典章》卷四二《刑部四·诸杀一·因奸杀人·傍人殴死奸夫》(第1469页)。
⑥参见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原刊《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年版,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