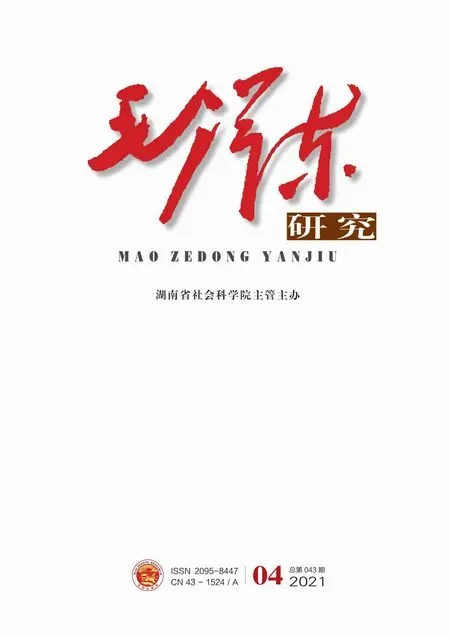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冯留建 孙海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4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高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问题。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0—364页。。这些原则是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3)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儒家生态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涵养。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汲取儒家生态文化的养料,实现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儒家生态文化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观念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演变,如“天地人三才”“万物皆备于我”“天人感应”“民胞物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体现了历代儒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天人合一”的理解。
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是指天、地、人同根同源,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天地最大的恩泽在于化育了生命,而“德”与“生”的表述,也从应然的角度阐释了天地化育万物的生命状态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又如《周易》构建了“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的宇宙生成链,即“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周易·序卦》),对其进行现代性意义的审视,可以解读出“自然界(天地万物)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而关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区别,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孟子·滕文公上》),荀子则更直截了当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荀子·王制》)。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儒家提出了“至诚尽性”,以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状态。所谓“至诚尽性”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何以达到至“诚”因明致诚,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高扬人类理性和主体价值,以“至诚”来“尽性”,以“尽人性”来“尽物之性”,以助天地万物演化繁育,让万物共同繁育而不互相妨害,各行其道而不相互冲突,从而“与天地参”,实现天人合一。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天人合一”的继承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深刻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重要理念,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坚持人类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协同演进、和谐共生。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通过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使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是坚持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内涵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以系统的整体的观点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天人合一”其强调以直觉体验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实践来科学理性地认识自然进而把握客观规律。在通往“天人合一”的道路上,面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天人合一”更多的是强调通过自我反思或后天的教化,以道德上的自我超越来实现主体意识上的“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性的现实考量,来源于对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反思,来源于对“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在总结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高度来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以协调推进现代农业、新型化工业、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现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现代信息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高度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实践为导向,进一步深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
二、从“牛山事件”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孟子从“牛山事件”中反思了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地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了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一)儒家生态文化中的“绿水青山”
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绿水青山中孕育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正如《中庸》所说:“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这指出山水孕育着宝贵的物质财富,在广阔高大的山中,花草树木依傍其生长,飞禽走兽凭借其居留,宝藏在其中孕育;在高深莫测的水中,蛟龙鱼鳖繁殖生长,万物繁殖生衍。人们从绿水青山中“取之”“捕之”“伐之”“牧之”,从这方面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也体现了儒家生态文化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着朴素的认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生态资源要取之有节、用之有度。孟子以牛山为例,对人们过度采伐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进行了反思。“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孟子·告子上》)。牛山曾经很美,但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乱伐滥牧,导致草木的生长更新速度跟不上伐、牧的速度,最终牛山变成光秃秃的山了。孟子还指出牛山难逃“濯濯”的命运,是“以其郊于大国也”,是因为其临近大城市边缘。“牛山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城市发展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牛山的事例,孟子还总结出恢复生态植被的经验,“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指出山林养护有利于恢复自然生态。
(二)吸取古代教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写入大会报告,要求我们必须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不可能也没有产生“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的认识,但“牛山事件”对于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仍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牛山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警醒我们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侵害,防止城市的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因为我们保护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还有附着在自然生态环境上的人文情怀,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3页。。
“牛山濯濯”是人们乱砍滥伐的后果,这就警示我们要正确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把握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决不能突破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1—362页。。这是对“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的否定之否定,也是对古人在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认识上从“朴素”“感性”向“科学”“理性”的飞跃。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不仅仅意味着“借鉴”基础上的“发展”,还意味着使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某些价值在穿越时空后仍然熠熠发光。儒家生态文化中对“牛山事件”的反思给我们开启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视角。绿水青山不仅是我们物质上的“金山银山”,也是我们精神上的“金山银山”。“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孔子以智者喻水,仁者喻山,用山水自然和道德人格构筑了一道雄浑灵秀的风景线。“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通过观察水,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子登山,眼界大为开阔。“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孟子通过观察水流的状态,来悟君子之道。山水是本体,青山绿水都存在,才能产生“山水”的情怀。置身于山水之中,才能体会到“青山绿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情趣,以及山水对我们人生哲学的观照。本体不存,情趣焉在?如果青山绿水都不在,那我们“哲学中的山水”“情怀中的山水”就会真正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看来,绿水青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是我们物质上的“金山银山”,更是我们精神上的“金山银山”。
三、从“使民以时”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儒家生态文化中还包含着“使民以时”的民本情怀,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目的,从“使民以时”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了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儒家生态文化的“民本情怀”
儒家生态文化蕴含着浓厚的民本情怀,即组织民众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生产,同时节约用度,以此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指出治理国家,要谨慎处事,节约用度并且爱护他人,征用民力时,要尊重民时,不要妨碍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这里的“使民以时”是指让民众按照自然规律来组织生产,在春、夏、秋的季节不要妨碍民众从事农业生产,不要让百姓耽误了耕作与收获,只在冬季征调劳力。孟子则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进一步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说的是按照自然规律,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网孔密细的渔网不入大池沼,鱼鳖就吃不完;砍伐树木按季节,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民众生死无缺憾,就是王道的开始。孟子指出按照自然规律,取之有时,取之有度,就能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从而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统治。荀子在《荀子·王制》中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的制度就是因时制宜,“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荀子·王制》),制定法规,让百姓按时节砍伐山林、捕捞鱼鳖,从而让老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儒家生态文化提倡遵循自然规律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
(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使民以时”的继承与创新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同志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中国共产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所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如果说“使民以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仅仅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的话,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是它的更高层次发展的体现。这体现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的物质性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更多的社会性、心理性需要,并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封建社会产生的“使民以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本质区别。“使民以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虽然包含着利民、惠民、养民等思想,但本质还是“使民”“用民”。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从“使民以时”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了从“臣民”到“人民”的转变,从“使民”到“为民”的转变。
四、从“仁民爱物”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
“仁民爱物”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路径和方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方法。从“仁民爱物”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儒家生态文化的“仁民爱物”
如前所述,在如何“赞天地之化育”上,儒家更注重主体意识和道德价值上的实现。笔者认为“仁民爱物”更具有实践指向性,从生态意义上来讲“仁民爱物”可作为实现“赞天地之化育”的具体路径和方法。
“仁民爱物”从“孝悌之本”扩展而来。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为“仁”不仅要孝敬父母,而且还要做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广施爱心,亲近有德行的贤者。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则进一步把爱的对象由“人”扩展到“物”,由亲爱亲人而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而爱惜万物。仁爱由“孝悌”“泛爱众”到“爱物”,由“仁者爱人”到“仁者无不爱” (《孟子·尽心上》),其“爱”的外延不断扩大,由对父母兄弟的孝悌之爱扩展到对百姓的爱,又扩展到了对草木禽兽万物的爱,对大自然的爱。
儒家生态文化提出了不仅要“爱物”,而且还谈到了“如何爱,怎么爱”的问题。在对“物”的认识上,儒家生态文化对生态的系统性有了模糊的、朴素的认识,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草木畴生,禽兽群焉”(《荀子·劝学》) 、“(天地万物)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荀子·富国》)等观点。在如何“爱物”、保护生态的问题上,儒家提出了遵循自然规律,取之有时、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等观点。孔子首先承认了规律存在的客观性,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不言,四季照常运行,万物正常生长,万物按照自然规律来运行。荀子则进一步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荀子指出了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性,不会因为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规律是客观存在,儒家提出要遵循自然规律去爱护万物,保护生态。“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义》)是对“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规律的遵循,应尊重林木、禽兽的生长规律,取之以时。“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则强调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度,不要用大网捕鱼,不射夜里栖宿的鸟。孟子则从反面论证了遵从自然规律的重要性,指出“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即再容易生长的东西,如果“一曝十寒”,违背事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也不能成活。荀子提出人应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尊重自然规律,达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和谐状态。
(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对“仁民爱物”的继承与创新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体性,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体性。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3页。用“命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方面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儒家的“仁民爱物”强调对大自然的爱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孟子·尽心上》)。 这体现了一种施由亲始、由近及远的差等顺序,君子首先是亲爱亲人,然后是仁爱百姓,最后才是爱自然万物。君子虽爱,但因对象的亲疏远近有所不同,而对大自然的爱,只是处在“爱的边缘”。在某种意义上,儒家“仁民爱物”还具有人类利益的本位观和 “自私物种”的狭隘性。而中国共产党提出“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足见其对生态环境的“爱之深、爱之切”,也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科学认识上的生动表达,指出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协调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各要素,如推进国土绿化,加强对天然林的保护与修复,严格保护耕地等,整体施策、综合治理,以达到生态系统的最优化。而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儒家对生态的系统性、自然规律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的水平。儒家所揭示的只是普遍存在的、较为常见的自然现象,其更多的是直观的经验式的理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五、从“时禁”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月令”制度的“弱化”和“虚化”,是导致儒家生态文化中的“时禁”等理念实践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制度性、法治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从“时禁”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礼记·月令》的“时禁”
“时禁”是儒家生态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礼记·月令》则是体现“时禁”法制性的重要文本。《礼记·月令》是一项具有强制性意义的保护生态的规定,是当时全社会需要遵守的生态行为准则。《礼记·月令》以时间为轴,记录了四季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并根据动植物生长繁衍的自然现象,规定了不同时期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例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这说的是春夏是万物复苏生长的季节,要着力维护动植物的生长繁衍所需的生态环境,禁止伐木和渔猎。《礼记·月令》蕴含的生态理念也对后世保护环境的法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秦律《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唐律》“非时烧田野”等古代的环境立法都体现了“时禁”的思想。儒家经典内涵的生态意蕴对古代生态保护法律的产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也有学者对儒家生态文化的“实际功效”提出了质疑,认为“‘天人合一’并没有改善中国古代环境状况”(12)肖巍:《“天人合一”并没有改善中国古代环境状况》,《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并进行了论证。其观点虽失之偏颇,但也表明了儒家生态文化的实践性不足。儒家生态文化虽然蕴含着“制度性”的理念,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会使“鲜活的意识”变成“实际中的成效”。有学者举例指出,明清时期,“月令”成为了缺乏有效国家强制保障的“虚化”制度,实际上是造成明清两代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重要制度原因之一(13)周启梁:《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通考——以土地制度变革为基本线索》,《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诚然,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环保制度因素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变量。从古代历史上来看,中国环保生态法治的强弱与生态环境的良莠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儒家生态理念并没有以法律为载体得到贯彻执行,或者承载着儒家生态理念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实施,是古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
(二)“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对“时禁”的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同志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即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贯彻执行才能为生态环境即保护提供可靠保障。这既是对古代某个时期某些地区生态恶化教训的反思,也是对现实严峻生态问题的考量。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而是生动的实践。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入宪”,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出台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印发,从一系列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制定到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不被遵循,就会形同虚设。习近平同志倡导并推动了生态文明监督机制的改革。改革后的生态文明监督机制以中央环保督查和专项督查行动为主要形式,以“环保问责”为手段,对全国督查全覆盖,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生态环境问题,督查地方党政以及环保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掀起了一阵阵问责“风暴”,“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3页。。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典型,对领导干部在其中的不作为、不担当,绝不姑息,一查到底。对祁连山生态严重破坏、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青海木里矿区非法开采等问题的处理,充分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制度执行和法治落实、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坚定态度。
强调法治性、制度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如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39.6%、34.3%、27.7%;完成营造林面积 2.35 亿亩,持续加强天然林保护,新纳入天然林保护政策范围的天然商品林面积近 2 亿亩(15)《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摘录一)》,《环境保护》2018年第11期。。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果进一步巩固,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海洋环境状况稳中向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定。
六、从“顺水之道”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由孟子的“顺水之道”,可以看出儒家在处理“国家之间”生态环境问题上所秉持的义利观。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所秉持的“正确义利观”实现了对其的传承与创新。
(一)孟子的“顺水之道”所体现的义利观
孟子在对“大禹治水”和“白圭治水”的比较中,提出治水应该“顺水之道”。
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对大禹治水的行为进行了论述和赞美:“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其意指大禹疏通九河,三过家门而不入,使民众在中原大地上得以安养生息。《孟子·告子下》中有记载:“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顺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这说的是,白圭洋洋得意地说,自己治水的功劳比禹大,孟子对其言辞进行了批驳,指出“子过矣”。大禹治水之所以伟大,在于其遵循自然规律,行“水之道”,以四海为沟壑,以利天下苍生,“中国可得而食也”。白圭治水,虽有益于本国,却损害了别国的利益。当是时,各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汉书·沟洫志》),孟子对白圭的批评意在抨击各国“以邻为壑”的卑劣行径。孟子对大禹治水的赞扬,对白圭治水的批驳,表明了他在生态建设中的价值取向,即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导向,计利当以天下计,重义轻利。诚然,当时孟子所指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内涵和实质与当代多种文明共存、冲突、交流、互鉴的国际关系截然不同,但其沉淀下来的价值原则和价值理念,仍然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中一般和共同要求的东西,仍能给我们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合作带来些许启示。
(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对儒家生态文化中的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也传承了儒家生态文化中的义利观。在中国周边地区跨国界河流问题上,中国坚持以“亲、诚、惠、容”为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积极探索和构建跨国界河流的协商和合作机制,着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并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应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9页。。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遵循的义利观,不仅是对儒家生态文化中的义利观的传承,更是对其的发展和超越。儒家生态文化中的义利观强调重利轻义,孔子“罕言利”,孟子则指出:“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儒家生态文化中的义利观虽然指出了当时各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承担的国际道义和责任担当,但在当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全球生态建设格局中,显然无法为中国的国际生态合作建构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的正确义利观,是对儒家生态文化中的义利观的“扬弃”和发展,即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坚持义与利的辩证统一。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博弈中,中国的生态建设和发展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但中国也决不放弃本国的正当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习近平同志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17)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辩证统一,秉持共建共论共享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共建清洁美丽的地球美好家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儒家关注的“重点”,儒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往往是作为其政治、哲学观点的“衍生品”而出现,但这并不能磨灭儒家文化的生态意蕴。理论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儒家文化的生态意蕴进行重新审视,对其的理解既不能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也不能故步自封、原封不动。
探析儒家生态文化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关系,有利于继承和发展儒家生态文化,为儒家生态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提供现实机遇,从而进一步推动儒家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有利于发掘儒家生态文化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和意义,从中汲取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不仅如此,探析二者的逻辑关系,有利于更深入理解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